中国一些学者非常喜欢举引美国学者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一书,来证明西方学者也认为古腾堡活字印刷术来源于中国的观点。实际上,卡特在其书中并没有明确做出结论判定古腾堡印刷术直接来自中国,他只是列举了古腾堡印刷术有可能受到中国影响的情况,以及该发明在欧洲出现的社会条件与技术基础。他在书中还专门强调:
我们不可认为以上所提及的人物(指包括毕昇等人在内的中国与朝鲜的活字发明者与使用者,引者按),都一定就是欧洲印刷发明者的直系祖先;特别是后面三位发明和改善活字的人,似乎属于旁支,他们和欧洲印刷发明者的关系,与其说是祖先,不如说是堂兄弟。
之后,卡特又非常明确地指出:
在远东的胶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和欧洲的印刷发明之间,究竟有没有直接的关联,这是一个很难置答的问题,但就现有的证据来说,答复是否定的。毕昇的活字始终未曾广为流行,到元代与欧洲发生密切接触以前,几乎完全为人置于脑后。使用木活字时,正是和欧洲的接触最频繁的时候,但关于贸易路线中断以后和欧洲开始印刷活动以前这一百年的情形,真相不明。

即便受到中国印刷术影响的朝鲜,在15世纪初叶率先发明字模,用金属活字大量印书,也不能证明古腾堡印刷术来源于此,“迄今并无表明两者有关系的证据”,因为,“就我们所知,在那个半世纪内,欧洲和远东几乎全无交通可言。”随后,卡特又审慎地总结:
不过现在要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朝鲜的活字印刷与欧洲的活字印刷没有直接的关系,还嫌过早。另一方面,现在还没有发现足以明白证实两者有关的证据,在我们掌握正面或反面的证据以前,我们必须排除成见,不作定论。卡特这里的提醒与警觉并非绝响,荷兰学者戴闻达(J. J. L. Duyvendak)在书评中,对卡特的研究及中国印刷术也有很多表彰与赞美,但他最后同卡特一样承认,“欧洲印刷术果传自东方耶?日今尚无确实不移之证据……”当时翻译为中文的Carlton J. H. Hages所著《近代世界史》亦认为,尽管印刷术最早发明于中国,并传播到日本和朝鲜,且有一定可能会传到欧洲,“14世纪,时在远东的欧洲旅客和商人当然会看到或听到印刷的书籍”,但“印刷的技术是否由亚洲传到欧洲,还没有确实的证据,西欧好像独立地发明了印刷术”。然后,该书又长篇描述欧洲活字发明的条件和大致情形,其中在谈及古腾堡时说:
印刷术的发明者,由应用印板至制成活字——印刷术真正的发明——实际的过渡时期的历史不得而知。有一般人说第一个制造和使用活字的欧洲人,是一位科斯忒(Lourens Coster),荷兰哈连姆(Haarlem)人。然而,我们实在只能知道,约在1450年时,有一人名叫古腾堡(John Gutenberg),在德国的马因斯(Mainz)城内一间印刷店里应用活字,也只能知道这个新技术的最初为人所知的出品是教皇的“免罪证”及一册《圣经》的译本。
中国学者亦有持类似见解的。陈叔谅(陈训慈)在《西洋通史》里写道:“欧洲15世纪印刷之发明,其所得于中国者如何?尚待详加考订。”陈书认为德国美因茨人John Gutenberg“始用活版印书(1450)”,到15世纪末,“罗马有印刷局,16世纪时则流行于欧洲各国。”有国语教科书亦持类似立场,“中国的印刷术发明得很早”,唐时就已经发明,北宋毕昇又发明活版,之后“渐渐传到外国如日本、高丽。”“至于西洋印刷术,同中国的关系,虽不十分明确,然而大致可以说:西洋的印刷术是受到中国的影响的。”稍后的沈子复参考了卡特著作,他同样认为:欧洲印刷术的发明一定受到中国的影响,但具体传播中介、途径及结果尚不清楚。
然而,卡特等人的谨慎和保留态度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他这本著作还是被当作论证古腾堡印刷术滥觞于中国,或受中国活字印刷术启发的权威论著,广为中国学者举引和有意无意的误引。同样情况亦见之于他们对培根、马克思关于“三大发明”论述的歪曲解释与使用。
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中曾言,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革命家马克思则更是豪迈指出: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培根与马克思的这两段话,为1949年后的印刷史学者、文化史学者及历史教科书的编者经常征引,作为论证中国三大或四大发明重要性和影响力的权威证据。
事实上,不管是培根,或是马克思,都未把这三大发明的专利权归于中国人,甚至前后文都是在谈欧洲的科学技术,根本未提及中国,更未把这三大发明与中国建立联系。从其论述理路推断,他们显然认为是欧洲人发明了这三大技术。但这两段话的很多征引者,尤其是印刷史、科技史的书写者,都歪曲了培根和马克思的本意,将这三大发明之前加上定语“中国”或者由中国传播到欧洲的,甚至武断地举引为培根和马克思认为中国的这三大发明如何如何。更有个别学者声称:“通过中外学者多年来的潜心研究业已证明,对世界史有如此重要意义的上述四项伟大发明都完成于中世纪时期的中国。”
通过这样的记忆打造工程,毕昇是活字印刷术的最初发明者、古腾堡印刷术来源于中国、中国三大发明经由马可波罗、阿拉伯人或蒙古人西传到欧洲这样的认知,逐渐在坊间盛行,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激励中国人自豪感与奋发图强、追求现代性的思想武器,绵延不已,迄今不绝:“考印刷之术,肇自我国,隋唐间已有之。”“综而言之,则我国发明最早,而今则一无进步。印刷术固如是,他亦何独不然?……虽然,同胞,同胞,能永此落伍,而不自强乎?自强之法,在乎努力科学……”“要使(印刷技术)落后的中国走上科学化的大道,这是我们当前的责任。”
因此,近代中国的印刷史书写者往往以昔日的辉煌反衬今日的落寞,通过感叹中国后来不若西洋来表现民族主义心理,激发国人自励和努力:
印刷术的没落,关系民族文化、国家盛衰至巨,实不应默然视之……“印刷是进步之母”,想要文化兴起,国家富强,科学昌明,工业发达,不能不着重印刷术啊!(李常旭:《印刷术与文化》,《西北实业月刊》第1卷第3期,1946年10月1日,第48-49页)
一些知识分子更是对中国近代的印刷术反有西洋传入的情况,感到“十二分的羞耻和警惕,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国家,但是今日的中国印刷术落后到如此地步……我国印刷界的人士,应当如何的急起直追,恢复我们中国固有的荣誉呢?”
相似言论在当时的印刷史书写中可经常见到,其意图均是希望给予读者刺激和鼓励,发扬光大中国固有的印刷文明。像张秀民之所以立志研究中国印刷史,即因有耻于卡特代中国人写中国印刷史,以及他要亲自为中国光辉、悠久的印刷术作史扬名的想法。这种民族主义的书写诉求,亦非常明显地体现在近年来中国学者大力捍卫活字印刷术发明权的论述中。其实,之前刘麟生所译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能在1957年被原封不动影印出版,吴泽炎重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于1957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不嫌重复地出版,张秀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在1958年2月由权威的人民出版社出版,再加上当时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为包括印刷术在内的中国科技成就大力背书,都反映或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新的国家政权建构的需要。如时人之言:
卡特和张秀民的书,给了我很多知识。不仅雕版印刷术是中国人所发明,而且活字印刷术也是中国人所发明。中国人已经利用造纸术和印刷术大量印书的时候,欧洲各国仅能用笔在羊皮上抄写《圣经》。从明朝开始,中国的科学技术才逐步落后于欧洲。读了这些书,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使命感,激发起发愤图强的雄心壮志。这些书是很好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王益:《总序——重视印刷史的研究和学习》,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中国印刷史料选辑·雕版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第3页)
综合上述内容可知,在很多情况下,与其说历史书写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中的叙述,为单纯的史事记载或存真记录,毋宁说它们是文化工程与载道工具。正如伯克之言,“知识的选择、组织和陈述不是中立和无价值观念的过程。相反地,它是由经济和社会及政治制度所支持的一个世界观的表现。”对于忧世伤生、历经磨难的绝大多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书写经常是有大义存焉的叙述政治,不但让他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汲取光彩和奋发图强的思想资源,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编排组织与书写,让中国找到在过去及当今世界的位置,获得自信和复兴的希望。

换言之,在某些情况下,此类行为或可被视为一种对抗和挪用西方霸权的“弱者的武器”,它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实用性、有效性,广为人们接受和运用。像在近代持久激烈的中西医论争中,包括印刷术在内的所谓中国三大发明流传到欧洲的故事,就成为一些人捍卫中医合法性的奥援:
中国之所以发生中国的医学,和西洋之所以发生西洋的医学,全然有其不同的地方环境和物质条件在。从历史上看,中国所有而西洋所无的学术,不只是医学,指南针,而西洋何尝自有?首先有的乃是中国,却不因为中国独有而腾笑万邦,转是万邦从中国学习了去,用在航行上,占取最主要的地位。印刷术西洋何尝自有?首先有的乃是中国,却不因为中国独有而腾笑万邦,转是万邦从中国学习了去,用在文化上,占取最主要的地位。火药西洋何尝自有?首先有的乃是中国,并不因为中国独有而腾笑万邦,转是万邦从中国学习了去,用在作战上,占取最主要的地位。整个的西洋文明都导源于中国,并不腾笑万邦,为什么轮到了医学,会要腾笑万邦呢?(张忍庵:《医学之空间性及其新旧观》,见苏州《国医杂志》第3期,1934年秋季出版,第15页)
此处的论述自然难逃“西学中源”论的窠臼,但显然,这样的论述意图不再是像晚清那样为方便学习西学寻找借口,以减少保守派的压力,而是为了保护中医的合法性,不得不从历史中寻找论证的资源,展现的是时人面对外在文化霸权强大压力下的焦虑,乃至感情上的一种尴尬认同——弘扬中国过去的辉煌和影响,却又被迫承认现在中国的江河日下与技不如人。为改变这种情形,他们希望通过“记忆政治学”(memory politics)的操作,重温或建构国史上的荣光,表彰中国历史上的原创发明,发挥史学经世的作用,来唤醒民族的自信心,振兴民族精神,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或可说,他们不是在发掘历史中的真实,而是在阐释被他们视为“真实”的历史,在诠释中同时进行自我反省、自我建构和自我认同,乃至希图将之付诸实践。对他们来讲,历史真实与诠释标准、价值判断不可分割,历史知识不只是对“真实”的再发现,亦是对现实世界所做的再诠释和重新规划。故此,阐发历史的真实并非为这些学者的终极目标,最重要的标靶,乃是阐发出来的这种“真实”,能否经世致用、能否对当下的社会实践有意义,这往往才是最优先的考量。如名学者陈垣的“夫子自道”:“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陈垣后来还补充道:“凡问题足以伤民族之感情者,不研究不以为陋。如氏族之辩、土客之争、汉回问题种种,研究出来,于民族无补而有损者,置之可也。”
确实,如某些理论家所揭示的,历史书写不是中性和透明的,而是充满意识形态与道德判断的行为,是对一定脉络下知识与权力互动的描述,它制约着我们表现过去“真实”的效果,亦即历史的“真实”必须仰赖书写来呈现,无法外在于历史书写的模式和策略。对于中国印刷史和古腾堡的叙述和诠释自然不会例外。实际上,古腾堡是谁,他发明的是木版活字或是金属活字,到底是不是他发明了活版印刷术,什么时间发明了印刷术,活版印刷术的真实技术情况如何,与木版、雕版印刷作用有哪些不同,造成的影响与中国印刷术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有何差异,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且不断有人涉及与考掘,然而,这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真正书写意图。相较起来,许多人真正在意与追求的,乃是获得论述和参与的权力,将古腾堡和欧洲印刷史同中国印刷史接榫,替中国印刷术尤其是毕昇的活字版发明找到位置,阐发其现实意义,进而为中国在过去和当下的世界中找到地位,为学习西方的印刷现代化和中国应该参与全球化进程找到立足点——中国发明的印刷术(或三大发明)既然能使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黑暗,自然也能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如在1919年写成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就基于印刷术之于知识普及、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性,特意将印刷工业作为工业现代化设想中的一个方面,加以高度强调:
此项工业为以知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纪述之,一切人类知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中国民族虽为发明印刷术者,而印刷工业之发达,反甚迟缓。吾所定国际发展计划,亦须兼及印刷工业。
可以看出,从一般知识分子,到影响大局的政治领袖,在中国社会实现印刷现代化均是他们关注和追求的目标,其诱因之一则为中国是印刷术的最早发明者这样的历史认知。
职是之故,近代中国的印刷史书写者,后来不但果断抛弃了就古腾堡谈古腾堡、谈欧洲的历史书写模式,还迅速延续与深化了对中国印刷史和欧洲印刷史进行比较联系的书写模式,他们希望透过回溯或重构“真实的”中国印刷术发展史,辅以合适的叙述策略——以时间差距来弥补空间错位、以历史中介的传播可能表征实际达到的传播效果,孜孜以求古腾堡印刷术同中国活版发明的相似性及继承性,刻画或暗示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通过揭示印刷术对于欧洲近代社会的巨大作用,从而凸显中国发明的伟大和应该继续追求印刷现代化的必要性,这其实是一种现代性视野左右下的“‘价值’优先下的‘事实’重建”,恰巧呼应了后现代论者所谓的“历史(历史书写)是人们或民族产生他们认同的方式”的悬鹄,正是在如此长期不断的生产、复制与传播、接受过程中,包括印刷术在内的四大发明被塑造为今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吊诡的是,当近代中国的印刷史书写者在积极建构古腾堡印刷术同中国的关系、急于追求印刷现代化之时,焉知不是在参与另外一种古腾堡神话的打造和复制?因为潜藏在这样的建构和追求下的前提,就是在去脉络的情况下,以线性的历史观及化约论思维,简单对比中西印刷术,将古腾堡印刷术的作用抽象化,大而化之地认为中国的木版印刷技术不如古腾堡的活版印刷技术,所以无力促成中国的印刷现代化,从而严重忽视和大大低估了木版印刷技术在中国与近代欧洲所起的巨大作用及导致的社会效果,无形中也夸大了古腾堡印刷术的意义。
暂且不管欧洲一直存在的,关于古腾堡是否的确为活版印刷术最初的发明者、何时发明这样的争议。实际上,西方历史书写中的古腾堡神话亦可被视为一种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与被发明的传统,或像周启荣教授提醒的,初期的古腾堡印刷术具有很多缺点,非常耗费铜和劳力,即便是古腾堡印刷术被大规模运用后的近代欧洲,木版印刷还大量存在,广为印刷商采用,因为木版印刷在很多情况下,尤其在插图、图像、美术品印制等方面,都远比古腾堡印刷术和后起的照相版为方便、实用,且更具美感。此种情况直到19世纪以后,相关的物质配备与技术革新进一步完善之时,木版印刷技术始逐渐淡出欧洲乃至世界印刷舞台,古腾堡印刷术才所向披靡。饶是如此,就像晚清教会杂志《格致益闻汇报》的一个读者“丹徒何宾(左侧有“山”字笔画)生”的疑问:
石印、铅板书籍,藏之年久,字迹率多模糊。仆取书箧中旧本,实有销退者。中国木板则无此弊。当用何法刷印而得不变耶?
面对这一既是技术又是文化的问题,《格致益闻汇报》编者也做出了一个聪明的回答,并没有直接回应各种印刷方式的优劣,但为铅印和石印技术进行了辩护:
无论笔誊、木板、石印,皆须纸墨两佳,乃字迹历久不灭。今各书坊石印、铅板纸墨多不精良,以致数年之后,字迹模糊,无足怪也。藏书须择干燥地,又以汞绿二防虫蛀,则万卷楼头无忧浸患矣!
进而言之,与活字印刷术相比,除了方便便宜之外,如钱玄同当年曾指出的,在印刷比较冷僻的中文字之时,铅字模中多无其字,“强使刻之,率大小不一,字体位置不匀,且点画之间,多有舛误。”所以木版印刷仍然有其优势:“若欲认真刻书,木版既不可必得,则求其次,石印可也。盖如今印刷局所言之字,多就一般时下文章所通用者,且字体一遵《康熙字典》,俗讹之体,杂出其间。”
饶是如此,正似王汎森教授曾指出的,我们对印刷术在传统中国所起的正面作用也不能估计过高,在近世中国其实还存在诸多反印刷和主张焚书的论述,但这些声音“从来未被正面讨论过”,而处于印刷时代的我们也有意无意在以今天的眼光放大了印刷文本在明清中国社会的普及度与流行性,不但夸大了印刷文本所导致的社会影响,也无形中贬低了抄本及那些反印刷言论的作用。
最后,一如法国文化史家夏特里埃(Roger Chartier)在对法国大革命同启蒙书籍之关系的探索中所指陈:
在一定意义上,是大革命“造就”了书籍,而非相反。正是法国大革命赋予了某些特定书籍具有先见之明与可昭法式的意义,在事情发生之后将其精心结撰,追认为大革命的源头。
由此,我们是否也应该追问:是古腾堡印刷术引发了欧洲的现代化?或是欧洲的现代化造就了古腾堡印刷术?抑或是二者互相作用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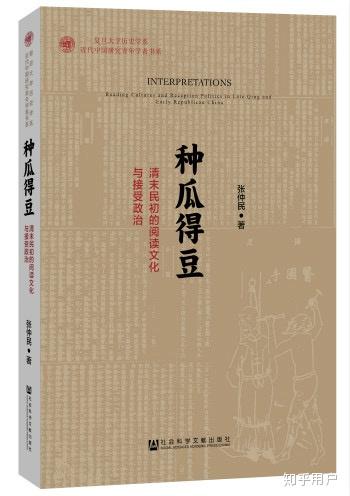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张仲民著《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11月。原题为《历史书写与记忆政治》,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略去。)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