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美学”的嬗变
刘悦笛丨文
载于《艺术评论》2010年第12期
当代中国艺术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程,步步发展的进程都与“生活美学”直接相关,这是由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始终是当代中国艺术史的主题。笔者也曾经参与在798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的“再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学术部分的首讲“从‘新艺术史’到‘图像霸权’”,这个系列的大型展由吕澎、朱朱和高千惠共同策划,试图梳理最近十年的当代中国艺术史。而如果将反思当代中国艺术的视野拉伸到三十年,就更能得见当代艺术流变的美学轨迹。易英的专著《从英雄颂歌到平凡世界》对艺术思潮的历史转变已着墨颇多,进一步也可以从美学视角来加以阐释:一方面“历时性”地梳理生活美学与当代艺术之间所形成的历史关联,另一方面“共时性”地解析这种美学与艺术之间相互连接的理论模式,但无论是历史还是理论的考量,其中的关键词都是“生活”。
一、政治生活美学·前现代语境·现实主义
1978年正式开启的当代中国艺术,由于打开了政治局面而廓清了自由空间,然而仍因为上世纪中期更多只向苏联文化开放,使得最初的当代中国艺术难以接受“现代性”的要素,同时,也难以延续上世纪初就已开始的“现代主义”艺术探索,从而整体地处于“前现代”的历史语境当中。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的初期,中国艺术曾经皆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特别在文革美术当中,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曾被推上了顶峰。由于“文化大革命”独特的文化塑造力,使得当时的中国艺术只能以领袖形象和参加革命运动的工农兵形象为主要题材,这些形象必须符合“高、大、全”的创作要求,并一定置于“红、光、亮”的背景当中,而且,这些历史肖像是“介于肖像画与历史画”之间的独特类型,因为其中的人物必须“处在历史事件与他的活动”当中才能获得革命的现实意义。
确立“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信条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方面强调了源于生活的艺术并不是生活的“翻版和备份”,而是“生活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另一方面认定艺术作品较之“普通的生活”“更具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如今观之,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活美学”思想,某种“先在”的意识形态观念既介入了生活,又介入了艺术。按照这种美学原则来指导艺术,就势必要求“一个艺术家应该随时随刻都生活在战斗(指政治斗争)之中,随时随刻都在进行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而对艺术家的首要要求就是“在创作生活上具有社会主义精神。”在当时的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曾被奉为圭臬:“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需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1)“美是生活”是最基本的要求,它规约艺术必须去反映现实生活;(2)“美是应当如此生活”则是更高层的,它解决的是“要反映的是何种生活?”的问题;(3)美要“显示生活”是针对创作者要去反映生活而言的;(4)美令人“想起生活”则是针对接受者从艺术中“见证”生活来说的。如此可见,“美是生活”的主张已经全面地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的本质与属性。这种艺术观沿袭了自模仿论以来欧洲式的“艺术再现世界”理论,它特别要求油画“把物体描绘成在自然中存在的那样和像我们的眼睛所见到的那样”,关键不是让观者看到作品的素描关系、大的笔触和漂亮画面,而是要看到“活生生的人以及这些人的心情”。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在中国的现实主义当中,被转化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工农兵所接受,要为工农兵所利用,从而最终为工农兵生活的工具。
在这种艺术理论的指导之下,当时中国艺术中所能加以表现的主要就是一种“政治化的生活”,这是由于本属于“食色本性”之类的基本日常生活,相比之下难以得到很大的再现空间。与此相反,绝大多数的艺术都直接地被笼罩上“政治美学”的色彩,绝大部分的艺术再现的内容都是从革命活动到工作锻炼之类的社会主题,即使是家庭这样的最私人化的生活领域也被“政治公域化”了。
当代中国艺术的真正转机,是从现实主义内部出现的,而并没有过多借助外来的影响力,当时油画的创作无疑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随着文革的结束,作为对于文革的内容上的反拨,在中国艺术界短暂出现了所谓(以控诉文革为主题的)“伤痕美术”和(以回归乡土文化为主题的)“乡土美术”。在风格取向上,前者易同非政治内容化的“唯美主义”相结合,而后者往往走向了非政治形式化的“自然主义”。然而,这些艺术浪潮都很快消逝,并迅速流于现实主义的矫饰。此后,取得更大成就的是属于学院派谱系的“新古典”式的油画,还有就是尚未摆脱官方脉络的“生活流”艺术。所谓“生活流”,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影响最为深广,它一反传统写实的内容的戏剧化与形式的唯美化,以现实的笔触直接将藏民的群像“照搬”进了画面,以文化的深厚力量与画面的现场感感染了观众;而真正将回归乡土取向并用美式“照相现实主义”风格加以呈现的名作则是罗中立的《父亲》,它将一张承载着千年文化苦难的父亲沧桑头像搬上了画布,从而以文化性的反思替代了政治化的思考。尽管这些取代旧现实的“新现实”艺术获得了最初成功,但这些艺术内部的进步取向与创新意图,却已暗示了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开始走向衰落。
二、精英生活美学·现代性启蒙·现代主义
在现实主义走向衰落之后,当代中国艺术还是按照“自我的逻辑”在发展,最初主要仍在现实主义内部试图找到艺术创新的方向。但是,真正给当代中国艺术带来冲击的,却是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个重要的“他者”。从“八五美术运动”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为止,现代主义艺术几乎成为了中国前卫艺术家们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80年代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现代性启蒙”事业在中国得以复兴。五四时代“美育代宗教”的名论就已显现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独有特色,它始终没有像欧洲那样要直面强大的宗教问题,而且“审美现代性”问题出现在“社会现代性”问题之先。这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社会特征,形成了“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二元对立的基本格局。作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思想基础,“主体性”哲学思想被高扬了出来。这种“主体性”思想激发出艺术家们对于“艺术自律”与“审美自觉”的双重追求。
现代性的任务在中国至今尚未完成,在现代性诸多方面相杂揉的局面下,中国艺术延续了其历史传统从而被要求承担“世俗的拯救功能”,80年代的现代主义者们最初就将自身定位为“社会的立法者”,艺术界也开始形成一种特殊的“自律文化领域和体制”。而正因为“审美现代性”成为了“社会现代性”的先导,审美和艺术功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才得以抬升。现代主义艺术就是在这种历史境遇当中出场的,它最初同“审美现代性”紧密契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结合体,而前卫艺术遂而又以另一种“反审美”的姿态逐步登场。吊诡的是,欧美前卫所反击的是市场体制,但是中国自从政治波普以来的前卫艺术家却越来越成为市场的同谋。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在“八五美术运动”之前,在现实主义的主潮之外,艺术创新的实验就早已出现了。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1979年发表的《绘画的形式美》一文在当时的艺术界激发起了强烈反响,他强调聚焦“形式美的规律”的美术其实就是“美之术”,从而直接置疑了以再现为主宰的艺术观,在当时美术界激发了关于“纯化语言”的大讨论。这种讨论背靠的美学思想,恰恰就是前面提到的“艺术自律化”与“审美纯粹化”的观念。然而,有趣的是,这种关乎形式的谈论,在中国语境当中却是“非形式化”的,它恰恰带有反击传统意识形态与艺术主流的色彩。
随着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兴起,在“八五美术运动”当中脱颖而出的艺术家们,尽管在现实身份上开始摆脱了限制,但是,在精神和气质上却表现出试图完成“现代性”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在艺术当中高调倡导去建构一种“人文精神”,并自诩作为“文化精英”而进行创作。他们特别倡导一种所谓的“理性绘画”成为了主导性的形态,与之相对的高扬“非理性主义”的所谓“生命之流”绘画则成为了一股潜流,而这两种绘画形态皆采取了精英的立场。按照“八五美术运动”主要参与者的意见,八五美术运动是一种“中国的人文主义”。当时的艺术家们,无论是秉承现实主义,还是接受超现实主义,都力图在绘画语言当中去表现某种“哲学纲领”的东西。然而,在90年代之后的中国艺术尽管“启蒙现代性”的重任并未完全完成,但是激进的艺术家们却开始接受“后现代”的话语,从而开始了另一种“去启蒙化”的艺术实践。
由此而来,在当代艺术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之后,艺术家们反过来提出了“清理人文精神”的口号,“逃避崇高”成为了共同的选择,并开始逐步解构“理性绘画”所形成的宏大叙事。在这个转折的时代,古典主义与现代艺术之间的对峙张力才是最重要的,这完全不同于90年代以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所形成的混合张力。按照当时艺术家自身的反思,古典与现代的关系并非如此紧张,“其实‘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语言发生之原点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应当抛弃掉艺术对于人文热情的依赖关系,走出对艺术的意义追问,进入到对艺术问题的解决之中”。【王广义:《“清理人文热情”,《江苏画刊》1990年10期》】这位艺术家深深感叹,从80年代延续到90年代的艺术转变,他被认定为是从“具有崇高精神的理性主义者”转变为“信仰阙如的人”和“文化虚无主义者”,这也正是艺术家角色在两个时代之间加以转换的实证。
这意味着,这一代艺术家已经自觉放弃了“启蒙精英”的“艺术创作者”角色,而是甘愿成为专业的“艺术制作者”,他们非常厌恶在艺术当中去承载“艺术之外”的东西,并认定艺术创造其实也不过是某种游戏而已。这样,当代中国艺术家们就变而成为对于自身生活的“阐释者”了。不过,当艺术家们成为自身阐释者的同时,他们不仅脱离了主流文化的限制而且与大众文化也相互分离,成为了仅仅关注个人生活的“常人”,一种与“精英生活美学”根本反向的“日常生活美学”开始出场了。
三、日常生活美学·后现代话语·当代主义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步入新的世纪,当代中国艺术逐步融入“全球化”的格局当中,同国际艺术的最新走向取得了越来越密切的外在关联,“后现代艺术”已经稳固地成为了一种主流的艺术形态。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当代中国艺术几乎是在短时间的历史场域内,上演了欧美艺术几百年来的艺术流变,这些艺术传统在当前的中国艺术界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局面。在这个新的阶段,无论是前现代的“新文人主义”,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抽象主义”,还是具有后现代风格的当代艺术都具有发展的空间。这种最新的多元发展局势,我们可以用“当代主义”来加以概括,因为前现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都被整合在具有“当代性”的中国艺术实践当中。
从90年代开始至今,在占据主流的当代中国艺术语言当中,出现了三种当代艺术话语方式:第一种是“政治波普艺术”,其取向在于“反讽意识形态”;第二种就是“玩世现实主义”,其取向在于“逃避崇高内涵”;第三种最初以“新生代”为主导,随后当代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更是蔚为大观,其基本取向就在于“回归日常状态”。
如果说,“政治波普”只是对于过去的“政治生活美学”的追忆和借用的话,那么,“玩世现实主义”则是对于“精英生活美学”模式的根本拒绝,而从“新写实派主义”开始的架上绘画最早提出了“回归日常”的新道路,而这条道路终于在当代艺术的各种媒介当中得以全方位地拓展了。就广义而言,这三种艺术话语都属于走向日常的道路,“政治波普”是将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加以并置,“玩世现实主义”是从精英生活反叛到日常生活,而此后的各种当代艺术形态则直接把“日常生活”当作“日常生活”,这三种艺术话语分别主导了“日常生活美学”的三种不同类型。
在中国独树一帜的“政治波普艺术”,以美国的波普艺术作为范本,从而将政治意识形态与波普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艺术家放弃严肃的形而上姿态,高举解构主义的旗帜,纷纷转向政治化的波普风格。”其中,一位重要的艺术家就是王广义,当他将文革宣传画与国际名牌并置的时候,艺术家本人将自己的作品视为“解决商品经济问题的后波普作品”,借用文革图像的目的其实是要给予现代商品经济调侃和揶揄,这同时也暗示了当代中国艺术的语境的转变:从政治话语转向商业话语,而政治波普正身处在这种转变的过程当中。“玩世现实主义”则是另一种艺术话语方式,是一种以讥诮与冷嘲的态度冷眼看待现实和人生的艺术形态。这批艺术家们已经决然不再相信传统与新构的价值观,而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无可奈何的救赎,所以一种面对现世的“无聊的存在感”成为了艺术家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艺术家方力钧乐此不疲地去描绘北京秃头男人形象的时候,其真正呈现的是画面人物的内在状态:身处时代现实巨变当中,却对于现实采取了“玩世”的消极态度。
在“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成为当代艺术经典之时,更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取向则是向日常生活的直接复归。这类“新生代风格在本质上是一种都市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反映,它将前卫艺术的理想主义转换为一种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世俗主义”,从而代表了一种“处于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主流风格”。这条道路具体包括两种,第一种是偏向学院派的道路,刘小东等为代表的新写实被认为是出现在“古典写实主义”与“乡土写实主义”之后的新流派,是将新潮艺术与学院派巧妙结合的范例。艺术家所描绘的室内外空间都有很明确的普通生活意味,从而表明其所要展示的就是“可信的现实”,从而逼迫观者不得不去注视他们的生存现实。另一条则是最初属于“新具像”派别的在野道路,以张晓刚的独立创作为代表,他的《大家族·血缘》系列所创造的图像在外国人看来是最具“中国性”的,单眼皮、瓜子脸、中山装、全家福,这都恰恰迎合了外国人对于中国“这一类人”的文化想象。这种绘画语言恰恰包含了“模糊个性而强调共性,含蓄、中性又充满诗意的审美特性”的中国普通人长期以来所特有的审美追求。
目前当代中国具有实验色彩的艺术,基本上已摆脱了架上绘画的束缚,从而走向了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乃至大地艺术的新的天地。以笔者2010年9月最新参与的青年艺术家的“大声展”所见,当代属于“青年文化”类型的艺术形态的确凸现出更为突出的回归生活的趋势,从中发现了这样三种回归生活的取向:第一种就是指定日常为艺术,这种艺术取向需要参与者“直接把生活当作艺术”。第二种则是通过否定艺术而成为生活的方式,一个艺术小组创造了“忘记艺术”这个集体艺术活动,希望每个参与这件艺术品的人都忘记他置身于艺术当中。第三种更为观念性的艺术取向,则要求日常生活与艺术直接加以等同,一位年轻艺术家在日常生活里每天通过一个创意来完成一件作品,从而获得了“使生活本身雕塑化”的亲身体验。举出这些最新的艺术例证,并不是说这些当代艺术探索都是成功的,而是要说明,具有真正“当代主义”特色的当代中国艺术的确走上了更为开放性的道路。
四、反映生活模式·提升生活模式·回归生活模式
从政治生活、精英生活到日常生活美学,从现实、现代到当代主义,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艺术这三十多年来,已经基本形成了三种生活模式,也就是“反映生活模式”、“提升生活模式”与“回归生活模式”。
所谓的“反映生活”模式,与之匹配的艺术类型就是现实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在文革美术当中达到高潮并在80年代初期仍具有影响力都是明证。这种反映生活论,其所背靠的则是“美是生活”这类的现实主义理论,但是在真正的艺术实践当中,我们看到,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成为现实主义的反映对象,只有那种政治化的生活才能成为艺术创作的题材,其中的政治生活本然具有“非日常化”的特质,从内容到题材可以说都被“政治话语化”了。所以我们说,这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政治生活美学”,这恰恰就是本雅明所说的“政治审美化”的产物。
所谓的“提升生活”模式,与之匹配的艺术类型就是现代主义,某些具有现代特色的写实艺术其实也大致属于这个范围。这种“提升生活”所背靠的理论则是“审美主义”理论,这是由于,按照康德意义上的非功利的审美观念,艺术一定是超越于生活而自律存在的,甚至就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否定、拒绝与颠覆。在这个意义上,一种阿多诺式的力主艺术自律的现代美学观念,的确与这个时代的艺术思潮是相契合的。按照这种模式,“艺术否定日常生活”成为了定律,而其所力求呈现的精英生活却无疑也是一种“非日常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在艺术家的表现那里已经被“审美乌托邦化”了。
所谓的“回归生活”模式,则是当代各种艺术类型所具有的共同诉求,这种理论背后所形成的背景则是“审美泛化”,也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及其相互的结合。按照这种模式的要求,要将日常生活作为“日常化”的生活来加以看待,既不能走生活“政治化”的老路,也不能让生活得以“精英化”的呈现。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美学诉求拒斥了非功利的传统审美观,从而具有了一种“大众生活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从而崭露了当代中国艺术的新取向。这三种生活模式之间的对比,可以图示如下:
目前,通过中西方的积极对话和深入交流,全球美学界对于当代中国艺术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其内在存在的两重张力:一个是“全球与地方”的张力,另一个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张力,这两个问题也是国际美学界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关注的焦点。既然全球化不再等同于西方化或者欧美化,那么,全球化给当代中国艺术所带来的挑战就在于:中国艺术家所创造的中国艺术如何具有“中国性”的难题。针对于此,笔者在2009年度的《国际美学年刊》曾提出建构“新的中国性”(Neo-Chineseness)的中国艺术观的问题,而“生活美学”就可以被视为——建构“新的中国性”的——当代中国艺术发展的内在基本目标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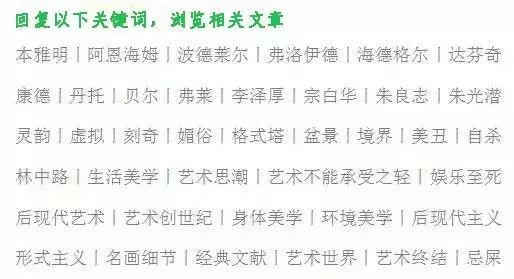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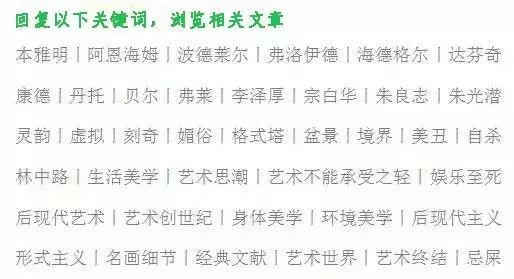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