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新媒体与品牌传播创新应用重点实验室
本期作者
想插上翅膀的Endless
本 期 关 键 词
社会情绪 | 舆论监督 | 公共事件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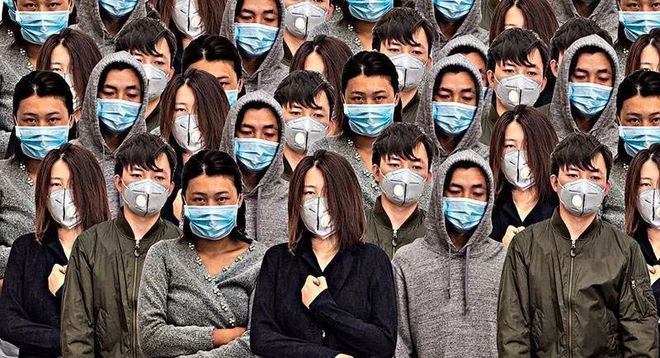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与之相关的信息就一直牵动着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心。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这可能是近年来与大家关系最为密切、距离最近的一次公共事件,也是情绪蔓延时间最长、波动最为剧烈的公众事件。
沉浸、见证和亲历所带来的情绪积累,在这一阶段涌动着极大的能量。也许它会成为社会舆论失控的催化剂,也许它会是时代进步后回望时留下的难忘民族记忆。
不良情绪引发的社会失控
近日来,每天成千计上涨的确诊人数以及病毒新型传播方式的发现,提醒着此次肺炎病毒的传播速度之快与病毒的生存、传播能力之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成为自2007年颁布的管理全球卫生应急措施的《国际卫生条例》以来,世卫组织宣布的第六次“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之下人人自危,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焦虑和恐慌情绪遍布国际国内。

2003年非典时期的抢购板蓝根、2011年日本地震时福岛核电站泄漏导致的抢盐现象之后,熟悉的场景再次出现。口罩、消毒水、酒精迅速脱销,媒体报道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冠状病毒以后,一夜之间线上线下药店的双黄连相关药品也迅速脱销,民众对疫情的焦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演化为一种集合行为。在此种情绪之下,民众的慌张与焦虑会蔓延、也会被利用。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当个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时,他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当这个人融入了群体后,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而当一个群体存在时,他就有着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
而就目前反应在网络新闻、网民评论中的焦虑情绪来看,其已然由个体情绪聚合成群体情绪再反过来影响群体中的个体,民众的判断意识与判断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被集体的情绪化所替代。情绪大于理性、判断能力退位后,民众被诈捐、成为转载谣言的机器、煽动情绪和伤害他人的“杀人武器”,为不良社会舆论的形成推波助澜,造成了更大范围的舆论失控。
社会情绪促成的舆论监督
在近期的网络热点事件当中,既能看到网络民众对武汉市政府早期瞒报的谴责、对黄冈市疾控中心负责人一问三不知的愤怒、对红十字会内部管理混乱与贪污腐败的悲愤,也能感受到他们对部分感染者在发烧状态下逃离武汉、部分商家回收旧口罩再次售出、部分民众拒带口罩并且辱骂工作人员等个体行为的谴责与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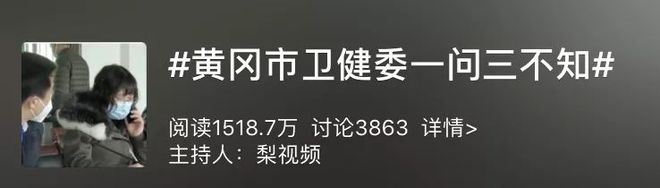
这些社会情绪背后蕴藏的,是社会大众对于个人道德行为规范的普遍要求与期待,具体体现包括作为公职人员应在其位谋其职、不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作为社会公民应具备良好的社会公共道德意识。网民维护理想中的正义成为其愤怒情绪下网络声讨的行为出发点,当其足够强大从而凝聚成一股准绳后,会成为督促政府的社会舆论压力。

换言之,这就是一种舆论监督。这种广泛的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是公众和媒体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对社会进行的监督。舆论监督包括批评、建议、表扬和赞扬,具有主动性、动态性、公正性、批判性等特点,在社会中起着监测、调整、控制和制衡的作用。
在本次疫情中,质问湖北武汉政府领导、质疑红十字会捐赠事宜、质疑疫情数据真实性等都表明了舆论监督一直在线。在这种情况下,舆论监督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使监督意义最大化。同时媒体要坚持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的和谐统一,以防舆论监督转化为媒介审判。
不难发现,社会民众的情绪在社会重大事件中一直处于突出的位置,社会舆论的形成、大多数网络热点事件的发展走向都离不开对社会民众的情感动员。社交媒体将原子化的人们重新网络化,他们的社会情绪也得以聚集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其中蕴含的巨大能量爆发时带来的是正向的舆论监督所促成的社会进步,还是负面的舆论失控所造成的社会混乱,我们无从知晓也难以预测。在此情况下的社会舆情引导是迫在眉睫,也是大势所趋。
共建稳定和谐的疫情舆论场
1. “权威效应”:主流媒体专业合理的议程设置
互联网问世至今,伴随着大量自媒体的涌现及发展,“人人皆有麦克风”、“人人皆记者”的观点开始出现。传统媒体在新技术的冲击下,黯然走下“神坛”。政务媒体是信息的垄断者、自媒体是信息的引领者、传统媒体则变成了信息的跟随者,这一说法似乎成为大众的普遍印象。在新媒体环境下,微博的确具有强大的舆情发现能力,微信的人际传播力也难以匹敌。但从传播内容看,真正被广泛传播的内容大多源于传统的主流媒体及其所属的网络媒体,无论是新闻事实的求证、观点的引导还是信息的综述,都离不开传统的大众媒体。这与后者长期积累的媒介素养、专业的编采能力和坚实的公信力密切相关。

因此,在舆情治理中,面对“人人皆记者”的传播幻觉,传统媒体要做的不是放弃专业精神,而是不断强化专业素养,进行合理的议程设置。唯此,才能在舆论引导中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在武汉爆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的疫情后,主流媒体不断打造关于疫情的议程产生权威效应,不管是各媒体歌颂奋斗在一线的医生,还是强调民众出门一定戴口罩的提醒,都向民众传达了当前疫情的严重性,让民众从思想上认识到该议题的重要,为态度改变和行为反应奠定了基础。
而政府部门在加强新型政务媒体建设的同时,应该高度重视传统大众媒体的专业素养对舆情治理的重要价值,主动为其提供更多的信息,而不应该固守自己的政务新媒体,甚至处处设障,阻挠专业媒体的采访与报道,更不能依赖“删帖”等传统的、落后的舆情治理方法。否则,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舆情危机。
2. “共情效应”:舆论主体内化情绪的“亲历”行为
与“非典”相比,相对新的媒介与不同的“抗疫”公共心理环境,让媒体与公众对特定事件和城市的关心走向多元化。舆论主体能够认识到真相的重量,用“亲历”的方式化解不良情绪,这与公众对事实源头的追究形成了呼应。随着疫情与恐慌的蔓延,一些记录武汉真实日常生活的vlog开始走红。许多媒体发布的文章,诸如,澎湃新闻的《一个“重症肺炎”患者的最后12天》等都向读者描述了发生在疫区现场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将他们因无所适从引起的一系列情绪串联成民族记忆。
一方面,随着疫情的发展,在最初的混乱转为相对有序后,更多的“亲历体”文章在这一阶段得以释出。在更低的时间成本下,人们有更多的心境去消化第一现场的故事,能够形成共情。另一方面,一些诉诸源头的讨论在这一阶段得到延续,形成升格。
1月30日,武汉市四医院爆发伤医事件,当事医生以“不要关注我”、“大家要团结”的姿态平息了这一舆情热点。虽然媒体对公众心理状态,尤其是湖北人民心理状态的关切正在上升,但总体来说,情绪所带来的张力仍非主流媒体所能控制。在普遍性的信心存疑下,“亲历的力量”仍然对公众的情绪和行为有极大的安慰作用。
3.“皮格马利翁效应”:政府部门的有效交互和信任重建
自媒体时代,平等交流和有效对话是政府面对舆情危机最基本的解决方案。在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后,政府应该及时公布舆情信息,主动接受公众监督。面对群体性事件引发的舆情危机以疏通为工作出发点,尊重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合理诉求,为民意表达拓宽渠道。
兰德尔·柯林斯于2003年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指出,互动的基础是获得情感能量,这是人类交流互动的核心要素。根据柯林斯的观点,在互动仪式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人们会分享共同的情绪或者相同的情感体验,当互动仪式诸多因素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后,其关注的焦点到达了高峰,从而产生群体团结的现象、个体的情感能量得到良性宣泄和爆发。
2月7日,关于李文亮医生之死的缅怀和讨论依然无休。而对于冠以李文亮医生“造谣者”不实名号的道歉和为其正名的声音也层出不穷。李文亮的符号含义,已然超过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这一名头,成为公众对此前一系列问题倾诉的一个出口,以此为外延,也引发了“何为吹哨人”、“何为人血馒头”、“情绪的作用”等相关问题的讨论。

7日上午,《人物》杂志“普通人李文亮”一文在朋友圈刷屏,《经济观察报》则将“请为武汉造谣者正名”置于头版。在主流媒体之中,《人民日报》公众号则发表锐评,表示“全面调查李文亮事件,让正义抵达人心”。
当天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当晚,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中。在全民关注的重大舆情事件之中,政府的有效互动和合适作为重建了民众的信任,合理有效地降低了争议和众怒、引导舆情向良性发展。
重大疫情应对中,社会民众在集体慌张与焦虑情绪中的失控、在道德诉求下的愤怒与怨恨,是激发中国语境下某些网络事件的情感逻辑。一场空前的、沉浸式的、裹挟着亲历与情绪的、带来了伤痕的疫情,正在通过每一个舆论主体不断施加的影响,而无限放大。在复杂的情绪中,“人类悲欢并不相通”仿佛需要再仔细斟酌,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每一个舆情事件,一面是最深刻的共情,一面是最难过的悲伤。
吴琼 | 文字
胡云华 | 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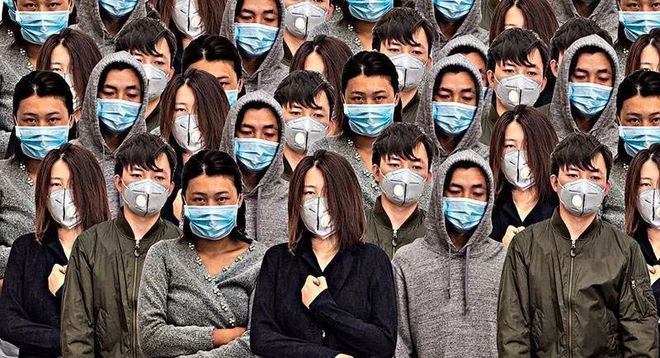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