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深刻之处在于李大钊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唯物史观(经济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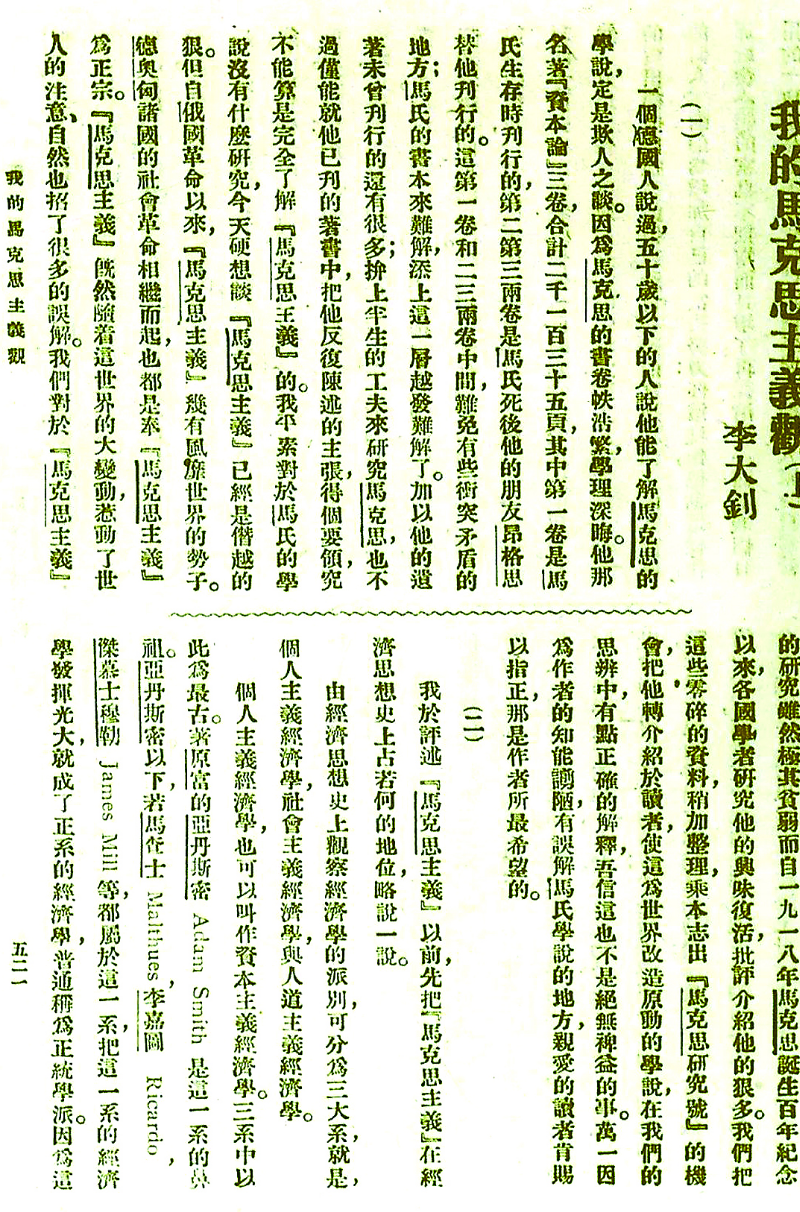
供图 钟诚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李大钊开启了培育新文明之新理路。从历史过程着眼,应特别重视他在两个时期的思想,即留日时期、北京大学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有:《民彝与政治》《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新旧思潮之激战》《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其中,《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可以视为中国版的新文明论。其主要特点在于:深刻反思东西两大文明,深入剖析两大文明之特点,指出培育新文明的前提是自主地“迎受”西方新文明。要享“动的文明”之便利,启“静的文明”之蒙昧,努力使固有之文明“变形易质”,实现西方文明的中国化,这里当然包括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思。
在比较研究中结合中华文明之特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五四时期出现的进步社会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双重影响下,中国思想界发生了近代以来最大的思想变动,其主要标志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尤以社会主义更具实践意义。此刻,李大钊已进入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因为对“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他开始反思“其文明之真价”,在比较研究中结合中华文明之特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其实,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接触并了解了社会主义思潮和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但那只是局限于书本和课堂。真正触发他进行深入研究的源头是他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间发生的一场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讨论,即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从这场讨论中,李大钊得到启示,必须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其中尤其要关注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式。
离京回到湖南后的毛泽东了解到《每周评论》上李大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异常兴奋、深受启发,决意迅速做出回应,期望讨论能够继续深入进行下去。他全力起草了一份《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邓中夏,托他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这份章程共列出了144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社会、国际等诸方面,着力强调解决问题必须“先从研究入手”,这与李大钊的思路完全吻合。此时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开始发生转变,他响应李大钊在与胡适的讨论中提出的“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的号召,准备尝试国民革命实践。而在社会组织方面,他则准备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同李大钊的步调完全一致。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进程中,对社会主义进行严肃的“学理”探讨是从李大钊开始的。在他之前,一些学者在其著述中片断式地译介过马克思生平和社会主义学说,但都仅限于一般性介绍。而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建立在对“学理”的探究之上。他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等于能全面、准确理解其理论内涵、思想内容等。他说:“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李大钊坚持绝不盲从西方文明,而是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尤其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坚持独立思考,正确对待西方文明
李大钊所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反映在其主持的《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开宗明义,首先说明他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本意:“‘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为此,“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
这篇文章是中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富有奠基作用。人们一定会问:这篇文章最为深刻之处何在?依我看来,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正在于李大钊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唯物史观(经济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这篇文章的深刻内涵在今天还有待于重新认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用传统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来界定李大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即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践出发动态分析理论,更不是从认识论角度观察问题。而李大钊明确强调,要用“思辨”的态度对待这“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文章开门见山提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尤其是《资本论》三卷,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极其贫弱”,要“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在这篇对马克思学说进行“思辨”的文章中,李大钊在中国第一次将社会主义的概念和人民联系在一起,提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他主张以唯物史观和认识论为导引,探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尝试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最富思辨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资本论》上。
应该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五四运动的产物,该文以“我”字当头,反抗奴性,充分展现了五四运动的启蒙精神。该文还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坚持独立思考,提出要正确对待西方文明。同样的思想也体现在李大钊《强力与自由政治》一文中,文中提出立言原则:“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完全依循苏俄模式建党,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努力实现自主建党
社会主义作为学理的研究从北京大学开始后,直接推动了在北大建立党团组织的实践活动。社会主义研究会与北京早期党、团组织建立的时间几乎相同,只是各自使命不同,但都被李大钊看作是社会主义实践。这个实践亦包括重点训练有知识、有朝气的青年学生,改造五四时代的学生团体,以实现“大团体”的“强固精密”。
1920年9月至11月间,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李大钊尤其关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他亲自出任执行委员。至1923年,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一定规模,“近增团员,计各校已250余人,皆谋主义之发展,改造社会,拥护工友,推翻军阀为目的”。随后,北方各地在李大钊和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的帮助下相继建团,其中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建于1920年11月,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建于1921年4月,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建于1921年7月。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政治现象,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早于共产党诞生。
这种现象与李大钊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启发有很大关系。1898年,日本共产党创始人片山潜等人在日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两年后,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1906年,日本社会党诞生。1920年12月,日本多个社会主义团体组成社会主义同盟。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均成立于此时。可以想见,李大钊试图以社会主义信奉者的“大团体”方式组建新式政党。在中国北方的特殊条件下,他采取了以“建团”优先的方法,团结更多的青年朋友组建同盟,自然也使得党团界限并不明显,导致“党团不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历史现象。
由此可见,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革命活动的实践,证明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完全依循苏俄模式建党。他们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革命方略,努力实现自主建党。这是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初心”。
阅读链接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综述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李大钊研究中备受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20年来,学者们立足双重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是李大钊之所以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客观条件。从主观层面看,李大钊具备良好的个人素质:其一,勤思好学品质,认真学习、研究并较全面、准确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其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工作作风;其四,对共产主义事业无比坚定的信念。同时,李大钊在探索救国道路过程中,其学术价值取向、人生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之间能自然地契合相通。从客观层面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日益使其中国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迫切需要新的科学理论和新的思想武器。
二是李大钊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李大钊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直接而又热情洋溢的讴歌、缜密而又富于远见的探索以及不懈而又富于创新的躬行过程中,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他最早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前提;其二,他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创建工作,培养了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政治组织保障;其三,他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方法论原则。总之,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从学理到实践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领域作了诸多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陈景阳摘自2019年第4期《党的文献》刊发的《20年来国内李大钊研究述评》
(原标题:《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思辨地对待“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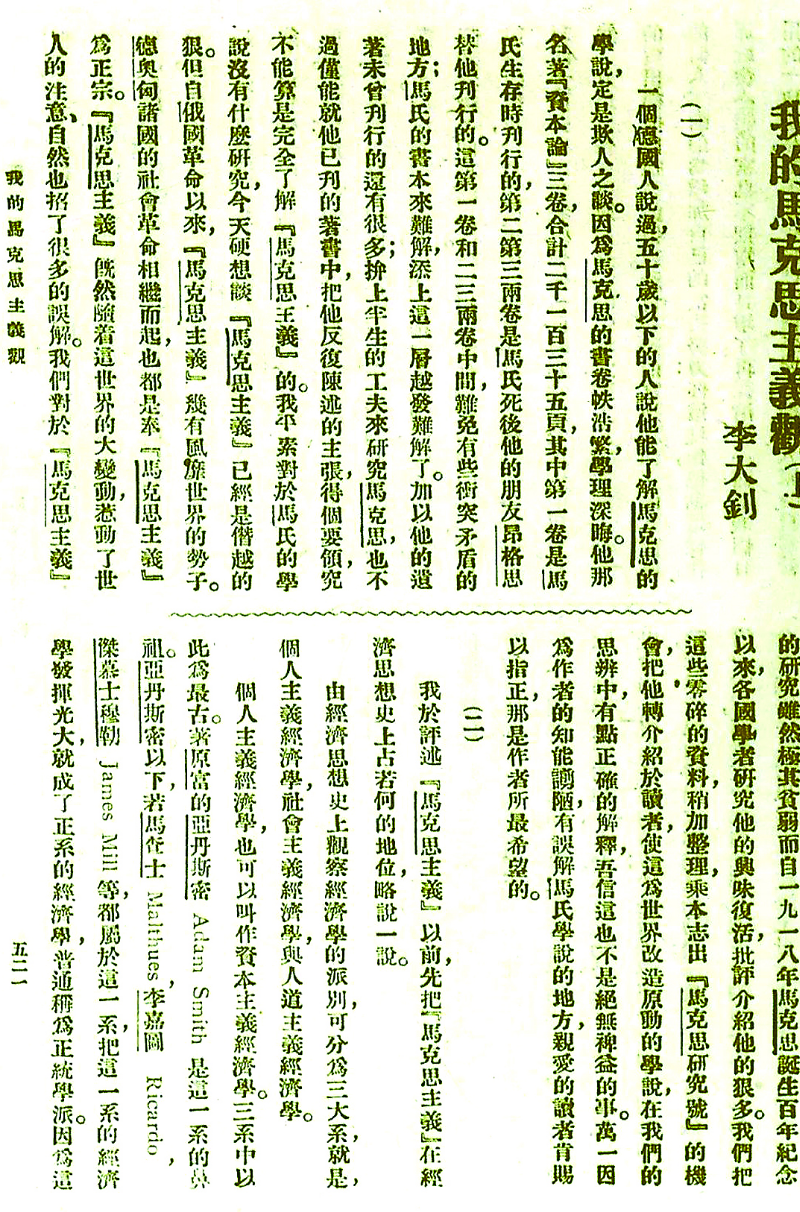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