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国学热”的透视与反思
文 | 李中华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三智书院导师)
从上世纪来到本世纪初,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随着经济的强劲发展,在文化上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这是继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又一次文化热潮的兴起与展现,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与文化的又一次跃升,同时它也向人们传达着一个新的信息: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已经开始找回文化的自信,中国开始迈向文化自觉与注重软实力建设的时代。那么,何谓“国学热”?为什么会产生“国学热”?怎样看待“国学热”?等一系列问题,由于所站的立场不同,观察的方法不同,所秉持的观念不同,所了解的情势不同,故对“国学热”的理解、诠释、分析和评价也就大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上述容易造成困惑的一些问题加以阐明。
“国学热”的兴起及其成因
历史发展到今天,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这是继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90年代的“国学热”所出现的新一轮的“国学热”。
为什么会出现“国学热”?就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是基于对10年“文革”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思想僵化、人性扭曲及文化的严重破坏等痛定之后的全面反思;那么,当今出现的“国学热”,则是对20多年来改革开放及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同步出现的负面效应的一种全球的、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乃至文化的全面反应。
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
首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人类面对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在进入新世纪后,不但没有缓解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中,最为严峻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能源、环境、生态、人口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已经发展到难于挽回的程度,以天人二分或工具理性指导下的工业文明形态似乎已面临绝境。由此,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思维方式的变革要到东方文明中寻找动力”的文化观点,得到较为普遍的呼应。
对文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警觉和抵制
其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Francis Fakuyama)的“终极价值论”和“历史终结”论以及“9·11”以后美国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警觉和抵制,因此提出“文化多样性”、“文明对话”等概念,企图以此消解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并把文化权利作为人权的组成部分,把尊重包括生活方式、共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在内的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看做是和平、安全及发展的最佳保障之一。文化多元化、多样性及文明的对话几乎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表示人类对现代文明的认识不仅超越了冷战思维水平,同时也超越了整个工业文明水平。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多元文化的未来世界里,一个没有文化核心,或只用政治信条或狭隘的意识形态来界定的社会,只能陷入“文化孤立”之中,丧失对多元世界的灵活反应,丧失在当今文化转型中的自主能力,甚至失去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对话的话语权。
改革开放带来生机
第三,从国内背景看,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尽管还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和一些难以预见的潜在危险,但它的发展变化确实令人惊叹不已。用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话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包括古埃及、希腊、罗马和波斯等)能像中国这样,既有悠久的历史,又能在经历百年衰败和屈辱之后重新中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几乎不可思议。”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变化固然有许多原因,但这种变化与文化,特别是与“国学”或传统文化有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有联系,其联系的关键所在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出现“国学热”的又一原因。
对“东亚发展模式”或“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
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都信奉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持的观点,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因此东方只有在皈依基督教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发展。但是,这一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受到挑战。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香港、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超越了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于是一些西方学者又提出所谓“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以区别“西方模式”。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为“东亚模式”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还增加了“根据本国国情谋发展”、“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等许多新内容。对“东亚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本身的研究及其与“西方发展模式”关系的研究,成为“国学热”的一大动因,因为离开中国传统文化,便无法理解和诠释“东亚发展模式”或“中国发展模式”的真正内容和意义。
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文化资源的思考
第五,如何发展和完善“软实力”资源的组合和配备,是实现中国“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当务之急。何谓“软实力”?虽然当前国际、国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这并不妨碍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讨论。美国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提出大国或强国有四条标准: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战略与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学者贝茨·吉尔在《中国“软实力”的源泉和局限》一文中也提出:文化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源泉。
这就是说,来自“软”性因素,其中包括文化吸引力,国内政策的亲和力、国际外交的合理化及其所体现的道德威信等,是大国地位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是与经济、军事、科技同步发展的重要环节。这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是在经济、科技、军事现代化的同时,必须加强“软实力”的建设。这种“软实力”的一个基本内涵,便是文化的影响力,其中包括全民素质的提高、政治文明的进步、国家管理者的道德水平以及各级政府的清廉形象等等。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智慧能否成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文化资源?这也是促成“国学热”兴起的一种重要思考。
总之,“国学热”的成因一定有很多,但是,我们如果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上述诸项应是“国学热”兴起的基本的或主要的原因。
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
面对当前兴起的“国学热”,国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今出现的“国学热”,与一个世纪前国人对“国学”的争辩有本质的不同。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国学”论争,是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题下进行的。当时国人面对的是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入侵,提倡“国学”的动机,是为了通过“保教”、“保学”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反对提倡“国学”者,认为“保教”、“保学”达不到“保种”、“保国”的目的,只有通过“民主”、“科学”等手段,才能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二者目的相同而手段各异,从而导致中西文化的长期论争。
当今的“国学热”,是在人类进入全球化、世界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中华民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痛苦挣扎和艰辛努力,摆脱了巨大的世纪厄难,在文化多元化和文明对话的世界潮流中,“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成为时代主题。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一个经受那么长时间屈辱的中华民族,能够复兴崛起,除了经济的奇迹,我们要寻找这一“奇迹”背后的文化信息,以支撑我们民族复兴的大业能够最终得以实现、完成、发展和巩固。然而,人们的认识并非一致,尤其对“国学热”的理解、诠释也各有不同。
对“国学”概念的差异性理解
对“国学”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就存在很大差异。如前所述,“国学”不是单指“五经”、“六经”或“十三经”,也不是单指诸子百家或诸子百家中的某一家某一派,更不是单指儒学或孔子。“国学”是一个集合性很强的概念,它应该是指中国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所积累、积淀的思想文化的总和。其外延很广,内涵很深。它虽然不是单指某一家、某一派或某一人,但它又是通过某一家、某一派或某一人所具体表现出来的。因此,必须对“国学”内容作辩证理解。
在当前的“国学”文章和“国学”宣讲中,既有专指儒学或孔子的,也有精华和糟粕不分的,可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比如,风水、算卦、相面,甚至推背图一类,算不算国学?这在“五四”时期就有过争论。就一种社会思潮的演进来说,这一现象也不奇怪,但我们确实需要仔细地甄别、小心地论证,不能把“国学热”引向某一极端。一些极端的思想,实际上是在扼杀“国学”。两千多年来的“国学”也正是在这种不断地被“扼杀”与反扼杀中发展的。这样说,似乎还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并不是一见即明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过许多弯路。因为对精华与糟粕的鉴别,也是有不同立场、不同标准的。
在今天,它不应该影响我们对“国学”的理解和评价,因为“国学”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其中包括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或思想体系,都有精华和非精华的成分,这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应该吸取“五四”和80年代“文化热”时期关于中西文化讨论的教训,不能用二元对立思维来看待“国学”。其中,也包括不能因为某些极端的看法和做法,而全盘否定“国学热”的历史成因及“国学”的合理内涵。
“国学热”的意义及其基本精神
其次,“国学热”的意义及其基本精神,不在于形式化的理解传统文化,更不能以“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的口号为招牌倒退到“文化本位”或“华夏中心”的立场。这正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概念。应该说,“国学热”包含有“文化自觉”的成分和意义,但“文化自觉只是指包括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概念,可以成为对当前“国学热”意义诠释的经典表述。这种表述所包含的双重含义,即是为了避免最常容易出现的两种偏向:一是不知“国学”为何物却盲目地排斥,谓“国学”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因此主张要像“五四”时期那样,把“国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二是以“国学”为“回归”而一味主张“复古”,径直主张“全方位的复兴儒教”,并在行为方式上“言古言”、“服古服”、“行古礼”。这两种极端,在当前的“国学热”中都先后出现过。这两者其实都缺乏文化上的“自知之明”。
走中西文化融通之路,创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文化体系
鉴于历史经验,对“国学”既不能采取故步自封的保守主义,也不能采取批判打倒的激进主义,应该是既继承又超越,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走中西文化融通之路,创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文化体系。因此,“国学热”不应是排他主义。所谓“国学热”,应热在民族精神和世界文化的融合。因为在未来世界里,没有哪一种文化形态可以独霸世界,它必定是在充分理解自身文化的同时,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
在当前,最需要注意的是处理好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三者的关系。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后乃至整个20世纪,实际上存在着中学、西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三股强大的思想力量,它们各自以其自身特有的话语系统和思想张力,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各自起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作用。但如果从更高的角度看,直到今天,中、西、马三者之间仍缺乏全面的沟通和整合。在国学热中,有人担心,讲国学的结果,会冲淡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误解。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三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互的比较、借鉴、吸纳和融通并形成了新的文化传统。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是通过“国学热”,更加自觉地选择一条在充分吸收先进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既不忘记本民族的地位,也不轻贱本民族的文化智慧,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调适,使其成为新时代的思想文化资源,从而使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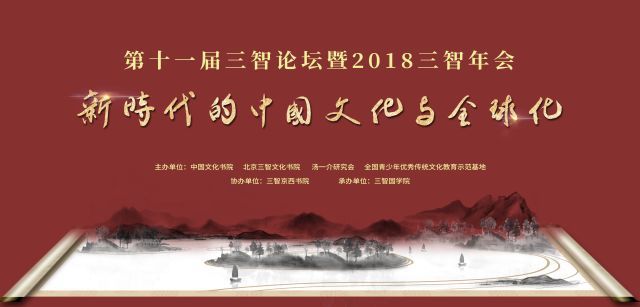
2018年1月27日至28日,由中国文化书院、北京三智文化书院、全国青少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示范基地主办,汤一介研究会、三智京西书院协办,三智国学院承办的“第十一届三智论坛暨2018·三智年会”将邀请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三智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王守常,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李中华,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霁,著名佛教文化研究专家、印度宗教研究专家于晓非,独立学者徐达斯共聚北京,探讨“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与全球化”这一命题,求解新时代如何讲好和传播好“中国故事”,为解决人类问题奉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
报名通道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