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史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领域,四十多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有亟待提升的必要与空间,文化史研究的碎化和泛化已危及其学科地位。那么,摆脱困境的出路在哪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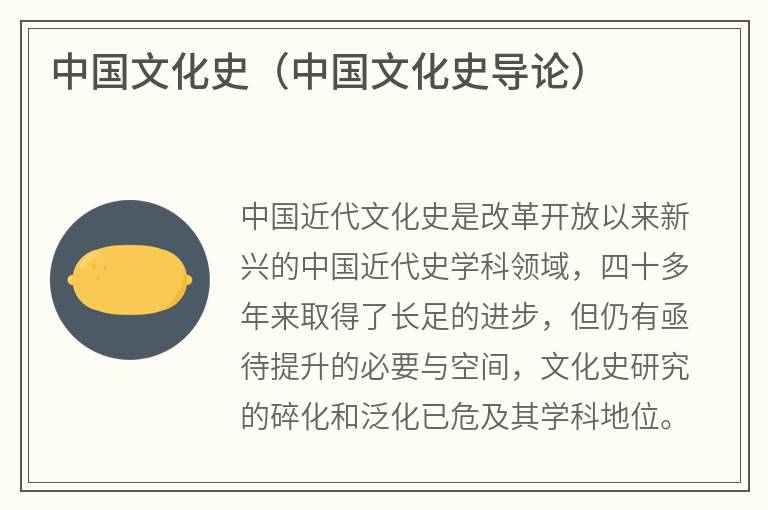
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导论)
文化史研究存在碎化和泛化现象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兴起,并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但近年来,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多及西方新文化史理论的引入,文化史研究出现了较严重的碎化和泛化现象,其学科独立地位存在着被消解的可能。
其一,研究主题的拓展与碎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近代文化史研究主题不断拓展和细化,目前已涵盖思想文化史、学术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政治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大众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图像文化史、媒介文化史、概念史、观念史、知识史等诸多领域。专门化和专题化是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本无可厚非,但现实中出现了见木不见林的现象,有人甚至径称之为“碎片化”。针对“碎片化”现象,有学者提出,“非碎无以立通”,无小难以成大,但问题是,基础性研究和重大问题所要追求的目标、研究的对象、问题的层次和结构并不是量的相加。
其二,研究视角的扩大与泛化。新理论、新方法给文化史研究带来了活力。近些年来,历史人类学、新文化史学、全球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等各种理论方法相继传入中国。其中,新文化史学主张将文化史看作视角和方法,故研究内容所含甚广,不仅指上层文化,更重视下层和弱势群体的文化,还包括习俗、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日常文化。应当承认,新文化史学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但也带来了新问题,其极端表现为,一是过分推崇方法论,强调文化史仅是视角和方法,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那么,文化史就失去了独立性,中国近代文化史作为学科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处;二是夸大文化的主观性和相对性,程度不同地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和语境。
其三,史料和工具的扩充及其带来的问题。电子计算机技术、互联网和大数据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一方面,各类大型数据库的开发和利用极大地扩展了史料搜求的范围,提高了利用史料的效率,为文化史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另一方面,史料的丰富与工具的现代化对研究者的能力,特别是史料鉴别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些研究者满足于搜索引擎所提供的资料,甚至停留于浅阅读,缺乏对选题重要性的鉴别和对大局的把握,也加重了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碎化和泛化。
当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出路
显然,文化史研究的碎化和泛化已危及其学科地位。那么,摆脱困境的出路在哪里呢?尊重文化史的特性是文化史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学术质量、有效规避文化史碎化和泛化的有效手段。科学重专门、重分别,而人文重整体、重会通。文化史在科学与人文两端之间,与政治史、经济史相比,它的人文(或文化)色彩最为浓厚,但这一点恰恰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彼得·伯克所著《文化史的风景》一书在讨论文化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时明确指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今天这个史学碎化、专门化和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文化史变得比以前更为必要了。”文化史之所以变得必要,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整体性。据此,笔者提出三点对策。
其一,回归文化本位,重置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位置。
整体性是文化和文化史的特性,也是文化史研究者追求的价值与目标。诚如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所强调,文化史家的最终目标是考察一种整体的文化。在理论上,不仅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不可分离,而且文化内部的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等也相互依存。换言之,理想的文化史并非专题史和专门史的相加。
对文化史作整体性理解也是时代的要求。历史是过去与现在视域融合的结果,历史正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其参照系,才能被理解,才有了价值和意义。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整个社会发生了“文化转向”,文化渗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经济、政治等趋于一体化。政治上,中共十九大报告把文化建设摆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济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98514亿元,接近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文化与政治、经济已高度融合,仅从狭义上来理解文化史,把文化界定在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范围内,或将文化视作经济基础的决定物,已不能很好地理解和解释现实问题。
职是之故,笔者一再主张,文化史研究应回归文化本位,重置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位置,建设一种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社会科学分科意义上的较为综合的历史学。在新的时代,从整体而非仅是分别、统一而非仅是差异、协和而非仅是对立的角度看待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的关系,十分必要。
其二,优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主体结构,彰显文化史的主干。
文化史要求整体性思维,然而,历史书写必须有所取舍,如何克服文化史的整体性与历史书写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一大挑战。笔者以为,对“文化转向”和新文化史学思潮必须审慎对待,不能一味跟风,仅把文化史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而不重视文化史的实在性,不注意区分研究对象的主次。
老一代学者在处理近代文化史时,基本上把文化史视为一种专门史,将文化史几乎等同于精英文化史。当重置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位置,调整文化与政治、经济等的关系后,我认为需要重新确认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就当下而言,突破专史定位,对文化史作较为广义的理解非常重要,且成为可能。(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