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观察,年纪越大的学生越不喜欢上课举手:稚气的小学生暂时有着举手回答问题的自豪感,年轻的中学生已经觉得回答问题是一种折磨,到了大学,哪怕教师用绩点威逼利诱,年迈的大学生们往往还是无动于衷。


学生们对于课堂发言的态度各不相同。有些学生选择保持沉默,并不一定是因为不知道答案,而只是单纯地不想回答问题。这篇文章旨在探讨为什么中国学生不喜欢在课堂上举手发言。
我们可以从其他文化中找到线索。有趣的是,不仅是中国学生不喜欢在课堂上发言,日本学生也同样不喜欢在课堂发言。相比之下,那些喜欢上课发言的美国学生并不是按照规定的举手方式发言,而是较为随意地发言,甚至可能会打断教师的讲话。这种看似无礼的课堂行为在西方文化中却是普遍现象。

中国学生不喜欢在课堂上发言,但这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正常的,却往往不被西方人所理解。不同的国家的学生对于上课发言的态度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自我概念和文化,即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和相互依赖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
心理学家金和马库斯设计了一项实验,以研究不同文化思维的影响。他们随机选择了一些美国人和东亚人,让他们填写一份问卷,然后再从五支钢笔中挑选一支作为奖励。然而,问卷只是吸引参与者注意力的幌子。最后,看似无关紧要的奖励成为了真正的实验。当参与者被要求从四支同色的笔和一支不同色的笔里挑选一支时,77%的美国人选择了颜色不同的那一支笔。相比之下,只有23%的东亚人选择了颜色不同的那一支笔。这个实验表明,受个人主义影响的人更喜欢独特性,而受集体主义影响的人更喜欢一致性。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体现在许多其他方面。
例如,当向中国和美国的孩子展示牛、鸡和草的图像,并让他们指出哪两个物体更可能在一起时,美国孩子更可能认为是牛和鸡,因为它们都是动物。相反,中国孩子更可能认为是牛和草,因为牛可以吃草。这表明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更关注物体之间的关系。
回到上课举手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偏向集体主义,所以我们在思考是否要上课举手时,比西方学生更可能思考上课举手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我们可能会担心,如果回答错误,会不会给老师留下负面印象?会不会让自己难堪?会不会让同学觉得自己很愚蠢?如果回答正确,会不会让同学觉得自己在讨好老师?会不会让同学觉得我很自负?会不会让同学觉得我很傻很天真?如果我主动提问,会不会打断老师?我的问题有价值吗?会不会影响其他同学听课?
在这一系列的对人际关系的思考下,上课发言成为了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非常重视人际关系,强烈地不想成为特殊的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个人主义可以应对个人的复杂性,挖掘每个人的潜能,但是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利益和公平。集体主义则可以让集体获得长远的、广泛的利益。一个切身的例子是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表现得远比西方国家好,因为我们愿意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一点个人利益,愿意在公共场合戴口罩,放弃一些个人自由。这些措施在西方却受到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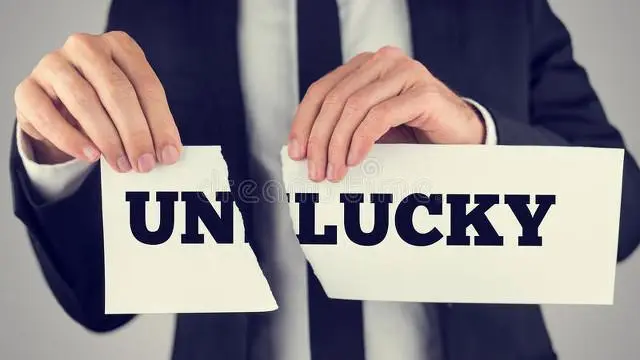
集体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容易成为道德《绑架者》的口号,许多强调集体主义的集体只是借着大义剥夺个人权利。我们需要先明白所谓的集体是真正人人平等的集体,还是内部不平等的空泛的假集体。也正是因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各有优劣,如今的世界正在向个人与集体之间摇摆移动。我们需要试图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现在,西方并不那么推崇个人主义,东方也不那么具有集体主义了。在近几十年,我们可以听到越来越多的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声音。比如,“做自己的事,相信自己可以的,喜欢独处。”我们喜欢独特性和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感。但是我们同时也是社会性动物,有归属需求。因此,我们需要平衡自己的独立需求和归属需求。
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西方学生在提问时会考虑其他人的感受,中国的学生在举手时也不会那么焦虑。我相信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是获取别人的喝彩,人际关系的重量不应该大到把个人挤没掉。在人际关系之外,我们还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一个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遵循自己内心的地方。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