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是历史,职业训练培养了我追寻发展过程的习惯。而且,一切事物的现况,都有其过去,有切不断的因缘。
因此,我还是尝试在历史的视野里瞻顾“中国学”的演变途径。
虽然本书的主题是美国的中国学,但我还是想先讨论欧洲的中国学,亦即所谓的“汉学”。毕竟欧洲的汉学早于美国,美国早期的中国学长期受欧洲学术传统的影响。
01欧洲的中国学
欧洲学术界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兴趣,早在启蒙运动时代就已经萌生。
当时,为了摆脱天主教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体制,欧洲人对东方的另一文化传统政治体制有一番向往,盼望借他山之石,作为改革的依据。一些学者,包括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从来华耶稣会教士寄送欧洲的报告中,撷取资讯,建构了理想化的东方。
这一番努力毋宁是为了发抒自己理想的郢书燕说,难免有失真之处。
18世纪以后,西方与中国的接触较多,西方商人与外交人员从东方带回的讯息,与过去建构的东方大不相同。欧洲学术界遂开始认真地尝试了解中国。法德两国的汉学是将西方近代学术的经验直接施之于中国研究。
那些学者,各自在语言学、档案学、考据学等方面已有训练。同时,他们也从西方及中亚旅行者的记录深入研究中国,其成就遂能在欧洲最高学府有资格与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分庭抗礼。法国的儒莲、沙畹、伯希和、马伯乐,德国的福兰阁和傅吾康父子,北欧的高本汉等都对中国学研究有重大贡献。
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也很受这些人物的影响。
在传统汉学领域外,欧洲的学术课题对于中国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冲击。
马克思理论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及其衍生为东方集权政体的性质;韦伯资本主义研究中的中国模式及为何资本主义萌生于西方;后来李约瑟提出的中国优秀工艺科技传统为何在16世纪后不能赶上西方的近代科技:这三大课题,其潜台词毋宁都隐含着西方与东方有极大差异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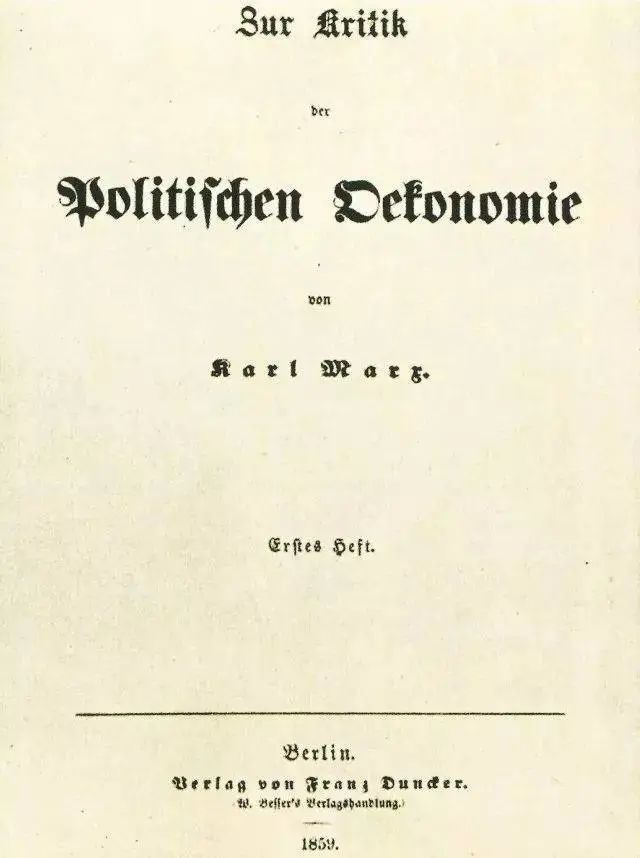
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犹如吉卜林所说,东是东,西是西,两方永远不会交集。爱德华·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其实即是指陈西方人以其自己的尺度,界定东方是“他者”,这一潜台词,反馈于中国与日本,也是东方自居于西方界定的性质,甚至于袭用西方的尺度,以界定自己。
例如,长久以来,中国与日本都用西方历史的“古代—中古—近代”三段分期。又如,马克思已将东方列入不同于西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却还在硬生生地套用“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段分期。
02早期美国的中国研究多出于实用目的
欧洲的近代学术研究已经相当发达时,19世纪到20世纪的美国学术界不过是欧洲的附庸。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也还有一段成长过程,方能逐渐发扬光大。
美国人开始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与英国的中国研究颇为相似,都与19世纪以来的在华传教与对华贸易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英国剑桥大学的汉学讲座是由传教士翟理斯出任的,美国耶鲁大学的汉学讲座也是由传教士卫三畏开始。
美国派出的传教士,有很大比例是前往中国;在华外国传教士中,美国传教士占了半数以上。他们在华传教之外,还参与不少社会服务,例如教育、医药、救灾等等。
同时,美国对华贸易乃是美国外贸的重要部分。来华美国人,包括传教士、商贾、外交人员,及在教会学校执教的教员,都将有关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资讯转输给美国的学术界和文化界。

清末福州传教士雅丹金(右)
国会图书馆、东北诸州的大学及博物馆等都获得了丰富的文物和图书。而由华返美的学者,则转入大学,培训中国学的人才。另一方面,美国青年赴中国传教,既能学习中国语文,也有直接观察的机会。
然而,如此庞大的储才库却没有能促使大学和研究单位发展专业的研究群体。到20世纪40和50年代,全美的中国研究专业学者还只是以百计。
胡适之曾经组织巴尔的摩中国研究圆桌会议,参加的学者不过数十人而已。那时的华语教学体系,学生也有限。20世纪早期,若有学生要学中国文言文,以研究中国典籍,只有追随贝托尔德·劳费尔等有数的几位学者。
整体言之,美国的中国研究受惠于传教与通商,也多出于实用的目的。
美国门户开放的外交政策及传布福音的教化心态,也有着潜台词:强大,富有与文明的“我者”,尽心尽力,施惠于善良、贫穷与落后的“他者”。
两者之间的主从关系,也决定了早期美国中国研究的课题。
03二战后的美国以西方思维揣度中国特质
1930年美国经济大恐慌,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迅速恢复了经济发展,很快成为世界列强。从此至二次大战以后,依然执国际之牛耳。
在为期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也经历了关键的历史时期。北伐成功后,日本不断侵犯中国,终于爆发成为时八年的抗战。国共之间的对抗,最后又经过五年内战,中国身处惊涛骇浪的大变化中。
这期间,美国却正在迅速扩大其国际影响,中国更是美国可以伸张的空间。反映这一形势,美国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也有了自己的方向。
美国的中国研究,因基于美国人寻求了解中国现状的急切需求,媒体人员与学者纷纷报道有关中国的讯息,媒体注意重点在政治与战争,学者的研究课题则超越了传统的“汉学”,不再局限于文史语文为主的范围。
赛珍珠的丈夫约翰·巴克、葛德石、德效骞、施坚雅、莫顿·弗里德等人的研究广泛包含了社会结构、地理条件、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课题。他们的著作至今还有相当的价值。
抗战前及战时,也有不少文史哲学者来华,例如顾立雅、费正清、德克·卜德、傅路德、恒慕义、狄百瑞等人与中国学术圈有颇多切磋,吸收了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配合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很多人遂成为中国研究的一代宗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的大革命及之后的冷战,创造了美国对华研究的重大发展。
美国青年,在远东战场上归来,对东方有了直接的认识,美国的《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资助复员军人深造,公私基金会的补助研究计划,战后大学的扩张等等,都使美国的“区域研究”有了空前的开展,其中尤以“中国研究”为发展重点。
当时的国际情势,使在美国的中国研究有机会吸纳欧洲与中国的学术资源。希特勒反犹太政策使许多犹太学者辗转来美,例如艾伯华等人。而中国的抗战及内战,使许多中国学者来美国执数,如赵元任、李方桂、萧公权、洪业、邓嗣禹、杨联陞、刘子健、杨庆堃、许烺光、刘大中、周舜莘、何炳棣、袁同礼等。
他们谙熟中文资料,又能掌握当代的研究方法,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发挥了关键性的扶翼之功。他们与美国已经有所成就的学者彼此之间,亦师亦友,却经常自居客位,让学者叱咤风云,成就学者的领导地位。
这一代的弟子们,在此后二三十年,分布于全美各大学及研究单位,1960年代以来,各处公私大学设立中国研究专业者,不下百余所。其中大型中心有十余处,中型中心有十余处。大多院校则大致会有三、五位中国研究人员,分别在人文社会学科执教。1950至1960年代培养的学者,早期有贺凯、芮沃寿、芮玛丽、史华慈、列文森、傅礼初等人,后期有魏斐德、史景迁、伊佩霞、罗斯基与罗友枝夫妇、白威廉等人,都卓然有成。
美国的中国研究规模已颇为宏大,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会员人数,也约有三、五千人之多。

亚洲协会(Asia Society)是1956年在美国创办的民间组织
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研究已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外,拥有了最大的阵容,最多的图书,最丰沛的资助经费。出版的论著,也不是其他西方国家的中国研究所能望其项背的。
1950至198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范围几乎涵盖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变动、经济形态的变化、族群关系、国家权力、中央与地方、城乡关系、宗教与民俗、经典文学、艺术、音乐等等,无不有学者倾其心力,沉溺研究。
其中,若以研究课题定,在早期(1930、1940年代),大约涉及中国能不能走入现代世界,后则提出共产主义革命为何在中国能够夺取政权,这两个题目先后凝聚为“西方对中国的冲击与中国的回应”,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两大陈述方式。
接着,日本汉学界提出的东洋/中国之变、中国国家特色理论及内藤唐宋转型理论所涉及的中国“近代的起点”,凡此理论,都融入美国的中国研究之中,成为讨论聚焦之处。
不过,美国的中国研究终究还是有其潜台词:中国为何不能演变成像西方一样的“现代国家”与“现代文明”?
这种心态,还是以西方尺度与模式揣度中国的特质,及因为这些特质而不能发展为“现代”。
1950年代,麦卡锡参议员发动反共的学术迫害,应对美国朝野的质问“美国如何失去了中国”?言外之意,中国本来应是生存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的。

发动反共学术迫害的麦卡锡
这种心态,还是自居为老大哥,亦因为中国的变化,竟是如此地不可思议!
借用轻歌剧“My Fair Lady”的句子,稍加修改:美国的中国研究,可能也是“为什么中国,不能像我们(美国)一样?”(原句是:Why can't women be like men ?)
04改革崛起后中国成为热门研究课题
1980年代后,情势起了变化。中国在改革后逐渐崛起,引起世人注意,研究中国成为热门。
柯文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历史学家,在1983年和1985年两次撰文对以西方立场研究中国的做法提出批评,他提出“中国中心论”,主张中国研究应以中国及中国文化为主体,讨论其内容与发展。
柯文的论文引起相当热烈的讨论。

史学家保罗·柯文
我们必须注意,柯文的论点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1960年代以来,美国经历了异常宁静的文化革命。自由主义者坚持回归个人自主性,以求摆脱权威与传统的规范。同时,世界各处接触频繁,不同的文化必须共存,文化的多元性已是日常经验。
再则,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引发了妇女运动,各种弱势人群也要求机会平等,不容所谓“主流”社会独占发言权。中南美各处的独立革命运动,也指斥殖民主义下弱者的依靠与附属于权威。
他们的指证证实了赛义德“东方主义”症状对于区域研究造成的扭曲。这股思潮伴随而起,加强了冲击力。
柯文的观点,也反映了一时的文化剧变。
当时在法国已有相当影响的年鉴学派,研究方向指向文化与自然条件和相应的社会与经济情况,却将政治与上层思想认为是较为短暂的表面现象。
于是,年轻的学者们,感受时代风气,选择研究课题时逐渐改变了趋向:常民生活与心态、地方与边陲、妇女、劳工、农民与弱者的地位、生态环境等种种问题遂为学者关心之所在,一改以帝王将相、国家制度、战争与外交,思想大师等为研究重点的传统。
05“中国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项目是否还有意义
20世纪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昭然可见,虽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世界性经济系统的出现,追溯到16世纪时大洋航运联络了几个大陆,形成庞大的经济网络。

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20世纪的两次大战,发达的交通工具,以及最近迅速发展的资讯革命,地球各处的人们确实已经连在了一起。“地区研究”在全球整合为一体的情势下,已是明日黄花。
因此,最近十余年来,跨地区的研究,包括地区之间的接触、交流与融合,以及地区之间的比较与对照,已是常见的学术课题,有人甚至认为“地区研究”已不再重要。
这些现象令人悚然警觉,今日再将“中国研究”当作一个学术项目是否还有意义?尤其百年来的学术传统,在此大转变的阶段,下一步究竟会走向何处?
我经常参与美国地区学术评审的工作,这二三十年的变化,可以看到一些趋势:无论是人文社会学科,抑是中国研究的范围,研究课题逐渐由国家转向社会,精英思想转向平民心态,典章制度转向日常生活,使用文献转问访谈与计量,关心主流转向关心弱势,宗教研究转向信仰与仪节,个别人物转向一般众人,静态结构转向动态运动,单一现象转向多项的整体讨论,以及经济之外,还注意生态与天人关系等等。
凡此现象,都指向一个趋势:过去的传统与今后的发展之间,未必再是单纯的延续与开展。
不过,议题分散也可能造成无法聚焦的后果,以致虽有陈述,却不易分析:数量增加,却难有累计增长。虽然学术探索领域开拓了,却可能发延而难以阐释其义。
这是一个拓荒的时代,如何整合,有待学术界的努力。
05海外中国研究的现状
回到编纂本书的宗旨,亦即海外中国研究的现状。
一百多年来,前一段乃是西方在摸索中国的面目,中间一段是西方想要改变中国,冷战期间,西方欲了解其敌人的内情。因此,所谓“观察中国”(China Watch),曾经是政治、社会、思想各个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
最后一段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已不再是吴下阿蒙,西方更是投入了大量资源。如何面对这个不可忽视的中国,将中国当作既须合作,又难免冲突的伙伴。
这段发展,恰恰叠合于学术研究出现大转变的契机。从西方学术界的形式论,将来的中国研究可能不再是列在“主流”学术圈外的一片“边区”。
一百多年来的成果,无论质量抑或数量,“中国研究”已可与主流的西方研究相埒。下一步,中国研究将融入“学科”之内,以“中国研究”的成果,参加建构理论的依据。
这一防线,大概势所必至,好在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关键只在能否走得顺畅。
从中国人的立场看,海外中国研究的成绩确实有可佩之处。尤其中国曾有过数十年的寒冬,学术田园形同荒芜,至今已有转机,但还谈不上春华秋实。海外中国研究的成果,颇有填补空白的功能。
国内学术界,久旱之后也可能敞开胸怀,照章全收,甚至视西方的中国研究为范本,不假思索,亦步亦趋,奉为真理。
但我身居海外数十年,常常感觉人文社会学研究不同于数理科学,学者终究必须通过语文关口,同时文化的临场感也制约了观察与陈述的能见度与敏感性。

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许倬云先生
如果说西方人在使用与领会中文资料方面有其不足之处,但他们对西方文学表达与复述方面则有驰骋的空间。在临场感方面,西人可以客观地观察中国人所习以为常之处,却也未必人人都能有鱼在水中的直接感。
反过来,中国人恰是在理解中文资料方面有其长处,却不易掌握西文的表达与复述。且中国人身在庐山深处,又未必能见到庐山的真面目。任何学术研究人员,尤其“地区研究”的学者,都必须具备能出能入的反省功夫,既能从情境外做客观的观察,又能进入情境,领悟体会其不着言诠之处。
如此徊还映照,方能得到适当的分寸表达陈述。再进一步阐释解读,终于建构理论,以抽绎其普遍性的意义。
西方学者中的前辈及中国学者中的通人,往往可以到此佳境。
近数十年内,台港大陆的学生,中文能力已有不足,目前未必能够欣赏传统文化,将来是否有人能出入内外境界,颇令人担忧。
总之,中国人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中国文化的发展历时久远,人类社会的共同经验库中不能缺少中国这一大块。
陈述与解释中国经验,是了解人类经验的宏大事业,不论华人或西人,都应有人投注心力,参与其中。西方人已提供了不少成果,中国人更该投身于这一共同的志业。
(2009年6月17日 于匹兹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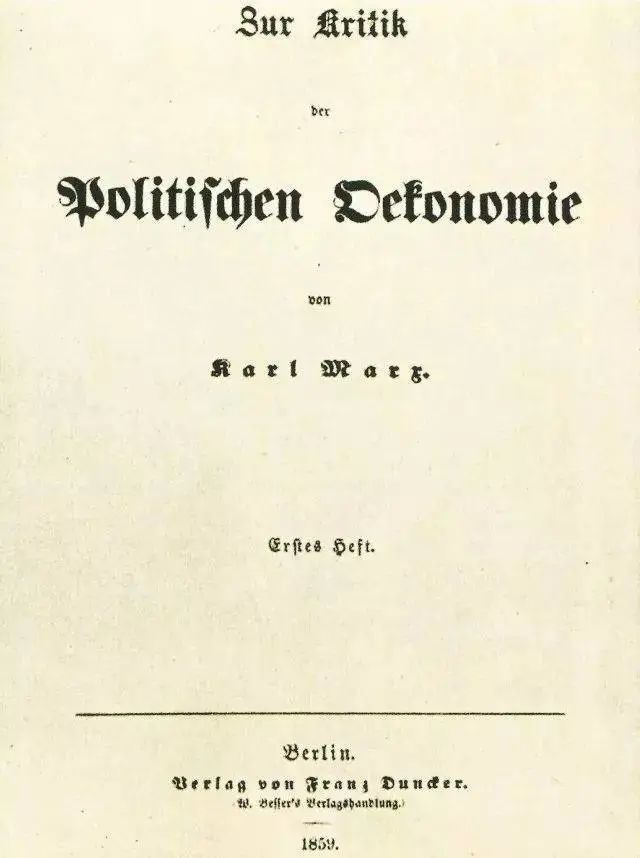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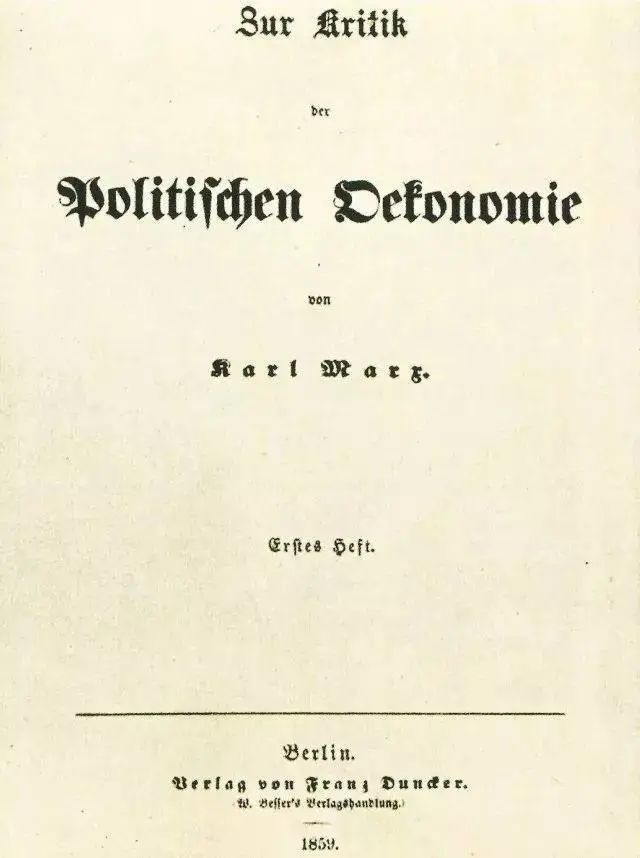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