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民国重看“国学热”,梁启超嘲讽“传统”,今天的人该怎么看?

梁启超有言:“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过渡表现在方方面面,思想文化的过渡变迁也是“千年变局”中的重要一环。传统的思想、文化在近代面临着西潮的巨大冲击,这是中国古代所未有的。自从80年代“国学热”兴起以来,传统是什么,传统如何与现代结合,不仅仅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问题,也是在“过渡时代”下的中国转型的重大议题。
一、西潮冲击下的中国
作为历史上主体相对统一并延续至今的国家,中国在全世界仅此一例。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历史悠久,思想文化自成体系,今人看来自然十分自豪。但这在梁启超眼中,却是不折不扣的“老大帝国”,传统在他看来是“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垒,为过渡之大敌,然被有形无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过渡之途者也”。这样的观感无意中点明了一个现实,当中国在近代面对着西方文化的冲击时,似乎难以转身,甚至不知何去何从。
中国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从不缺乏文化自信,这表现在传统天下体系下的“夷夏之辨”。在天下体系中,中国顾名思义是处于天下之中的,西周何尊的铭文即有“宅兹中国”一语。当时的中国尚单指洛阳一地,但随着疆域的扩张和文明的扩展,中国也成为王朝统治下地域的称呼。中国内的百姓,皆是华夏,是知礼仪、明是非、孝父母、尊君长的人群。孟子有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华夏文质彬彬,而蛮夷则是野蛮的代表。在中国古人看来,华夏的自信便来自于文化,来自于传统的礼乐制度。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通过文化的感染力,自然可以怀柔远人。

周润发饰演的孔子
但在近代,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华夷态势逆转,中国由“文”至“野蛮”,从“华夏”降格为“蛮夷”。
作为较早睁眼看世界的郭嵩焘,在出使英国时,切身感受了西方文明,不由大加赞赏,心中已对既有的“华夏”“蛮夷”之分存有疑虑。早年留学美国的胡适曾说:“当中国酣睡之时,西人已为世界造一新文明。”这是一个不断演进强化的倾向,愈往后的读书人,对中国传统的怀疑愈重,对其批判也愈激烈。百日维新的参与者谭嗣同,便曾大加批判中国两千余年的制度:“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稍后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更是说:“传统既然是个整体,就必须全面反对,即使孔教并非无一可取,也不能不彻底否定之。”可以看出,中国对传统的信心已经消失,更重要的是,传统作为一个“整体”,被认为是负面的文化,所以要被遗弃。

胡适
这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前所未见。古代中国也经历了多次文化变迁,域外文明的传入也曾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知识思想体系。但其都被中国传统消解、融合,例如中国化的禅宗。此外,古代士大夫从未对儒学,对整个历史所遗存下来的“先王之法”做完全的切割。同样是西潮的传入,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也尚未引起士人对自身的全面怀疑。
如若将原因全部归结为政治上的失败和西方船坚炮利的极大诱惑,似乎不大能讲得通。古代中国也多次面临“蛮夷”的入侵,且大多时候中国武力不占优势。例如宋朝被元灭国,清朝作为满人入关,也是被华夏传统所“涵化”。应该说中原王朝即使处于战略守势,甚至被外族灭国,但文化依然保持着生机,并同化了入主中原的外族。近代中国虽然在西方侵略下被打开国门,但主权尚能维持,亡国灭种的危机并不太显著,况且在以往中国人的认知中,并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为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首先就立不住呢?原因当在于中西学战、文化战的过程中,中国传统落下阵来。
近代的西潮传入,是西方有准备的学战的结果。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有传播西方文明的任务,西方以成体系的知识对抗中国。国人的观念逐步被西方的判断准则所改变,便不得不对西方亦步亦趋。

传教士
二、社会权势的转移
近代的西方文明,带有全球扩张的性质,对全世界的前现代国家都有着巨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前现代国家不是被征服成为殖民地,就是自身内部的社会结构开始变化。中国的情况属于后者,社会结构的改变,更使得传统无法立足。
清末新政里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废科举。在传统中国社会,科举制是相当重要的一项国策。诺大的一个农业国家,政权控制无法有效地下达到乡村地区。“皇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的说法可能稍显绝对,但在整体社会结构上确实如此。而科举制不仅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社会流通渠道,更是将国家所提倡的思想文化和价值理念传播到基层。儒学以此成为帝国内部通行的价值体系,也使得整个国家结构相对稳固。这其中,士大夫(乡绅)的作用不可忽略,他们在朝为官,在乡为绅,是国家的中间阶层。一方面,士大夫是“道统”的传承者,他们自身便是读书人、学者,维护着既有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地方权势的掌控者,肩负着维持地方秩序,教化百姓的责任。

1905年,科举制废除,导致社会权势发生了改变。科举制废除后,曾经的上升通道被断绝,改以新的方式选拔人才,这些乡间的士大夫们,无法再以曾经的方式上升。而且科举改革后,西学逐步成为主流,代替中学成为主要考试科目,而西学在传统的乡间是无法习得的,无奈之下,大批士人只得走向城市,另寻出路。这不仅带来了城乡分离的结果,更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传承人。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生长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便是扎根于农业社会的乡间土地上。离开了乡土的士大夫,放弃了地方的权势,也放弃了传统的文化,从以往社会权势的重心,变为了社会的“边缘人”。
大批进入城市的士人,思想不中不西,不新不旧,既未受到严格的中学训练,一时间也无法系统学习西方知识,他们初通文墨但不精,他们不再留恋乡土,在认同方面,更倾向于西化的城市精英。例如尚处于上海求学时期的胡适,“见人则面红耳赤”的不自信、“自命为新人物”的渴求以及一直在等待“我的机会来了”的心理,正是思想文化过渡时期士人尴尬处境的体现。在城市中,这一批人只是边缘知识分子,像胡适这样做到留洋而成为知识精英的尚为少数。要跟上城市的脚步,被认同为精英,他们必须趋新,由此便走向了激进化的道路,更为强烈地反对传统。
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传统士人的转型,当然不会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消亡。但是,曾经传统文化的辩护人已然转型,乡间的农民又无法有意识地以中学对抗西学,种种变化自然导致思想权势移位。

三、失去思想重心:中西、新旧的纠葛
近代中国应当可以说是失去思想重心的时代,不同的个体表现出不同的纠结。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学体系下,逐渐无法自我表述,而民族主义的情绪,使得当时人不得不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方面的转型都面临着许多问题。
且以学科建设和中医为例。中国传统并无如近代西方一般的严格学科划分,经史子集并不如历史、哲学、政治等学科有着明确的界限。近代中国跟随西方的脚步,以西方的学术分科框架来审视中国传统学术,不免会有削足适履之感。胡适对历史的态度是“截断众流”,倡导“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便是希望以西方的学问重新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以此再造出适应现代文明的中国文化,但这个过程却异常艰难。让胡适暴得大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的书名,便被陈汉章所嘲笑,他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以今天的眼光看,哲学史自然不是哲学的大纲。但在新旧交错的近代,陈汉章之言不得不重新审视。大纲和史的差别,其实体现了两人对史学和哲学的不同理解,在近代的分科体系下,各科畛域不明,传统文化是史学还是哲学,一直是争论至今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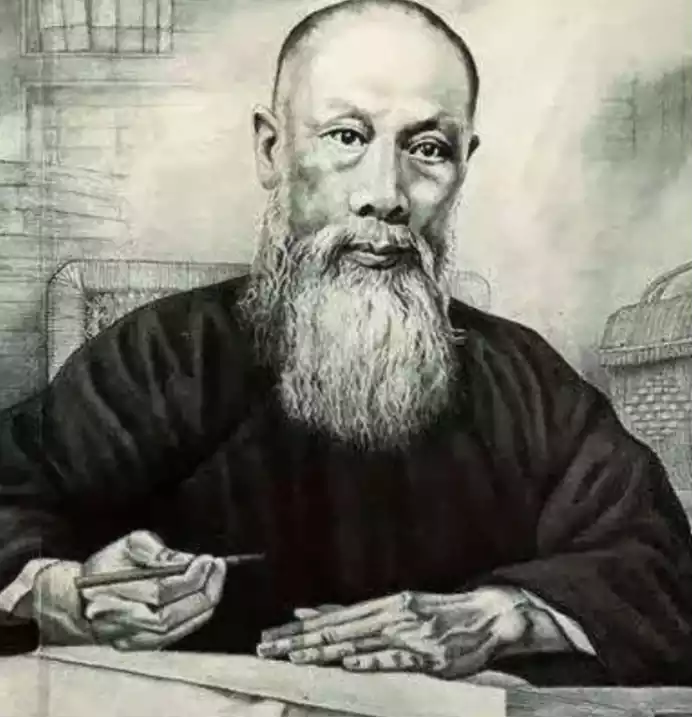
陈汉章
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在近代西医的冲击下也显得无法适应。传统中医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其与传统的思想有着很深厚的联系。中医的上层被称为“儒医”,与儒学有着共同的可理解的话语和知识,一定程度上,中医也是中国人传统世界观的表现。中医因其直觉性的思维,以及更多经验性的诊断方法,面对西方科学体系的冲击,往往“理屈词穷”。相当程度上,中医的衰落是儒学体系对抗科学体系的缩影。当然,时人也有拯救中医的措施,历来希望将中西文化接头的梁漱溟,便有志于沟通中西医。但当他亲身研究后却失望地发现,中西医是“彻头彻尾的两种方法,竟然是无法沟通的”!所以他得出,沟通中西医在他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但在将来却有可能,但这需要依靠西医自身的转变。显而易见,仍然有人相信传统,但这种自信却无法用已经占据话语主导地位的西方科学来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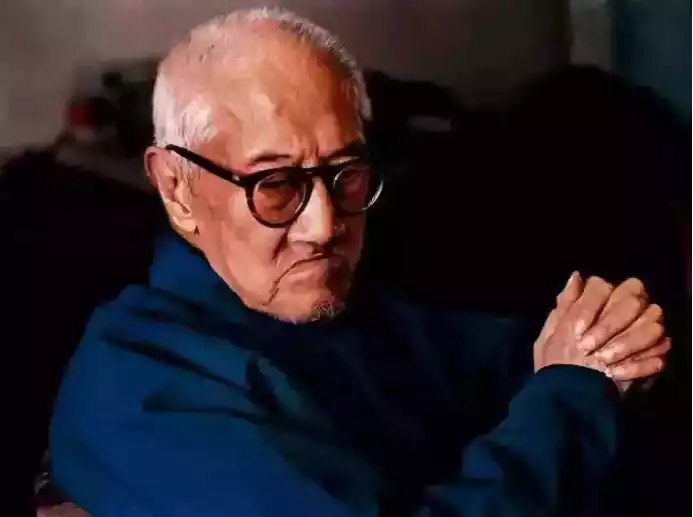
梁簌溟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的思想人物并无完全的新旧、中西划分,更多是新中带旧,旧中有新的混杂状态。所谓的守旧派,例如钱穆、陈寅恪,实则含有新的成分,更显著的例子是留着长辫子却精通西学的辜鸿铭。而新派中的胡适、傅斯年等人,却认为“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这种状态,使得中国近代的思想界,缺乏一个稳固的重心,总是兴起一拨人未过多久,又一批更新的人兴起,直斥前者守旧,显示出老师跟着学生走的趋势。
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无法在新旧、中西里找到稳固的落脚点,而沟通中西又难以完成,中国近代的思想也愈发激进化。

辜鸿铭
文史君说
近代中国传统逐渐“失语”,而新思想的重心又无法有效建立,导致近代中国思想界错综复杂。今天我们仍旧面临着同前人一样的问题,在高谈文化自信,重新发掘传统的今天,由谁来定义和解释传统,仍然悬而未决。钱穆先生言,“文化只能放在历史中去理解”,当传统只属于历史时,如何面对现实呢?若只将传统当作维系今人认同历史的工具,或许太对不起心系天下的古人了。
最后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仅仅需要“坐而论”,也需要大众的“起而行”。这个工作,不是近代时人可以完成,也不是我们这一两代人可以完成。或许,向古人学习,多一些“天下胸怀”,浑融中西古今,在将来并非不可完成。
参考文献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