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相册《随手拍第三片——富顺孔庙》里的“棂星门”说起。这座“棂星门”据说是世界之最,高22米,比曲阜的还高。四川话里的“灵醒”就出之于此,“棂星”的本意是文曲星,可川话的“灵醒”不光是学习好的意思,还有聪明伶俐,机智懂事的意思。不但包含智商,还包括了丰富的情商含义在里面。想来夫子应该认为川人的理解和运用要比专家好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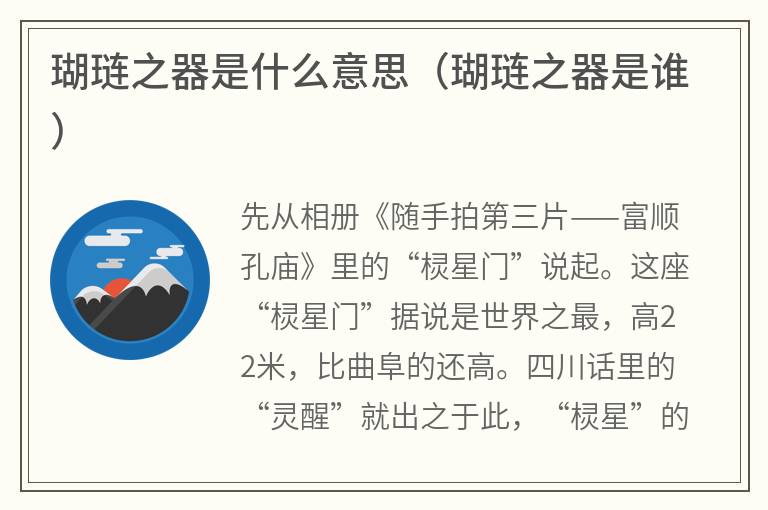
瑚琏之器是什么意思(瑚琏之器是谁)
成都方言的文化底蕴很是深厚,富于幽默与豁达。和“灵醒”一样,“宝器”大概又是比较经典的一例。把圣贤之道能体味到这种程度,又融贯于日常用语,至今常用不衰。真是把文化的传承做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了。
京派贬人“二傻子”,简称“2”。这是俯视看人的感觉,自己是老大,是A,对方是老二,是傻B(B的本意是“妣”的声母)。再深究一点,就有考据称:皇上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排行在“二”比较的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天生就是吃亏的傻命。
海派人贬人“十三点”,有点像猜字谜,言语里透出狡黠和不屑:“侬晓得13点唔啦?”
“弗晓得。”
“‘痴’呀!”
成都人不同,踏谑某人时,可以当面平静地来句:“你娃宝器。”或简称“宝”,缀副词以加重语气是“宝得很。”被称为“宝器”的如果争辩,一般回一句:“你才宝器。”但在很多时候还来不及回嘴,就被指出现了“宝”像,比如裤衩外穿楞充超人之类的行为,登时也就沉默无语,反思己过了。成都人斯文,一般不会:“老子就要这样!”地耍横,也很少脸红筋涨地硬撑,多半是解嘲而已。
这“宝器”的来路也如“灵醒”一样,很是高雅。《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典出《论语》,不得了的。为了明确“宝器”这个词的高贵血统,首先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如果把“宝器”写作“宝气”那是肯定不对的。“宝器”肯定出自《论语》,而绝不可能出自“珠光宝气”那样俗不可耐的俗语。
再者,最为意味深长的也就在这里了。把夫子夸赞高足的比喻发展成戏谑贬低别人的方言,是不是有点不敬经典呢?哈哈,我说川人对经典的理解可能还高于某些专家,而且更加贴近夫子想表达的本意。在这里,“宝器”一词就是这样滴。不是虚夸川人,真的有文化哎。
当时夫子办学,好像还没有单元考、月考、半期考、期末考等等规范的考评体系。对学生的考试评价大多是夫子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行为,比如人尽皆知的“朽木不可雕也”就是评价宰予的。要是行为就很雷人了,比如看重那个劳改释放犯的学生公冶长,就把女儿嫁给他,直接整成女婿。而且“宝器”出处的这一章就叫“公冶长”,夫子看人还真不是只看分数的。
也许是才华也很好、财产也很好、相貌衣着都很好。也许是瞧不起公冶长。反正端木赐,也就是子贡有点急了,直接开始向夫子讨要评语:“你看我怎样?”
夫子多客气的说了个:“你娃还算是个东西。”
子贡是啥子人,子贡的特长就是嘴好使,紧接到连续发问:“那是个啥子东西?”
夫子心想晓得你娃嘴长,早就准备好了答案。曰:“瑚琏也。”
这个“瑚琏”就是资格的“宝器”,是一种用玉装饰的礼器,所以“瑚琏”两个字都是玉傍。庙里用来装祭祀贡品的器皿,尊贵而堂皇。但也仅仅就是礼器,百分百的面子货。顺便一提,当时的庙还不是后来宗教的场所,而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在分封的年代,祖先是真正有血缘有血统继承关系的。所以,当年对祖先的祭祀是真心而隆重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而这个整天在已经升天的领导身边,别人不得不尊敬,面子上也光鲜靓丽的东西,就是“宝器瑚琏”了。
要说夫子的学问大如天,深似海也就表现在这里了。他对子贡的评价客观准确又是彬彬有礼,既直白地说出子贡的不足,又给足了面子。就是能言善辩的子贡,也只有接受的份了。
成都方言里的“宝器”,正是贴切、恰当地引申和发挥了夫子对子贡褒中带贬、先褒后贬的评价。理解和运用夫子的意思再一次超过了专家。为了说明此言不虚,再引两句《论语》:
第一句,《论语·为政》子曰:“君子不器。”这句直译为:作为真正的君子就应该不是个东西。呵呵,这不是夫子在骂自己,而是话没说完。下半句是:真正的君子应该是个人,一个完人。(这也是中国话复杂纠结的地方,从这里引申出来:“不是东西”;“不是人”就都是骂人的话了,使人忍不住要大吼一声:“到底应该是啥子嘛!”)由此可见,如果夫子以“器”喻人,本身就已经带有贬义了。随你学者咋个编出花样翻新的解释,也不如成都方言一句“宝器”的意思来的精准直白。
第二句,《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夫子眼里,子贡就是要比颜回差许多。二人在对话时,貌似子贡还在谦虚中,夫子已经直接了当的说出:“我同意你的意见,你就是不如颜回。”颜回已经很接近君子了,“回也其庶乎?”因此,颜回是个人。子贡嘛,就是个东西了,充其量是个好东西。多啰嗦一句:把“吾与女弗如也”解释成“我和你都不如颜回”。并且说:这是夫子很谦虚的说法。凡是这样给人家讲《论语》的,就是“宝器”砖家。
在成都方言里,以“宝器”喻人。和京派海派都有所区别,先扬后抑、褒下是贬,与夫子用法完全一致。只是成为日常方言,使用时意识横流,含义早已更加多姿多彩。但是,它始终并不指坏人和可恨的人,而是指带有可爱的喜剧色彩的人,特别是那种自我感觉很好的人。
另外,“宝”、“包”同音,“宝”进了脑壳就成了“包”。“包”又被想象力丰富的成都人形象成了乒乓球,“脑壳有乒乓”和脑壳有包;脑袋被门夹了;脑袋进水了都是“宝器”形成的一些基本条件。不过这些现代语言就走远了,和《论语》本意;和穿梭纵横的政治家、外交家、情意深重的大富翁子贡都不相干了。
说了这么多,“宝器”在那里?身边“宝眉宝眼”的也时常遇得到,如表哥、凤姐之类。但要说找个现实中大家都晓得又可以作为标本的,还真不容易。麻起胆子提一个: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解释成“就是女人和婴儿不好将就。”在两千多年后成功傍定夫子的妖冶女砖家,可以算个“宝器”。但估计要是由夫子自己说,虽然心中暗喜这小蹄子的“不孙”,也是万万上不得台面,绝非“瑚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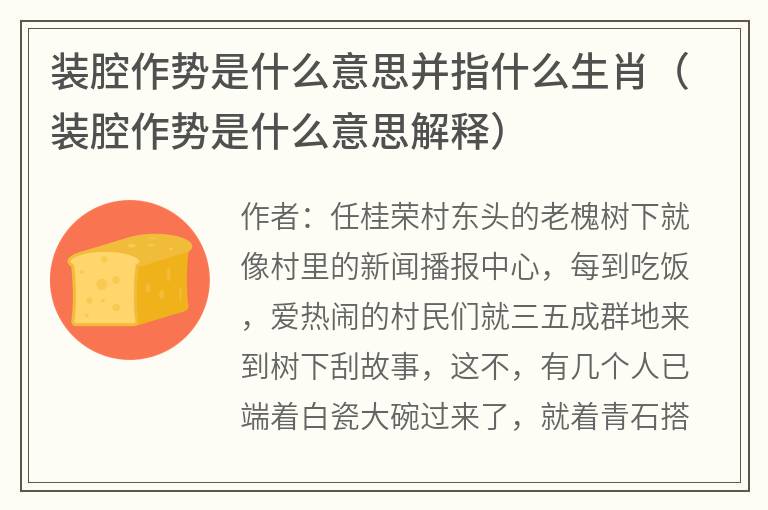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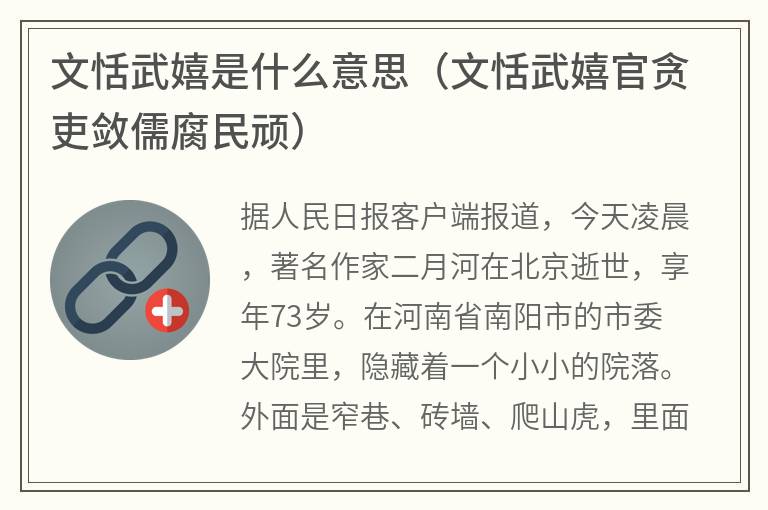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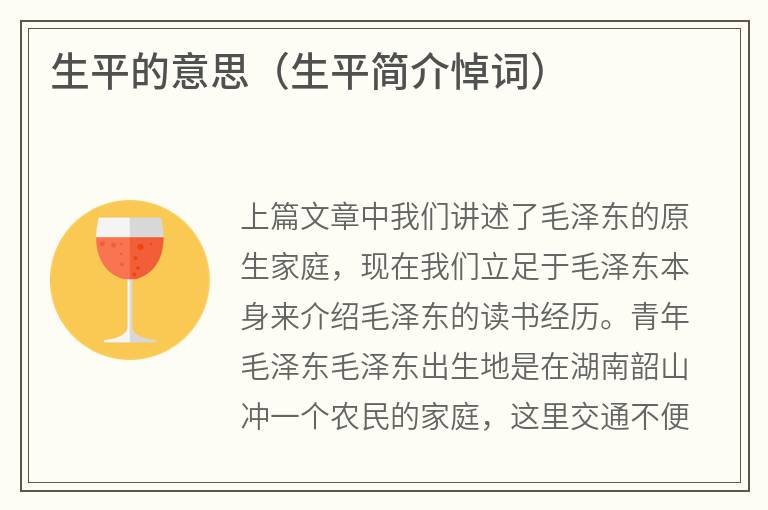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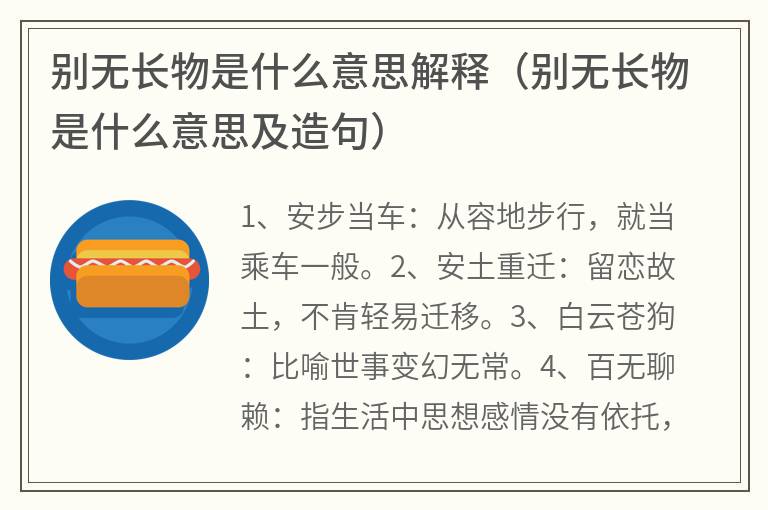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