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劻,这个被称为晚清“中国最有名望之人物”,一生中,“从未做一稍有荣誉之事”,而其贪黩之声,却遐迩中外,直可与前清的和绅比肩列坐。在他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置国家衰弱民族危亡于不顾,唯利是视。“彼于官场中实为一罪大恶极之人”
(一)行贿钻营
道光十八年(1838年)奕劻出生。其时,家道由隆而衰,作为一皇族,已是贫困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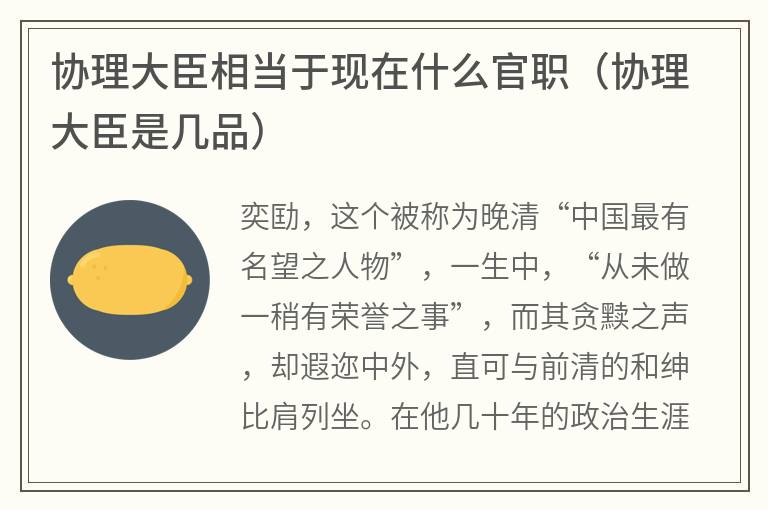
协理大臣相当于现在什么官职(协理大臣是几品)
奕劻的祖太王爷永粪系乾隆皇帝第十七子,也是最小的儿子。他与嘉庆皇帝是同母弟兄。嘉庆四年(1799年)仁宗亲政后封其为惠郡王,不久改封为庆郡王,是为清朝第一代庆王。嘉庆二十五年永璘病危,仁宗亲往视疾,晋封庆亲王,死后谥号“僖”。按清朝惯例,一般的世袭爵位都是降一等承袭,即亲王之子袭郡王,郡王之子袭贝勒,贝勒之子袭贝子……永璘逝后,其三子绵慜例袭庆郡王,成为清朝第二代庆王。道光十六年绵慜去世,溢日“良”(奕劻因之称“良太王爷”)。绵慈无子,奉旨以仪顺郡王绵志之子奕綵为嗣,再袭郡王一次。庆王族系从此衰落。道光二十二年奕綵因在孝服中纳妾,下宗人府议处。奕綵行贿请免,水璘第六子辅国公绵性觊觎王爵,行贿谋袭,事发,奕綵夺爵,绵性发配盛京(今沈阳市)。道光二十九年,十二岁的奕劻(绵性子)承袭辅国将军爵。庆王族系至此由亲王降到了辅国将军。
然而,就是这个辅国将军奕劻,非但没有使庆王族系继续下滑,反而开始升腾飞跃。咸丰二年(1852年)封贝子,威丰十年晋贝勒,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大婚,加郡王衔,光绪十年(1884)晋封庆郡王,由此恢复了家族的荣誉。但奕劻不以此为满足,继续钻营,青云直上。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寿庆,又亲旨晋封庆亲王,光绪三十四年更获得亲王“世袭罔替”(世代父死子袭)的最高待遇。但还没容他的子孙承袭王爵,为他授爵的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覆没了。奕助是清朝第三代庆王,也是最后一代庆王。
威丰十一年“祺祥政变”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成为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首脑。其秉国,政刑擅专,顺者昌,逆者亡,权势熏天。奕助对慈禧太后言听计从,百计奉迎,无所不至,由是渐见信任。自同治六年后,他历任镶红、镶白、镶黄旗蒙古都统,镶白、镶黄、正蓝、正黄各旗满洲都统,镶黄、镶蓝各旗汉军都统,挤进官场,所在纳贿,聚敛财货,转“孝敬”慈禧。
晚清政治腐朽,卖官鬻爵,货赂公行,朝野上下贪污受贿之风日盛一日,连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也不例外。史载,慈禧“好贡献”,日以积蓄为事,到晚年,资产达二千五百万磅,“遗产之富,为满清所罕有者”。作为官迷的奕劻不能不投其所好。他除将其第四女即四格格送进宫中,陪伴慈禧纵情玩乐,日进甘言外(四格格最为慈禧宠爱,奕劻的飞黄腾达与之大有关系),再就肆行贿赂,“岁费巨亿”,竭其禄俸所入兼广纳货贿还不够,后与袁世凯交结,月有贡品到京,珍宝奇巧填塞慈宁官。慈禧太后满心欢喜。
奕劻由于深得慈禧宠信,官运享通,扶摇直上。同治十一年授御前大臣,光绪十年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次年会同醇亲王奕譞办理海军事务。其间,勾结奕譞、李鸿章等,挪用海军军费一千多万两用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之用。
奕劻的丑行,深受慈禧太后赏识。光绪十二年慈禧命奕锄在内廷行走,同年使与英使欧格纳订立《中英缅甸条约》,承认英对缅甸之主权,次年又与法使恭斯当续订《中法越南界务专条》及《商务专条》,开龙州、蒙自、蛮耗为商埠,出卖国家主权。光绪十七年命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六十万寿。还在两年前,慈禧即派奕助与礼亲王世铎总办“万寿庆典”。两年中,奕劻颇为卖力,为筹办庆典物品多方奔走,效尽犬马之劳。这次庆典,共计挥霍白银不下一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岁入的六分之一。也正是在这次“万寿庆典”中,奕劻爬到了庆亲王的高位。
慈禧庆寿之年,正是甲午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击沉高升号舰,中国官兵七百余人罹难,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攻占平壤,十八日挑起大东沟海战,几百名官兵壮烈殉难。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占领大连、旅顺。中国处于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而慈禧、奕劻等置之不顾,沉醉于“喜庆”之中,“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岂非咄咄怪事!慈禧“万寿”和奕劻的“走红”、“荣升”,凝聚了多少将士和劳动人民的血泪!
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有识之士,无不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奔走呼号。光绪二十四年酝酿已久的改良主义思潮,终于发展为戊戌维新运动,暗暗长夜透露出一缕晨光。然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助,作为一个关键性人物,为保全既得利益,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沆瀣一气,极力阻挠变法运动,对光绪皇帝命议施行的变法事项“抑压迟迟”,对康有为建议开设制度局一事,以“成宪昭垂,法制大备”为辞,予以全盘否定,顽固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终于与慈禧等顽固派一起扼杀了维新变法运动。
戊戌政变后,奕劻对遍地而起的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极为仇视,表示要“严拿为首之人,从重惩办,以靖闾阎而消隐患。”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偕光绪帝狼狈西逃之时,留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联军议和。谈判中,他卑躬屈膝,甚至向联军统帅瓦德西表示“吾深望以后中外成为一家”,忠实执行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路线。光绪二十七年,他代表清政府与英、美、俄等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奕劻与侵略者关系颇深,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期间,京城的王公府第大多惨遭践踏,而庆王府因得到联军的保护而安然无恙。由于奕劻卖国有功,益受慈禧青睐,出任外务部(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大臣,光绪二十九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次年领班,兼管外交、财政、练兵等事,总揽清廷大权。宣统帝即位,虽有载沣摄政,但奕劻仍不失为影响政治之强有力者,举凡朝廷大政之失,无不与其有关。
(二)百般聚敛
晚清对“权利”这一名词,往往析为“权”、“利”,赋予特定的涵义。未得权,不惜丧名屈节以求权;既得权、又不惜丧名屈节以求利;既得利,更荒淫奢侈,无所不为。奕助正是这种“贪权”、“贪利”、“贪色”之辈。经过苦心钻营,其权势愈来愈大,而利欲也随之膨胀。
在奕劻没显达之前,穷困潦倒,“以其为中国绘画山水之能手,兼擅长书法,尝为人教读,且资书画以糊口,藉以略增其收入”。有时甚至上朝穿用的官衣,还得去到当铺中取黩。然而,后来却一跃成为京中首富,其聚敛之术堪称无比。
我们姑且不论其如何聚财,不妨先粗制一个他生活方面的“备忘录”:
先看奕劻的住宅,座落在北京西城定府大街的庆王府,威丰元年奕劻刚搬进时仅有房屋一百六十多间,“到奕劻时又在府内大兴土木,修建了万字楼和戏楼等处,建筑华丽精致”。“其中房屋分五个大院落,大小楼房约近千间,大门口是纯粹封建王朝的特殊形式,朱红大门。院内主房有九处,高大如宫殿,只是屋顶为泥瓦而不是琉璃瓦”,
——庆王府费用每年“三十余万,虽有禄俸、养廉相差甚巨。”
——皇族载润说:“常闻人云,奕劻为贝勒时,家道甚窘,到光绪三十三年,我守护西陵任满回京,见其邸第扩充三倍,焕然一新。至次年二月二十九日伊作寿时,近支晚辈王公和蒙古在京王公暨各部大臣等无不前往祝寿,我亦前去。伊设宴、演戏,大肆铺张,其子载捜夸耀于人日:此一日用费不下万金。按其当时的豪奢举动,绝非亲王之所能办到者。”
——宣统年间、革命军起;北京某报,还有其他几种资料,均披露奕助私有金银珠宝衣饰详单所值在现金亿两以上。
如此大兴土木,挥霍无度,且能积蓄亿万资财,资金从何而来?看来只有“贪”之一途。
奕劻贪墨,当时朝野上下,路人皆知,有人就曾指出,“醇王奕環之贪黩,远比恭王为甚;而庆王奕劻之贪黩,尤十倍于醇王,此已成为晚清北京一般之奥论。”而其聚敛的手段,也是花样百出,有秘密的,也有公开的,不一而足。
北京有个崇文门关卡,向被认为利之渊薮,需索“最侈且暴”,不仅商贾视为畏途,而且“凡外官入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即如左宗棠进京觐见,行经崇文门,也受“门者留难,索巨贿,始放入。”皇室亲贵有出任崇文门监督者,无不立见其富。奕劻由于得到慈禧太后的格外青睐,同治、光绪年间,就曾五次得到崇文门关正监督的肥缺,侵吞巨额税款。
地租收入是奕劻又一大财源。
奕劻并不经营土地,却坐收“带地投主”而来的源源不断地租。所谓“带地投主”,是大小地主对政府纳地租的一种避重就轻的形式。当时大小地主对政府直接交纳的地租不但租率高,而且常常被租吏勒索挑剔,因此不少地主将自己土地投到王府名下,诡称王府土地,每年只向王府缴纳比较少的地租,就可以安然而不被税吏勒索。当时依附在奕勤名下的土地就有千顷之多,散布在华北、东北、内蒙等地。这样一来,奕勤轻而易举地从地主剥夺农民得来的地租中瓜分出来一部分,至于这种“带地投主”对清政府的统治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的社会后果,似乎与他无关。此外奕劻还经营典当多面,“挟势敛财”。
至于奕劻鬻卖官爵,广收“门包”、“运动费”之类,更是公开的秘密。据当事人回忆说,奕劻见钱眼开,谁要有事去求他,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明要办的事情,当面将一个装有银票的红纸包递给他,说一声:“请王爷备赏”。他接过来看一看,虚情假意地说:“您还要费心。”随手把红包压在坐垫下面,这样就算是交易已成。杨士骧就曾以银十万两贿得山东巡抚。他如袁世凯、徐世昌、赵秉钧、唐绍仪等等,莫不以重贿破格擢用,就连吴禄贞之得第六镇统制,也曾花了运动费二万两。吴是当时很有声望的军人,奕劻尚不肯轻易放过,其他更可想而知了。
奕劻当国时,有一个名叫董遇春的粗野之人,与奕劻颇亲善,“动以万计因之,连捐带保至直隶省候补道,一时大僚有以裁缺而反得高位者,有以升任而进不已者,有不论阶级而速化者,有以废员而破格起用者,皆缘之以进。闻一次费多至十数万,少则数万,其陆续费用亦至十数万数万不等,其他万千以下之数,道府以下之官更仆难数”。因董能为奕劻广开财源,甚“博得庆邸欢心,爱之重之在其他亲友之上”.
奕劻本是一个追名逐利、贪鄙成性之人,可他满口“澹如斋”、“澹如斋主人”,把自己装扮成澹泊如水、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清官,还叮嘱他的子孙操守“四留”之训,即“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其子载振就根据此训名其别墅为“乐有余堂”。另外,他还将庆王府库存许多他认为不费重的物品,诸如文玩、字画、玉器、瓷器等,委托“品德祥行”代为拍卖,以“表示穷困”、“掩盖社会上的耳目”。
但毕竟纸里包不住火。奕助的秽声丑行,早已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人们讥讽奕劻领衔的军机处为“庆记地皮公司”;还有人在北京出版一种石印画报上为他画了一幅肖像:一个老头,头戴双眼花翎的朝帽,戴着大眼镜,身着袍褂朝珠,手里拿着一把农民用的粑子,在地上楼银元宝。这足可说明他当权时的贪污情况和人民的怨恨了。而其贪鄙害政、误国贼民的行为,更激起言官的交章弹劾。从光绪末年直到清王朝崩溃,弹劾奕助之案接连不断,成为清末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我们不妨再顺着这条线索看看奕助的丑态和矫矫不阿的言官的命运。
光绪三十年三月,御史蒋式瑆首揭其奸,说他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汇丰银行收存,该亲王自简授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露不计外,尚能储此巨款。朝廷以查无实据为辞,令蒋回原衙门行走,以示惩罚。
继蒋式瑆之后,又有“台谏三霖”即赵启寐、江春霖、赵炳麟站了出来,捋虎须而探虎子。赵启霖弹劾奕助案更演成波及全国的“丁未政潮”和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
光绪三十二年,奕劻子载振受慈禧之命前往东三省查办事件,道经天津,见到一个色艺双绝的歌妓杨翠喜(直隶通州人,家贫为妓,名噪津门,为一时女伶之冠),为之倾倒。天津道员段芝费以为奇货可居,便以一千二百两银子将翠喜从大观园戏馆赎出,待载振回来时献上,并从商会王竹林处借得十万两作为奕助寿礼,谋得黑龙江巡抚缺。载振大喜,欣然受之。光绪三十三年东北改设行省,段芝费果然如愿以偿。以道员升任巡抚,前所罕见,举朝震惊,御史赵启霖起而弹劾,将奕劻父子丑行揭露得淋漓尽致。并且说:“段芝贵无功可记,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骤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界之专,椎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然而,奕助不仅巧为弥缝,蒙混过关,而且还与袁世凯勾结一起,党同伐异,采用卑劣手段,搞垮了赵启霖和较有政治才能的军机大臣翟鸿机、邮传部尚书岑春煊。
奕劻是慈禧的宠儿,慈禧死后,监国摄政王载沣也不得不受他的挟制。权势之大,“举朝莫敢撄其锋”,“撄其锋者立糜碎”。宣统二年(1910年)一月,御史江春霖“激于忠捆,冒死直陈”,又落得个莠言乱政,有妨大局,命回原衙门行走的下场。同年,资政院通过弹劾奕劻案,“折上后,奕劻见之甚怒”,竟将议长溥伦“叫至板房(车机处)痛加申斥”。
奕劻之所以如此器张,亦非偶然。清王朝自乾隆信任和珅之后,经嘉庆、道光两朝,贪驻枉法、收受贿赂之风日渐盛行,到晚清光绪、宣统时达到了顶,点,成为普天之下的恶习和公害。奕劻不过是晚清腐败官僚群的缩影。
(三)沽售国柄
王闿运在《祺祥纪事》把清王朝的覆没归结于统治集团之“贪黩”,那是说到点子上了的。而奕劻贪财竟将国柄转手卖给了袁世凯,真是财迷心窍,昏聩之极。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本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纨椅子弟。光绪二十一年以道员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此人素有野心,权欲特盛,擅长奉迎拍马,也是一个秽声远播的贪官。在奕劻没有入值军机以前,他全部心血用于巴结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旋充军机大臣要职的权臣荣禄,肆行贿赂,无微不至,居间谄媚慈禧以邀荣宠,而对权势稍轻,时为外务部领袖的奕劻,则难以满足其贪婪之欲,无怪乎奕劻不时对人发牢骚说:“袁慰亭只认得荣仲华(荣禄),瞧不起咱们的”。但在光绪二十七年后,荣禄躯体欠佳,竟至卧床不起,恐怕不能久于人世,而奕助入值军机的风声不断吹进袁世凯的耳际。袁世凯转而交结奕助。当时袁世凯遭心腹杨士琦给奕劻送去十万两银子,预祝奕劻入值军机,奕劻见了十万两一张银号的票子,初犹疑为眼花,仔细一看,可不是十万两吗?就对杨士琦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士琦回答得很妙,他说:“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慈禧太后),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奕劻听了,不再客气。等到荣禄死,奕劻出任军机大臣,杨士琦的话,并无丝毫含糊,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有奕劻及福晋(妻妾)的生日,唱戏请客,及一切费用,甚至奕劻的儿子完婚,格格出嫁,孙子弥月周岁,所需开支,无不悉由袁世凯预为布置,不费庆王府一分一厘。事实上,奕劻贪权固位,也需要这样一个手握重兵的汉族军阀作为自己的“灵魂”。“钱可通神”,经过“孔方兄”的穿针引线,奕劻就范于袁世凯,与之朋比为奸。奕劻让子载振与之结拜,遇缺极力保荐;袁世凯晋升不已,当然也就馈贿不已。“弄到后来,庆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袁世凯,表面上说请他保举人材,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其结果,朝野上下遍布袁世凯党羽,成为不可摇撼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
奕劻、袁世凯相互勾结,贪赃枉法,结党营私,招致言官接二连三的弹劾,不能不使慈禧太后疑虑丛生。为预防不测,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907年9月4日)免去震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调为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阳为升迁,阴夺其对北洋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为时已晚)。又过了一年,慈禧忽听袁要废光绪、立奕劻之子载振为帝的谣传,着实大吃一惊。奕、袁关系太密切了,外间盛传朝廷大政皆由“袁世凯言之,庆王行之”。自己年事已高,难保不变生肘腋,奕劻贪污不堪,与子载振日以招权纳贿为事,朝野比之严嵩父子,将来无论如何不能再委以“大任”。十月十四日(11月7日)慈禧病势危笃,在面临“交班”的紧要关头,将奕劻支到东陵去查看菩陀峪万年吉地(慈禧陵墓)工程,防其结袁世凯谋为不轨,还没来得及收拾袁世凯,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11月14、15日)光绪、慈禧相继“晏驾”,正在冲龄的溥仪入承大统,改元宣统;其父醇亲王载沣,慈禧弥留之际降懿旨,让他监国摄政,所有“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光绪皇后隆裕)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皇帝的弟弟。光绪在戊戌政变时为袁世凯出卖,被慈禧囚禁于瀛台。载沣监国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除掉袁世凯,为兄报仇,杜绝后患。可是,当他拿着拟好的将袁革职惩办的谕旨征求奕劻、张之洞意见时,被袁重贿买通的奕劻首先表示反对,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起反来怎么办?”的确,袁的势力很大,载沣不能不有所顾虑。
载沣为人“谦抑退让”,“好逸畏事”,是一个优柔寡断、平庸无能之辈。在奕劻的挟制下,没有断然诛袁,仅“开缺回籍养疴”,铸成了“纵虎归山,养痈贻患”的大错。
度世凯回籍后,戴笠垂钓,纵情享乐,似乎看破“红尘”,决心“退隐林泉”了。其实,他在静观时态的发展变化,期待东山再起。
溥仪即位后,奕劻等当权者对外卖国对内残暴掠夺的政策,激起了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抗捐抗粮运动、抢米风潮、保路运动、会党起义等等,此伏彼起。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在湖北武昌发动武装起义,揭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全国各地,闻风响应,纷纷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宣布独立。袁世凯看时机已到,又向奕劻着实贿赂了一笔很大的数目。奕劻一方面放出风来,说他已年老,非袁世凯出山不能力挽危局;一方面与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连为一气,压迫载沣用袁。载沣虽极力反对,最后还是不得不“任听摆布,忍泪屈从。”初发布上谕,任袁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不就,继之让其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原任奕劻辞职,改任弼德院院长),组织责任内阁,总揽军政大权。清廷的命运完全操纵在袁世凯手里。当他利用武力镇压了北方的革命运动后,便开始演出“逼宫”的丑剧。
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手捧要清帝逊位的奏折,来到故宫养心殿,装腔作势地痛哭流涕、断断续续向隆裕太后诉说民主制如何优越,劝隆裕“俯鉴大势,以顺民心”,否则皇族就要遭到“靡有子遗”的可悲结局。隆裕为人,庸碌无识,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听了袁世凯的一番恫吓,吓得举止失措,连忙召集皇室亲贵,商量对策。载沣表示反对,愤而辞去监国摄政,退归藩邸。此时奕助的灵魂完全为袁世凯的重贿收买,力主自行退位。为迫使清廷屈服,竟当众耍起撒谎的花招。他在应隆裕召对时,进宫即对大众声言:“革命军队已有五万之众,我军前敌将士皆无战意。”旋至听候召对室,又复申前言说:“革命党已有六万之众,势难与战”。当时就有人嘲笑说,“数分钟内,革命党军队又增加了一万之众,何其如此之速耶!”奕劻此举,并非他能“顺从民心”,认识到共和对国计民生有何好处,正如载沣胞弟载涛所说,他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廷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心上。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屈服了,她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的清王朝至此覆没了。
奕劻售柄袁世凯之后,便回庆王府“纳福”去了。不久,他携眷到了天津,用贪污来的钱购买了一幢中西合壁、富丽堂皇的楼房,从此,闭门谢客,深居简出,过起隐居式的生活来。至民国六年正月初六日(1917年1月28日)默默无闻地病死。溥仪听说,愤愤地骂道:“奕劻贪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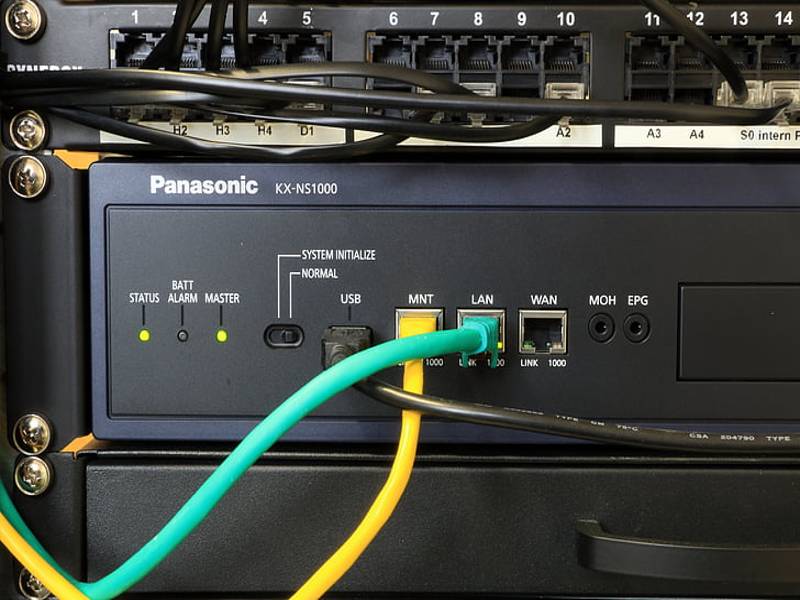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