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的体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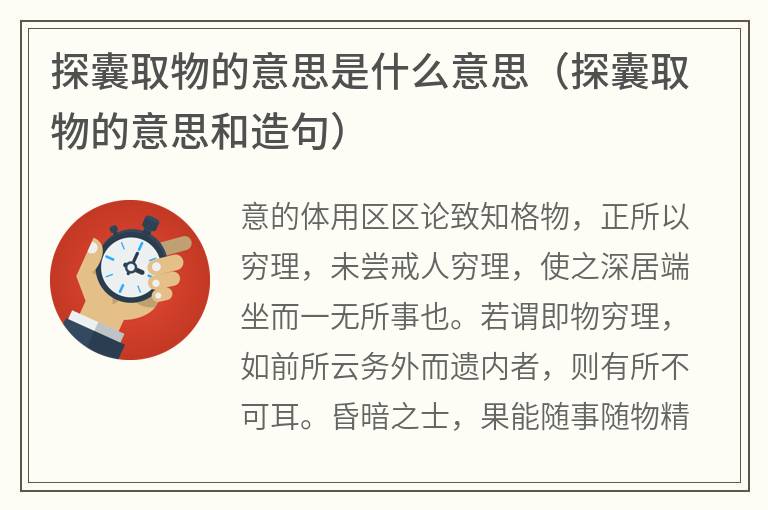
探囊取物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探囊取物的意思和造句)
区区论致知格物,正所以穷理,未尝戒人穷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若谓即物穷理,如前所云务外而遗内者,则有所不可耳。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大本立而达道行,九经之属,可一以贯之而无遗矣,尚何患其无致用之实乎?彼顽空虚静之徒,正惟不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遗弃伦理、寂灭虚无以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孰谓圣人穷理尽性之学,而亦有是弊哉?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 “格”字之义,有以“至”字之训者,如“格于文祖①”“有苗来格②”,是以“至”训得也。然“格于文祖”,必纯孝诚敬,幽明之间无一不得其理,而后谓之“格”;有苗之顽,实以文德诞敷而后“格”。则亦兼有“正”字之义在其间,未可专以“至”字尽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且《大学》“格物”之训,又安知其不以“正”字为训,而必以“至”字为义乎?如以“至”字为义者,必曰“穷至事物之理”,而后其说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穷”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穷”、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 夫“穷理尽性③”,圣人之成训,见于《系辞》者也。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则圣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穷理”,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以启后世之弊邪? 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故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吾子盖亦未免承沿积习,则见以为“于道未相吻合”,不为过矣。
①《尚书·舜典》:“归,格于艺祖。”格,至、到。艺祖,即文祖,尧祖先的庙。格于艺祖,即到文祖庙。
②《尚书·大禹谟》:“七旬,有苗格。”意为有苗族人到来。
③《易传·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阳明先生回答说,您这么理解,真的是冤枉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禁止人穷理,深居端坐啥也不干了?务求于外和追求内在之间不是非此即彼,不能共存的关系,只是分个主次先后而已。我从没说过不让学的人去穷理,不让学的人去务实的话。
我讲的心学,入世治世是其精髓所在,怎么可能教导学习的人偏离务实呢?朱熹先生讲的东西是把“即物穷理”当做第一要务来做的,我讲的是先把心摆正,把存养良知放在首位,再谈其他的事情,这就是我和朱熹先生的根本区别所在。
就算学习的人天资悟性比较差,无知愚昧,起点很低,也不要紧,只要能把心先放正,坚持在入世中体察自己心中的天理,致其本来就有的良知,坚持不懈,人就会变的聪明睿智,内心也会逐渐强大起来。
按照这种方式,即便天资悟性不好的人,也能把五达道之类入世的事情处理好,也能对九经之类治世的事情触类旁通一以贯之而没有什么遗漏。能做到这些,对于学以致用,入世应对人情事变这些事情,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五达道指的是五种最基本人际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广义的君臣关系指的是上下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
九经这里指的是《中庸》九经,原文是“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九经是治国平天下的九项具体工作,做好这九项工作,是天下大同的重要保证。
而您所讲的顽空虚静的一类人,正是因为在应对人情事变中,没有随外物变化时时内求自己心中的天理,致自己本来就具有的良知,同时又遗弃了伦常之理。怎么可能指望这种人入世治世呢?
对于入世而言,有两个极端是烦恼比较少的。一种是变成单细胞动物,啥也不管,自然就啥也不想,拥有着“弱智儿童快乐多”状态。坠入顽空断灭,就是把自己心封闭起来,不被红尘所扰动,安于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没有万花丛中过的干扰,自然容易保持心态平和。另一种是存养本心,不断事上磨,从下学到上达,拥有洞悉真相的智慧。应对世间万物,如探囊取物般从容,坦坦荡荡的幸福感自然随之而来。
这就是我理解的圣人穷理尽性之学,我按照圣人本意来说,怎么可能会有弊端呢?
心是身的主宰,心就是天地之气落到躯壳上的根本,失去这个根本,人就只是个行尸走肉了。
心之虚灵明觉,“虚”是说摸不着看不到的意思,“灵”是说感知触及到就会有反应;“明觉”是说心就像一面一尘不染的镜子,有外物从前面通过,马上就能照出来。心之虚灵明觉就是心学中说的人本来就具有的良知。
这个“意”字,是会意字。从心从音,合起来表示发自内心的声音。虚灵明觉知觉到外物就会做出反应,就是意动。当心感知到物的时候的一涌动,就是“意”。意之所着为物,“物”指的是这股关注到“事”的气。“格物”就是把这股气导正。
心知觉到具体事物了,就会有“意”动,如果没有知觉到事物,自然就不会有“意”动的事情,意能产生,必定有其产生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物”,物就是事。
接着阳明先生举例,意用于事亲,事亲就是一物;意用治民,治民就是一物;意在读书,读书就是一物;意在听讼,听讼就是一物。显然“意”和“物”是成对出现的,不能有“意”没“物”,也不能有“物”没“意”。
阳明先生接着说,格物的格,一般理解为“至、到达”,比如典故“格于文祖”“有苗来格”,都是这个意思。但是“格”如果仅仅理解成“至、到达”,意思未免就过于单薄了。
“格于文祖”出自《尚书·舜典》,原文“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意思是,正月初一,舜先去拜尧庙,然后与四方诸侯议政,确定政策方针之后昭告天下。拜尧庙,舜一定会用一颗纯孝诚敬之心的。无论何时何地,舜都能存养良知,没有一丝一毫的念头不符合天理。这里用“格”字,应该也有这层意思。
“有苗来格”中,以有苗氏的顽钝不化,要靠文德去感化,这里用“格”字,就有“正”的意思了。
像《尚书》中的“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格”字全部都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的意思,而不能解释成“至、到达”的意思。
综上所述,《大学》中“格物”的“格”字,应该理解成“正”,才符合圣人本意。
如果把“格”理解成“至、到达”的意思,“格物”就是“穷至事物之理”,只有这样理解,整个文意才能解释得通。这样的话,下功夫的重点就全在一个“穷”字上了,下功夫的对象,全在一个“理”字上了。如果上文去掉一个“穷”字,下文去掉一个“理”字,就成了“致知在至物”(到达“知”的路径在于穷尽物之“理”),这怎么可以讲的通呢?
圣人在《易经·系辞》里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如果圣人认为“格物”就是“穷理”的意思,直接说“致知在穷理”就完了,干嘛给后世人留下自相矛盾,含糊不清的弊病呢?难道是圣人没事干绕圈圈吗?
《大学》中“格物”和《易经·系辞》中的“穷理”大意是相同的,细微之处稍有差异。
“穷理”兼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内圣功夫,提到“穷理”,约等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都包含在其中了,也就是说“穷理”等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功夫的集合。而“格物”只是“穷理”范畴内的事情。
“格物”是不包含“行”的,把“格物”等于“穷理”,等于把“穷理”认为是“知”,显然这是不妥当的。这样理解的结果,不但不能抓住“格物”的主旨,并且连“穷理”的意思也丢失了。
阳明先生最后总结说,把“格物”和“穷理”混为一谈导致儒学日益割裂,日益碎片化且晦涩难通。后世求学的人,正是因为此处的谬误,才会把“知”与“行”分割为先后两截。您也未能免俗,所以才会认为我的说法偏离了儒道,完全可以理解。
刘长志
儒学学者、阳明心学践行者
正本清源,吾辈本分!
微信公众号:刘长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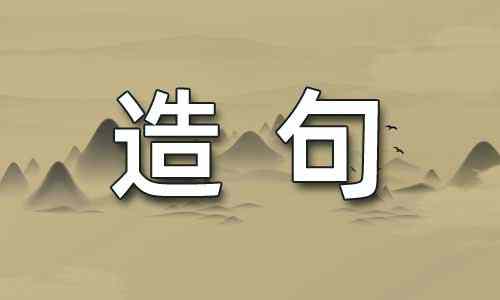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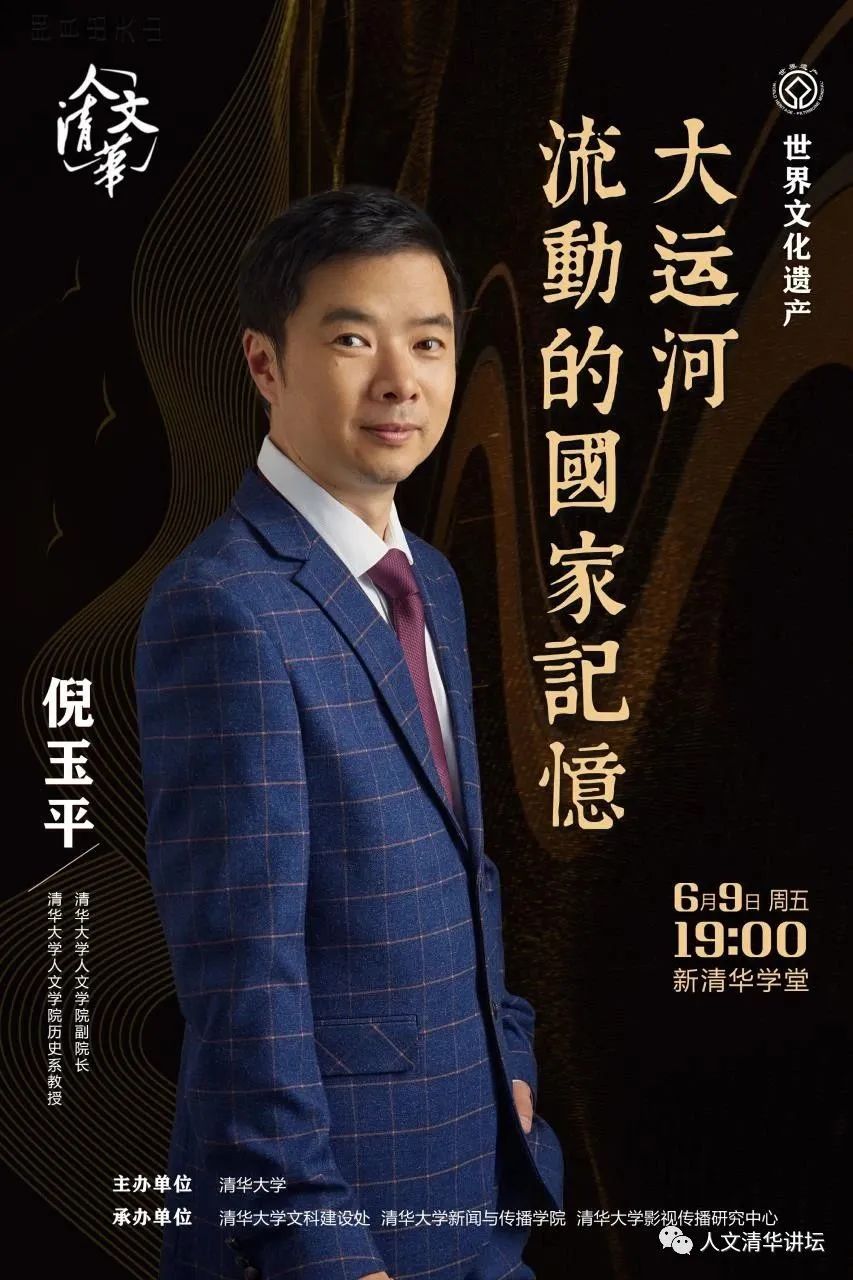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