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书生余光乾,博览群书,学得满腹经纶。读书之余,便打拳踢腿,活动身体。十七岁时,余光乾读书遇到难题,便去请教当地著名儒生虞子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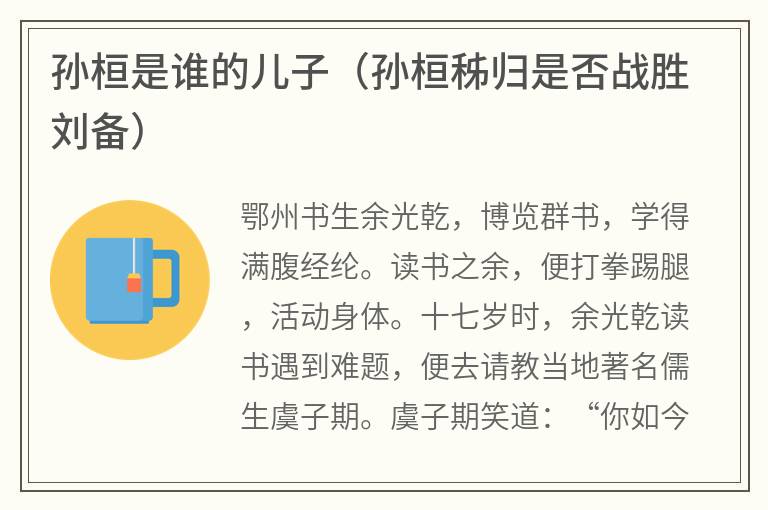
孙桓是谁的儿子(孙桓秭归是否战胜刘备)
虞子期笑道:“你如今的学识,与我相差无几,我没有资格教你。我与大儒周野渡有些交情,他如今在嵩阳书院授业解惑,我写封信,向他引荐你。”
余光乾谢过虞子期,收拾行囊,带了书信,千里迢迢去嵩阳书院,拜访周野渡。
途中遇到下雨,地上泥泞难行,有辆马车疾驰而过,带的泥水四处飞溅。弄脏了余光乾的衣服。有个麻衣道人张开双臂,拦住马车,并大声呵斥车夫。
车中少年掀起车帘,向道人道:“你挡我马车,是要拦路抢劫吗?”道人怒道:“弄脏别人的衣服,不该下车赔礼吗?”
少年冷笑道:“我弄脏他衣服,轮不到你来说话!看你是出家人,不与你一般见识,赶紧闪开,不然让马车撞死你!”放下车帘,命令车夫快走。道人一掌拍断车辕,大笑道:“道爷偏不让开,你能怎样?”
少年大怒,下车拔剑直刺道人。道人双指夹住剑尖,微微用力,将剑尖扭断。少年见势不好,转身就跑,却被道人飞脚踹倒,冷声道:“光天化日,提剑杀人,谁给你的胆子?本想杀了你,却又怕脏了我的手,今日饶你不死,给道爷滚的远远地!”
少年不敢说话,任由车夫扶起,冒雨远去。
余光乾感谢道人仗义执言。道人摆手道:“你不用谢我。换成别人,我也要管。”余光乾说道:“也许他有急事,才如此赶路。”道人瞪大眼睛,道:“他拔剑杀人,也是有急事吗?”
余光乾道:“人生而为善,就算是为恶,也不会坏到哪里。”道人道:“正是你们这种人,事事隐忍,坏人才横行无忌。”
余光乾笑道:“道家讲究静心养气,道长为何如此暴躁呢?”道人道:“只为了静心养气,便不管公平,就算空活百岁,又有何意义呢?”余光乾笑道:“道家讲求拿起放下,我已经放下了,仙长为何还纠结不放呢?”
道人怒道:“你是个迂腐的读书人,不愿与你说话!”快步离开了。
峻极峰下,双溪河畔,三面青石墙,围住几间茅屋。周野渡听到虞子期的弟子来访,非常高兴,让余光乾进去。
余光乾进院时,见那个麻衣道士,正在古松之下,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说话。道人故意转头,不看余光乾。
余光乾向道人行礼,笑道:“不想在这里,与道长相遇。”白发苍苍的老者,正是周野渡,问明缘故后,笑道:“素不相识,分而重聚,道门讲求的机缘,不就是这样么!”
那道人手指余光乾,向周野渡说道:“这人很迂腐,不想与他说话!”周野渡再次大笑,道:“都叫你癫道人,实至名归!”
他向余光乾介绍,麻衣道人道号光烈。因脾气火爆,人称癫道人。癫道人道,“周兄做个评断,我与他谁对谁错?”周野渡笑道:“一张一弛,都没有错。”癫道人瞪眼道:“最不诚实的,便是读书人,说话两面三刀,圆滑得很!”
周野渡微笑道,“我若如你一样火爆脾气,每日至少打三架,还如何做朋友?”
便在此时,外面一阵喧哗,却是有个书生,要被赶出嵩阳书院,那书生不肯离开,大声道:“说什么房子紧张,都是托辞,你们分明是不想得罪李纨!”
周野渡白眉紧皱,命令童子关门。癫道人却不解风情,连连追问。周野渡一声长叹,说起往事。
外面那书生,名叫陆松,是山东莱州人,来此求学不久。前几日陆松出门,遇到个老汉,要悬梁自尽。陆松问起原因,那老汉自称姓石,有个十三岁的独女,名叫灵秀,依靠卖花度日。
一日灵秀上街卖花,不想遇到了李纨,被当街调戏。女儿回家不久,忽然变得疯癫。石老汉跑去衙门喊冤,被差役乱棒打出,求人写状纸告状,得知要告李纨,人们纷纷拒绝。石老汉万般无奈,只能求死。
陆松一听之下,义愤填膺,替石老汉写了状纸。
癫道人道:“后来如何了?”周野渡手指门外,叹口气,说道:“官府如何结案,还不知道。但陆松帮石老汉写状纸,得罪了李纨,因此要被赶走。”癫道人呸了一声,两指用力,掰下石桌一角。
他大声道:“你也是有名的人物,怎能让他们胡作非为?”周野渡叹口气,说道:”我只是受邀,来此讲学,很多事情,不好干预,李家在此经营多年,根基深厚,整个书院,都靠他家供养,书院又如何肯为了名寂寂无闻的书生,得罪了衣食财神?“
余光乾怒声道:“我是个读书人,以动武为耻,但李纨欺人太甚。若我能见他,定要先打个痛快!”癫道人伸出大拇指赞道,“小事糊涂,大事不忍。之前错怪了你!“
便在此时,外面有人大声道:“你说得不错,要赶你走的,就是本少爷!替死老头子写了状纸又怎样?如今官府判了妄告不实,老子欺负了他女儿,他照样赔我银子!”
那声音余光乾有些熟悉。一时之间,却想不起是谁。癫道人看向周野渡,皱眉道:“外面说话的是谁?”周野渡摇头苦笑道:“除了李纨,还能是谁?”癫道人大笑,“我这就出去,打他狗娘养的!”
两人推门而出,见先前遇到的车中少年,衣衫华丽,站在高处,大声指使几个恶奴,推得一名书生踉跄后退。
余光乾大叫“李纨”,那少年应声抬头。身边风声飒然,却是癫道人抢先冲到李纨近前。李纨稍稍惊慌,随即狂笑,“路上侥幸,让你们逃了,这次老子人多,打死你们!”指挥恶奴,向癫道人冲来。
癫道人随手抓起一名恶奴,向后扔出,撞中另一名恶奴,两人同时倒地。又有一名恶奴,斜刺冲来,却被癫道人起脚踢飞。
李纨见大势不好,转头就跑。癫道人快步追上,提起他衣领,重重摔在地上,怒道:“早知你如此混账,当初就该打断你双腿!”喀喀两脚,将李纨双腿踩断。李纨大声惨叫,昏迷不醒。
余光乾怒气难消,又踢了李纨几脚。周野渡急忙劝阻。癫道人道:“我知道你怕事,不会在书院搞出人命。”他手指余光乾,向周野渡说道:“他人品不错,你好好教他,将来做个好官,也是百姓的福气!”
说完之后,转身离开,周野渡连问道兄去哪儿,癫道人却大笑道:“痛快!痛快!”拾级而下,很快不见踪影。
周野渡原本担心,李家会来书院闹事,不想风平浪静。
经常有人来书院,拜访周野渡,也带来各种消息。据传知县大人,半夜醒来,见床边坐着个道人品茶,右手上下抛举一把小剑。
道人说道:“我知道你收了李家很多银子,若是再做坏事,我便替天行道,将你杀了。”道人说完,用剑削着知县的白玉枕头,锋刃所及,玉片纷纷而下。
县令跪在床上,连连磕头。道人冷笑道:“你当初收人钱财时,可曾怕了?”县令浑身冷汗,伏地不起。道人放声大笑,走到院中,一跃上房,笑声渐渐远去。
县令以为是在做梦,但杯中残茶温热,李家送来的那些银子,也不见踪影。县令呆坐许久,愣愣无语。夫人李氏冷笑道:“大人刚才仪容全失,若是传出去,有损官威,必须想个办法,将那道人杀了灭口,顺便找回那些银子。”
那道人忽然在外面冷笑道:“知县如此混账,多拜你这刁妇所赐,将来何愁不人头落地!”李氏大喊来人。一截树枝透窗而入,穿透李氏发髻,将她钉在墙上。
差役们闻声赶来,只见大人昏倒在椅子上,夫人靠墙站立,抖作一团,脚下大片水渍,吓得尿了裤子。
人们说得栩栩如生,如同亲眼目睹。余光乾闻言微微一笑,不置一词。
余光乾在嵩阳书院住了两月,得周野渡悉心教导,得益良多。他离开之时,听人说起,李纨腿伤痊愈大半,但极少出门,乡人无不拍手称快。
余光乾回家继续苦读。二十四岁时,金榜题名,被朝廷委任为莱州知县,上任途中,闻听周野渡在一所书院讲学,专程过去拜望,向周野渡请教为官之道。
周野渡笑道,“当初在嵩阳书院,癫兄说过,希望你做个好官,我对你的叮嘱,也只有这一句。”余光乾起身离坐,恭敬点头,道:“学生记下了。”
余光乾到任之后,做事公正,铁面无私,深得百姓拥戴,官声很好。一年冬天,天降大雪,余光乾忙里偷闲,坐在窗边,命人煮雪煎水烹茶,看鹅毛大雪飘满乾坤。就在这时,外面鼓响震天。
余光乾匆忙升堂,有个书生站在堂下,手持状纸,大声道:“如今大人治下,有人为非作歹,你管不管?”余光乾记性极好,马上认出,书生正是当年在嵩阳书院,帮人写状纸的陆松。
他不动声色,接过状纸。
那状纸,是陆松替人所写,具状人名叫毛本一,务农为生。妻子早逝,留下个女儿毛灵儿,从小心灵手巧,稍微大些,学会刺绣之术,绣些荷包香囊,拿到集市上,换些铜钱,苦熬岁月。
毛灵儿长到十四岁,蓓蕾初开,也有几分姿色,几家媒婆上门提亲,都被毛本一拒绝,说道孩子太小,过两年再考虑婚配之事。
前几日去集市上卖香囊,不想遇到恶少孙桓,毛本一赶紧带女儿躲避,还是晚了一步,被孙桓当街拦住,毛本一挡住女儿,却被孙桓飞脚踢中心窝,当街昏迷。孙桓拉住毛灵儿,百般调戏。
还好有人大呼官差来了,孙桓悻悻离去。经此事后,毛灵儿郁郁寡欢,每日躲在屋里流泪,家中光景,一落千丈。
屋漏偏逢连夜雨。孙桓突然找上门来,说在集市上被毛灵儿咬伤了手指,要毛家拿几十两银子治病,不然就上门抢人。
余光乾看完状纸,不怒反笑,道:“当年在嵩阳书院,有个纨绔李纨,强霸民女,与今日之事何等相似。”陆松冷笑道:“可惜当年的道长,书生,都不在了。”
余光乾大笑:“道长不在,但书生还在!”陆松冷笑道:“读书人很多,敢出手打人的读书人,太少!”
余光乾手指自己,笑道:“你看我是谁!”陆松惊喜交集,道:“大人便是当年书生?”余光乾笑着点头,陆松跪地说道:“刚才多有不敬,请大人海涵。”
余光乾当即派人,去抓孙桓。之后带了陆松,去后堂等候消息。
两人说起这些年过往,才知道陆松过得并不轻松,他替人代笔,换些微薄酬劳,勉强度日。几个月前,家中老母生病,过得更是艰难。
余光乾叹口气,说道:“你可以来县衙做个书吏,多少赚些银子,补贴家用。”陆松笑着拒绝了,“这些年过来,也已经习惯。我若因为与大人相识,来这里做事,会让大人名声受到牵连,我也不会感到快乐。”余光乾笑了笑,不再强求。
晚些时候,捕头过来禀告,孙桓突染恶疾,卧床不起,无法移动半步。陆松冷笑道:“这病来的好是时候。”余光乾道:“便是死,也要抬来见我!”捕头又急匆匆的去了。
余光乾留陆松吃了晚饭,听陆松说起孙桓其他恶行,气得拍桌叹气。眼见到了二更,雪已停歇,风却吹得厉害。捕快仍未回来。陆松说道:“孙家根基深厚,这棵大树,极难撼动。”余光乾道:“再难的事,也要有人去做,若是可以,就从我做起。”
屋外突然有人冷笑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有个老者,推门进来,手指陆松说道,“我跟大人说些事,你滚出去。”陆松冷笑道:“君子无背人之言……”话音还未落地,已经被老者提着衣领,扔到屋外雪地之中。陆松翻身而起,手指老者破口大骂。
老者纵身跃到陆松近前,抬手要将他击杀,余光乾大声道:“你若是杀了他,我不会与你谈任何事!”老者右手不停,减了八分力气,将陆松拍晕。
他重新走进屋子,在余光乾对面坐下,打开随身盒子,指着里面珠光宝气,说道:“大人放过孙桓,这些都是你的,以后还有大礼奉上。”
余光乾冷笑道,“是孙桓要收买本官吗?”大喊来人。老者笑道:“院外当差的,都被我打翻了。大人若执意不收,我只能用这盒子,装了大人的头,找个风水绝佳之地埋了。”
余光乾正色道:“我是朝廷官员,你敢杀我?”老者笑道:“我本就是亡命之徒,是孙家让我活了一次,再死一次,也没什么。”
余光乾大声道:“即便是死了,也不饶他!”老者突然抽出短刀,向余光乾急刺。余光乾滑步闪开,绕着桌子疾走。老者冷笑道:“老朽看走了眼,大人居然懂得武功!”伸腿横扫,桌椅应声碎裂。
老者短刀再刺,快如电光石火,余光乾拼尽全力扭身,仍是慢了一步,胸前衣服被短刀划开。老者箭步向前,冷笑不止,抬手再刺。余光乾向后躲闪。老者右脚高抬过头,急砸而下,余光乾应声倒地。他纵身而上,挥刀再刺,狞笑道:“今晚割开你肚皮,看你胆子多大?”
突然一团雪破空而至,击中老者手腕,将他短刀打落。老者惊疑未定,一道人影带着寒气,急冲进屋,身子未落,腿影飘忽,将老者踢倒。
那人身穿麻衣,须发皆白,正是癫道人。
癫道人用一柄短剑,指住老者胸膛,冷声道:“想杀我朋友,道爷先杀了你!”老者全然不惧,撕开胸前衣服,露出身上一条出水蛟龙,从左肩斜贯右肋。蛟龙中间一条陈年旧疤痕,触目惊心。老者手指胸膛,冷笑道:“你有种,就在这里刺下去!”
癫道人冷声道:“一名漏网的水盗,在我眼前,装什么狗屁英雄!”老者面色微变,随即大声道:“你认错了人,我不是水盗!”癫道人大笑,“你腰上这道伤疤,当年便是被我一剑贯穿所留,如今你变了模样,若没有这条疤痕,我便认不出你!”
癫道人突然将短剑高高抛起,短剑激射出屋,绕着院中一株梅树,旋转三圈,重新飞回,落在癫道人手中,癫道人冷笑道:“你便是记不得我,也应该记得这手剑法!”话音未落,屋外梅树上,一根巨大树枝,应声而落。
癫道人继续道:“我这剑法,去留随心,更有个特别之处,留下的剑痕,如同梅花,时间越久,越是清晰。”余光乾举起灯光靠近,那老者腰间,一朵梅花灿然。
癫道人手指那老者,说他原本是君山岛水寇,专门在洞庭湖水面,打家劫舍,害了不少来往商旅性命,官府屡次剿灭,都未能成功,反而贼众越聚越多。成为官府心头大患。
后来各方侠士联手,攻破君山匪巢,癫道人参与其中,恰好遇到匪首君山蛟,两人恶斗许久,癫道人飞剑贯穿君山蛟腰腹,君山蛟落水。
癫道人跟着下水,却没了君山蛟踪迹,本以为他重伤之后,会死在洞庭湖,喂了湖中鱼虾老鳖。不想许多年后,在莱州县衙再次遇到,才知他做了孙家的爪牙。
余光乾笑道,“天理昭昭,公道不虚。他躲藏许多年,报应还是来了。”那老者低头不语,气焰全消。
癫道人笑道:“当初周野渡说起,与你相遇,便是机缘,今日想来,果真如此。”他向余光乾说起,原本是去蓬莱见个朋友,路上听人说起,莱州新任大人与余光乾同名,一时好奇,便过来查看。
他途经孙家,见孙家正在宴请几位差役,听他们说话,句句不离余光乾,便驻足偷听,越听越气,大吼一声,挺身而出,将那两个捕快,连同孙桓,一起捉了,送了回来。
颠道人轻拍双手,两个差役拉着个锦衣少年,出现在院门口,三人满身雪泥,狼狈不堪。颠道人道:“你是好官,手下却没几个好差人!”此时外面雪地中,陆松从昏迷中醒来,见癫道人在此,大叫一声,跑过来相见。
癫道人大笑,说道:“你很对我脾气,读了那么多书,却毫不做作。不如跟我,一起去做道士。快活无比,强似在这人间受气!”陆松苦笑道:“家中老母病重,无法追随道长。”癫道人笑道:“我擅长医术,可以为老夫人诊病。”不顾余光乾挽留,拉了陆松,出门便走。
余光乾追到门口,却见癫道人与陆松,在大雪中走出很远。他望着背影,愣了好久,这才悻悻返回。
三年后,余光乾因政绩卓著,再次升迁,调往别处。人们纷纷前来送别,其中有个老汉,跪在路边,哭了很久,有人悄悄告诉余光乾,那老汉名叫毛本一。
路过陆松的院门,发现房子早已坍塌,院中长满野草。
三年前,大雪之夜,癫道人跟随陆松连夜回家,为老夫人诊病。半月后,老夫人康复,身体还胜之前。到了春天,陆松赶着牛车,接走了老母亲,不知去了何处,家里破屋无人打理,很快坍塌。
余光乾驻足良久,这才继续上路。三日后,因为着急赶路,错过了客店,便在一处破庙安歇。庙里原本有四个人,带着刀剑,坐在台阶上喝酒,低声商量着事情。
四人见余光乾一行人来到,便收拾了吃食,去了另一个院子。
赶路辛苦,下人们很快睡去。余光乾就着灯光看书,直到后半夜,感到倦意袭来,趴在桌子上,昏昏欲睡之际,听到外面有响声。他连叫几声来人,无人应答。
余光乾提灯而出,见手下人东倒西歪,倒在廊檐下一动不动。此时庙门外,传来挖土声音。余光乾循声而去。庙墙之外,有个道人,正在弯腰挥铲,向土坑中扔土。
道人闻声回头,正是癫道人。余光乾见坑中有四具带血尸体,正是白天遇到的带刀汉子。他惊叫道:“仙长杀人了么?”癫道人笑道:“他们打算杀你,我就把他们杀了!”
癫道人见余光乾满眼疑惑,说道,“这几人是水匪君山蛟同伙。当年你将君山蛟法办,他们得到消息,特意赶来,为君山蛟报仇。不想在此相遇,见你们人多,便等到半夜,麻翻了你手下,要对你不利。可惜被我撞见,将他们杀了。漫漫长夜,闲着无事,索性挖个坑,将他们埋了。”
说完撕开四人衣服,每人胸前,都纹着出水蛟龙图案。
余光乾满头冷汗,再次感谢颠道人救命之恩。颠道人笑道:“你若不是好官,如今这坑里,埋的就是你了!你将来别做昏官,就是报答我了。”将四人尸体埋葬之后,颠道人不顾余光乾挽留,再次飘然而去。
余光乾不敢忘初心,一心为民,四十岁时,积劳成疾,卧床不起,百姓们闻讯,自发为大人上香祈寿,但毫无效果。有人私下议论,余光乾杀人太多,招致仇家记恨,暗地里对他下了巫术。
中秋节前后,有个身材瘦削的书生上门,五天之内,喂余光乾服下三粒药丸,余光乾病体大有起色,余光乾醒来之后,发现那书生,正是陆松。
陆松笑道:“我救大人,是为天下百姓,大人不用谢我。”说起老母身体康健,他如今跟随颠道人习武,闲暇之余,读书习字,日子过得非常逍遥。
陆松又传给他一些吐故纳新的方法,说道:“按此练习,可保你身体康健。”一个月后,余光乾身体恢复,陆松便执意离开了。
余光乾官职越做越大,也越来越忙碌,尽管如此,每日里抽出一点时间,练习吐纳功夫,果然不再生病。
他年老之后,在杭州为官,一次在钱塘江观潮时,有个孩子被大浪卷进潮水,眼见小命难保。有个麻衣道人从高处飞掠而下,踏波飞奔,将孩子救起,放在安全处,转身离去。
那道人,正是颠道人,几十年不见,他还是当年的样子,甚至比当年,还年轻了些。余光乾大叫仙长留步,颠道人脚步不停,很快消失在人群当中。
从那以后,余光乾再也没见到过颠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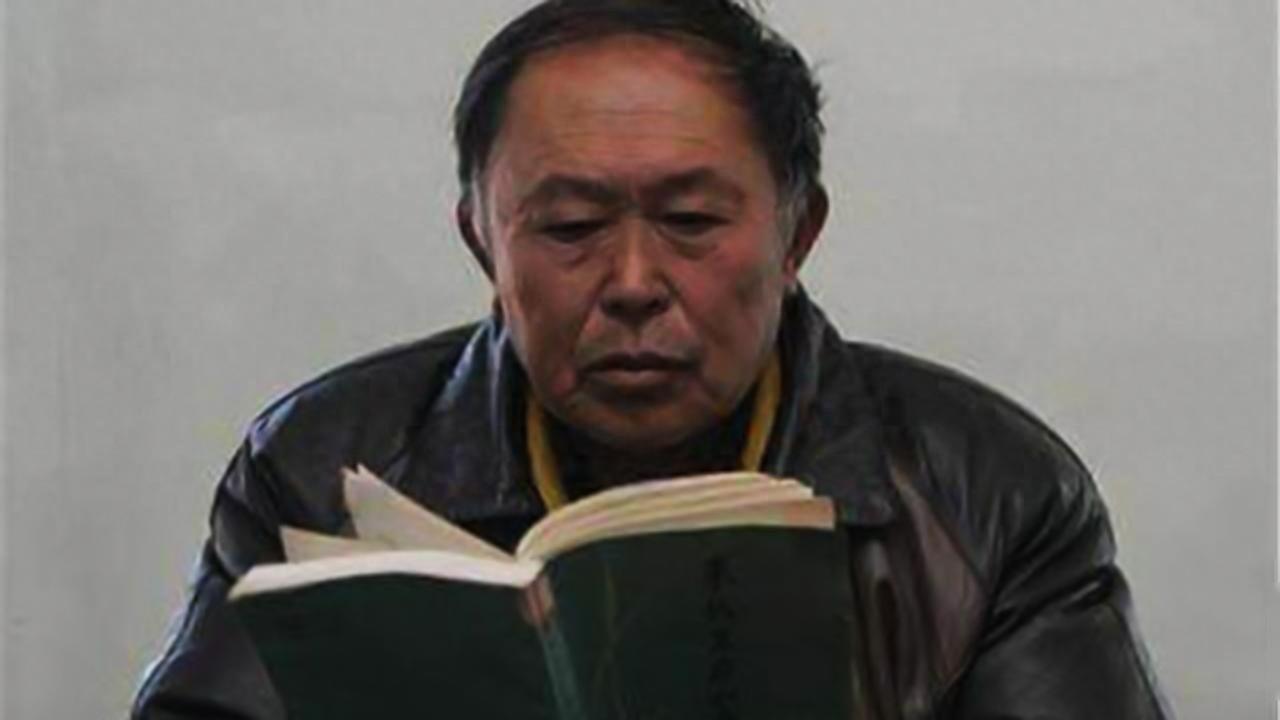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