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美国到西欧,反建制政党及其候选人通过把自身包装为保护国家免受外来移民和腐败精英破坏的守卫者而屡屡获得民意的广泛支持,这种民粹主义思潮泛起对世界秩序带来的两个最大冲击便是,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和特朗普胜选成为美国总统。因此,不少观察人士把这两个标志性事件发生的2016年视为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政治元年。事实上,回溯近年的政治发展态势可以看到,2014年欧洲各国议会选举中就已经开始泛起民粹主义的浪潮,丹麦人民党、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等右翼民粹政党都开始在各自国家崭露头角。很大的原因在于从2012年开始,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难民数量剧增。随后,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几乎所有右翼民粹政党的代表都对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表明了强硬的姿态。

左翼民粹主义是好是坏(左翼民粹主义什么意思)
右翼民粹思潮集中爆发
虽然民粹主义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有左有右,且没有普遍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诉求,但是借“人民”的名义彰显不同的意识形态诉求和政治追求是各种民粹主义的共同特点。在民粹主义的对抗性话语中,“人民”的对立面(即“他者”),也就是所谓的腐败精英和外来移民,对“人民”造成了政治迫害。在左翼民粹主义的话语中,反抗更多地指向权贵阶层,在右翼民粹主义的话语里,却更多地指向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反移民倾向。因此,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其实是有左翼和右翼之分,但是,左翼民粹主义在希腊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失败政治实践,使他们很快丧失了民意基础,他们的激进政策只有口号上的新意,却无法真正改变民生和经济困境,针对腐败精英的斗争也毫无起色。相反,在英国“脱欧”、法国巴黎恐袭等重大事件的冲击下,右翼民粹思潮集中爆发,在反移民、反全球化和反欧洲一体化的口号下冲击了左翼民粹的政治势头。所以,当前西方民粹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右翼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相结合所形成的右翼民粹主义,是一种受右翼自由主义即政治保守主义推动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昭示着保守的自由主义再次主导了西方的政治风向。
如果仅仅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国内经济发展不均,那么强调经济平等的左派其实更应该受到民众追捧。然而,从如今这种转变可以看到,尽管人们仍然认为物质性的个人利益很重要,但是,身份和尊严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一些群体开始认为其民族、宗教、种族、性别或其他身份,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为之进行斗争成为核心关切。世界各地的右翼政党对支持者的动员几乎都来自这个相似的观念,这也成为解释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概念。
反移民与反全球化成导火索
从某种程度来说,反移民与反全球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与外国移民的横向对抗也是对全球化日益侵蚀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应激反应。由于自由贸易政策和宽松移民政策所导致的大量移民作为“他者”正在威胁“人民”的主导性、正统性和纯粹性。从英国“脱欧”公投到欧洲各国的疑欧主义政治乃至给美国内政外交带来重大改变的特朗普主义等现象都表明,右翼民粹主义正在成为欧美主流政治的强劲对手,对自由民主价值提出了严峻挑战。右翼民粹主义拥护者将其核心使命重新定义为对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式维护,这种身份通常明显与种族、族裔或宗教相关。在这样的核心叙事和旗帜标榜下,那些与本地民族、宗教信仰并不一致的外来移民理所当然成为了攻击的靶子。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右翼民粹主义就抛弃了原本对自由市场的追求,转而投向所谓的“福利沙文主义”,致力于保护福利国家,这种福利只限于那些值得获得福利的人民,自然就排除了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
当然,现实事件的发生也推动了右翼民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2015年,法国这个有着最大穆斯林人口的欧洲国家爆发了一系列穆斯林恐怖袭击,2016年、2017年的多起恐怖袭击更使得穆斯林成为众矢之的。必须承认,难民危机是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重大导火索,但是绝非根源之所在。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何在?一类主流的解释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切入,认为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失败者对本国全球化精英阶层的反抗,也是对全球化的抗议。然而,经济因素并非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对于解决民粹主义带来的政治和社会紧张也非常有限。美国耶鲁大学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DanielGros)的研究表明,欧洲过去10年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基本稳定,甚至还要更好一些,德国、奥地利以及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很强劲,失业率不高,但是民粹主义政党的号召力却蓬勃发展。因此,用经济因素来解释民粹主义的兴起过于简单化。
文化与身份认同是根源
事实上,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主要的原因是来自文化和身份的困惑和冲击,确切地说,是对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多元主义的反弹。20世纪60年代,由于各国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使得民族文化多样性快速发展,少数民族要求被承认和平等的民权运动广泛兴起,世界上发达的自由民主制国家都爆发了强有力的民权运动。这种状况为每个边缘群体呈现了一个新的选择,此类群体可以要求接受像主流群体成员一样的待遇,或者可以为其成员坚持另外一种身份,并要求人们尊重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差异。例如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早期马丁·路德·金要求的是“以对待白人的方式对待黑人”,发展到60年代末,黑豹党(BlackPanthers)和伊斯兰国度(NationofIslam)等组织却认为黑人应当为自己的身份骄傲,而不是遵从社会想让他们成为的样子。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多元主义的文化有力地保存了非白人群体在文化、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认同与传统,但也导致了国家内部的分裂,导致了移民群体传统与所在国家民族传统之间的冲突。少数族群地位上升的同时,白人族群地位相对下降,导致了白人族群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在面临人口庞大且宗教信仰互相冲突的穆斯林群体时,表现得尤其强烈。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自并存于世界便冲突不断,在全球化的时代呈现了全新的斗争高潮,即来自身份的竞争。“我们是谁?”这种对身份危机感的认识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并与此前的个人主义传统发生着冲突,原本原子式的个人主体在身份危机面前统一归向我们是“基督教白人”的集体认同之中,这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回归,也意味着当今的右翼民粹主义所内含着的保守主义传统,目前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几乎同时都在倡导保卫欧洲人的家庭、宗教和传统价值观。在基督教白人的旗帜下,右翼民粹主义的身份对抗正在全面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要想对抗这种身份政治的负面影响,将会非常困难,因为多年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所塑造的身份藩篱正无所不在地妨碍着文化融合。
如果西方国家想要改变身份政治的现状,遏制右翼民粹主义的泛滥,需要从根本上思考多元文化主义的弊端,降低人们对固化身份的看重,本质上身份是可变的,并且是多重的,是由社会互动形成的,不需要把自身或某个群体刻板地印上某个身份标签。这就可以使人们意识到身份的可包容性和可整合性,个人可以与更广大的其他群体共享价值和信念,并不需要因此而否定个人的生活经验。换句话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以神化“身份”的方式获得传播,那么如今应该做的基础工作就是把“身份”拉下神坛,把民众的关注引导回范围更广、相互尊重的形式上,着眼于将小群体融入到更大的整体中,鼓励公民认同围绕核心价值和信念建立的国家根本理念,而不是共同的个人生活经验、宗教信仰或历史传统,并利用公共政策有意识地融合新成员。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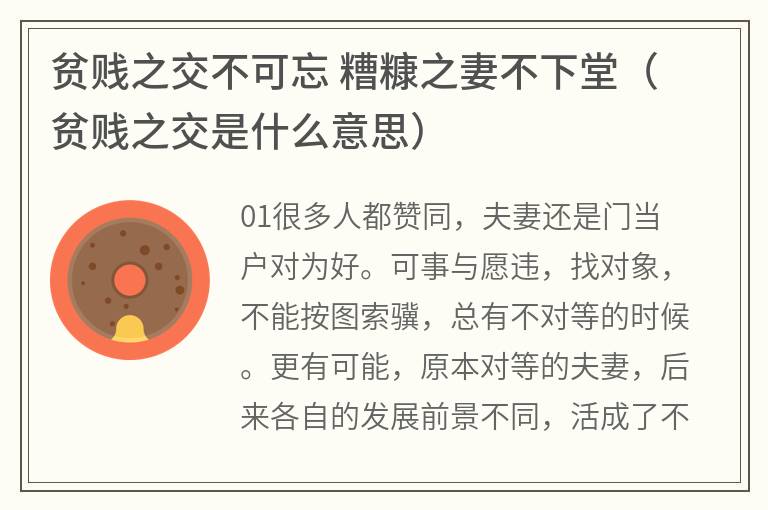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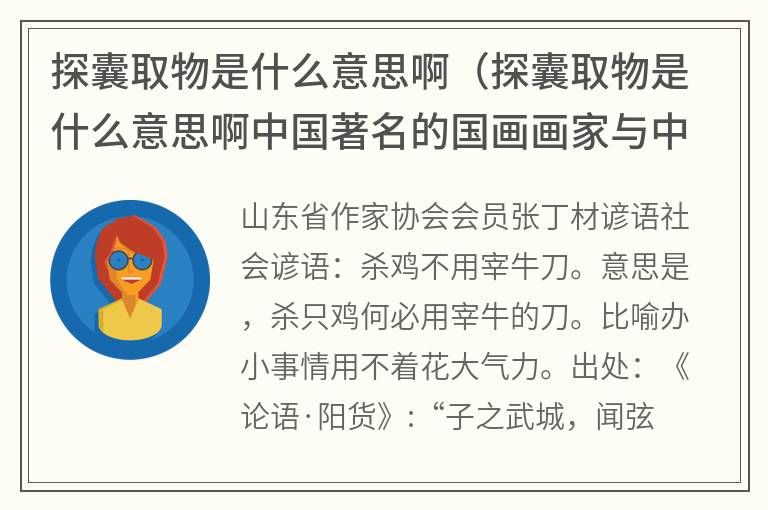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