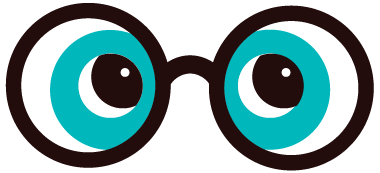
编者按
随着
随着技术的进步,数字电视、网络视频、移动视频纷纷出现,收视调查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电视时代的新特点。在多屏时代,收视调查除了要对不同终端受众收视行为进行准确测量外,还要将这些收视数据进行整合,以综合性地把握传播效果。不管在哪个阶段,收视调查的演进都与人们了解传播效果的意愿、与媒介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基于这一特点,本文从多屏时代收视调查的历史、现状出发,对多屏时代收视调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多屏时代的收视调查:历史、现状与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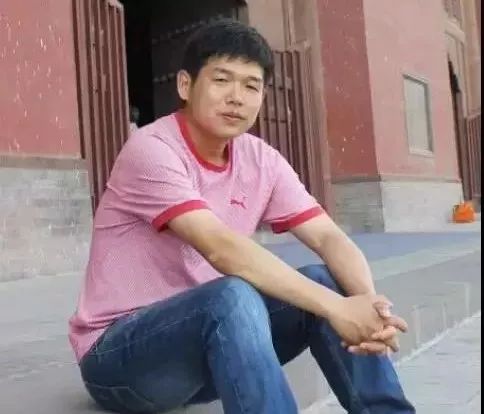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谷征,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讲师,中传受众研究中心博士毕业生,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本文原载于《编辑之友》2017年08期
【摘要】从收视调查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来看,传统电视、数字电视与网络视频、移动视频的收视调查在测量方法、测量理念等方面并不相同。多屏时代的收视调查除了要对不同终端受众收视行为进行准确测量外,还要将这些收视数据进行整合。但不同阶段的收视调查也有其相同点,即都是基于媒介产业产生。当电视媒介与广告商、广告主的交易日益频繁,几方都迫切需要有一种可以评判广告投放效果的简单快速有效的标准,这种标准就是收视调查数据。基于这一特点可以预测出多屏时代收视调查发展的几点趋势。
【关键词】多屏时代收视率趋势电视时代网络视频
一、传统电视时代的收视率调查
收视率调查首先诞生在作为商业电视体制代表的美国。1947年,胡珀公司(Hooper)开始用同步电话法进行电视收视率调查,并用日记法来收集其他相关资料[1]。20世纪50年代初,AC尼尔森将受众测量仪正式引入收视率调查领域,但当时这种测量仪比较简易,不能提供受众的人口学资料等信息。包括AC尼尔森在内的很多公司通过由被访者自己记录的日记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到了60年代以后,美国收视率调查日益规模化、规范化。AC尼尔森开始占据美国收视率调查产业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
AC尼尔森在20世纪80年代前使用的家庭测量仪,只能提供家庭收视数据。在竞争压力下,该公司于1987年开始提供基于人员测量仪的全国电视网收视报告[2]。在样本户安装人员测量仪后,家庭的每一位成员在收看电视时首先要通过遥控器确认自己身份,这就能够获得其较为准确的人口统计资料,因而更受广告主和广告商的欢迎。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电视频道的迅猛增长、电视媒体市场化进程不断加深,传播者对电视观众日益重视,我国的收视调查工作开始快速发展。1997年,由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CTR)与Kantar Media集团共同合资建立的专业收视率调查公司央视-索福瑞(现为广视-索福瑞,以下简称CSM)成立。大抵相同时间,尼尔森媒介研究以及后来的AGB尼尔森媒介研究公司开始在中国市场开展收视率调查业务,不过2009年后该公司退出中国大陆市场。因此CSM成为目前中国市场上全国范围内最主要的收视调查数据提供商。
CSM网站显示,截至2017年6月,CSM已建148个提供独立数据的收视率调查网络(1个全国网,25个省级网,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122个城市网)[3]。在不同省网、城市网,分别使用人员测量仪和日记卡法进行测量。
从上述中外收视率调查的发展可以看出,传统电视时代的收视率调查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方面,垄断成为收视调查行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另一方面,收视率的调查方法渐趋统一为日记卡与测量仪两种方法。早期视听率的调查方法与模式比较多样,面访、电话调查等方法共存于收视调查中。而面访、电话调查的缺点其一在于隔天回忆会造成被访者的记忆模糊,其二在于调查对象并非秩序性固定样本组,因此测量误差较大。之后收视调查方法主要演变为日记卡法和测量仪法。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对固定样本进行收视测量,但是日记卡同样需要样本户回忆自己的收视情况,也存在一定测量误差;而家庭测量仪只能获得家庭收视数据,很难获得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个人收视数据。人员测量仪则弥补了这一缺憾,不过出于成本等问题的考虑,大部分调查公司同时使用日记卡和测量仪两种方法。
二、数字电视的收视率调查
在模拟电视阶段,收视测量时使用的测量仪主要是根据模拟信号来获得频道信息,但是数字电视同一个频段可以容纳若干套数字节目频道,因此一些新的技术被应用到数字电视收视调查中来,比如声音比对、图像比对、在节目与广告中植入辨识密码等。目前的交互式数字电视机顶盒也已具备双向传送数据的能力,加以改造就能精确记录和传送用户的收视数据。
在欧美市场,AGB尼尔森的UNITAM技术、主动/被动电视测评技术(Active/Passive Meter技术)等使用了声音对比等技术。此外,尼尔森媒介研究(NMR)与美国数字录像(DVR)服务提供商Tivo和一些有线电视运营商合作,利用其数据进行收视情况分析。KantarMedia集团开发了RaPiDview、DIRECTView等技术或者产品,可以从用户的机顶盒下载收视数据进行分析[4]。
伴随数字电视的普及,一些新的公司逐渐进入这一行业,原来从事视频租赁和票房统计的Rentrak开始涉足测量视频点播(VOD)、数字视频录像(DVR)和机顶盒用户的收视情况,并取得不错成绩。一些有线电视运营商则开始亲自测量和出售收视数据。
在中国市场也大抵如此,CSM目前主要使用植入辨识码和声音匹配技术进行有线电视收视测量。一些新成立的公司通过与当地有线运营商合作开始占有部分市场,如尼尔森网联开发了数字电视收视测量仪WatchBox等技术,用于海量样本收视监测,并建立了实时传输实时监控的数据回传渠道。
与美国类似,我国有线运营商同样开始进入这一领域,2014年11月,歌华有线宣布首个收视数据实时采集分析系统建成,并开始发布收视数据。
首先,基于双向交互机顶盒的收视调查,其优点是实现了大样本甚至某一范围的全样本调查,但是此类大样本数据无论多少,都只能反映部分观众的收视行为,不能体现那些不拥有交互机顶盒家庭和个人的收视情况。
其次,这种利用数字电视机顶盒、基于海量样本的收视测量,只能反映家庭收视情况,很难获得广告商关心的个人收视行为数据。如果要获得个人数据,就目前技术来看,依然要在用户收视终端上安装相关设备。由于成本等因素限制,这种设备不可能在海量样本的所有家庭户安装,只能在抽取的样本户家庭展开,因此很难得到基于海量样本的个人收视数据。而这种抽取样本的个人收视数据如何能够与海量样本的家庭收视数据相匹配,也是一个难题,目前各公司均没有明确说明这一匹配的算法。
再次,利用数字电视机顶盒的回路数据进行收视测量,只能获得单个有线运营商网内的收视数据。像我国有线电视网络基本一省一网,条块分割,目前来看,一家调查公司基本上只能与一两家运营商合作,获得当地的收视数据。不同地区、不同网络、不同运营商、不同公司的数据之间很难进行比较。
最后,如果由有线运营商本身而非第三方调查公司进行收视调查,其可信性将大打折扣,电视台会怀疑其是否提高节目录播、点播时的收视率,而广告商会怀疑其是否暗中提高收视率以获得更高广告费用。另外,此技术只能测量机顶盒的开关情况,而非电视机开关情况,会导致收视数据的不精确。
三、网络视频的收视调查
对于网络视频节目的收视调查,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后台终端的监测,比如视频网站服务器对于视频的点击量、浏览人次、浏览人数等指标的监测。不过视频网站众多,并没有一个获得共识的评判标准。另一个则是用户端的测量,即在样本户的电脑或手机中安装插件,并对内容加码,来获取其收视行为资料。
一些知名的网络调查公司利用自身优势进入网络视频收视调查领域。作为知名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商,ComScore推出了ComScore Video Metrix,能够进行较为透明的视频测量服务。
Kantar Media集团开发了虚拟测量仪(virtualmeter),顾名思义,所谓虚拟,即不需要各种硬件,它是需要安装在样本组电脑里的软件。不同于传统的互联网测量,它不仅能测量直播节目的收视情况,更能利用声音比对等技术来监测延时收视行为,并且能够识别视频的来源[5]。在视频网站节目测量方面,尼尔森2008年启动了视频测评服务(Video Census),基本原理与虚拟测量仪类似,它能够从收看人数、平均播放时间等多个指标对网络视频媒体进行综合评测[6]。
在我国,艾瑞咨询研发了iVideoTracker系统进行网络视频市场监测,研究网络视频收视行为。同时,秒针科技、精硕科技等一些营销数据技术公司开始染指网络视频、移动视频广告的收视效果测量。
视频收视测量与传统电视收视测量的不同除了技术外,更多体现在理念上。传统电视的收视测量,通过抽取样本,以样本户安装人员测量仪或留置日记卡的方法来获得人口统计学信息。数字电视尽管能获得大样本数据,但仅仅是家庭收视率,如果要获得个人收视率,依然要在样本家庭安装类似仪器。而网络视频或移动视频可以获得用户的所有上网行为,因此可以由大数据来推及其人口属性等资料。比如从用户的新闻浏览、网购行为记录可以推测其性别、爱好等信息;移动终端可以对用户进行位置定位,推测其居住和工作地点,借此进一步推测其收入和所在阶层。受众不再是一个无人格化的数据,而是寓于情景中的立体信息,这点对于广告商尤为重要。不过,考虑到与传统电视收视调查数据的融合问题,老牌的收视调查公司还是倾向于使用样本组进行调查,在多屏时代,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四、多屏时代的收视调查
从传统到多屏时代的收视测量,最大的变化在于将原来的电视受众测量(TAM)发展为视频受众测(VAM)。由于传播载体、传播终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收视测量方法不断更新。不同传播终端还涉及计算口径、受众基数及结构等问题,因此,收视测量除了要对不同终端受众收视行为进行准确测量以外,还有一个将这些收视数据进行融合的过程。“目前全世界范围比较认可、实行较好的解决方案依然是各做各的,最后融合在一起。”[7]
在多屏时代,如何把电视、电脑、手机、iPad等包括大、中、小不同屏幕的多种终端的收视情况整合起来是一大难题。仅大屏就收视测量方法等指标又可以分为模拟电视、数字电视和智能电视等类别。尼尔森早在2006年就携手NetRatings公司推出A2/M2计划(AnytimeAnywhere Media Measurement),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将传统收视率调查与网络视频、移动视频的收视数据相匹配,形成涵盖三屏合一的数据报告。2013年5月,尼尔森开始在移动设备端进行收视统计测试。其先与ABC展开合作,测试用户在手机、Pad端安装ABC Watch应用收看ABC视频节目的情况。此外,尼尔森还与Syncbak公司展开合作,这家公司推出了能够收看CBS四家电视台节目的APP。2013年9月,尼尔森推出了全新的硬件和软件对收视情况进行监测,此次样本接近23 000户家庭。这一测量系统除测量传统电视收视外,还包括机顶盒收视情况,对X-Box、PlayStation设备,以及对Netflix、Hulu和Amazon等网站的视频收视情况测量。同时这一系统还将加入手机与Pad的收视监测,并且尝试建立一套能融合各终端收视率的计算方法。
除了尼尔森,也有公司在尝试其他同源多屏收视数据的测量方法。阿比壮公司(Arbitron)研发了一种叫作便携式个人测量仪(Portable People Meter,简称PPM)的设备。这个设备不仅便于携带,而且能够记录受众在多种媒体上(无论是数字电视、模拟电视还是网上视频、移动终端)的收视情况。
在我国,CSM、国双科技、酷云互动、上海泓安等公司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地区进行整合各终端媒体收视率的尝试。不过从国外对于多屏环境中同源样本的尝试可以看出,同源样本难以实现不仅在于多屏的复杂性,还在于其对样本量的要求较大,成本巨大。因此国内很多测量机构仅仅侧重于一种收视载体,如酷云互动在“智能电视操作系统或机顶盒中安装自动内容识别系统(ACR),以此监测智能电视的收视”。而其他一些国内调查机构对多源样本的整合“则以多源混合为主”[8],同源仅仅存在一些样本数量不多的试验研究。
五、多屏时代收视调查的发展趋势
传统电视、数字电视、智能电视与网络视频、移动视频的收视测量尽管在很多方面并不一致,但也有其相同点,即这些调查都是基于媒介产业而诞生。当媒介与广告商、广告主的交易日益频繁,几方都迫切需要有一种可以衡量广告交易、评判广告投放效果的简单快速有效的标准,这种标准就是收视调查数据。
收视调查产业的发展是媒体与广告业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一个广义上的媒体行业同时包括了作为内容生产的媒体、作为播出平台的渠道,为媒体获得资金打通渠道的广告代理系统以及为上述几方面提供数据支持的收视率调查系统。对于媒体市场中的成员来说,产业链已不是一个链状的结构,而演变成网状的组织。
广告主投放广告就是要获得广告效果,而最直观的数据就是广告到达了多少人,有多少人看到了广告,即收视率所调查内容。收视率调查公司想尽方法监测那些看不见的受众,评价媒体传播效率和所刊播广告的效果,为市场的平稳运行提供通道。收视率数据的存在减少了媒体、渠道与广告商、广告主之间的交易成本,他们以购买收视率调查公司的数据作为对其调查成本的补偿。
收视率呈现方式相对简单,它将受众抽象成客观数字,让媒介与广告主、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能够通过这些数字来了解那些看不到、摸不着的广大受众。同时,收视率调查更新速度快,它不是恒定的结果,而是一遍一遍地建立,是一种迅速消失的产品,过期它们会立刻失去价值。它能够为媒介与广告主、广告公司提供最新的收视情况,满足商业运作的效率。因此收视率作为电视节目和电视广告交易的“通行货币”获得了广告主、媒介和广告公司各方的认可。换言之,收视率调查之所以能够获得青睐,不在于研究的精确性,反映节目传播效果的全面性,而在于其研究结果的简单直白、更新迅速、能够满足各方的商业需要。但是收视率等量化指标只能考察受众是否接收到这些信息,很难反映其认知、态度等深层次信息。收视率数据操作的简单方便,是以牺牲研究的准确性与全面性为代价的。
因此,无论收视调查方法与手段如何更新、发展,其发展趋势都是要更好地服务于广告市场,更好地服务于收视调查行业的这一特点。
1. 测量主体日益多元,测量指标与标准亟待统一
目前就我国来说就有不同机构对收视情况进行测量调查。1.传统收视调查公司,如CSM。2. 基于收视接收载体的数据服务公司,如基于智能电视的酷云互动、欢网等公司。3.技术出身的网络调查公司或数据提供商,如国双科技。酷云互动实际也是技术公司出身。4.掌握后台数据的平台方。这里既包括视频网站,如优酷土豆、爱奇艺等;也包括电视台成立的网络平台,如CNTV、芒果TV;还包括歌华等有线电视运营商、百事通等IPTV运营商,以及乐视盒子、小米盒子、天猫魔盒等互联网盒子运营商。5.探究视频广告效果的广告公司,如秒针科技、AdMaster等公司
一方面,如此多的测量主体,每个调研机构都有独自的调研体系,其监测技术与测量对象不尽相同,各测量指标之间在名称、定义等方面存在差异,难以将不同机构的测量数据进行对比。另一方面,一些测量主体本身就是播放主体或是广告公司,比如优酷土豆、爱奇艺等视频网站平台以及秒针等公司,其测量数据各方看法不一。因此,虽然测量主体越来越多,数据越来越丰富,却缺少一个具有公信力的能够流通于行业内部、获得多方首肯的“通行货币”,测量指标与标准亟待统一。
2. 受众肖像更加精准,但数据整合、样本匹配有待完善
目前很多公司开始尝试将收视行为数据测量与消费行为调查相结合,进而描绘出更加精准的受众肖像,这点对广告市场各方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如前所述,传统收视调查是通过人员测量仪比较准确地获得样本个人的相关信息,但在多屏时代,网络和移动视频收视行为测量的人口统计资料往往基于样本其他上网行为的计算预测所得,并非真实情况。因此,一些收视公司尝试与拥有真实人口统计资料和超大数据处理能力的电商合作。2015年9月,酷云互动与阿里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利用天猫、淘宝、阿里妈妈的电商数据,不仅可以获得更为准确的受众人口统计资料,更能将受众收视与线上消费相结合,勾勒出更加精确完整的受众肖像,为媒介、广告商、广告主各方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还可以利用阿里云的存储与大数据计算平台进行数据挖掘。
但是这些逐渐清晰的受众肖像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其推测受众资料时所依靠的大数据并非真实社会情况的大数据,而是其平台内部的大数据。貌似清晰的受众肖像很可能是片面的、局部的呈现。而传统收视调查的抽样方法所得数据,尽管存在各种问题,如抽样误差,甚至可能会出现人为干涉等情况,但却可以从数理统计意义上代表总体。因此,如何整合各个调查机构各自的大数据与传统收视调查的“小数据”,是目前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3. 数据日趋实时呈现,深度挖掘远远不够
与传统电视时代的收视测量相比,多屏语境下的收视数据呈现更加方便快捷,甚至可以实时提供。目前已有公司提出和践行了实时收视率的概念,比如尼尔森网联(Nielsen-CCData)开发了一款名为iTVRC的随身数据客户端;酷云互动则推出了酷云EYE,都能实时呈现基于自己定义的收视行为数据;2016年6月,CSM联合欢网科技也推出实时收视率平台——CSM-huan智能电视实时收视系统。
实时收视数据的出现,迎合了各方对于收视率调查操作方式简单、便捷、快速的渴望,但也极大牺牲了收视研究的准确性与全面性。实时数据的测量样本局限于不同调查机构所监测的部分收视用户。比如酷云互动等公司的收视数据主要基于智能电视,一方面,尽管从目前电视销量来看,智能电视渐成主流,但是从实际拥有量来看,智能电视还没有占绝对优势;另一方面,调查机构也很难掌握全部智能电视的数据,而仅仅是与部分智能电视厂商合作。同时其测量指标也简单。因此,这些数据往往被市场各方作为参考而已。
因此,一些机构也开始尝试从单一的收视行为测量发展到引入传播效果的研究,以吸引行业各方的重视。传播效果的学术研究,研究过程更加严谨,研究方法更加全面,但是其结论并未成为广告商、广告主与媒介议价的评判标准。其主要原因在于效果研究的期限过长,过程较为复杂,不能满足快速提供数据的要求。而在新媒体语境下,效果研究可以利用大数据针对新媒体特点更加深入、有效、迅速地展开。因此,收视调查需要也可以引入包括满意度、传播口碑等在内的多种维度测量,采用的指标也不用仅仅局限于量化指标,应加入质化指标来全面评价电视节目与视频节目的传播效果。如一些调查机构和学者已尝试进行电视节目的网络影响力研究,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来获得网民在论坛或微博上对于某一电视节目的评价,并加入到收视评价体系中去。尼尔森推出了“Twitter电视收视率”,以Twitter用户的关注与讨论情况,作为评估某一节目的辅助数据[9]。CSM与新浪微博则推出了首个微博收视指数,而作为视频网站的优酷也推出了基于自身数据的优酷指数。上海浩顿英菲市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则开发了“广告创意效果评估”系统。CSM在原有的电视收视率测量基础上设计了新的跨媒体传播效果测量与评估体系。
不过这些挖掘还不够全面、深入,如果能将学术界对电视节目、视频节目进行的效果研究与目前收视调查行业的各种方法结合起来,或许更能反映受众真正的收视情况。
注释
[1]刘燕南. 电视收视率解析:调查、分析与应用[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32.
[2]韦伯斯特,法伦,里奇. 视听率分析:受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M]. 王兰柱,苑京燕,译. 2版.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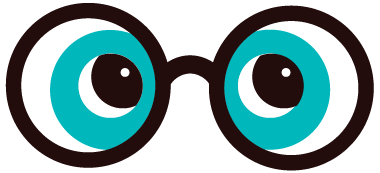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