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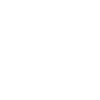

前面几章,梁先生介绍了史学的定义、意义、范围以及过去的中国史学界,让我对过去的史学有了基本的认识。然而,正如上一篇结尾所说,中国历史之悠久,史书数以万计。所以治国史适宜读什么书,梁先生都回答不上来。梁先生提出:青年男女是否有能力读此浩瀚古籍?费如此大力读此浩瀚古籍,有收获的又有几人?我辈想了解我们的先人的事业,是不是从此获得就够了?如果否,恐怕读遍数十万卷史书也不够。那该如何?从而引出“史学的改造是目前最急迫的问题之一” 这一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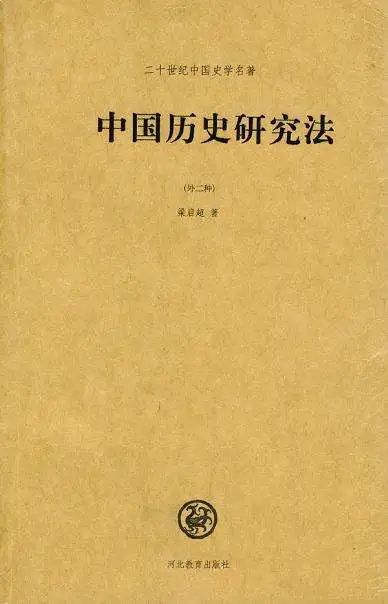
梁先生首先讲到第一个问题:史书给什么人读?他拿《春秋》、《资治通鉴》和《史记》举例。《春秋》供当时贵族中为人臣子的人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其主目的是供帝王读,其副目的是供大小臣僚读。司马迁《史记》,自言“藏诸名山,传与其人”,将来供后世少数学者读。所以读者不同,而书的精神及内容组织也会不同。反过来,不同的读者,他看的书也会不同。所以,梁先生认为旧史无论何体何家,总离不开贵族性,其读者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
梁先生讲到第二个问题:历史为古人而写还是今人和后人而写?对于这个问题,他不像“治国史宜读何书”那样给不了答案,而是直接给出答案:为今人或后人而写。但是历史上的史书和史家并非如此。经过一番论述,他认为史学界改造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以生人为本位的历史代替以死人为本位的历史。
梁先生讲到第三个问题:史学的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中国古代,史外无学,所有人类智识的记录都纳入史,后经分化学科,渐渐与史分离。梁先生举了两个例子稍加说明。例如天文,从《史记.天官书》到《明史.天文志》更多的内容属于天文学,而不宜入史。当然,何时发明岁差,何时发现中星,等等是属于历史范围。又如音乐,各史《律历志》及《乐书》《乐志》等详述五声十二律的度数,曲辞等,应该由音乐家研究,应该属于音乐学,而不是音乐学。所有学科都是如此。梁先生可能觉得不够,又举几个学科为例。总而言之,因为没有区别分开专门学科和历史学,导致虽然学者读破万卷,而想得到的智识,却没多少。所以,现在写史的人,应该首先明白这一点,才可以把精力利用在真正历史学里。这是梁先生认为需要改造的又一个方面。

梁先生讲到第四个问题:历史的客观性。梁先生批评了“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的弊病。有的是历史和经书混为一体,有的是颠倒事实来迁就写书个人的主观目的。他认为,历史就是历史,道义大义是道义大义,不能混为一谈,导致混淆历史,疑惑后人。所以,梁先生认为,今后的写史的人,应该尽可能摒弃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史为手段。
梁先生讲到第五个问题:史迹不能不从旧史中获取资料,才能一直记载下去。而旧史往往编辑不精,甚至缺失,而且旧史著作的目的又跟现在所需求的多半不对应。所以,对史迹需要有人重新搜罗补缺和考证真伪。只有经过此番艰辛工作,我国的历史学才可能完善,别人才可以节约时间了解历史。
梁先生讲到第六个问题:古代写书,包括历史,大部分短句单辞,不相联属。人类的活动,应该是连贯的,一体的,有方向的,有关联的,所以,今日的历史也应该是有机体。
梁先生认为今日的历史应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他提出治各专门学的人需有的觉悟,希望他们还原各部分的历史真相。当各专门史成立了,那么普遍史就比较容易了,此时,普遍史就是史学家的任务了。
从六个问题引出,梁先生阐述了旧史的问题以及表达了他对新史的希望。下一章,梁先生将会讲到历史资料,篇幅比较长,更需要耐心阅读。
作者简介
读书者:子良,广东惠州人,园洲诗词协会会员,喜欢阅读各种书籍,拙于文字,只约稿,从未投稿。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