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学名张复;参加革命后,改名张春木、张椿年,后因立志“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遂改名太雷以铭志。张太雷小时候,家境艰难。1906年,张太雷的父亲就病故了。为了维持生活,他的母亲到常州张绍曾家帮工,但所得微薄,经常需要亲朋接济。所幸张太雷聪明伶俐,颇得张绍曾看重,因此资助他入学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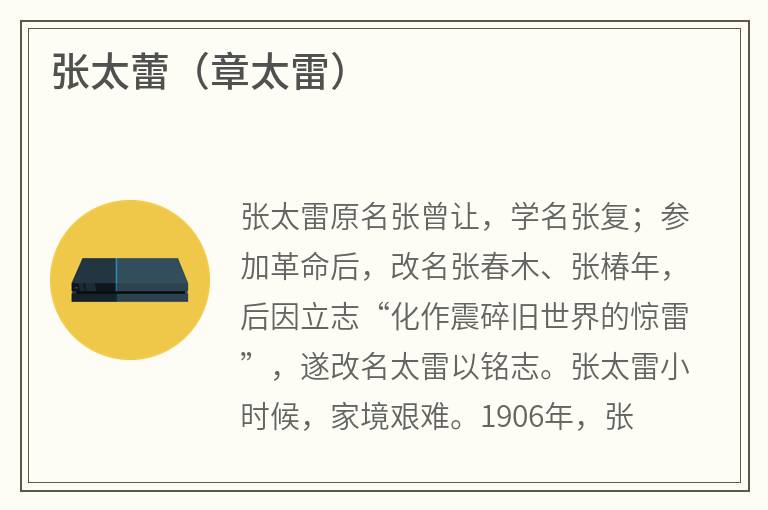
张太蕾(章太雷)
张太雷读小学时,除课本以外,特别喜欢读历史故事书。他常常仿照《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书中的情节,将同学们分成两组,玩两军对垒的游戏。他的家乡常州是岳飞抗金、太平天国反清的历史发生地,因此他对这些故事格外留意,常常设法找野史笔记来读。而且,他很有正义感,爱打抱不平,看到弱小同学被别人欺侮,总会挺身而出。由于自己出身贫苦,张太雷从小就对穷苦人有同命相惜之情。有一天,他和伙伴们在街道上玩耍,这时一辆黄包车从他们身边驶过,一阵风吹来,刚好把车夫的帽子吹掉了。伙伴们都大笑起来,因为车上拉有客人,他们想看车夫如何才能捡回帽子。正在车夫面露难色之际,张太雷紧跑几步将帽子捡回来递与车夫戴好。伙伴们不解地说:“何必呢?我们正准备看笑话呢!”张太雷却说:“他拉着车子,上面坐有客人,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又要去捡帽子,就会更费力气。但对我而言,举手之劳而已,何不帮他一下呢?”
1911年,张太雷进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于是他特别注意阅读报纸新闻,了解时势变动。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既读《民呼报》《民立报》《申报》,也读《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和《仁学》;对于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他都找来仔细阅读。
学校里有几个教员是同盟会会员,他们经常向学生们讲述邹容、秋瑾等人的革命事迹,张太雷往往听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十分讨厌脑后的那根辫子。为表示对清政府腐朽统治的反抗,他与同班同学瞿秋白带头剪掉了辫子。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带头上街游行庆祝,宣传革命主张。
辛亥革命后,国家政权被北洋军阀篡夺,社会依旧动荡不已。1915年,袁世凯又与日本签订几乎要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张太雷亦为之痛心不已,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要独占中国、灭亡中国;而袁世凯为了要当皇帝,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张太雷的这些爱国举动,引起校方不满。不久,校方就以张太雷“素行不道”、擅自组织罢课为借口,强迫他离校。同年秋,张太雷考入北京大学法科,不久又转入北洋大学法政科临时预备班。1916年秋,张太雷正式升入北洋大学法科法律学门。
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张太雷看后深受启发,从此开始努力去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次,他的中学校友来访,谈及人生未来规划,张太雷坚定地说:“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张太雷积极参与其中。他组织同学们到乡村去演讲,由于言辞痛切、激情澎湃,听讲的百姓大受鼓舞:“先生讲话真对。能一月来一次,使大家永远不忘才好。”返回市区时,他们又利用等火车的时间在车站月台演讲,“听者塞途,人人点头称是”。及至他们上了火车,听讲的群众依然“相聚不散,引颈遥望,似恨时间短促,不能尽所欲闻”。8月,为营救被捕学生,张太雷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赶赴北京,与北京的同学们一起到总统府请愿,慷慨宣示:“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抛头颅、洒热血,绝不迟疑!”由于同学们的勇敢斗争,北洋军阀政府最终释放了被捕学生。
1920年9月,李大钊发起组织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0月,张太雷加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规定:“我们党的其他创始人,其入党时间都应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时算起。”因此,1920年10月就是张太雷的入党时间,他的入党介绍人即是李大钊。是年冬,张太雷与邓中夏等人在北京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既教工人读书识字,同时传播革命思想。为团结劳动群众,他还经常到工人家走访,一起吃窝窝头、睡土炕。当时,张太雷每月只有7块钱的生活费,但他省吃俭用,常常1个月下来花销不到3块,节约下的钱就用来接济工人。因此,工人们很感激张太雷,很快就与他建立了稳固的友谊。
1921年2月,中央决定派张太雷前往俄国伊尔库茨克,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行前,他给妻子陆静华留书一封:“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但是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这段朴实的话语表明,张太雷已经被共产主义思想深深感染,已经有了更高尚的人生追求。
1922年秋,上海大学开办。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太雷到上海大学做教员。据当时在上海大学读书、后成为张太雷夫人的王一知回忆:“他给我们不少指教和解释。他的语言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总是在我们谈论得非常热烈或是有争论、有疑难的时候插进几句话。而他那简单的几句话,总是能深入问题的本质,有不可争辩的逻辑力量,常使我们疑难解决,争论停止。他没有架子,总是朝气蓬勃、愉快活泼的。他还喜欢开玩笑,有他在场,总是谈笑风生,欢腾四座。”1923年8月,张太雷随“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讨论苏联援华、国民党改组以及国共合作等事宜。代表团任务完成后,张太雷继续留在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1月,列宁逝世。张太雷悲痛不已,专门写悼念文章寄回国内发表,文章在记述列宁棺木抬出萨拉托夫斯基车站那一幕悲壮的场景时写道:“当时头上大雪纷纷,鸟雀无声,只似乎听见接者的心底哀音。出站后棺木在前,送者随行,走过的街道,两旁军警排列,阻止拦入行列,然而屡见老幼争相冲入重围,冀得随送。街中澈静,两旁观者无数,然而一声不闻。”这充满深情的笔触,表现出的岂止是他对伟大革命导师的哀思与敬仰,更表现出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无比坚定的信仰。在苏联期间,张太雷广交革命战友,经常与日本共产党人片山潜、越南革命家胡志明讨论东方国家的革命问题,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4年8月,张太雷自苏返国,在党组织安排下负责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时,他还在上海《民国日报》任主笔,又兼着社论委员会的委员。但他总是神采奕奕,毫无倦色。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省港大罢工,由张太雷负责发动与领导罢工。为了发动群众,他大量地写作和演讲。他说:“笔杆和舌头是我们革命者政治斗争的武器,应该不断运用,不写不讲是不对的!在这个时候,群众是多么希望我们写和讲啊!况且我们现在有条件写和讲,那就更应该多写多讲!”
有的同志没有演讲经验,不敢登台讲话,张太雷就鼓励他们大胆去讲去练,并将到群众中演讲称之为“上阵”。每次同志们“上阵”前,张太雷都要对演讲内容仔细把关,并提醒大家注意演讲技巧。同志们演讲完毕下台后,他都会打趣地说:“这一仗打得如何啊?”如果同志们回答说“又打败了!”“没打好!”他就说:“没关系!下次再准备得好些!”如果同志们说“还可以”,他就会兴奋地说:“你看,我说对了吧,世上没什么难事,只要肯学肯练,就一定会成功!”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之余,他常到广州郊外踏青。他热爱这个国家,热爱大自然赋予这个国家的一切。然而,他越爱这美好的河山,就越痛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对这美好人间的破坏与践踏。有时,他站在屋顶俯瞰广州繁华的市容;有时,他又乘坐小船欣赏珠江两岸的美丽夜景。这些生活的美好,都唤起他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他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抒发对未来生活的向往:“生活多可爱啊!我们将来的新社会,一定比现在更美好!”他还常常唱起《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可以说,他始终对革命的胜利抱有最大的信心,愿意付出最大的努力,乃至做出最大的牺牲。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时,国共合作已显破裂端倪。张太雷的心情异常沉重,他预感到事件绝不会这么简单。事实上,早在“中山舰事件”之前,他就对蒋介石叛变革命有所警惕。3月19日,亦即“中山舰事件”前一天,他还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广东革命的危机仍在呵》的文章。对于当时微妙的时局,张太雷敏锐地指出:“广东已经统一了,反革命的军阀大半已经铲除了,但是广东的危机仍然是存在着呵!一般革命党人醒醒呵!”他一针见血地提醒道:“革命的同志们,广东的危险仍在呵!去年打倒刘杨后大家以为广东大害已去,可以安然了,不知道暗幕一揭开,内面不知道一重一重有多少阴谋诡计!我们现在又看见这种情形了。同志们,提防着。”“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又提出“整理党务案”,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中共党员全部被迫辞职。对此,张太雷愤慨不已,这时他已确信革命存在着危机。1926年3月底,张太雷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严正指出:“共产党决计不因敌人的造谣而放弃他的革命工作,并且警告社会:帝国主义反革命派对于共产党这一种的造谣是分裂国民革命的势力,破坏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危害广东和平的一种阴谋。”
5月26日,他又发表《反动派在广东之活动》一文,再次疾呼:“广东革命基础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危险的情形。”可以说,张太雷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少有的头脑清醒者。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革命的工作重心北移。1926年11月,张太雷随同鲍罗廷、宋庆龄等离开广州前往武汉。此后直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方才再次衔命返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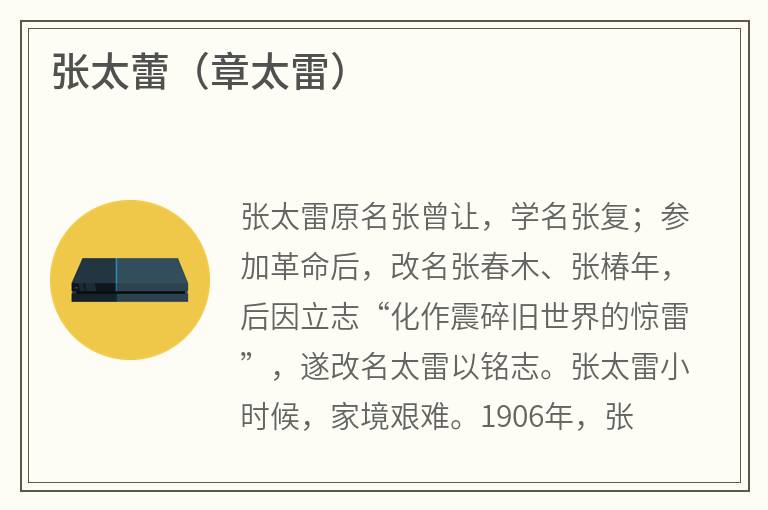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