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史学*何以可能?
—余新忠《追寻生命史》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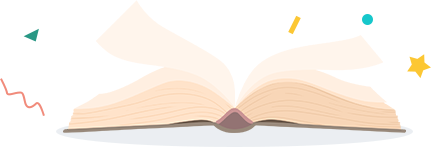
【摘要】余新忠教授新著《追寻生命史》一书,是其十多年来在医疗史领域围绕“生命史学”展开探索的学术结集,也是作者学术生涯的重要阶段性总结,更是中国医疗史研究领域的一部代表性成果。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生命史学”的学术概念和方法,以及秉持相关理念在医疗史研究领域的努力探索和多方实践,对于生命史学的开展具有典范性意义,同时对于推动和深化中国医疗史乃至史学研究也有着诸多启示。
【关键词】余新忠《追寻生命史》生命史学新史学思想
2021年6月,余新忠教授新著《追寻生命史》[1]一书出版。该书旗帜鲜明地倡导“生命史”的研究取向,使其与一般史著大异其趣,在出版之初即广受学界关注。作者对人的生命健康以及人性的着力强调,也使得书中的文字细腻灵动,充满着脉脉温情。对于依然处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人们来说,读来更加具有意味。作为中国医疗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余新忠教授自21世纪以来在医疗史领域沉潜反复、孜孜矻矻,近年来不时有重要的著述发表或出版,《追寻生命史》一书便是其“近十多年来围绕着‘生命史学’而展开探索的心得”的结集,所收录的成果多发表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人民日报》《韩国医学史杂志》等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该书可谓是作者学术生涯的重要阶段性总结,更是大陆医疗史学界的一部代表性成果,对中国医疗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引领作用。
《追寻生命史》一书所收录的成果上起2003年,下讫2014年。这十余年正是作者的学术研究日益精进和成熟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医疗史研究蓬勃发展的机遇期。全书所收录的文章论题广泛,研究视野开阔,学术理念新颖,既有对医疗史在中国发展的学术脉络的梳理,同时也有着如何进一步深化医疗史研究的学理探讨和研究实践。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医疗史而展开,并可统合在作者倡导的“生命史学”的学术理念之下。通读全书,不仅能够清晰地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医疗史研究的学术进路,同时也能够触摸到作者致力于医疗史研究十余年来的心路历程,更能从中认识到作者基于对生命健康的关注而提出的“生命史学”对于推动中国医疗史和历史学研究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一为何要提“生命史学”?
“生命史学”的提出,是国内外史学发展的逻辑结果,同时也与当前中国医疗史研究的状况相关,更是余新忠教授多年来在医疗史研究领域上下求索、勤勉耕耘的心血凝结。
从国际史学的发展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史学文化转向的影响下,学界对于历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已逐渐失去兴趣,转而着力探讨并解析历史上“人”的生存状态及其文化意义。新文化史学一枝独秀,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其流风所及,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史学界,并最早在台湾史学界产生了回响。在大陆史学界,随着对僵化的革命史观和陈旧的史学命题的反思与扬弃,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接连兴起,并同样表现出了对历史上不同时期人们的精神思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等领域的探究热忱。大陆的医疗史研究便脱胎于社会史的深入开展。对此,余新忠教授在《追寻生命史》一书中有着如下总结:“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史学界都提出了‘还历史以血肉’或‘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的诉求,进而发出了‘人’到底在哪里的追问”(页155)。在这样的一种史学发展理路下,医疗史在海峡两岸兴起。由于与人的生命健康直接相关,医疗史在兴起之初就呈现出了鲜明的“关注生命”的研究取向。[2]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年轻学人的不断加盟,在短短的二十余年间,医疗史的研究团队不断壮大,专业的医疗史学术期刊创刊,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成立,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大陆的医疗史研究已然“开宗立派”。特别是医疗史的研究成果不断在国内的重量级刊物上发表,为史学界吹进了一股新风。然而时至今日,医疗史在大陆史学界似乎仍尚未真正成为主流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医疗史研究在选题和材料的使用上颇有新意,但多数学者在学术理念上却相对陈旧,众多研究依然在传统的社会史框架内进行,特别是不少学者缺乏对生命的真正观照和理论自觉,导致医疗史的研究并未呈现出应有的“学术新气象”。
对于医疗史研究存在的上述问题,余新忠教授在数年前就曾敏锐地指出,医疗史研究的“红利”正在日渐消退,并对学术理念和方法的总体滞后的研究状况颇有隐忧。为了论述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局限,余新忠教授曾以其成名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为例,指出该著的研究旨趣主要在于“清代江南瘟疫的流行情况及其相关分析,时人对瘟疫的认识,以及由此显现出的清代江南社会的社会构造和演变脉络”,但“并没有想到想去探究当时社会对诸多瘟疫的描述和命名体现了怎样的社会文化意涵,也没有去考虑19世纪以降社会认识和应对瘟疫方法变动背后的权力关系,而且也没有意识到,现代的医疗卫生制度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也并非是不证自明的”。作者坦陈,《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尽管在出版时颇受好评,但还是“一部比较纯粹的社会史作品”(页79)。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作者则结合自己早年的研究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医疗史研究中缺乏对生命的真正关怀,“以往自己和国内其他同仁所作所谓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果真是关注生命吗?反躬自省,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研究……真正关注何尝是生命,实际只是社会而已”(页155)。作者的上述检讨,既是对个人学术道路的一种内在省思,同时也是建立在对当前大陆医疗史学界研究状况上的深刻批评,“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相当多研究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往往缺乏对国际主流学术成果、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了解和把握,‘新瓶装旧酒’,以旧理念、旧方法探讨新问题的情况还相当常见”(页156)。
那么,医疗史研究又当如何进一步蓬勃发展?这成了作者要着力思考的重要命题。通过多年的深入思索和研究实践,作者认为“‘生命史学’作为新的理念、方法和学术概念,对于当下的医疗史研究来说,不仅具有适切性、可行性,而且对于在总体上推进史学理念的更新,与历史研究特别是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也终将大有助益”(页172)。作者强调,“如若能够举起生命史学的大旗,在生命史学的视野下展开这一研究,那么其意义就不仅仅在于弥补了以往的历史研究忽略疾病、医疗这一人类生活中重要内容的缺憾,而更重要的还在于,作为一项新兴的研究,它将有助于我们更新观念,强化生命意识,……从方法论上推动历史学的发展”(页156)。
关于生命史学对医疗史和历史学的推动意义,作者认为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使历史书写更具“人性”。即通过观照历史上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的具象的人,增强历史书写的情趣和人性,“提振历史论著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二是从历史的维度加强对疾病和医疗意涵的理解,更加全面地认识疾病并不仅仅是医学可以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还是“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作者指出,对疾病与医疗问题的文化意涵的进一步揭示和强调,将会大大有利于推动现代医学人文的兴起,有助于解决现实中所面临的诸如医患关系紧张等医疗难题。三是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加强整个社会的生命与人文关怀。针对当下社会中重视科技而轻忽人文的现状,生命史学指引下的历史研究通过“关注不同时空中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入情入理去梳理和思考健康文化和生命状态的变迁”,将有利于引导和熏陶人们更多地拥有生命关怀意识,推动社会生命和人文关怀的培育(页173~175)。
不难看出,余新忠教授之所以要着力倡导“生命史学”,其中既有国内外史学发展的内在根源,也与当前医疗史研究中出现的“红利”消失直接相关。如果从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化来看,生命史学的提出则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史学研究从社会史到新文化史(或曰“社会文化史”)研究演进的轨迹,是作者多年来在医疗史领域总结和提炼出的前瞻性智慧成果。
二什么是“生命史学”?
关于“生命史学”,目前学界并没有相应的定义。此前虽也有个别学者使用这一概念,但并没有给出深入的解释,[3]特别是在研究取向和旨趣上,也和余新忠教授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追寻生命史》一书中,作者首次对“生命史学”的概念和理念进行了辨析。
在作者看来,生命史学不仅仅可以被视为“ 一种研究领域”,同时更是指“一种意识和研究理念”。“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史学所要探究的是“ 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事务,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页154)。
在明确生命史学的核心取向后,作者又从三个层面对“生命史学”的内涵进行了阐发。一是“历史是由生命书写的”。历史,是由人的生命创造和书写的。因此,探究历史时“关注生命、引入生命意识是理所当然的”。作者提出要“将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的具象的人拉回到历史中”,关注他们的“疾痛体验、困难经历、健康观念和生命状态”,便是由此一理念生发而来。
二是“生命是丰富多彩的、能动的”。作者认为,历史固然有结构、有趋向,但历史的演变不是所谓的结构可以全然决定的。出于对历史决定论的警醒,作者认为正是生命的丰富多彩才促成了历史充满着偶然性和多样性。因此,书写丰富、复杂而生动的历史成为可能并且变得必要。作者进而认为,“生命本身作为一种自在的存在,其价值与意义也自有其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苦难的应对与拯救等日常生活中的主题,对于社会的宏观大势来说,或许无关宏旨,但确是生命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页169)。
三是“健康是生命的追求和保障”。尽管生命史学探究的范畴并不仅仅局限于医疗史,但关注健康并聚焦于健康却显然是医疗史研究的核心内容。[4]因此,生命史学成为医疗史的重要实践领域,更是不言自明。
通过对生命史学的概念和学术旨趣的讨论,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历史上个人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的强调已然上升到了历史哲学的层面。这与既往的对于宏大历史叙事的追求以及在宏大历史叙事下遮蔽或牺牲掉普罗大众的历史的做法是迥然有异的。作者高度认可并着力进行的历史研究,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冰冷的历史,而是散发着生活气息和生命温度的有情感有厚度有“人情味”的历史。作者坚信,“如果能自觉地在生命史学的关照下展开中国医疗史的研究,它的价值和意义终将会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同,它也终将会成为中国主流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页157)。对于生命史学的开展及其对医疗史将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作者予以了相当程度的期待。
三 生命史学研究如何展开?
如何在医疗史领域使生命史学研究成为一种可能?这是余新忠教授在着力思考并探索的另一核心议题。经过多年的思索,作者认为,通过“具象的生命展现历史的意义”是可行的学术方向,同时也是推动医疗史研究深入开展的“未来之路”。而积极借鉴国际学界特别是西方史学的新理念、新方法,显然是打通这条路的“不二法门”。“如若能将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以及全球史等一些新的研究思潮和方法很好地引入当前的中国医疗史学研究,不仅可以极大地推动医疗史研究向前发展,而且对深化当前中国的史学研究亦有重要的意义。”(页148)为了论述相关论断的“适切性”,近年来作者结合微观史、日常生活史和环境史等新兴史学领域进行了系列学理探讨,试图从学术和实践的角度寻求相关理念和方法与医疗史研究的契合与相互促进之处。
以微观史为例,为论述医疗史和微观史的“适切性”,作者专门撰写了理论探讨性文章,通过对微观史学研究理念的深入分析,指出微观史学主要是通过转换研究对象(“目光向下”),并更新学术视野、理念(选择“例外的常态”以小见大)和方法(强调历史叙事是最好的方法)以及尽量扩充并细致解读历史资料来弥补过度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的缺失,从而“将个人角色、具象生命以及历史的多元和复杂放入历史的大厦中”(页1 19)。研究认为,微观史学的研究旨趣与作者提倡的“在具象的生命中呈现历史的意义”的生命史学是相当契合的,“微观史学是要让具体的生命回到历史中来,而这一旨趣与当前医疗史的研究是高度一致的”(页121)。
除进行学理讨论外,作者同时还结合新文化史的研究理念,就如何从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上进行生命史学的研究给出了系列建议。“一是通过广泛搜集、细致解读日记、年谱、笔记、医话和医案等私人性的记录,尽可能系统而细腻地呈现历史上日常生活中之人的医疗行为和模式、疾病体验、身体感、性别观和健康观等情况。二是将从各种文献中搜集出来的相关史料,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来发掘破解史料的背后关乎生命的文化意涵,观察和思考时代社会文化情境中人们的生命状态、体验及其时代特色。”(页171)
最后,作者对如何开展生命史的研究进行了探索尝试,为学界特别是医疗史研究提供了示范。作者对晚清余姓族人法云和尚与温病学家李炳的生命轨迹和人生历程的梳理与探求,就是两则生动的案例。
法云和尚是作者老家浙西昌化的一个余姓族人,生活在晚清时期。由于历史的久远和资料记载的缺失,人们对其生平事迹已了解无多。不过,昌化当地却流传着诸多法云在京城与达官显贵交游的传说。相关传说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大,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昌化民众将信将疑。例如,一位出家在末邑小县昌化的和尚如何跑到了都城北京?又是如何因缘际会在北京立足并与翁同龢等高官建立了联系?法云和尚是否真的做过翁同龢的代笔?如此等等,说来都是一头雾水。在作者的细致爬梳下,类似问题逐一得到解答。通过对地方志、笔记、诗人文集和日记等资料的综合利用,此前晦暗不明的线索逐渐明朗,法云和尚的人生轨迹渐趋清晰。原来法云八岁在昌化的石室寺出家,后来跟随师傅北上,到了石室寺在北京的下院夕照寺,并在日后成为夕照寺的住持。尽管读书不多,但法云却在书法上有着异于常人的造诣。在晚清北京上层社会崇尚书法的风气下,法云和尚得到了贺寿慈、翁同龢与袁昶等达官显贵的赏识,并同他们建立了不同程度的交往联系。相关证据表明,法云和尚做过贺寿慈的代笔,与袁昶交情颇深,但与翁同龢的交情则属一般。至于法云和尚为翁同龢做代笔的传说,则系捕风捉影,并非真实历史。
扬州名医李炳的人生命运和生前身后名,似乎和法云和尚有很大的不同。通过对史料的深入挖掘,作者发现,这位在中国的温病学史留下重要一笔的温病学家,生前生活拮据且并没有多大的声誉。其原因也不是历史文字所记载的李炳“拙于求富,巧于济贫”,而是在医生地位低下的时代,其耿直率真甚至有些“孟浪”的性格和固执己见的行医方式使得他并不为社会上层人士和同辈医家所喜。尽管如此,李炳在死后却得到了文人焦循的作传纪念,并在此后的历史书写以及后世温病学家的不断“建构”下,成为历史记载中的著名温病学家。
通过对史料的细致铺陈,作者不仅还原出了法云和尚和李炳这两位历史上的小人物的生平履历与人生遭际,同时也让人们对当时医家的社会交往、人际关系、活动空间、声誉营求等世情世相的“大历史”有了全面的认知。与此同时,作者通过相关研究所进行的学术讨论也颇具新意。如指出传说并不一定没有真实的依据,而文字记载也不乏失真的成分。只有将历史传说和历史资料两相对照,才能更为有力地逼近历史的真相。相关论断的得出,既水到渠成又颇有见地,令人激赏。相关研究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很好地实现了作者所提倡的“全体史”的研究诉求。
关于法云和尚和李炳的两篇专论,可谓是作者的两篇得意之作。相较而言,关于法云和尚的研究似更胜一筹。该文不仅考索精当,同时文章结构分明,历史分析有如剥茧抽丝,层层递进,特别是笔端流淌着的情感,使文章语言细腻,叙事灵动,读来引人入胜,体现着作者高超的史料解读和文字驾驭能力,更体现出作者对新文化史理念的切实践行。作者的研究不仅在实践层面推进了生命史学的探索,同时也有助于相关学术理念的深入研讨。
四 结语
当然,由于《追寻生命史》一书是一本结集之作,全书在布局结构上不免会有一些缺憾,各个篇章对生命史理念的贯彻也有着程度上的不同。然而,该书对生命史理念的提倡,以及对这一理念的躬身践行,对于“红利”正在日渐消退的医疗史研究来说却具有诸多启示。
首先,如何在生命史的观照下选取“一流”的题目。当前,医疗史研究中“红利”的消退,也与医疗史学界的同仁难以提出颇具历史穿透力的论题有关。为推动医疗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余新忠教授在《追寻生命史》一书中建议从日常生活经验、日常生活体验以及日常生活经验和身体感的意义分析与诠释三个层面加强医疗史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可供深入研讨的题目则包括:生“病”及其应对、求医与治病生活、日常健康维护、病人对疾患感觉的表述、日常环境和生活习俗与身体感的互动、身体感与近代中国“不卫生”意象的形成关系,等等。不得不说,相关题目不仅颇具新意,同时也更具有新文化史的特色。相关问题的研究旨趣直接关乎人们的生命情感,如若在相关论题上做出成就,必然会让读者产生共鸣。总之,生命史学的深入发展需要有分量的优秀史著不断面世,这显然更需要有与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切实将“人”的生命情感引入历史且极具张力的医疗史论题的提出。
其次,如何更好地提升医疗史研究者的学术素养。正如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生命史学属于跨学科的学术概念,需要学者具备较为充分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眼光。因此,在推动生命史学的研究中,不仅需要学者有着国际化的视野,对日常生活史、微观史等国际上新兴的史学理念和方法也要有较为熟悉的掌握,同时更要对欧美医疗史学界的研究现状有着清晰的认知,进而在进行相关题目的研究时能够做到和西方研究不时对话。此外,作为医疗史的研究者更需要具备医学学科知识,至少要具有一定程度的传统中医和现代西医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做到所谓的“内史”和“外史”的融通。显然,要做到上面的任何一点都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这却是每个有志于在生命史学研究上希图有所建树的学人应当去努力的方向。
再次,如何更好强化医疗史研究的历史解释力。在进行史学的研究中避免就事论事,并提炼出为学界所关注的重要命题是非常重要的。现实中对于医疗史的批评,除了有人将其视为“赶时髦”的小众领域外,还有一种更有分量的质疑的声音,那就是医疗史研究的历史解释力往往较为薄弱。换言之,相关医疗史研究尽管很重要,却很难同主流学界所关心的核心问题进行对话。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切实存在的。余新忠教授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因此其在《追寻生命史》一书中提倡“在具象的生命中彰显历史的意义”,但却反对“就事论事”,而是提倡一种“全面史”的研究取向。这种取向在作者展开对法云、李炳等的专题研究中有着精彩尝试。可见,对于生命史学研究来说,能否自觉地参与到主流史学界重要命题的讨论中,或者在研究中提出独到的历史命题并为主流史学界所关注或重视,直接关系着医疗史的深入开展以及生命史学的发展前景。
最后,如何丰富生命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在《追寻生命史》一书中,作者用了相当篇幅论述医疗史研究应多方汲取日常生活史、微观史等的学术理念和方法,相关认识是非常精到的。西方的医疗史研究呈现出的眼光向下、重视病人形象的呈现以及对病人身体感、疾痛感的揭示等新的理念与方法,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向等史学思潮的影响是一致的。在新的史学思潮影响下,西方的医疗史研究也构成了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医疗史研究主要由社会史的发展脉络而来,在学术理念上与西方的医疗史研究并不同拍(确切说是“慢一拍”)。因此,多方借鉴西方史学流派中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是非常可取的。此外,还要看到,当前西方的史学研究又呈现出了从局部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的史学转向,全球史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异军突起就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西方的医疗史研究上,关乎医学知识、药品、医疗技术等的全球史研究成果正在不断涌现。对于西方史学研究呈现出的上述现象,也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如何积极借鉴西方的史学研究理念和现有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生命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同样值得每一个对医疗史有兴趣的学人持续深入思考。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变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项目编号:18ZDA175)、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党史百年”研究专项)“中国共产党治理典型社会问题的历史经验研究”的阶段成果。
马金生,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
注:
[1]余新忠:《追寻生命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2]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该文未收入《追寻生命史》一书。
[3]此处指的是台湾学者李建民先生的《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一书。在该书自序中,李建民先生指称“《生命史学》旨在建构一个完整的古典医学研究体系,同时也发掘真知识”,并没有进一步解释。相关讨论参见余新忠《追寻生命史》“自序”,第4页。
[4]余新忠:《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人民日报》2015年6月3日。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