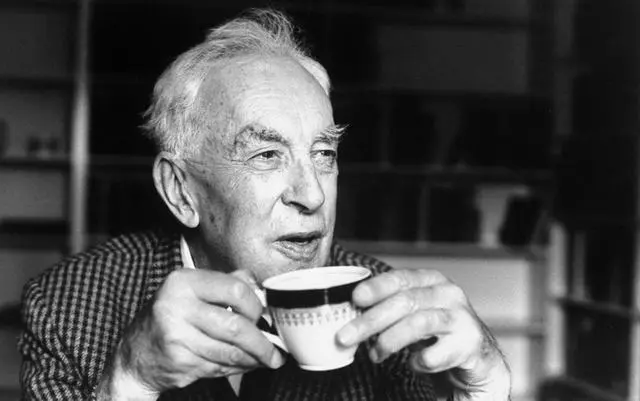
阿诺德.汤因比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研究》浓缩了其对人类文明大半生的学术积累和思考,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1947年,时代杂志评价《历史研究》为英国自马克思《资本论》后最具争议性的历史理论著作。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考察了世界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26种文明的兴衰,试图建立一种统一、普世且带有普适性的理论模型,为人类文明演化寻找终极解释。《历史研究》可谓大一统历史学的最后一次努力,它的流行与后继乏人,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汤因比出生于历史世家,早年在牛津大学和英国雅典学院接受了专业而系统的古典学训练,但从青年时代起,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反专业化”的学人,他的《历史研究》虽篇幅宏大,素材丰富,但归纳多于考证,例子多过数据,从严谨、客观的角度而言,《历史研究》并不是一本标准的历史学术著作,而更像是一本历史哲学,甚至宗教性质的著作,试图从精神的,辩证的角度,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从文明的演化中,寻找人类社会的普遍解释,此外,由于汤因比早年深受基督教和希腊罗马史诗的影响,他在写作过程中似乎也沉浸于希腊英雄式的情怀,试图将自己的精神展现于上帝面前。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和个人成长的角度,追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大一统历史思想的由来。
自十九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和工业体制在西方世界逐渐确立起牢固的统治地位,此时的历史学家们也免不了受到这两种制度的巨大影响。
从社会层面,在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民主主义与拿破仑战争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结合,产生了代表狂热大众热情的国家主义,而工业体制带来的动员和管理能力,又支撑起这种热情,国家意识与好战本性结合,代替了原本所追寻的自由、平等、博爱,正如韦伯所言,此时的学术与政治已经成为了“双螺旋式的结构体”,学术很难从中脱身。一战耗尽了传统王朝政治最后的荣光,也让世界见证了国家主义的恐怖摧毁力,汤因比本人也在一战期间,加入了英国的外事办公室,并参与了巴黎和会的谈判,陷入政治与历史的螺旋之中。在历史研究方面,与民族国家本位的政治架构捆绑在一起的,正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观。当时的历史学家们不少都沉醉于本国古今的辉煌文明,不时还会附会于种族优越论,流露出基于本国立场的宏大叙事也数不胜数。进一步的,他们也逐渐将本国的历史与整个文明世界甚至人类历史混淆在一起,歪曲甚至割裂了不少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进而忽视了文明圈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研究。最终,到了二十世纪早期, 所谓“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塑造并凝聚列强国家主义精神的一个工具。
从学术层面而言,自兰克之后,“叙述主义”便在西方史学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伴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将历史“科学化”的呼声也是风起云涌。但是在“结构--功能”的范式变革过后,兰克学派的解释范式逐渐受到质疑。汤因比学说的产生就是基于前述“国家主义史学”和“叙述主义史学”的弊端逐渐显现之时。他继承了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传统开始,马克思、孔德等19世纪著名思想家参与的西方史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大一统史学”的衣钵,试图为整个历史归纳出普遍的历史解释范式,他的《历史研究》,就是作为他这种思想的汇总而出现的。
针对当时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国家主义史学研究惯例,汤因比强调“把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大至以文明社会为单位的范围”刻意从文明层面划分研究单位。在确定合适的研究单位后,通过筛选分类得到: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这三种文明形态的代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希腊模式。1914年,当汤因比再次阅读修昔底德关于古希腊世界内部的“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论著时,惊人的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早已为修昔底德在他那个世界中经历过了”。尽管年代相去甚远,但修昔底德生活的那个世界,与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一样分崩离析,各邦开始互相残杀,修昔底德隐约预见到这场战争将彻底的改变正处于顶峰期的古希腊文明的走向,而汤因比也发现了“一战”将会带来相同的后果。因此,关于古典希腊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某种内在的共时性,亦或说大多数相同模式或境遇下文明都会经历的共时性,就被这样挖掘出来了,这种共时性,恰恰是汤因比联系过去文明的兴衰与日后文明走向的一个重要桥梁。其中最出名的解释范式莫过于对于各个地区文明的发展进行了解读的“挑战—应战”学说。从根源上而言,这一理论深受柏格森的解释范式的影响,并且结合了新黑格尔主义,部分的斯宾格勒的学说,以及马克思阶级论等一系列思想。
汤因比的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双元革命”后产生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等思想家们所预料的那样,迅速萌发出超越国家的阶级意识,反而在国家机器和大众政治的不断发展、鼓噪之下,激发出无产阶级们的狂热的民族意识,并在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下冲击着自维也纳和会以来的欧洲列强们的“贵族—大资本家双元决策架构”,又在后者的二次煽动下,将全欧洲的青年,扔进1914年的绞肉机里。崩溃的帝国与横陈的千万尸体一同,构成了绞肉机最终的肉末,见证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这正如汤因比所认为的那样:文明的衰弱,既不是偶然因素所能随意决定,也非“天然法则”所决定,文明的衰败只可能是文明内部自身的、人为的原因。此时,西方文明的欧洲部分又一次跌入了雅典与斯巴达式的,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工业化和成熟动员系统的助推下,这次大战的规模和破坏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在四年的相持后,欧洲几乎陷入崩溃边缘,与国家和生灵崩溃同步发生的,还有精神世界的崩溃,于是斯宾格勒怀着对现实的失望,埋头写作《西方的没落》;茨威格怀念于过去沐浴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德语中产文化圈的“昨日的世界”;这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子爵早在对德宣战伊始的感慨:“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这句话是这个文明黑暗岁月最苍凉的一个注脚。
霍布斯鲍姆曾说:“1914年前的几十年……对于欧洲的富人甚至一般中产阶级而言,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结局却是像恩格斯在更早之时预言的那样:“……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这些惨状便是所谓文明衰败的这个内部的、自身的、人为的原因的核心—“文明体内部创造性冲动的丧失或表达阻塞”的结果。民族主义的过度泛滥恰恰是这自身原因之一,其所诱发的“一战”,乃至包括它的延续—“二战”,毁掉的正是西方文明欧洲部分的“创造性冲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不列颠殖民者在印度次大陆留下来的兵站,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是寸草不生了,这和两千年前罗马人在不列颠岛北部留下来的哈德良长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看到这熟悉的场景,汤因比不由对西方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产生担忧。1258年巴格达的陷落,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克,1947年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崩溃,“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一个个曾经伟大的文明,最终都因其自身内部的结构性腐化,而最终瓦解。人们对这些过往文明的衰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通过研究历史的方式去寻找它们能给我们的教训。因此汤因比眼中,历史学家们的任务恰恰就是深入到这些文明里“那些不曾谋面的无名朋友们”的情感中去,这也是为了将来不重蹈他们的命运的一种要求。
“很显然,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以及现实之间的三向关系是具有互动性的”,汤因比格外强调好奇对其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历史学家们作为将人类自发的好奇心转化为行动的那部分人,在现实语境下对过去的一切“事实”进行挖掘、解释,并让人们从中得到对当下以及未来的启示。不过汤因比在总结分析出各模式的“规律”后,对于未来的走向仍然充满不解和忧虑,核能的军事化利用也让他更不确定人类是否会为了“进步”而真的会“杀害大地母亲”。
作为一名在浓厚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汤因比把解决世界病症的办法总结为回到传统的基督教传统以及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当然,他也吸收了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中的类似因素,诸如中国儒家的“世界大同”思想等,“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病的唯一有效方法。”。显然,汤因比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未来发展仍以悲观态度为主,他并不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工业化来解决依然存在的环境恶化、饥荒、生活物质匮乏、贫富差距等问题,而是希望以一种超阶级的博爱和情怀来调和类似的矛盾,并尽可能的用相对平缓的和平方式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以维护和平,保护资源,教育人民,限制生育”。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开头中提到,他极反感那些打着世界史称号下的民族主义历史,因此他力图写出一部不偏不倚的历史,不带有任何民族感情色彩。这一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没有任何人能超然社会之外,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作为一个深受西方传统和古典学熏陶的学者,尽管汤因比考察了世界各地代表性文明的演进过程,但依然无法脱离西方中心,或者说自我本位的视角,他过于强调高级宗教在文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而忽略了不同文明真正的价值观与推动因素。从文本而言,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使了大量的宗教和哲学话语,使得文本比较晦涩难懂,此外,他试图建立的范式也忽略了一些偶然性事件带来的误差以及一些技术层面的因素。但他为努力构建的所谓“新史学”而得出的这个范式,仍有很多可取之处,不失为一个观察研究历史乃至当代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
如今,距离汤因比去世已有数十年了,尽管从哲学的角度审视历史,从人类的高度解释历史的大一统史学在学术圈内的影响力已不如往昔,但这种解释框架,依旧吸引着学术圈外的研读者们。尽力超越自我本位,西方中心的视角,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元,如今似乎成为了不少全球史学者的共识。恐怖主义、新殖民主义、环境恶化、资源短缺这些上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仍旧困扰着全人类,汤因比的解决方案依然无法得到落实,但对于我们今人来说,最重要并不是像几十年前的智者们那样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而是基于对历史的现实性研究或体验,去探寻汤因比思想的现实意义。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本就不是为世界寻求终极的的合理解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很难,也许永远无法达到科学的标准,但它也不必屈从于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科学主义,进而丧失本身的特色。科学是无法整理、传达并塑造多元化的个人见解的,但历史、文学和艺术却可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研究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研究过程本身,阅读和反馈的过程同样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无论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以小见大的微观史学,还是碎片化的个案研究,其中的案例与文本中都可以向阅读者传达时代的状态与气氛,帮助不同的个体构建或深厚,或多元的世界认知。尽管物质世界随时都在改变,但对人类社会总体性,超越性的思索,依然具有永恒的时效,虽然在学术圈内,“大一统历史”的叙事方式和思考框架也许已经进入黄昏,但对于每个读者而言,汤因比与他的历史研究却还是能常读常新,保持不变的精神价值。
正如汤因比所一再感叹的,过去的历史至今依旧不断地重演着,虽然世界一直在变化,但在表象的背后,却时刻隐含着一种共时性。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如今不断被提及,成为中国复兴过程的一个注脚,这个国度的无数年轻人们如今又一次沉浸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热诚之中,迷失于消费主义和泛娱乐社会的纸醉金迷之中。尽管全球化的元素,新技术的变革在身边不断的闪现,但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走入这个时代,而依旧迷恋于狭隘的现实生活圈中,丧失了对广阔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好奇,以及对人类文明,乃至整个生物圈的关切。小中并非无法见大,微观史学研究同样可以传递世界性的历史状态,但随着学科分类和研究的精深,如今我们愈发执着于细微或零散的修补中,每个专业的常识,愈发难以被外人所理解,当学术圈与普罗大众无法进行流畅对话时,学术本身的意义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在这个时代,我们依旧需要像汤因比这般,出生于学术圈,但致力于从另一个角度,向学术圈和大众传递另类观点的独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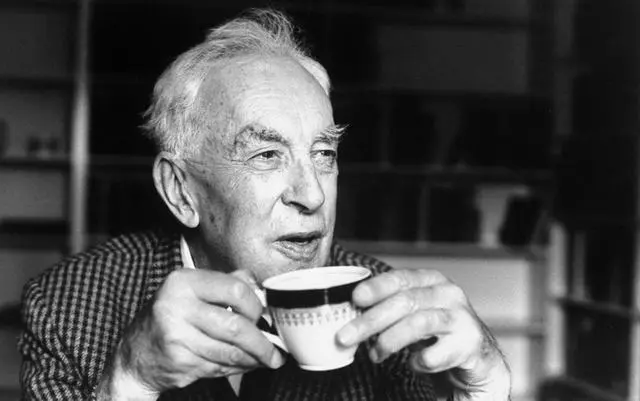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