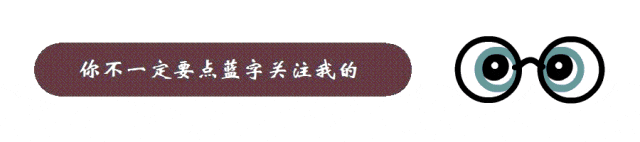
“我们相信,电影史研究已经到了应该审视过去提出的电影史问题以及审视过去赖以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的时候了。”[1]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影研究者罗伯特· C·艾伦和道格拉斯·戈梅里提出了一种从实在论哲学层面,对电影史研究方法的考察。区别于传统的电影编年史书写,他们的研究对象并非电影本身,而是历史角度下的电影研究,这也使得他们的研究更加倾向于对电影史学家采用的方法、哲学取向以及得出的结论提出大胆质疑,并且对现有电影史中一直被看作是“真理”的电影知识进行重新反思。本文对道格拉斯等人提出电影史研究方法的起点——“作为历史的电影史”和“作为电影史理论的实在论”两个命题进行深入分析,对其采用的历史观念及哲学取向进行阐释,考察道格拉斯等人所提供的电影史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电影知识生成与更新的路径所产生的启示性意义。
01
从经验事实走向历史事实
传统电影史研究倾向来源于一种作为艺术批评、文学批评、新闻报道或口述史料的产物,而在对电影史的接受和应用过程中,引发了一个问题:电影史的接受者(或消费者)惯于将这些历史材料作为有关电影的事实或真理?换言之,电影是否构成了检验电影史的唯一来源?亦或是,电影只是电影史研究中的一个元素?就一般历史研究而言,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发展历经从叙述史学向道德史学、资治史学的阶段转变。进入近现代后,历史学研究转向基于科学主义的客观性研究,也被称为科学史学研究阶段[2]。然而,历史研究的阶段划分,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根据这一阶段历史研究的目的进行的。这也即是说,即便是强调客观性的科学史学研究,依然携带着特定的视阈、条件、方法等。这便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历史研究视为一种知识叙述的可能,那么一方面,所谓历史事实的唯一合法性将受到检验,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H.Carr)所言:“并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过去的事实也并没有全部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来处理。”[3]另一方面,又如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所指出的,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就生发了一条通过真理的指示性陈述和正义的规范性追求统合而成的知识建构路径,并将理性确立为人的主体性确立根本,由此形成了利奥塔所谓的,强调一致性、普遍性、统一性的“宏大叙事”。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1892-1982)
对于“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卡尔阐释了事实与历史事实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卡尔看来,历史观念的发展与事实(fact)这一概念相伴相生。19世纪近现代西方哲学与思潮,在科学的成就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与经济的提升中,明显展现出了对“事实”的现实崇尚。19世纪30年代,西方哲学家将科学知识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科学知识源自观察的经验事实基础上,从而,实证主义哲学思想的确立排斥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中,基于抽象理性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把握方式,而是在哲学与科学关系的交融中,将哲学的任务确立为一种对现象的归纳、概括的研究。由此,这一时期的历史观遵循了一种“如实地说明历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原则。
卡尔指出,这种将确定事实作为首要前提,从中得出结论的历史观,源于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即一种预先假定主客体完全分离的知识理论。并且,在这种经验主义认识论的统摄下,事实,即我们认识的客体,蕴含着外部世界知识的绝对性和统一性。而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即便处在不断探寻这种绝对统一的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却始终与客体的外部世界对立着。而在卡尔看来,历史事实并非由这一层面上的事实,作为一种原始的历史材料构成。甚至,这些基本事实本身的特性并不能够作为历史事实构成的依据和基础,历史事实实际上依据的是历史学家“先验的”(a priori)决定[4]。无论是卡尔还是道格拉斯等人,对于历史研究的态度,都始终强调的是历史学家作为研究主体对于知识建构的主体性作用,其根源在于康德将人确立为认识论的主体地位,强调知识的形成来源于人的主体认知能力。由此,形而上学传统中,主体被动接受客体的认识论,以及知识的经验原则的唯一性被取消,由此确立了西方哲学从主体出发、以人作为轴心的认识主体的认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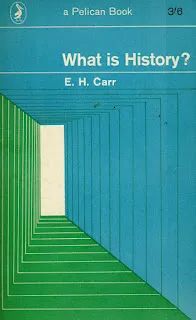
《历史是什么?》爱德华·卡尔,1961
如果将电影史作为一种历史研究,那么根据卡尔有关历史事实的观点,衍伸出来的结论即是,电影史中的历史事实同样蕴含了电影史学家及其知识理论的主体性,却经常被遮蔽在电影史文本和电影史料背后。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一方面,尽管电影史的研究在材料、手段等方面伴随时代和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但对于电影史及其知识建构方式这一自身问题的研究却鲜少出现;另一方面,电影史在通史书写的范式下,亟需有关电影史观念的变革,而变革的依据既源于电影本身观念的变革,也来源于其他学科的参与和介入,以及电影史研究对自身发展脉络和历史变化的反躬自省。
02
将电影视为一种开放的系统
实际上,无论基于怎样的研究视阈、方法和路径,电影史研究必然蕴含着电影的本体观念,当人们将电影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那么首先,他们的研究就已然建立在他们对于电影构成的认知上。基于实在论的观点,将电影作为一种开放系统,那么除了电影文本自身之外,与电影相关的一切构成和影响因素都应该被纳入电影史的研究范畴中。
如果说,对于电影史研究中的某一现象或者事件的研究,是以其生成(因果)机制为最终目的的话,那么其中,就蕴含着现象/事件之间或之外所存在的因果关系。自休谟以来的实证主义传统将现象之间的“经常联结”和“规律性序列”等关系,作为判断现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前提。而批判实在论者罗伊·巴斯克(Roy Bhaskar)对这样几组概念加以区分。首先,在巴斯克看来,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casual regularity)并不等同于它们的生成机制(generative mechanisms)。生成机制是事物的行动方式,并由其构成“因果规律”(casual law)的基础。因此,在科学活动中,可以对事件的因果联系进行描述,却很难在开放系统中,对事件的生成机制描述,因为机制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科学活动就是在一种人为封闭的系统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因果规律及其描述的可能性。基于批判实在论的思想立场,巴斯克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社会实在,并进行了三个层次的划分:经验层次、实际层次和真实层次。其中,巴斯克认为,“生成机制”就存在于真实层次层面,我们无法通过经验层次获得对于它的直观感受,却不能够否认机制的真实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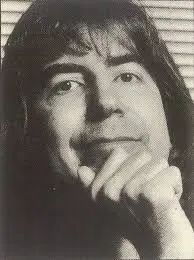
英国哲学家罗伊·巴斯克(1944-2014)
与此同时,巴斯克对于开放社会系统中的“突现”(emergence)特征进行了解释:“像活的有机体这样复杂的系统,似乎具有这样一些特质,它们不能被全部归结为它的个别组成部分的特性,或不能由后者得到预见。这些性质看上去不是那种系统的组成部分的总和,而是由它们的结合而产生的某种新的不同的东西。”[5]突现特征显示出了以社会实在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区别于以自然结构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的明显特征。在以人类行动及其意识活动构成集合的社会实在中,突现正是社会实在依赖于处于动态变化的人类及其意识的趋势和力量的、最为显著的特征。
如果我们将电影视为一种社会实在,那么在经验层次,我们能够切实感受到对电影的直接经验感知;在实际层次,我们能够观察到某种电影现象及其状态;而在真实层次,则指向于引发电影现象的生成机制,并且处于一个开放、复杂的社会实在系统中。因此,基于实在论的电影史研究,需要我们整合经验、实际和真实三个层次的知识,在真实层次的本体层面,在不断变化的开放系统中,挖掘电影现象背后的生成机制。尽管实在论关注并强调生成机制(因果分析)对于理解和阐释历史事件的重要作用,但并非呼吁使用某一种方法对待历史和社会实在。巴斯克认为,突现(emergence)现象是构成社会实在区别于自然现实的本质属性,这其中便关乎人的存在。事实上,无论是从艺术的生产主体还是阐释主体的角度,还是从艺术表达的对象和内容来看,无疑都与人相关。而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一种由人的集体创作的生产活动,以及关乎人的思想和意义表达的语言形态,不管我们如何定义电影,但它始终都与人以及人如何看待、认识、理解世界的方式脱离不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实在论对于电影史研究而言,并不是一套固定的范式或单一路径。生成机制对于电影史的研究者而言,不仅提供了一种从电影现象出发,关注引发现象或事件产生的各个维度的因果效应;更警示研究者,以一种反向的思维逻辑,通过新出现的现象或事件,检验原有生成机制中被忽视和缺失的因素。这也符合实在论在认识论层面的观点,对于社会实在的认识,即社会实在是在真实层次客观存在的,我们或许无法真正触及它的真实存在,却可以不断通过更新我们的认识和知识去接近它。

《水浇园丁》海报,1895
电影史研究者对于某种新出现的电影现象,往往具备敏锐的关注,但总在抽象层面的哲学论题阐述的忽视,即:“电影史的读者们(既是第一次阅读电影史)不应贸然认为这一严肃工作的本质是毫无疑义的,虽然电影史学家有时也持着这种看法。”[6]使得长期遵循着某种生成机制的阐释原则,或基于固定背景知识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研究路径。根据波普尔的解释,背景知识是:“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地并且针对讨论这个特定问题而构成我称之背景知识的东西。”[7]而面对固有的背景知识传统,要想推动知识的增长和发展,在波普尔看来,需要反例进行不断地检验:“如果一种理论经受了许多这样的检验,那么由于己把检验结果合并到背景知识中去,过一段时期以后可能就再也不会有(从我们的新的背景知识来看)可高度概然地预期出现反例的余地了。”[8]
03
历史语境中的电影文本及其“文本变体”
作为电影史研究的一手研究材料来源,影片作为一种文本(text)“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它们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被生产和消费。”[9]英国历史学家艾伦·穆斯洛(Alun Munslow)曾指出,现代历史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条路径:重构论、建构论以及解构论。其中,重构论认为,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发现和揭示真理;建构论认为,历史研究需要借助多个学科的理论,以此整合诸多细微的事实,从而得出有关结构和趋势的把握和结论;依托于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解构论则认为,历史研究是一种“思想实验”和“虚构性想象”,需要在颠覆统一性的基础上,从话语、权力、知识生产等层面,采用多维的、跨学科的研究路径,由此对建构论奠定形成的理论性进行解构。上述三种历史研究路径,在某种意义上,都面临着历史文本与阐释方式的问题。
基于阐释主义哲学视阈,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曾提出“历史语境主义”(Historical Contextualism),将语言哲学引入历史研究,对传统的观念史研究提出批判,并指出了传统历史研究中“文本中心主义”的弊端。文本中心主义主导下的观念史在斯金纳看来,构成了一种“学说神话”(mythology of doctrine),即通过文本寻找出思想家在所有无可争议的主题上的学说体系的无意识的历史研究范式。同时,这也引发了文本中心主义带来的最大的危险——“时代误置”(anachronism)。作为历史研究方法的语境主义,强调通过历史语境揭示思想家的意图,即将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中把握其意图,并包含了三个维度的问题:文本关注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文本作者展开论辩时诉诸的思想资源;文本对当时的政治做了何种介入[9]。

“剑桥学派”历史哲学家昆廷·斯金纳(1940-)
在上述理论的观照下,将电影视为一种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文本构成层面,首先,电影史学家将影片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时,需要考察影片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并且,在阅读电影史时,不仅需要对影片所处的特定历史语境进行考察,同时需要对电影史学家阐释影片的特定历史语境进行梳理。由此,才构成了完整的文本“意图”诠释与解读。一部影片的阐释,不仅包含着影片所处历史语境中创作者、观众、社会的意图,亦包含了阐释者基于特定历史语境的意图,其构成是复杂的,具有流动性的意涵和具体的历史性,关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社会心态的交错关系,需要充分地考察文本、理论、概念及其意义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动态变化。
在胶片电影时代,受技术和经济条件限制所致,胶片电影的贮藏、保存、放映都不具有稳定的安全性和长时效性,因此对电影历史研究者研究早期电影提出的最直接的问题即是:看到的电影是什么?真的是这部电影吗?还是这部电影的版本之一?通过以文本化为主导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将电影视作一种蕴藏含义的文本并进行分析,则面临着对于“什么是含义,它们从哪里来,它们是怎样巧妙地在客观实物和社会活动上留下印记的?”[10]等问题的回答,同时也面对着“文本化代表着对含义的预先安排,结果造成对冲突和变化的抑制。”[11]
然而,“文本变体”这一电影史研究中的现象,并不只存在于胶片电影时代。尽管数字时代中,技术的发展为电影的保存提供了更具便捷性、稳定性以及应用性的数字存储方式。然而,“文本变体”依然受到电影审查、新型媒介传播等各种多元化、更具不确定性的因素影响,并不断参与着人们有关定义电影的方式。换言之,人们对于电影的观念,以及电影的社会功能,在数字技术时代,更加难以仅凭电影文本自身加以描述。从诞生之初,电影就超越了自身文本,作为一种复杂的媒介、社会角色,在文本和泛文本的互为型塑与建构过程中,不断挖掘自身的意义所在,有关电影历史的研究也在此过程中,拓展、丰富着研究对象的范畴和研究路径。

《天堂电影院》,1988
无论是电影《天堂电影院》(Nuovo cinema Paradiso,1988)中,放映员艾佛特留给多多的礼物,正是被检查员禁止放映的吻戏组接镜头;还是电影《一秒钟》(2020)中,为了看到女儿在电影映前新闻中的画面,张九声不惜冒着风险越狱找到那卷携带着女儿影像的《英雄儿女》胶片。这些情节都向人们展示了,电影超越自身文本的力量。在“文本变体”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其他版本、更多或更少镜头的文本,更关乎被用以作为“历史证据”的文本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社会运作秩序,而那些没有被看到的文本,又在哪些方面,与当时的社会规则形成了怎样的冲突。电影的审查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电影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功能的存在的最佳确证。无论是电影文本本身,还是电影的整体系统,无疑以各种方式参与社会的建构之中,影响着无论是作为个体的还是集体的人的社会生活。其中,伦理是电影审查中主导因素之一,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所具有的伦理功能,参与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行为、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并关乎着社会大众心态和社会道德伦理秩序。但电影的伦理功能并非仅就文本意义而言的,而是对于整个电影系统而言的。因此,“我们不是要设计一个价值体系,将电影分成伦理的和非伦理的,而是把伦理作为电影活动的语境......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涉及欲望和责任的关系,我们就置身于伦理的场域。”[12]
结语
在实在论哲学层面,道格拉斯等人提供的电影史研究方法,可以被视为一种关于电影知识及其系统建构的更新路径。对于艺术知识系统的建构而言,由于艺术知识系统中长期围绕“艺术是否具有客观性”这一问题而产生一种基于主观主义内部存在的矛盾,通过对科学阐述和艺术知识中的客观性加以重新界定,对艺术知识的客观性的追求,并非是打造一台对艺术作品产生判断的“超级计算机”,而是建立一套具有多样性的研究标准体系,艺术知识系统的建立标准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研究主体、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时代不断动态发展的,尽管客观性在其中似乎难以把握,但缺少了标准的艺术知识系统一定失去其价值与意义,确立其客观性的意义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充满着不断地批判,以及人们能够从这一过程中获得知识的增长。也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此等历史知识,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固不能脱离以往之史料,惟当在旧存之史料中耐心检觅。”[14]
参考文献
[1][6][10] [美]罗伯特.C.艾伦 道格拉斯·戈梅里著.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最新修订版).李迅 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2] 包伟民:如何研究历史.皮庆生编:人大课堂——名家的16堂历史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3] [4]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5]吴芳:实证主义的视角: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兼论罗伊·巴斯克的批判实在论思想,《经济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12期。
[7][8]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 等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9] 林默彪:中国现代观念史研究视域与方法探略,《东南学术》2019年第6期。
[11] Christopher Herbert,文化与反常:十九世纪的人类学思想,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12] [加]朗·博内特著:《视觉文化——图像、媒介与想象力》,赵毅 等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13] [英]丽莎·唐宁,莉比·萨克斯顿著:《电影与伦理:被取消的冲突》,刘宇清 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14]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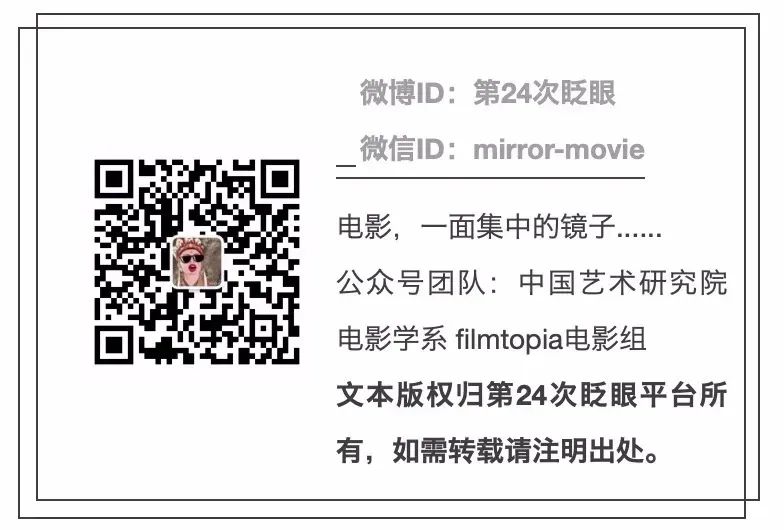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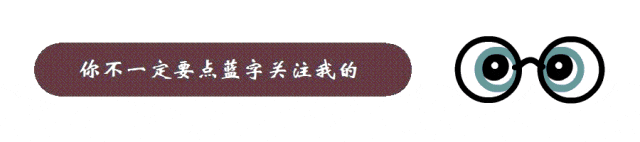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