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已觅不到昨日镜花水月般的幻象。就如同旧时一件夜行的锦衣,初看只道是内敛的奢华,定然匿藏着不为人知的绮丽,无意中掀开那薄如蝉翼的纱,才大失所望。原来,昔日所有的华美都消融在这扑朔迷离的夜色中,再不见半点痕迹。
许多人艰难地拨开尘封的岁月,试图挽住那并未远去的过往,却发觉这根本就是一场欲盖弥彰的闹剧。于是,只能黯然神伤着寂寞,醉生梦死着记忆,或者,索性只是等待着,一切繁华湮灭时,用那首长恨的离歌当哭。
不知王珠是不是该庆幸,她没有对那一段盛世年华的清晰记忆,所以,长安深夜的月下,她轻声拨动琴弦,流淌出的那首《霓裳羽衣曲》才没有人走茶凉的荒芜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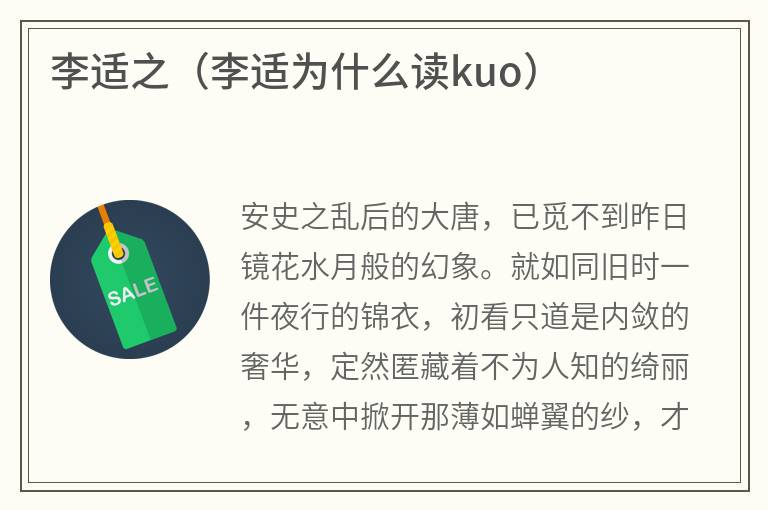
李适之(李适为什么读kuo)
然而,不悲戚不代表不感伤,正是因为没有亲临其境,才更加不由分说地嗔怪。如果说女人,注定要在男权世界里俯首称臣,那么,宫闱深处的她们,是否自沦陷的那日起,就注定了一生的无可救赎?
怕是除了王珠,少有人从这首似梦如幻的曲子中,听出怜悯的意味。一笑倾城百媚生,富丽堂皇的大殿上,披挂着五彩羽衣,在觥筹交错中,在君王迷离醉眼的注视下,在馨、笛、箜篌“跳珠撼玉”般的乐声里,旋转再旋转,一直到自以为是的地老天荒。
可是,真的到了那一天,有人却忘了华清宫长生殿夜半无人时的誓言,本应紧握着的两只手,倏然松开。马嵬坡前的那一坏净土,掩得了红颜薄命,却掩不了时过境迁的离殇。
王珠将这种遗恨,归于君王必然的无情,自来被数不清的人捧着,簇拥着,哪里肯真地舍下千金之躯,放下千秋万代的伟业,挡在她的前面。那比翼鸟、连理枝的承诺本来就是盛世逢场作戏的笑闹。
莫说这些对于王珠,只是台上一出剧,一段不关己的旧事,曾经的确是,但当她遇见了太子李适,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天宝十四年那场动乱发生时,李适刚满十四岁。潼关陷落,长安失守,他跟随曾祖父唐玄宗仓皇逃往蜀地避难,历经了一段与曾经天壤之别的日子。那正值一个少年最敏感的年纪,他像是比那些社稷之臣更加担忧李氏家族看上去摇摇欲坠的江山。好在不久,祖父李亨便于灵武继位,父亲李豫被任命为“兵马大元帅”,率军抵御叛军,收复了长安、洛阳两京。
能同父亲一样,身披炫目的盔甲,骑在高头大马上指挥千军,是李适少年时代最大的梦想。终于,六年后李豫继位,给了李适同样的封号,命他铲除叛军最后的余孽。
那已经是一群没有了气焰,再也嚣张不起来的人了,李适不免觉得有些遗憾,他终于盼到一个机会让少时的梦想实现得淋漓尽致,为曾经的颠沛流离复仇,可是,对手却这么不堪一击。
那场动乱终于被抚平后,李豫论功行赏,拜了李适为尚书令,还赐予免死铁券。然而,李适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在他心底,一直有一处难以言说的伤痛。
那关于他的母亲,一个名叫沈珍珠的宫女。初时逃离长安,唐玄宗哪里顾得上皇富那么多人,能保住嫡亲血脉便是万幸,所以,沈珍珠同许多宫嫔一样,未及逃走,被叛军俘获,从西京长安劫到东都洛阳。后来,李豫收复失地,终于在掖庭将她救出,安置在了洛阳宫中。
可是,再后来发生的事,却让李适永远都不能原谅父亲。李豫一直不曾给沈珍珠一个名分,也没有将她迎回长安,乾元二年,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沈珍珠自此失踪。
如今,已经成为太子的李适已经有十年没有见到母亲了,他知道父亲也在遗恨曾经,屡次派人到各处找寻,不但一无所获,反倒引来了许多为了荣华富贵甘愿冒险的人。
那一天,就有一名崇善寺女尼自称沈珍珠,因流落乱世走投无路而皈依佛门。李适听了好一阵雀跃,自东宫飞奔而出,未到半路,就听说此人被盘问时,不小心露了馅,已承认是冒名顶替,原本只是太子所居少阳院里的乳母。
李适失望不已,转身回去后,更觉讪讪无趣,遂命人更衣出宫。长安城里,他有不少世家公子的熟识,但大多只是相携去勾栏酒肆的玩伴,只可举杯笑闹,不能倾诉心事。唯一可以称得上知己的,是长安一个大户家的公子,叫王承升。
王家是世代官宦,书香门第,王承升虽生性倜傥不拘小节,却颇通诗曲书画,尤其好琴。这一点上,两人最有默契,李适继承曾祖遗风,精通音律,也是百般乐器中,独爱古琴。琴对于他,自来不是玩物,而是可以“观风教,摄心魄,辨喜怒,悦情思,静神虑,壮胆勇,绝尘俗,格鬼神”的良师善友。
因琴相知,继而一拍即合,王承升就成了李适真正的挚友。所以,这天李适心情愁郁,他想都没想便去了王家。
雨后乍晴的天气在炎灼夏日里最显可贵,不说池上芙蕖那晶莹的垂露,花间飞燕那细语的呢喃,单是轻风中一股夹着新鲜泥土、草上落叶的香,就已能让人微醺了。但是,在王承升看来,这样的醉显然不够,如果不饮上几杯酴醺,简直就是对眼前美景的辜负。
看来,李适来得正是时候。
小酌的案几就放在后园竹林的外面,不等坐下,李适就拿起一杯酒一饮而尽。旁边的王承升什么也不问,只拿起酒壶,又为他斟了满满一杯。这就是老朋友的会面,不用问究竟,因为一切都在不言中。
三杯酴醺下肚,胸中的闷已消逝了多半,李适终于能够腾闲出心情细赏这雨后美景。就在他不经意间望向竹林深处时,忽听里面传出了绵美悠长的琴声。
只听一声,李适便知,这是相传为孔子所做的《幽兰操》。昔日孔子周游列国,却得不到诸侯的赏识,归鲁途中,见一簇与杂草为伍的幽兰,遂生怀才不遇的感慨,写下此曲。这首曲子并无强烈复杂的音律,但那如空谷幽兰般静谧悠扬的意境却不是谁都能奏得出来的。
李适看不见幽篁深处抚琴的人,但他似乎能窥视到那个人的心。如若没有高洁空灵的性情,如何能将这首曲子诠释得这样淋漓尽致?于是,几杯酒平静下来的心绪,瞬时又被一首曲子搅乱了。
王承升好像又一次看透了他的心思,听了几声曲子,顺口说道,“是愚妹”。
李适什么问题也没有问他,但他知道,这是李适最想要知道的。其实,对于王承升的妹妹王珠,李适早有耳闻,寻常往来的世家公子早就把她的美貌与才情渲染过多遍,只是自持生于帝王之家,什么样的美色都见过,也就未曾放在心上。
今日,未见其面先闻其声已是这样令人心动,始知往日的错实在是不可饶恕。
李适多么想借着酒劲冲进竹林,去看看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佳人,可最终还是忍住了。到底是当朝太子,他不想在王承升面前过于失态。
一曲奏完,天又微微下起了细雨,琴声就再也没有响起。李适只得起身告辞,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失望。
这次小聚,留给李适些许遗憾,却给了王承升不曾预想到的惊喜。凭他对李适的了解,早知他已对抚琴的人动了心。妹妹王珠的美不说是天下无双,但到底是可以拿出手,与那些宫中女子争奇斗艳一番。“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王承升不是一个醉心功利的人,却也还是期待那不费吹灰之力的一步登天。
明明是只差一点便可水到渠成,但就是这一点,令王承升有些犯难。妹妹的脾性他知道,向来清高,哪里会任人摆布,让她去奉承李适,比登天还要难。
自那次离开王家,李适便有了放不下的心事,他耳边总是反反复复萦绕着竹林琴声,眼前闪现的却是一团模糊的佳人的脸。于是,他比素日更频繁地去王家,借故下棋,喝酒,却没有哪一次能真正安下心来,因为他再也没有听到那琴声,更别说见到人了。
又一次去王家,他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对王承升坦白。他们随意踱步到了竹林外,刚要开口,李适却惊喜地发现远处立着一个白衣女子,虽眉眼看不真切,但那袅娜的身姿,不是王珠还能是谁?
只是女子看有生人过来,一转身去了林子深处,李适下意识追了几步,却不见了她的身影。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好踌躇的,他回身请求王承升:能否一睹令妹芳容?
王承升去妹妹的绣房时,脚步飞快,心下的激动已经难以抑制。太子开了口,也算半个圣旨,不管妹妹愿不愿意,须得出来一见了。
王承升的朋友,王珠倒也见过不少,一同听琴弹曲、切磋棋艺,也是常有的。可李适是太子,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王珠平生最恶附庸,他人争相攀附的事,她却唯恐避之不及。她一点都看不起哥哥那急切的样子,恨道,太子有什么了不起?难保不是一个纨绔之徒。就算是真有什么了不起,和我又有何相干!
可怜李适,并非纨绔之徒,只因沾了皇家名姓,就被她拒之千里。
不过王珠总还是善解人意的,她看着一旁心急如焚的哥哥,早就软下心来。她知道,太子是哥哥的好友,如果执意不见,恐怕是太让他为难了。
平日见客,她还略梳洗装扮一番,此次见最尊贵的人,她反而素面朝天,家常的旧衣也不曾换下,就径直出了门。王承升虽无奈,却也只能由着她去。
唐朝女子衣饰的典雅华美,少有朝代能及。王珠身旁的两个侍女,都是一身五彩罗纱的阔袖衫襦,眉间贴着花钿,两颊晕着斜红。周身虽未有多少首饰,但颈上璎珞和发间金步摇总还是少不了的。相形之下,王珠的装扮太素淡,一袭白裙上只是点缀着几朵梅花,那发髻也不似大户小姐繁缛的式样,只挽了简单的盘亘髻,插一支玉簪了事。全身上下,除了臂上的一串金丝跳脱,再找不出半点金银饰物。
可是,她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让人能弃去万紫千红只盯了她一个看,并且见后忘俗。
当初听曲时,只道曲已是绝好,见了抚琴之人,才知人才是最好。李适也是少年英雄,文武全才,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回想这许多年,还没有什么样的场合能让他像此时一样,呆立着说不出一句话。
待他回过神来,眼前已经不见了王珠的影子。他下意识地正要惊呼一声,忽然想起方才她匆匆行礼告退,他好似是点头应允了的,又懊悔不已。一旁的王承升在忙不迭地替妹妹的怠慢道歉,可是,李适又怎么会怪她呢?
他真的要怪,只能怪自己生在帝王之家,如果他只是门户相对的李家公子,凭他的风流神采,凭他对王珠的心有灵犀,就算不能一见钟情,也定有发展的无限可能。现在可好,人也见了,话也说了,却寻不到半点可以渲染的成分。
李适走后,王承升将妹妹狠狠数落了一番,太子殿下诚心示好,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多少人盼都盼不来,怎么能当儿戏一般随意丢了去?
王珠也不与他争执,只冷笑道,有人在乎的,怕只是做不了杨国忠吧!
这句话说得太犀利,可又不得不承认是实情。昔日杨玉环兄妹的结局人人知晓,却还是人人都羡慕。王承升被妹妹噎得无话可说,甩手离去。
一连许久,李适都再也不曾到王府了,并非他是对王珠断了念想,而是相思已经成疾。
食不甘味、寝不安眠,无论做什么事,去往何处,眼前出现的总是王珠的影子,李适也觉得荒唐,可人心又怎么能掌控。不多几日,他就精神倦怠,形容憔悴了。
早有后宫妃嫔将此事告知了李豫,惹得他好一阵子笑。他不笑太子痴情,只笑如此简单的事,怎么还需费下这番心力。一国之君看问题,当然不同于常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个寻常人家的小姐还不是呼之即来。于是,李豫命人召了宗室李晟夫妇,去王家传谕,欲纳王珠为太子嫔妃。他用了自认为最简便的方式,替李适扫除困难。
可是李豫终究没有想到,还有王珠这样不同寻常的人,皇宫中的荣华富贵,她视若粪土。那是王珠第一次当着外人的面失态大哭,她边哭边乞求父母莫要将她送去宫里,到那一群女人争来夺去,见不得人的地方,能有什么好下场!
因前些日子与妹妹闹了不和,王承升一直不曾上前言语。但他看到妹妹当着宫中来人的面,越说越大胆,便赶忙将她拉去了里屋。他压低了的声音斥责她:可知抗旨不遵,忤逆圣意是什么后果?便是不为自己想,也不能不为王家着想!
这句话也算戳到了王珠的软肋,她渐渐平复下了情绪,但却依然不肯让步。她央求哥哥,替她想个缓兵之计,进宫的事拖些年月再说。
既然到了这个地步,王承升还能怎么办,他知道妹妹若是被逼急了,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得出来。于是,他只得先将李晟夫妇送走,而后又寻了个日子将李适约出,婉言推说妹妹年纪尚小,不懂礼节,害怕到了东宫有什么失礼的地方,连累家人。
深陷情感泥潭中的人,就是比素日糊涂,李适竟然没听出这是托词。他急急地问,王珠究竟想要何时进宫?王承升想了想,只得说,等殿下继承皇位,再进宫也不迟。
这话说得实在是有些无礼,可李适非但没有怪罪,反而一口答应下来。在他看来,王珠这样世间少有的女子便是要什么也不过分,况且,等到他真执掌江山的时候迎娶她,不是更加风光?
王珠当然不会在乎他是太子还是皇帝,她搬来时间做救兵,就是想要给他一时的激情泼上冷水。她深知,世间少有什么能敌得过看似轻盈却无坚不摧的时光,许多山盟海誓的爱情都不能,何况他们这样的一面之缘。等有朝一日,她的面容在他脑中渐渐消逝不见时,这段旧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连日来的纷乱已让她多时不曾抚琴了,如今一切暂时平静下来,她的手按在弦上,却不知该奏哪首曲子。《平沙落雁》太闲适,《胡笳鸣》又过于悲怨,只好作罢。
于是,她起身去窗边,嗅那竹林的香气。她喜欢看月光下竹叶斑驳的影子,不论多么黯淡的月光,折射在竹林里,都能晕染开来。白日有众多的花花草草,五彩缤纷的显不出竹的好,到了夜晚,才看得真切。
她喜欢竹就如同她喜欢梅,都是最娴静的,不能被人簇拥,便孤芳自赏。她低头看了眼衣襟上绣的梅,不知怎地就想到了江采萍。
江采萍是唐玄宗的梅妃,也是个不染尘埃、风雅清高的人,被杨玉环那株洛阳牡丹夺取颜色前,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王珠爱她的才,却总是感伤她的身世。这样一个孤傲的人,不在青山秀水间吟诗作画,却为了一个寡情的君王,争也争了,夺也夺了,最后还落得一个“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的下场,真是不值当。
无论如何,她也不能做另一个梅妃,至多一輩子不嫁,独守在青灯古佛旁,也好过寡廉鲜耻地去糟蹋自由和尊严。
可是,她不知道,自被李适喜欢上那一刻起,她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一个日后要进宫为妃的人,还有谁敢接近?就算有人真的敢冒风险,王承升也是不能允许的。
素日同游同乐的朋友,王承升早已暗中剔选了一番,与那些尚未娶妻,又风流倜傥的公子们邀约,常常借口去别处,再不同以前一样,随意请到家中。妹妹进宫还不知要何时,夜长梦多怕是难免,他只能尽力将这种可能降到最小。
所以,但凡碰见他在家中与人小酌、对弈,那人要么是已娶妻生子,要么就是性情与王珠南辕北辙,总之,须得王承升先认定,妹妹不会瞧得上。
元士会就是王承升的一个可以请至家中的朋友,他虽性情逸朗,文采飞扬,却早已娶钟府小姐为妻。王承升知他最重情重义,与钟小姐举案齐眉,琴瑟和谐,定不会生二心。
所以,那日与妹妹对弈,中途遇事离开,王承升才敢让来家拜访的元士会顶替。
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拿了黑白棋子在格子间上杀伐,也倒是有趣。许多人下棋,实应叫“玩棋”,哪里是真正的你追我赶,不过是偷寻一处闲情。素日里打点家事,往来寒暄,不知有多少烦,若还在外谋个一官半职,更是如履薄冰,漫长一生提溜着的心,什么时候敢放下过片刻?也就是在这黑白小天地里,可以长吁一口气,真正将输赢看淡。人生路上走错一步,有时是一错到底,终生不可悔改,而棋错一着,最坏不过片刻之后再卷土重来。
琴、棋、书、画常放在一处说,是因为它们的确是殊途同归,似王珠这般绝顶聪明的人,当然是一通十,十通百,全然不在话下。所以,她并未将元士会放在眼里。
大多个中强手与柔弱的女子对弈,总会礼让三分,为赢怜香惜玉之名。可元士会落棋,却招招逼人。那盘棋,足足下了一个时辰,最后,元士会赢了半子。
王珠似是不相信的样子,还在对着棋盘蹙眉苦想着,不知哥哥王承升早已归来,站在一旁对元士会玩笑似地怪道:如何下手这般狠,让愚妹一子又能如何?
元士会也有他的道理,“对俗人来说,博弈是游戏,但令妹是高手,故同她对决,不敢懈怠,若不尽全力,岂非是对她的亵渎”。
一番话,说得王承升哑口无言,也惹得王珠对他留心起来。只是,越留心她怕是会越感叹,才子佳人的相逢,却不占天时地利的半点可能。莫说她已经是太子选中的人,就算她尚待字闺中,那已有妻室的元士会也不会主动逾矩。
对待一盘棋都如此认真的人,又怎么会朝三暮四,喜新厌旧?
再见元士会时,他还是彬彬有礼,进退有度,从那眉目清朗的脸上看不出心底的一丝波澜。这恐怕就是有缘无分吧,王珠遗憾着,不得不将心收回。
生命中无奈的事,远不止这些,她能在一个尚早的年纪明白了,适时放手,也是一件幸事。
等待,尤其是漫长的等待,最易让人绝望。如果王承升知道太子继承皇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当初他一定不会为妹妹入宫制订那样的期限。此时的王家,已经是骑虎难下,王珠早已过了女子出嫁的最佳年龄,然而,他们不得不继续等下去。
那一等,就是十年。
大历十四年,唐代宗李豫病重,急忙诏令太子摄政。王承升得知消息后,窃喜不已,好似看到了一丝希望。终于,如他所愿,李豫不久后即病逝于长安宫紫宸内殿中,李适登基。
那些日子,王家就如同有喜临门,连守房的下人们都养成了时常向外张望的习惯,看看是否有宫里来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不说升天,剔出点小恩小惠,也够受用一辈子的了。
然而,日子久了,就又成了失望,而且这次的失望比从前更加重了几分。十年,毕竟是一个不短的时间,皇宫那么多可人的美女,李适十有八九是将王珠忘了。那段时间,各处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可又过了些日子,众人便是说都懒得说了。
只有王珠一人,心里是坦然的,时光果然不出所料,替她冲淡了一切。只是,她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每个女人在最好的年龄都应该有一段最值得记忆的爱情,然而她却是空白。
李适并不是故意将她忘掉,只是对一个指点江山的人来说,要做的事情太多。他要实施改革,要武力削藩,要大唐王朝重新回到曾经的盛世模样。而若想延续十多年前的那段情,需要闲情逸致和大把空闲时光,两样他却都没有。
他也还一直派人去寻找母亲,尊封她为“睿贞皇太后”,并在含元殿具册立牌。他多么希望母亲能够亲眼见到他荣登九尊、风光无限,可是,很多事并不是期待就能够实现的,就像此时的大唐,已经过了它最风华绝代的时候,任是谁都无法再扭转乾坤了。
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拥兵自重一直是李适最忧患的事,他唯恐重蹈安史之乱的覆辙,抢先进行了武力削藩。这本是集中权力的必经途径,可是却用错了方式,他让藩镇去打藩镇,使得那最敏感的矛盾更加激化。
建中四年的那场“泾师之变”,让他成为了大唐又一个出逃京师的皇帝,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二次狼狈地颠沛流离了。起初,他对重回京都已不抱希望,打算远走蜀中,去他少年时到过的地方,好不容易被人劝了下来,才改去了不远的奉天。
最终,只是有惊无险,他流亡半年后,又回到了长安,可是,从此锐气全消。他看出大唐的积重难返,而自己却并无回天之力。
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一直是王淑妃陪在他身边,那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她温婉、贤淑,可是紧急关头又有男人都没有的豁达与胆识。当初叛将占领长安,就是她冒着风险将传国玉玺带出的。
她自始至终都是他最名正言顺的妻,不管他日后又有了多少个女人。可是,他却一直未曾封她为后。直到动乱结束,她突然一病不起,他才慌了神。他为她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百官瞻仰,群臣朝贺,却未能将她的生命多留一刻。
人生失意,又痛失最爱,他有足够的理由用萎靡不振来疗伤。可是,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他见异思迁。
于是,有人便悄悄提醒,长安城里,还有一个王家小姐。
去王家传召,李适派的是翰林学士吴通玄,想着他博学善文,前去这样的书香门第之家是最合适不过的,不至于话不投机,再生事端。
其实,还能有什么事端,她就是有天大的理由,这次也无法推辞了。她虽依然排斥,依然痛苦,可不得不承认,还是感动的。十几年,有多少人事变迁,人心变迁,他竟还能回来找她。
再见李适,他已经年过不惑,王珠差点没能认出眼前这个成熟、沧桑的男人,就是从前潇洒悠闲的东宫太子。然而李适是惊喜的,他不住地在心里感叹,佳人依旧。
只可惜,她依旧的不仅仅是面容,还有冥顽不化的心。
宫中的生活果然如她想像的一般枯燥、烦闷,虽然他将她封了群妃之首,虽然他挤出一点时间也要陪在她的身旁,可是,她还是不能够,哪怕忍耐着,给他一个笑脸。
昔日,周幽王的褒姒不笑,惹得君主费尽移山辛力,不惜燃起烽火,失信于诸侯。李适不是那般昏庸无度的皇帝,但也是为此绞尽脑汁。他素日极其崇简,曾禁止地方官员进贡奇珍异品,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可是,为了讨得王珠欢心,他竟下令为她建一座水晶楼。
那日新楼落成,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来庆贺。笙歌艳舞,那晶莹剔透的水晶楼瞬间变得五彩斑斓。应诏前来的群臣命妇和后宫妃嫔无一不叹为观止,个个心里怕是都酸酸地想着,如若自己也能有这么一座人间稀有的水晶楼,今生还有什么所求!
可是,最欢腾热闹的地方,却不见王珠的身影。李适奔上楼去,一间一间房去寻她。末了,在最僻静的偏房里看到她,倚着窗,还是一脸的波澜不惊。
李适的心情顿时黯淡下来,想着他所做的一切,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该被打动了,为什么就打动不了她?
然而,这恐怕就是两个人永远无法诉清的隔膜,她不是个无情的人,如果是在宫外广阔天地之间,他即便只能在纸上画一个水晶楼给她,她也会心甘情愿地与他携手同归。而此时此刻,对着四周的耀眼炫目,想着日后人去楼空的寂寥,她便再也高兴不起来。
在她身上,李适太有挫败感了,半生的经历已让他知道,家国运势,生离死别,都是他所不能掌控的。而今,怎么连得到一个人的心也做不到?所以,他不甘心放弃最后的努力。
都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但在王珠看来,琴不仅是朋友,更是早已融入到了她生命之中。可是进宫时,她却有意将琴落在家中。李适不知其故,看她房中无琴,只当宫里的乐器她不能看上,私下命人快马加鞭去蜀中取琴。
时人皆知,自隋朝起,蜀地制琴名匠辈出。而其中最盛名的,是雷家所制的“雷公琴”。有传说雷家制琴技艺为神人所指点,雷家传人常于风啸雪飘时前往深山老林,听狂风震树时的声音以挑选良材。
初识王珠,是被她冠绝的琴声吸引,所以,在李适看来,只有天下无双的雷公琴,才能配得上她。
为皇宫制琴,雷家当然是拿出十二分气力。这把琴,琴面用了上好的杉木,做成落霞式,岳山、焦尾均用紫檀。琴面镶嵌着蚌徽,琴轸、雁足配的是蓝田白玉,似乎与当年唐玄宗赠与杨玉环的“冰花芙蓉玉”一模一样。
这些心思,王珠怎么能不懂,她看着琴,落下泪来。她真的不忍心再看着他绞尽脑汁,做一次次无谓的努力了。既然皇宫终究不是属于她的地方,与其最后两败俱伤,不如早日收手,各自解脱。
她平静了一下心绪,焚香净手,预备为他奏上一曲。这是进宫以来第一次弹琴,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二十年前听过的《幽兰操》再听起来,已经不复当年的模样,不知是因为琴变了,还是奏琴与听琴的人变了,如果说昔日是撩拨愁绪,那如今就是催人泪下了。
也是,当初弹琴是在那雨后竹林,海阔天空的世界里,没有耀眼夺目的荣华富贵,却怡然自得,而今怎么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放她出宫的请求,是奏完曲子,她跪在他面前提出的。余音绕梁,他尚沉浸在刚刚的绝美音律中,不曾回过神来。也许,他只是佯装着逃避,让她在他的面前多待一刻,让这场跨越了数年的爱恋结束得不要太过仓皇。
不知看着她坚定决绝的脸,他是不是也心生了恨意。这恨,因爱而生,更因一直不曾得到爱而生。他如今才知道,有一种人平生的梦想只是去到那山花烂漫的地方,如果束缚了她,也就是束缚了自己。
王珠在几日之后,被遣送回家,除了李适送的那把雷公琴,她身边并无一物。传谕王家的诏书也写得很冠冕,称王珠不能安享富贵,命中注定寒乞,故未违天命强留,日后也不得嫁与官宦之家。考究前因,又斩断后患,皇室做足了面子。
就这样,王珠又被命运抛掷到了原点,然而已经是物是人非的原点。她自己都知,她再不是炙手可热的王家小姐,生命中还余下的漫长岁月,怕是只能得过且过地活着了。
所以,当已尘封在记忆深处的故人突然出现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冥冥之中的上苍给予她的最大惊喜。
再见元士会时,他已经官至中书舍人。对王珠归家一事,他早有耳闻,所以此去王家,虽还是拜会王承升,但内心早在不由自主地酝酿着一场邂逅。
曾经望而却步,是因有些奉为圭臬的东西令他身不由己,而今,希望那一身重孝的素服能让她知道,他已是自由人。
在那条通往竹林深处的青石小路前,他踌躇了片刻,因为他知道王承升正在厅堂等候他,可是,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朝着那琴声走了过去。
窗下听琴,有时并非是一件绝顶浪漫的事,虽然那曲撼人心魄,技艺炉火纯青,但忐忑中,哪里还能真的听进去半点,不过是假借着这个姿态,缓冲思绪,尽力使得见面后的第一句问候、第一个眼神,有惊艳的效果。
琴声入微,必有佳客,这是琴与人的默契。所以,王珠起身朝窗外看去时,才恰好对住了他的眼睛。那一眼,又让他的心绪瞬时飞乱,已想好的动听的话,嗫嚅着,半天不曾说出。
最后,他竟然躬身施礼,喊了声“娘娘”。
他千不该万不该,说这么煞风景的话。或许身为朝廷命官,已经习惯了对于皇室有关的一切俯首称臣,可是,他应该知道,这个称呼对于王珠,不是尊重,而是诋辱。
王珠心中自然不快,待要发作,突然看到他一身缟素,那嗔怪的话就没有说出口。
她只当是高堂辞世,不想元士会解释道,是拙妻亡故。夫为妻穿此重孝,甚为少见,足见从前两人感情深挚。
王珠一时没有了话说,虽然她能自元士会的眼中看出些许温柔,虽然两个人之间已经看似没有了任何的障碍,可是,她还是不敢流露出半点迎合的情绪。
她当然是怕他拒绝,怕他无动于衷,怕他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的逢场作戏。她不想承认自己是残花败柳,然而的确就是。
元士会并没有同她一样,有那么多的顾虑,他知道,那个君临天下的男人给过她能令所有人为之动容的荣华与地位,而她却弃之如敝屣。所以,他想知道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此生此世,她究竟期许什么样的生活。
于是,他摸着那把名贵无比的雷公琴问她,君王垂爱,罗绮遍体,珠玉为屋,权倾后宫,为何视而不见?
她只当他也同那些个俗人一样,迷惑不解,替她惋惜,便冷笑一声道,昔日见君为真名士,今日才知原是附庸风雅之人。那皇宫不过是一个金玉牢笼,行动禁忌无数,好端端的女儿们搔首弄姿,围着那一个男人献媚,既不能白首不离,又不能生死与共,有何值得留恋之处!
看着她面露愠色,他竟然笑了,已经得到了期待的答案,还有什么好迟疑的。于是,他抢身上前握住了她的手,来时竭力思索的千言万语终于自然而又动情地一倾而出。
她这才知,原来他是在试探她。既然事已至此,她也需试探他一次,或许不是试探,而是严峻的考验。
这其实并不是她的意思,她只是突然记起了皇帝诏书上的那句“不得嫁与官宦之家”,从前并不在意,而今却成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学而优则仕,谁都知道功名对于一个男人的重要性。焚膏继晷,十年寒窗,只为一朝朝服披身,这里面的艰辛与不易是无法同外人道的。
何况元士会博学多才,刚正自律,颇为上司重视,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他们面前的障碍看似解除了,实际却更加艰难。王珠已经预备好了,像许多年前一样,让她的感情无疾而终。只是,她还不想立即说破,怎么也要将这种沁人心扉的甜蜜多留长一刻。
再进王家的时候,元士会直接前往上房,恭恭敬敬地献上聘礼,向王老爷与夫人请求,娶王珠为妻。旁边的王承升看着他一身布衣,大吃一惊,他知道,这是辞官归家的表示。
这段姻缘突然就这样水到渠成了,听到旁人叫她“元夫人”,她常常不能立马回过神来。可是,与曾经的王家小姐、唐宫贵妃相比,她当然更满意这个称呼。
有了新的名字,她也打算同她的过去告别了,她知道,元士会能够给她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
除了父母兄长,离开长安时,王珠没有同多余的人告别。能够远离尘嚣,是此生之幸,她不希望看到别人为她伤感的样子。
他们携手去了他的故乡郑州,在那里寻得了一处虽偏僻,却山水秀美的地方。他用他的积蓄买了几间房子,几亩薄田,与她过上了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
起初,他还担心这过于简朴的生活是不是委屈了她,可看着她怡然自得,安适愉快的样子,终放下心来。
此地虽民风淳朴,却不是没有好事之人。他们看夫妇二人神气清雅,举止不俗,知道定非寻常。于是,就有人偷偷在外打听了他们的底细,方知原来一个是当朝大夫,一个曾是皇宫贵妃。原本遥不可及的两类人竟然与他们相距咫尺,可想而知当地人的兴奋。
他们的平静生活很自然地被那些一传十、十传百争相观望的人们打破,起初,还只当是一时的好奇,而后发现,他们的热情只增不减。于是,他们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再不敢随意地在院内对弈、抚琴。
只是好奇的观望也倒还好,但有些人却因此起了欲念,对王珠的美貌和传说中的家财觊觎不已。
元士会自京城带出的细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被窃掠得一干二净,想来是未寻到什么稀世珍宝,窃贼恼羞成怒,还放火烧了大半间房子。
顷刻之间,两人陷入了真正的一无所有。可是,却没有一人苦恼、抱怨。曾经抛弃荣华富贵的时候,他们已经将这些身外之物放下了。只要人在,情在,便没有可以忧愁的。
天尚未全亮,只东边泛出一点银白,隔夜的露水自花叶上滴落,都还没有晶莹的色彩。元士会与王珠就在那样的静谧当中,携手走出了村落。
以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什么地方。有人猜测归隐山林,有人猜测游走江湖,还有人为了谄媚讨好,就迎合皇帝诏书中所言“命中寒乞”的话,称二人走投无路,流落到乞丐队中,乞讨度日。
谁都知道,这些全已不重要。他们同最爱的人一起,纵情于自然里,逍遥在天地间,用彼此最真的心,这匆匆而过的岁岁年年,和俗世早没有了任何相干。
然而许多人,却只能在这千疮百孔的浮世里,对着昙花一现的名利妥协,同错综盘桓的欲望纠葛不清。他们亲自为缚住双手的绳索打了死结,苟延残喘地活着。
也许,当绚美的容颜染上了岁月的尘埃,当祭奠的回忆沦陷在旧日的离乱里,我们会明白,那个华丽而潇洒地转身,原来是透彻生命的睿智!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关注遥山书雁,带您领略文化的博大精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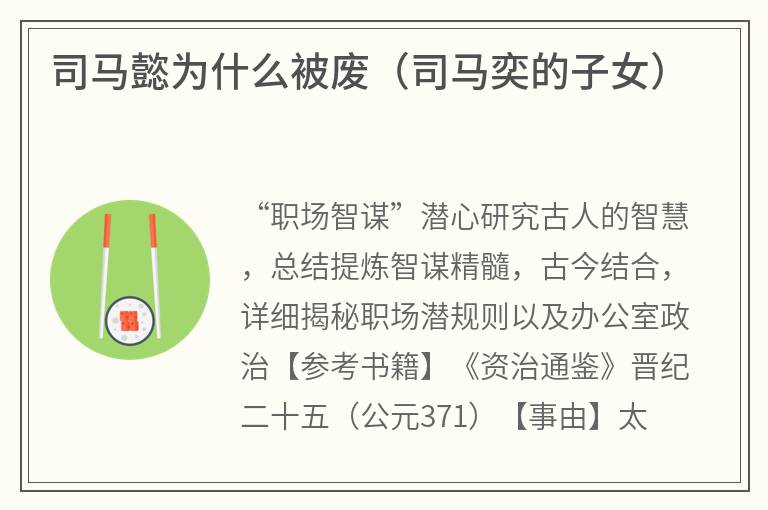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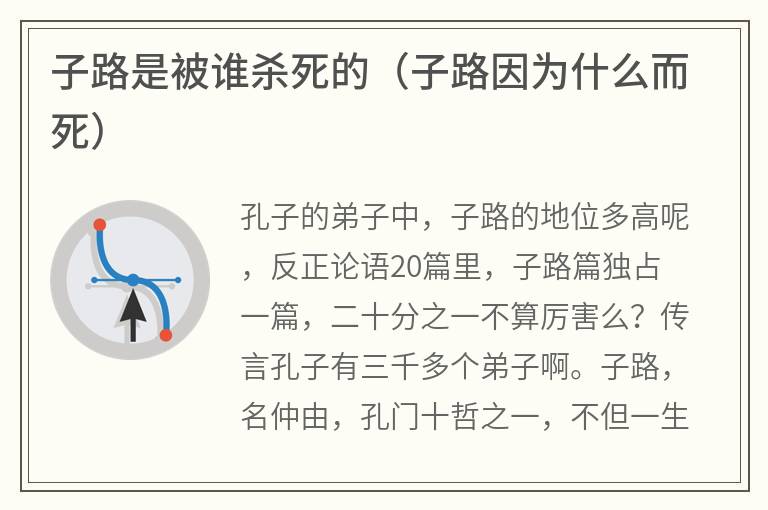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