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人类学界翻译的弗洛朗斯·韦伯教授(Florence Weber)的第一部著作,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这大概也是由法国学者撰写的人类学史首次译成中文。她出身并就职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一位非常典型和传统的精英式法国学者。马塞尔·莫斯《礼物》一书最新汉译本的读者对她并不算陌生,她为2007年最新法语版《礼物》撰写了富有洞察力的导读(见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附录)。实际上,近些年来莫斯研究的再度流行,韦伯教授功莫大焉。她是“莫斯系列”文集的主编,还编辑了莫斯的其他主题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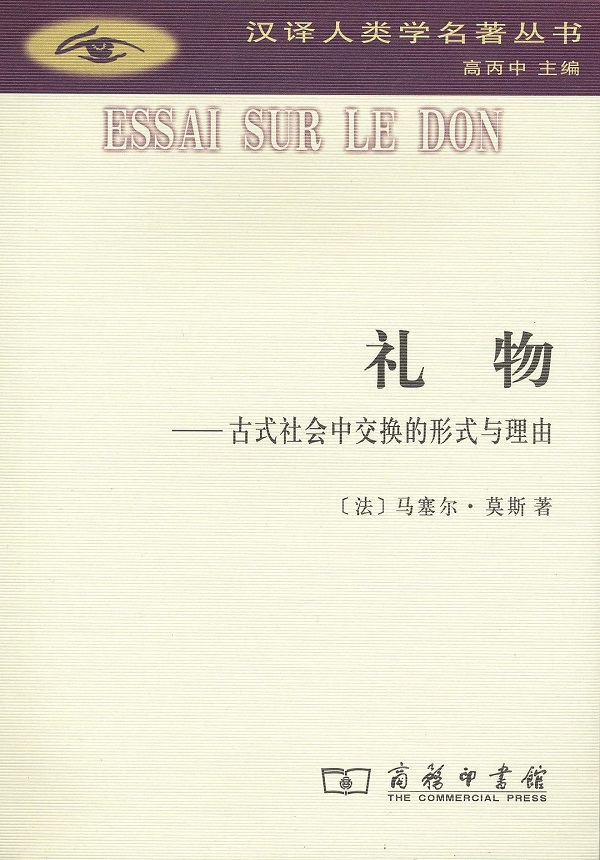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之《礼物 : 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与大多数人类学家不同,她做的不是非西方社会的异域民族志,而是从事法国本土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法国工厂的工人。这使她在撰写一部有着学科史性质的著作时,时时显示出与其他人类学史著作的不同之处——读者可与乔治·史铎金的系列作品试做比较。众所周知,法国人类学家很多是由哲学出身,看重思辨性,即便是由民族志调查出身的人类学家也往往会转向哲学式思辨。而韦伯教授是社会科学出身,看重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结合,非常强调民族志经验的实证性。在本土社会的研究经验和感受方面,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家在阅读这本书时,也许会在不少方面心有戚戚,至少对我自己来说便是如此。
这本书是为本行的人类学家写的。一本好的学科史作品描画来路,是为了探寻出路。韦伯教授在写作中将人类学——至少是“欧洲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这不是大学中的高头讲章的通行写法,在今日大学人类学讲堂上,随着亲属制度等传统研究领域的衰落,人类学正统教科书的位置早已岌岌可危了。因此,这本书不是在好古之癖的冲动下才回到古希腊,而是为了思考人类学这门学科在当前面临的危机感,才选定了一个特定的历史节点即古希腊理性时代,来思考人类学作为一种“思考方式”的内在价值。
在本书的知识谱系内,希罗多德堪称第一位民族志学者,他的《历史》(Historia)一书的现代法文译本即称《调查》(L’Enquête)。这种选择并非出于偶然。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开始,几大文明都从神话时代中脱颖而出,开始了对于何为“普遍的人(性)”的思考。中国也是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哲学的突破”。在百家对于人性及其伦理的争鸣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各家学派基于普遍人性之为善恶的讨论,也产生了对于文化差异的系统描述,更不用说老庄等学派对于文明本身的反思。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终于产生了与《调查》堪相匹敌的《史记》,而也如希罗多德那样,司马迁在游历四方之中(“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探访故老,采录口传,毋庸多说,他开创了中国古代“民族志”即“四裔传”的撰述传统。
回到这些文明的“源头”,重新审视人类学的研究重心,是有重大意义的。在其他学科如文学、史学或哲学中,欧洲、印度或中国这样的大型文明当然是重中之重,但在人类学中,它们的角色却恰好颠倒过来了,这些文明之外的社会才是人类学家的宠儿,韦伯教授戏称之为“三个贵族部落”:研究被视为“人类逝去的天堂”的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社会的人类学。这个天堂的基座都位于这个地球的南部而不是北部。众所周知,在英国和法国,非洲学家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显然与两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传统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相比之下,从事欧亚研究的人类学家则组成了“两个被支配的部落”,韦伯教授指出他们受到双重的支配:一方面,虽然他们研究拥有文字文明的社会,但这些社会多被视为欧洲殖民下的代表;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受到来自其他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支配。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也难说有重大改变之势,人类学家对此都有切身的感受。在目前的学科分工格局下,有些群体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本土社会的实证研究往往被“天然地”分配给了社会学。当然,这不是说非得颠倒过来才行。但在这种学科阶级格局中,有一个重大缺陷:既然自从埃文思-普理查德和马克斯·格拉克曼这一代人类学家开始,从田野调查到民族志撰述都再也无法与自“北方”而来的政治-经济权力脱离开来,哪怕是在探讨这个南方“天堂”所遭受的霸权性殖民支配方面,如果没有对“北方”本身开展有深度的民族志调查,那么,这个应该遭到批判的霸权本身恐怕也只是笼统而刻板的,它必然成为一个虚无的实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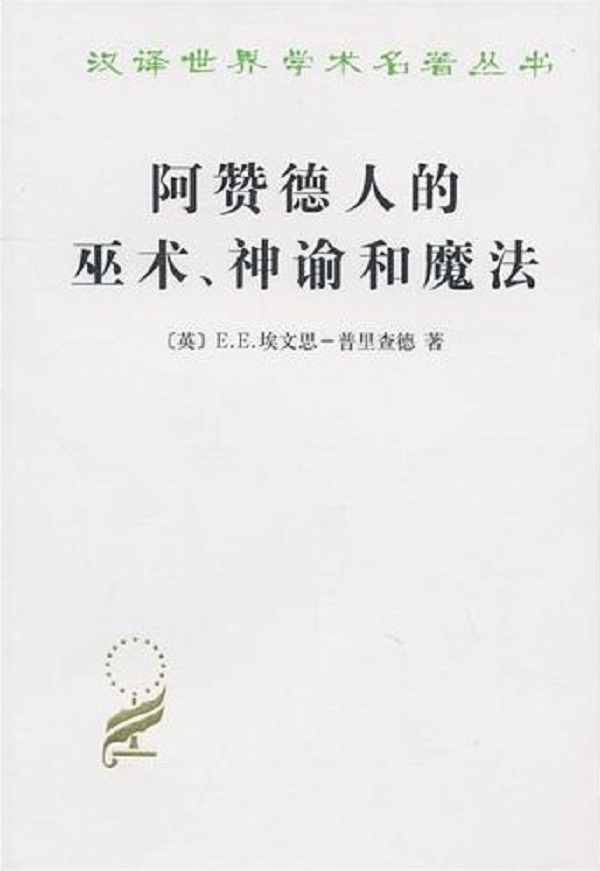
埃文思-普理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
但从第二个方面来看,那些从事欧亚社会这种“有文字的文明”研究的人类学家在“高贵部落”面前也并非没有优势,其实无须过分焦虑。应当焦虑的,倒是我们如何面对史学、文学和语言学家们在千百年以来积累的厚重传统。说这些文明是“传统悠久”的,再也没有比这种傲慢的言论更荒谬的了——既然每一个民族都活到了今天,又有哪一个民族不曾有着“悠久的传统”呢?但与口头传统相比,文字确实创造了不同的传统,也必然会迫使人类学家不得不从其他领地中借鉴,甚至发明一些“贵族部落”所忽视的技术。以无文字社会的调查和写作手法来对付有文字的文明,固然有它独到的长处,但在复杂社会里,那种孤岛式民族志显然会有捉襟见肘之感。
诚如韦伯教授所言,对于复杂社会的研究需要发展出更复杂的调查和分析方法,她在自己的研究中便坚持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看得出,尽管她不太满意于这两门学科的分离状态,但在我们以一种遥远的眼光来看,相比于美国的状况,在法国,由于涂尔干和莫斯创立的传统,这两者的结合程度其实要好得多。对于这种综合取向,中国同行们也许会更有认同感。比如说,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是从人类学起家的,却终生坚持这两个学科的合伙而不是分家。但无论从目前研究机构的设置还是从科系结构来看,难说令人满意。
不止如此,既然人类学这门学科原本也是从“古典社会” 的历史研究中分化而成的,那么,是时候适当回顾一下人类学的古典时代了。对此,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类学家实际上已经获得了比较充分的研究经验感,比如说,在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合作下发展而成的“历史人类学”已经是目前最富成果的领域之一。不用说,为了理解今天,我们不但要面对唐宋以来的“近世社会”,恐怕还要面对更为遥远的、如“古典学”这样的历史或哲学领域。(好比在法国人类学界,也有从事古希腊社会研究的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这种产生跨界影响的重量级学者。)从20世纪初进入中国学界开始,中国人类学便与考古学和历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李济),回头来看,如果失去了对于历史的纵深感和区域感,人类学社区调查的厚度也会大打折扣。即便是对历史研究并不算精通的费孝通先生在当年便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肃性,《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以及《乡土重建》等作品中的许多文章均可视为他想要将历史引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努力和尝试。对于中国人类学前贤们曾经做出的类似探索,不应当轻易地放过。

费孝通的作品
时至今日,随着许多传统研究领域的瓦解,随着反思的进行,综合性研究是实现自我突破的必然趋势。在经历了重重危机和自我怀疑之后,人类学家面临的重要议题可以说俯拾皆是。在生存环境日渐恶化的重压下,我们不得不重拾文化与自然这个古老的话题;在全球化遭到重大挫折之际,我们不得不应对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的危险;在人工智能、DNA或代孕等技术大举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之时,我们不得不警惕人类正在被过度“物质化”“异化”的生存伦理问题……所有这些无一不是迫在眉睫的话题。
这本书同时也是面向学科之外大众读者的作品。这并没有低估它的价值,恰恰相反,我们缺少这种充当“专家与大众之间桥梁”的好书。说到底,对于人文社会学科来说,哪一门学科没有承担着追究“人心”的使命呢?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如果一个学科没有办法以某种方式呈现到社会大众面前,探究人性,直追人心,它的社会意义又在哪里?从我们这片大陆的现状而言,一些学科取得的社会成就远在人类学之上,不用说历史学,甚至一向被认为冷僻的考古学普及工作都走在了这门学科的前面。在不那么严格的术语意义上,“启蒙”并未过去。这也是韦伯教授在“跋”中重申坚守人类学四大原则的关怀所在:相互、反思、自主与普遍。这不仅是为了拯救人类学这门学科,更是为了免于沉沦的呼吁。
(本文原题《法国视角下的人类学史》,系《人类学简史》代译序,[法]弗洛斯朗·韦伯著,许卢峰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5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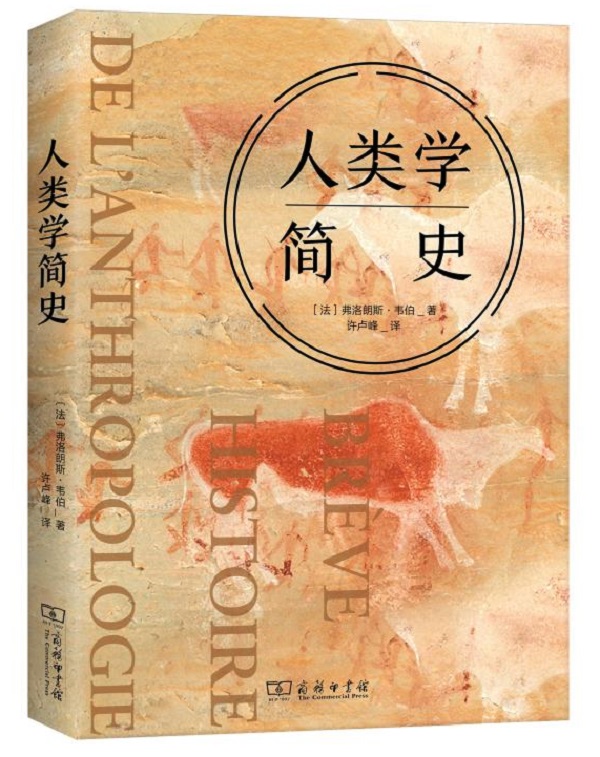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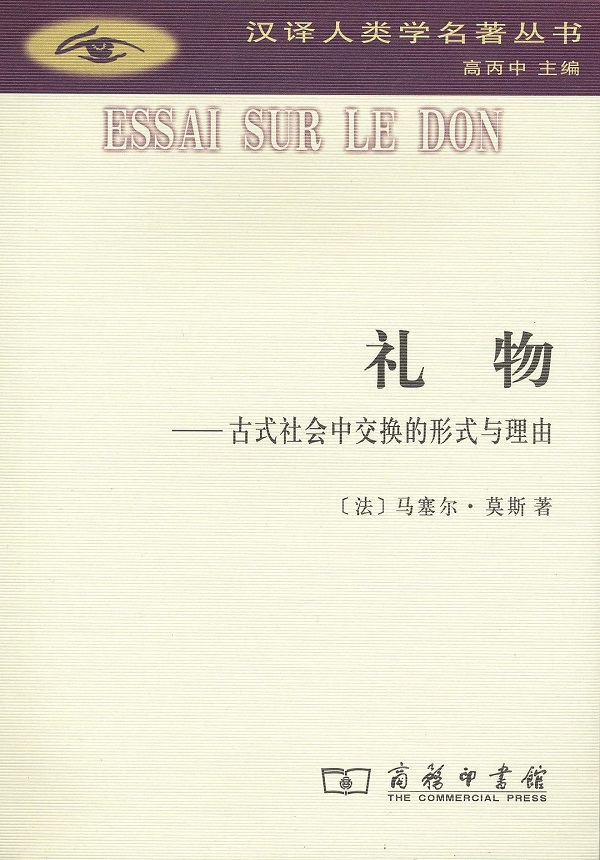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