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长久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交流与文明互鉴,都是现代历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想要创新性地继承并发扬前人的学术遗产,应该聚焦中西史学交流史研究中的前沿新作。本期特邀历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勇,爱丁堡大学历史学博士、古典与中世纪研究博士后刘铭,从中美史学交流、新时代中国英国史研究角度出发推荐相关史学研究专著。
——编 者
《中国现代历史学教育构建研究(1910-1937)》:
中美史学交流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文丨李 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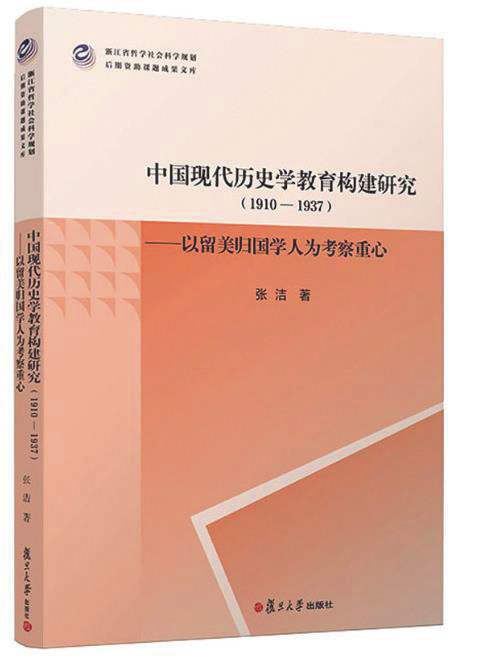
《中国现代历史学教育构建研究(1910-1937)》是史学史研究新趋势、新风气下的一部杰作。它既是对中美文化交流史的聚焦,又是对中西史学交流史,尤其是中美史学交流史的聚焦,更是细化到留美归国学人在中国现代历史学教育构建中的活动和贡献研究。
近日,细读了温州大学张洁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补充、修改而出版的专著《中国现代历史学教育构建研究(1910-1937)——以留美归国学人为考察重心》(以下简称《历史学教育构建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顾云深教授在该书的序言里,较为详细地陈述了具体意见。本文尝试谈一下自己的阅读体会,也可看作是在顾老师意见基础上的展开或细化。
聚焦和细化中西史学交流史研究中的
前沿问题
近些年来,国内学界研究中外史学交流史,是在6卷本《中国史学史》和6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出版的前提下,思考史学史研究再出发之后,重新兴起的一股风气。史学史领域的这种研究倾向,本质上在西方或称之为“跨文化”(Across Cultural)、“全球视野”(Global Perspective)。在西方学者这方面的成果中,当以沃尔夫(Daniel Woolf)《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和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等人的《近代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等为代表。当然,欧美学者的这些著作,部分内容涉及不同国家和民族史学的交流,跟国内专门研究史学交流史,还不可同日而语。
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史学互相交流、互受影响,在交流中还会出现文化因素的损失和增益,既有理解和认同,也有误读和拒斥,甚至还会出现冲突和交融,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其中的波诡云谲,是史学史研究不容忽视的观察点,正如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所言:“时人的历史研究倘止步于对各自历史学自身发展变化的探讨,就远远不够了……中外(西)史学的交流研究,便成了历史学家,尤其是史学史家之要务。”
案头这本《历史学教育构建研究》,就是史学史研究新趋势、新风气下的一部杰作。它既是对中美文化交流史的聚焦,又是对中西史学交流史,尤其是中美史学交流史的聚焦,更是细化到留美归国学人在中国现代历史学教育构建中的活动和贡献研究。
说到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建立、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或者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相关研究成果并不算少,本书的《绪论》已列举多种。此外,还有蒋俊的《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刘俐娜的《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赵少峰的《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研究(1840-1927)》、刘龙心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相关论文更是不计其数,恕不赘述。这些论著,从传统史学的更新和蜕变、欧美史学对中国史学影响的角度,论述中国史学在史料、观念、历史观、研究法、史著体裁、史学平台和载体等方面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展示了中国史学科学化、学科化的趋势。
《历史学教育构建研究》涉及上述这些论著的共同的宏大主题,但是走向了细化和具体化,细化和具体化到留美归国学人如何设立史学系、如何设置课程体系、如何从事教材建设、如何开展实践基地建设、如何用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培养学生、如何塑造学生的社会品格等。这些细化和具体化,表明作者的这些研究设想,完全处于中西史学交流史研究的前沿。
《历史学教育构建研究》所涉领域和角度,代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沿分支。学界照例可以研究留日、德、法、英归国学人的中国历史学教育构建活动和贡献,同时,还可以启发后人研究留学归国学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哲学、法学等学科的教育构建中的活动和贡献。
考察和展示留美归国学人的
历史学教育活动和贡献
本书多层面、系统地研究了留美归国学人的历史学教育活动,考察其建立史学系、设计课程体系、翻译和编写教材、输入和树立史观、讲授史学方法、开展史学实践,以及创办专业期刊和组织专门学会等,展示他们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学教育构建的贡献,具体包括:建立较完整的教学体系、提高史学在高校学科中的地位、开拓史学人才培养新路径、培养闻名中外的专业人才、开创现代学术研究新模式、影响现代史学整体发展态势等。
例如,作者根据《复旦大学志》《老复旦的故事》等文献,梳理了余楠秋在复旦大学历史学教育构建中的活动和贡献。余楠秋(1897-1968),湖南长沙人,清华大学毕业后,1914年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欧洲近代史,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会史。归国后于1922年受聘任外文科教授,1925年向校方提议设立史学系,提议获准并被任命为史学系主任,成为复旦大学史学系首任系主任。他担任系主任后,仿照美国的学分制,并把主修课设置为近代欧洲史、英国史、美国史、中国近百年史、第二外语、哲学史大纲,加重了外国历史的课程分量,培养出诸如谢德风、吴道存等这样优秀的学生。说起谢德风,在西方史学史研究者当不陌生,他参与翻译的汤普森(J.W.Thompson)的《历史著作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那是一部关于西方史学史的鸿篇巨制,时至今日仍不失为经典之范。为了解决教材问题,余楠秋组织翻译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译海斯(Carlton Hayes)的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1500-1815为《欧洲近代史》(上、下);译切尼(Edward P. Cheyney)的A Short History of England为《英国简史》;译沙比罗(J.Salwyn Schapiro)的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rory为《欧洲近代现代史》(上、下);译菲士(C.R.Fish)的Shor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为《美国民族史》;译司各脱(Ernest Scott)的History and Historical Problems为《史学概论》。前述翻译著作及时满足了学生的阅读需要,余楠秋的这些活动和贡献在书中得以全面呈现。
再如,系统论述了留美归国学人对于树立历史观、重视史学方法的贡献。留美归国学人从事历史学教育,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历史观问题,他们以课堂授课、课外演讲、教材翻译、研究论文等多种方式,传播欧美学者的历史观。通过这些努力,在学生中树立“实用史观”“多元史观”“文化史观”“比较史观”和“整体史观”,并引导学生重新评估中国的历史文化。至于重视史学方法问题,《历史学教育构建研究》考察留美归国学者对英、美、法、德等国史学方法著作的翻译,梳理各大学普遍开设史学方法论课程的情况,分析了方法论课程中的内容体系,总结其突显跨学科、追求科学性、超越传统的特征。这些考察和展示,为中国学人的史学史研究拓展了新领域,增添了新见解。
多口径统计表的支撑作用
和对后继研究的意义
《历史学教育构建研究》涉及留美归国学者众多,且从标题上看,时段长达28年,但从实际课题研究计,至少也要涉及40年的史事。因而,出于背景铺叙或在情况概述的需要,势必对这几十年留美学者的诸如生卒年、留学时间、留学学校和学科专业、获得学位等情况加以叙述,这就极容易导致文字枯燥乏味、缺乏灵动。可喜的是,作者从不同角度,设计了各种表格,避免这种可能产生的文字上的局限。
作者为本书制作了22份表格,其中有《1906-1949年留美生出国信息表》《1906-1949年留美生学位信息表》《1924-1937年留美学人译编教材一览表》《1924-1937年留美学人撰写教材一览表》等,这些表格对于本课题的意义很有参考价值。读者从《1924-1937年留美学人译编教材一览表》和《1924-1937年留美学人撰写教材一览表》中,可以一目了然地获悉史学系成立后直到1937年,留美学人为历史学教育的教材建设的成果。《北京大学史学系1919-1937年外国史教师名单》备注了教师的留学地,显示北京大学史学系外国史任课教师中的留美学人名录。这些表格既实现了对于作者观点的有利支撑,又给读者提供了阅读上的方便。
同时,这些表格的价值还在于,为他人开展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例如,后人想研究抗战前留美学人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情况,可以通过查阅表格了解那个时期有哪些留美学人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包括其姓名、职称、学位、任教课程和年份,以及他校兼职情况。同时,可以找到其生卒年、籍贯、出生地、出国前毕业的学校,再找到他们留美学校、所学专业、论文题目、留学年份,进而了解他们编译和撰写过什么教材,最后查阅他们回国后发表过哪些论文。这样,关于某位留美学者的基本情况就到手了,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具体问题,展开后续研究。
这种做法具有例示意义,后人研究留学其他国家归国学人做学术的课题,可以仿此制作留日、留英、留法、留德的表格,所谓举一反三。
逻辑张力呈现亟需继续探究的
其他问题
作者根据刘真主编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袁同礼《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1905-1960)》,以及相关的留学史著作,加之众多的个人传记和日记,统计出来的数据是1906-1949年留美出国者有119位,而在1937年之前结束留美生涯者就有56人。这56人分布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等10多所高校。
《历史学教育构建研究》论述他们在这些高校设立史学系、开设系列史学课程、开展教材建设、开辟实训基地、树立学生的历史观、传授历史研究法、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等,可谓内容庞杂、千头万绪。由此,一些方面难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这里略举几例以见其情:
例如,陈寅恪早年留学日本,后赴德国、瑞士和法国求学,再留学美国、德国,1925年回国,受聘于清华大学执教。他对于清华大学历史学乃至整个现代中国的史学贡献卓绝,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崇高,这是学界的共识。可是,陈寅恪到底属于留美归国学人,还是留学其他国家归国学人呢?即便抛开这个问题不论,从回国到1937年,在从事中国历史研究以及培养研究生这样的学术活动以外,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学教育的构建还做了哪些事务性工作?如果能够理清这个问题,对于他的相关贡献的认识一定会更全面、更准确。
再如,吴于廑在193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通过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考试,于1941-1946年留学哈佛大学,按说不在本书的考察范围。但是,《历史学教育构建研究》言及雷海宗在西南联合大学宣传文化形态学,吴于廑曾旁听过其课程,作者据此延展到吴于廑和齐世荣共同主编的《世界史》,并明确提出吴于廑之所以作出全球史观的教材来,是文化形态学引领的结果。吴于廑的全球史观跟巴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有怎样的关联,又与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或文明形态史观有什么联系,巴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跟斯宾格勒、汤因比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这些环节还值得讨论。否则,仅凭吴于廑在西南联合大学听过雷海宗的课就认为吴、齐本的《世界史》是文化形态史观影响的结果,仍然缺乏完整的理论支撑。
留学归国学人与现代中国高校史学系的成立、史学学科化的推进密切相关,这是不争的事实。从1910-1937年,无论是留学日本的,还是欧洲的亦或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留学地都处于史学专业化、学科化和新史学之风强劲之际。归国之后,他们带回了留学地的史学范式和历史学教育理念。就中国现代历史学教育构建而言,虽然作者在本书结语已经提到:“留美归国学人从事历史学教育的人数最多,做出的成绩也最为显著”,但如能和留学他国的学者做横向比较,明确留美归国学人是主导者、鼓吹者还是决策者的身份,其结论可能会更有说服力。
总而言之,《历史学教育构建研究》是中美史学交流史研究、美国文化史研究和中国现代史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多方面、系统地考察和展示了留美归国学者在中国现代历史学教育构建中的活动和贡献,为史学史宝库提供了新成果,为社会大众提供了新知识,为他人治学提供了范例。本书能够启发后学者的是,研究留学归国学人的现代学科教育构建,可能是一种可大有作为的走向,是一片可供长期耕耘的领域,是一系列有待探究的课题,是更加有意义的地方。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