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文字以来,便有对历史的记录。尽管有人说,“人类从历史中汲取的唯一教训,便是从不汲取历史教训。”这句稍有负气意味的牢骚话,常被史家用来调侃与自嘲。但纵观历史长河,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端赖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如此才有了经济的繁荣、暴力的递减和文明的演进。
前赴后继的史家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地域、运用不同的理论工具,对历史进行挖掘和阐释,试图从考古现场和故纸堆中寻获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与历史研究同步向前的,是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的不断演化,人类对历史的认识越深刻全面,越会创造出新的分析工具和思维方法。
作为强势的文化输出方,西方史学曾长期主导着世界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但最近数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和历史学科的繁荣,越来越多更具个性化的历史研究和写作范式涌现出来,并创作出大量经典著作,西方史学的核心地位也因此受到挑战。
历史学者王晴佳长期从事国际史学史研究,他在近期推出《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与《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两部史学史著作,对当代世界流行的史学理论做了细致梳理。而在本文中,他重点谈论了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的分离趋势,以及全球史、环境史、情感史、性别史、身体史的兴起,他试图揭示史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深层关系,以及当代史学所面临的诸种挑战,深入思考和应对这些挑战,将有助我们共同面对人类的未来。
撰文|王晴佳
(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历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由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西方史学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能充分代表整个世界史学的走向,相反,西方史学的发展变化,更多地呈现出与非西方地区史学之间的密切互动,形成交互影响的趋势。概括而言,最近几十年的西方史学及全球范围的史学,出现了一系列纵横变动的趋向。
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的结合与分离
首先,是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抑或历史哲学)之间的分叉化趋向。这一趋向,与20世纪下半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不同。二战之后,西方殖民时代走向终结,冷战时代开始,这对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历史研究的变化与历史本身的发展变化切切相关。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虽然冷战造成了共产主义阵营与西方所谓“自由世界”之间的严重对立,但美国主导的越南战争进展不顺,并且陷入泥潭,也使得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出现了质疑西方主流思潮的趋向。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化、现代性的批评,即是其中一个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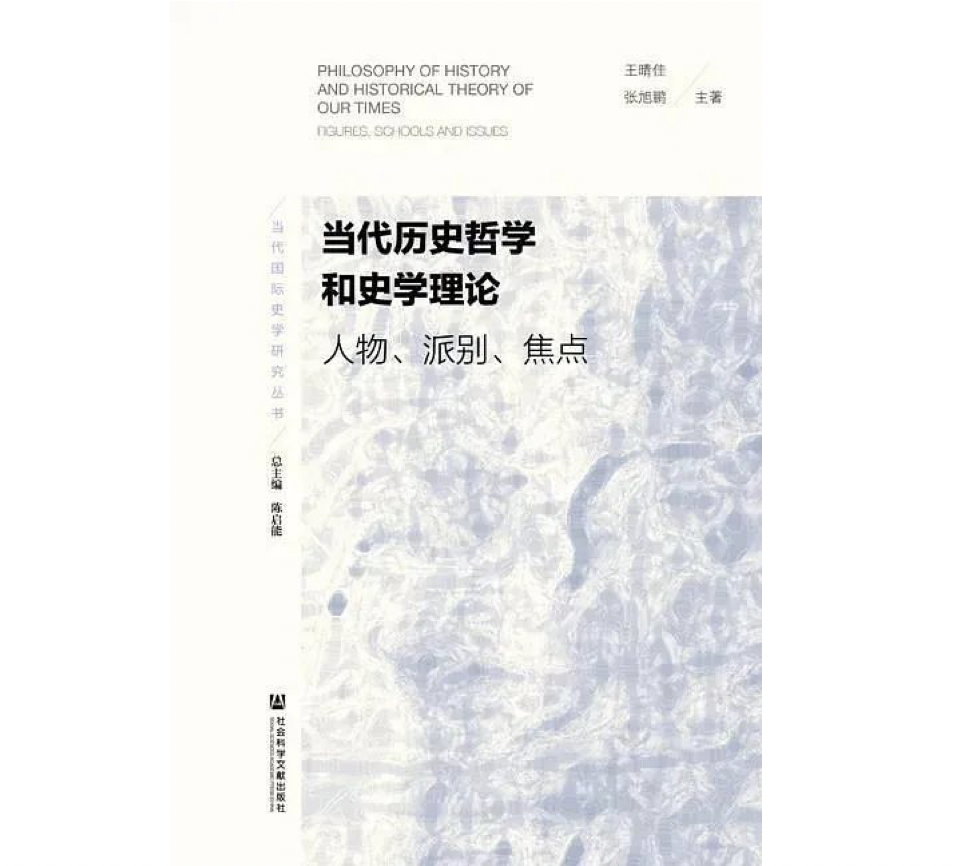
《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王晴佳、张旭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同时,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终结,也促成了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其目的是从思想和文化上批判性地检讨殖民主义的遗产。而这一检讨,又与西方的现代性的讨论和反思无可分割。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质疑近代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和现代性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1973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和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的出版,是这一时代思想界变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其代表和先声。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其观点并没有立刻被接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它们的争议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使得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问题,成为历史工作者所注意的热点,并且渐渐在其研究的论著中表现出来。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趋向,在史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史学界出现的所谓“语言学的转向”,为史家们所耳熟能详,即是一个反映。

《东方学》,[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9月。
但进入21世纪以来,理论与实践出现了一种分叉化的趋势。一方面,历史思想家、理论家仍然继续对其关注的课题深入研究,并从侧重史学与语言的关系,转移到其他重要的层面。另一方面,历史理论家热衷从事研究的课题,似乎不再激起大部分史家的兴趣,因此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某种脱节。
荷兰史家法兰克·安可施密特也许可以作为一例来说明。1989年,安可施密特在美国的史学理论杂志《历史与理论》上撰文,题为“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从实践的层面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不但值得史家的关注,而且,已经在一些史学论著上有所表现。这篇文章的发表,让海登·怀特提倡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为史学界人士所熟知。安可施密特本人也被人称为“欧洲的怀特”,但其实安可施密特本人研究史学理论多年,其关注并不与怀特完全重叠。
近年以来,安可施密特及其追随者(如莱顿大学的赫尔曼·保罗和芬兰的琼尼-马蒂·科坎能)试图走出“语言学转向”、历史叙述的范围,从经验/体验和学品/人格等方面来考察史学研究的特点和性质。简而言之,这些欧洲学者没有对怀特的理论亦步亦趋,而是希图有所突破,探讨历史研究中“后叙述主义”(post-narrativism)的可能。不过他们的研究,尚没有对史家的工作,产生明显的影响。就世界范围的史学而言,叙述体裁显然仍是主要的表述形式,而且在近期也不会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
跳出国别史的藩篱,全球史与区域史火热
就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化而言,全球史的发展仍然十分强劲,并且与环境史等其他新兴的历史学派相互携手、互动,形成了对近代史学的有力冲击。自17世纪以来,西方首先出现了民族国家,其后逐渐影响到整个世界,促成民族国家史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德国的利奥波德·冯·兰克被人尊为“近代史学之父”,与其说是因为他对史料批判的提倡和实践,毋宁说是他所关注和倡导的民族史、国别史的书写。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写作历史,在西方等地的图书编目上也有明显的反映。

《世界史:从最古老的种族到前现代过渡时期的西方历史》,[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著,陈笑天译,吉林图书出版公司, 2017年4月。
现有的历史著作,除了通论性的之外,其他都根据国别编目,毋庸置疑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但这一历史写作的主流趋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全球史、区域史的有力挑战。而这些挑战本身,又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氛围及其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均有渊源关系。换而言之,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的崛起,使得西方不再像19世纪的时代那样,其发展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走向。史家开始走出民族国家的藩篱,从区域抑或全球的视角进行历史研究,几成理所当然之势。
走出民族国家的视角,让史家得以从更宏观的方面,探讨不少历史问题,环境的变迁便是其中之一。如同美国环境史家约翰·麦克尼尔所言,“许多历史现象、特别是环境史所关注的对象,显然无法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进行研究”。这一道理显而易见,因为环境的变化,虽然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政府政策时有关系,但其影响却常常超出其国家的疆界,对整个区域乃至世界都会产生长远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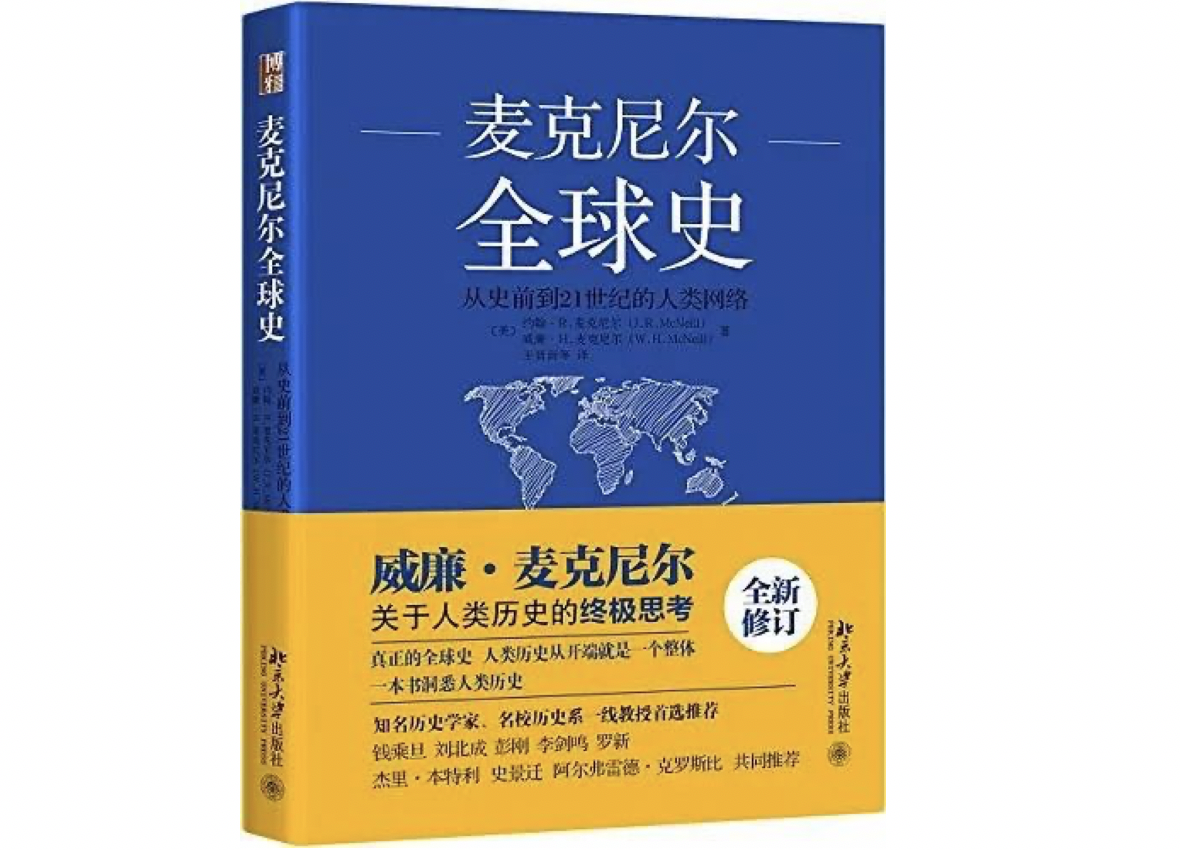
《麦克尼尔全球史: 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美]约翰·R.麦克尼尔 、威廉·H.麦克尼尔著,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从2007年开始,一些环境史家提出了“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概念,其中心意涵是在19世纪以前,地球的变化主要由自然界的力量所主导,但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的活动逐渐主宰了地球环境的变化,譬如全球变暖、森林消失、气候异常、雨水、风暴增多等等。如此种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地球不复是以往的地球,而是成了一个“陌生的大地”(terra incognita),人类在地球上的居住和生活便正在和将要面临巨大的挑战。
传统政治史衰落,环境史异军突起
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不但让人看到突破国别史的必要,也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了政治史的衰落。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研究,政治制度、人物和思想的出现和变化,自然是史家关注的重点。兰克及其追随者的历史论著,几乎清一色都是政治外交史,并以政府档案的使用为特点。这种史学模式,已经不再主导历史研究,尽管政治力量和权力如何影响历史,仍然为史家所重视。
201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的《剑桥世界史》,其中第六、七卷所概括处理的时代是1400年至当代的历史。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国家首先在西方兴起,民族主义思潮逐渐走向其他地区的重要阶段。但是在这部新编的世界史卷中,民族国家在西方的兴起没有占据什么重要位置,反而比较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在政治层面的多重变化。第七卷中有专章讨论民族主义,但其侧重点也是描述其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而非专注于民族主义在西方的缘起。同样,2011年出版的多卷本《牛津史学史》在描述近代史学变迁的时候,政治史同样受到相当程度的冷落。
《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
不过,政治史的衰落并不代表史家不再重视政治权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是反映了研究角度的变化。与兰克史学注重政治精英的作用相反,当代的史家更重视检查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渗透。近年兴起的记忆研究热,便让许多从业者看到政治对公众记忆的塑造产生的重大影响。诸如纪念碑的树立、纪念馆的落成、纪念仪式的策划和举办,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一种政府的行为。
传统政治史的式微及其转型,反映了当代史家在史学方法上的革新。专注政治人物的传统政治史,档案的批判和使用至关重要。但如果史家的研究兴趣是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那么政府档案便只能反映其中的一个侧面。记忆研究之所以能改造传统政治史,正是因为其所采用的方法,已经与以往大相径庭了。因为政府档案往往没有记录社会和大众层面的历史活动,史家必须通过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获取信息和资料。而如果想深入分析、调查大众的行为,那么社会学、统计学、人口学等方法的采用,就变得势在必行。因此这些史学方法层面的变化,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自下而上”、从精英转向大众的历史研究趋势,相辅相成。
但除了向社会科学靠拢,当代史学方法的最新趋势是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比如上面提到的全球环境史的研究,让史家开始注意使用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学、气候学乃至孢粉学等新兴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这些学科能帮助史家深入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这些史学方法革新的新气象,也为资深史家所认可。法国史和新文化史的专家琳·亨特,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全球时代的历史学》一书中指出,20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主要受到四大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族群和认同的观念。但她在书的结尾、展望历史学未来的时候也指出,历史研究一向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若要深入了解个体、个人,那就不但需要借用心理学,也要借助生物学的方法。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王晴佳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
在史学中把人作为生物并与其他生物种类一起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角度。近年已经有不少史家开始从事人与动物、生物关系的“跨种类”(interspecies)研究。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细菌和钢铁》在美国出版之后,迅速成为了一本畅销书,间接帮助了动物史研究的兴起。戴蒙德指出人类驯养动物,使其成为家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的演化。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牲畜的致命礼物”,也即各种瘟疫,比如天花、流感、疟疾、肺痨、麻疹等等。
近年的动物史研究者强调,研究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必须突破人类中心的主导思维,尝试如何从动物的立场来考察人类活动对它们的影响,由此来突出和强调人类与动物共存、互助的观点。这一崭新的研究取径,与大历史、环境史等其他新兴学派一起,参与和推动了“后人类主义”的思考,批判了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论哲学传统,由此而代表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史学思潮(顺便一提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病疫的暴发,将会有助于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
情感史与性别史,开始被国际史学界重视
以总体而言,人类及其活动仍然是当今历史书写的主要内容,但以往的研究注重的是人的社会和政治属性,比较忽视人的心理、情感的层面。这一倾向在近年开展的情感史研究中,得到了一些纠正。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这是国际历史学会成立以来首次在非西方地区召开该会议。而在那次大会上,情感史成为会议的四大主题之一,可见对其重要性的认可度。
对于人类情感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剖析,一般采用的是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等方法。但在近年的情感史研究中,自然科学、特别是脑神经医学的最新成果被史家所吸收和采纳,由此而激发出新的研究课题和热点。当然,科学家与史学家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似乎还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注重的是发现(比如通过对脑神经、细胞活动的变化)人类行为的共性,诸如罹患忧郁症的病人,其脑部神经的相同点,从而对症下药。史家自然也希望揭示人类情感的共性,但更注意在一定的时间段中考察这些共性的形成,并探究其与社会氛围及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举例而言,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之形成和特点,不但是情感史研究的重点,也足以反映历史研究注重时间的特性。因为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只是近代的产物,虽然受人推崇和赞美,但其稳固和长久性则往往不如前近代的传统婚姻模式。因此对婚姻和家庭组成的研究,能比较充分地展现情感变化的历史性。

《心灵革命: 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研究婚姻的形式及其变化的历史,让我们自然转入当代史学的又一个活跃的领域,那就是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妇女史的研究与战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目的是在获得了政治投票权之后,如何在其他领域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妇女史家希图发掘历史上的女性,以改变原来男性为中心的“男史”(His-story),转为“女史”(Her-story)。
1986年美国史家琼·瓦拉克·斯科特发表了著名的“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用范畴”一文,改变了以“女史”为宗旨的妇女史研究,提倡检讨两性关系,并分析这一关系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错综联系。性别史的研究开创了妇女史研究的新局面。显而易见,性别观念的形成是后天的——男女性的差别虽然有与生俱来的因素,但同时又牵涉一个人成长过程中诸如心理、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性别的差异并非一成不变,更非方柄圆凿、截然相对。因此在性别史研究中,对男性及其性别之构建塑造抑或男性史的研究,占有的比重日益增加。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美]斯蒂芬·平克著,安雯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19年7月。
如果希图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层面研究性别,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无可忽视。显然,西方社会所关心的两性问题,虽然有其共性,但又与其他地区有明显的不同。近年的性别史、妇女史研究,特别注意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以西方社会为准绳的倾向,而是强调如何突出各地区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其对妇女地位、两性关系的影响。简而言之,当今的妇女史研究者,不想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所关注、推动的论题,原封不动地搬到其他地区,而是努力发现世界各地区妇女和两性关系的特殊性和历史性。
举例而言,中东的妇女出门一般需要佩戴头巾,毛发不露。这一习俗通常会被西方人视为落后、保守的象征,但从中东社会的传统和现状而言,妇女佩戴了“希贾布”(头巾),能让她们进入公共空间,无异是一种伸权的行为。而且,穆斯林妇女往往享有比其他地区妇女更多的经济权利,因此对妇女地位的研究,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杆,更不应东施效颦、削足适履。
以上的纵论,涉及当代史学在观念、方法、范围和领域等方面的新气象,值得中国史家参考借鉴。但上面的讨论也指出,历史研究虽然有全球化的趋向,但这一趋向并没有取代乃至抹杀各种文化传统之间的个性。全球史的进程,反而强调和突出了历史的个性,值得当代史家重视和探究。
作者|王晴佳
编辑|徐伟 罗东
校对|李世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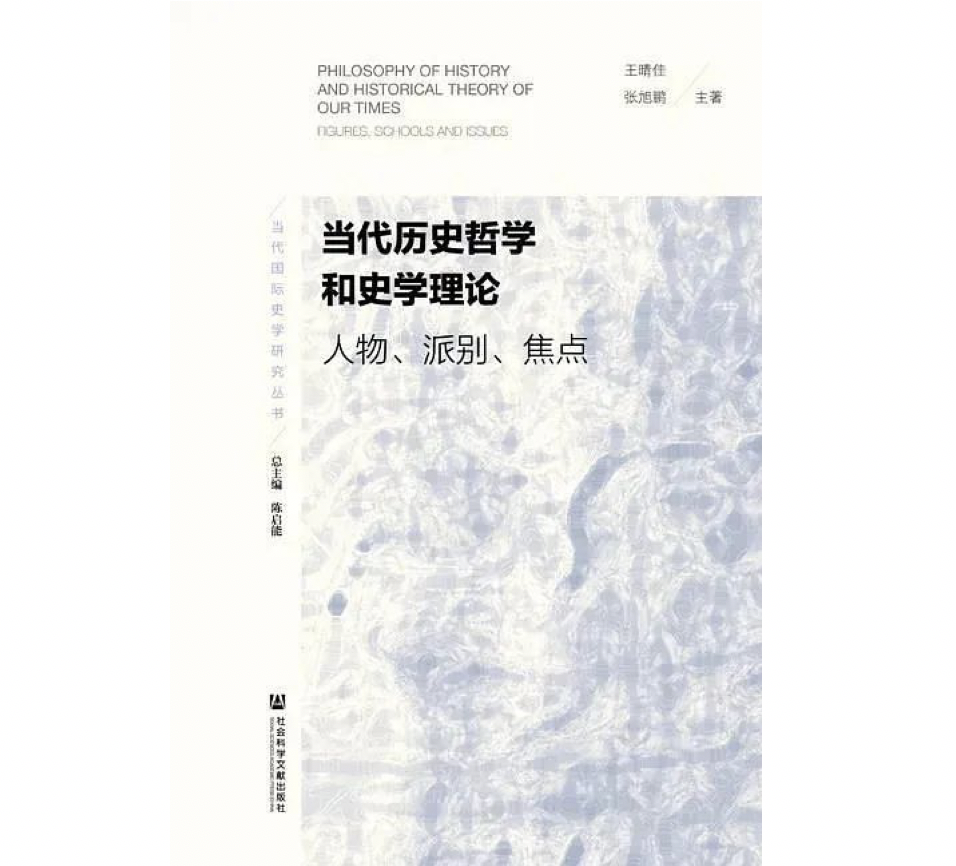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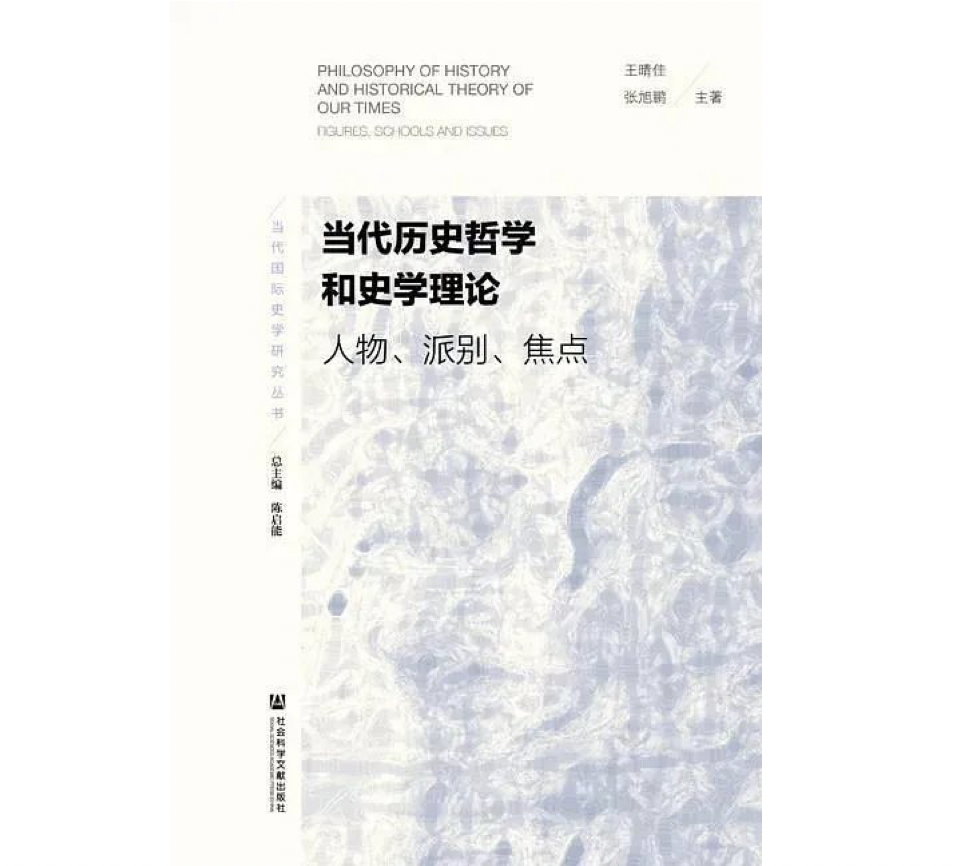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