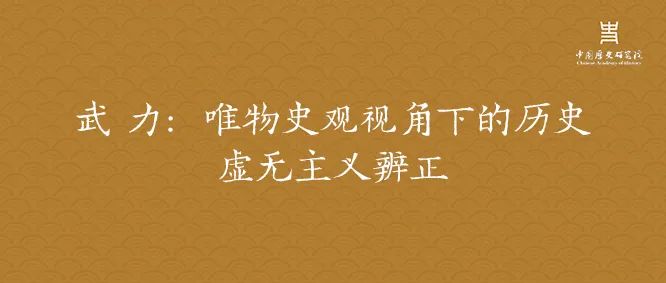
针对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已经有不少商榷和批驳的文章,也产生了一些效果。但是应该看到,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传播中的这种思潮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有其存在的经济和文化土壤,彻底消除它将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笔者认为,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和消除历史虚无主义,我们需要更多地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一、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
庄子在《秋水》篇中曾经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即是说,一个人的见识受到他所认识的时空和所掌握的理论方法的制约。
近些年来,在辛亥革命和民国史研究的热潮中,对改良与革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出现了怀疑民主革命、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赞颂改良,甚至为封建社会的糟粕、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唱赞歌的声音,而忽视了整个世界自1840年以来所显示出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潮流、大趋势,以及在这个潮流背后的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这种生产方式大转变的趋势。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也看到了这种“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丛林法则,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由于这种趋势和转变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侵略、压迫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方式进行的,因此这些被侵略、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同时遇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两大敌人的反对,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历史悠久的大国,更是如此。我们从这个大的世界历史趋势和社会进步去反观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去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就会准确把握近代以来的各种事件和历史人物。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是中华民族在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下不断进行反抗和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则压迫、阻碍这种进步,使得中国几乎每次改良都以失败告终。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中国不需要和平改良,也不是没有改良的机会,而是反动势力不愿意接受改良,不给先进阶级和阶层以改良的机会。从戊戌变法到清末立宪,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向袁世凯妥协到“国民会议运动”的失败,都证明改良道路走不通;又如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抗战时期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1946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等,都证明国民党不能容忍共产党与其分享政权,不允许以和平方式共同推进社会进步,而是要消灭共产党。整个近代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随着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落到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动员和领导中国最广大的农民来推翻阻碍现代化的“三座大山”。
20世纪前半期,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列强依靠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的时候,社会主义作为制止这种资本主义灾难的一种新生力量应运而生。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得以实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下,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统治地位。一句话,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还没有在这些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世界大战时,由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因此,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革命就必然包含有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也是列宁为什么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主革命纳入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范畴的原因。正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具有了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并且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呼应,所以,这些国家软弱的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就表现出对无产阶级革命因素的防范甚至镇压,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表现得远比1848年欧洲革命时更为明显。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世界背景。
如果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那么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则处于备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和政策的破产,随后掀起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则反映出封建顽固势力仍然把持着政权,不愿意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以巴黎和会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和中国政府外交失败引发的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寻找一条可以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最终促成孙中山“以俄为师”和国共合作。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得出“走俄国人的路”这个结论。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制度和方法,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同时还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暴露出来的对外侵略、对内压迫人民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弊病,即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超越西方现有制度的更加民主、自由、平等的制度。另一方面,十月革命为中国提供了动员、领导最广大民众参加革命的组织和办法,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进步力量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一生追求中国独立富强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晚年提出:“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十月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则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最彻底的民主革命任务。
二、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视角的多重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中国古人既说过“管窥蠡测”,也说过“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所窥者大,所见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这都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从多重视角观察问题,用多种方法分析问题,切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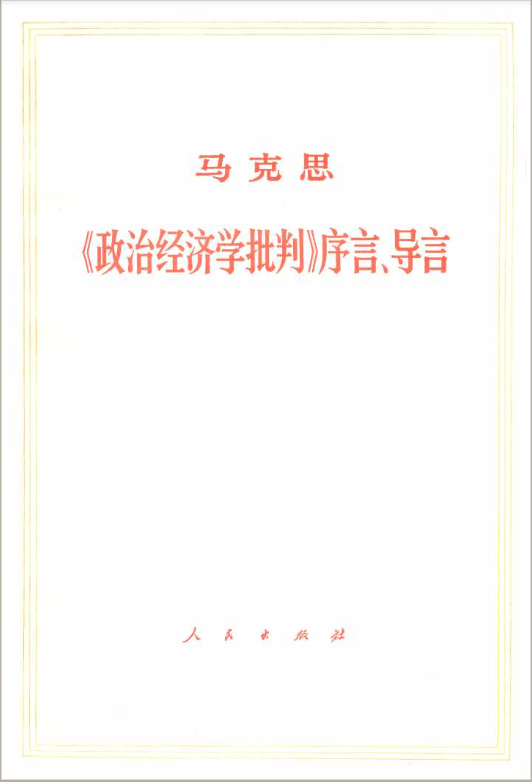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4月出版(图源: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
例如: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会建立起计划经济?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是照搬苏联经济模式的结果吗?怎样评价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新中国成立时,一百多年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使得中国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残破。以旧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1931-1936年为例,其消费率和投资率如下:1931年为104.1%和-4.1%,1932年为97.5%和2.5%,1933年为102.0%和-2.0%,1934年为109.1%和-9.1%,1935年为101.8%和-1.8%,1936年为94.0%和6.0%。这说明当时的投资率极低,6年之中4年为负数。因此,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探讨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时,几乎一致认为仅靠中国自己不能解决资金匮乏问题。新中国成立时,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是基本国情之一,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5.4亿人口中有4.8亿是农民,靠传统农业吃饭。当时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仅209公斤(毛粮)。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而且农业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1954年全国农户收支调查时,户均耕畜0.6头,犁0.5部,多数家庭即便独立从事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因此,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非常少。这种积累能力极低、剩余高度分散的情况,使得成立之初的新中国很容易陷入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
计划经济的形成,还与这个时期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边界冲突,都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选择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来考虑。美国阻止中国统一和直接威胁中国安全的行径,都是建立在中美之间相差悬殊的武器装备基础上,进一步说,是建立在相差悬殊的工业化水平上。正如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 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而要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就必须优先发展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
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第一次台海危机又使得新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的步伐,这个时候,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决定了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而十分有限又非常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积累的主要来源。为了加速工业化,中国就需要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而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指出:“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是中国百余年来多次社会变革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恰恰“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三、历史研究需要细节但不能碎片化
庄子曾经说:“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在历史研究中,存在着如何避免两种有违科学精神的倾向问题,一种倾向是只重视宏观历史和大事叙述,仅仅停留在历史概念的推演而不肯深入研究历史细节,正如恩格斯批评过的那种拿着理论和分析框架四处套用,自以为掌握了历史的规律和全景的人们;另一种倾向则是完全忽视甚至否定历史观和对整体历史的把握,只注重历史细节和个案研究,并以此为标榜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前者失之疏阔和空谈,很难推进历史研究的深入;后者则容易囿于细节和个案,失之偏颇,陷入以偏概全、盲人摸象的境地。这两种研究历史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近些年来,随着所有制结构和利益的多元化、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文化产业的繁荣,以及信息化带来的便捷,越来越多对历史感兴趣的非专业者进入历史研究领域。作为非专业的研究者或传 播者,他们往往更多地关注与自己有关的历史,关注具体人物研究、关注专业历史研究者因“轻重缓急”而没有顾及的历史细节和个案发掘,甚至为了吸引关注和牟取名利,故意标新立异,以个别事例来否定成说。后一种倾向越来越突出,这种倾向又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产生的土壤和蔓延的机会。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倾向中,有些专业和非专业的研究者是带有明显的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政治目的,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们试图通过有选择的个案和口述者历史,来颠覆或改写目前已经广泛传播和被接受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的结论。
以近些年来对土地改革的研究来说,随着社会史和田野调查的普遍开展,个案研究越来越多,历史细节也越来越清晰,但是正如庄子所说的“自细视大者不尽”,从这些个案中看到了革命的残酷、斗争的无情,但是没有看到土地改革的背景是解放战争,没有看到几千年来农民受到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没有看到从孙中山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到1949年国民党统治垮台,和平的、改良式的“耕者有其田”一直没有实现,甚至连“二五减租”(即将地租由50%减低至 37.5%)都没有做到,农村当政的地主阶级愿意改良、让步吗?

1946年山东解放区临沂县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图为农民们正在丈量土地。(图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从横向上看,在外部先发的强大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后发国家如何解决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难题之一,即解决传统社会留下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传统的农民战争和农民革命无法解决中国近代的发展问题,资产阶级也无法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由落后的、被动的阶级改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彻底的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由于环境的严峻、政策的不成熟、干部队伍能力不高以及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土地改革的确出现了一些偏差,出现了乱打、乱斗、乱划阶级成分的现象,但是这些毕竟是支流和运动初期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革命的代价。革命与改良相比,是残酷的、流血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但是当改良走不通时,革命又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也是如此。例如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和谈就是想走一条和平改良的道路,但是国民党不愿意,率先挑起了内战。
如何避免历史研究和知识传播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除了上述方面外,还应该提倡“走进历史”与“走出历史”。所谓“走进历史”,就是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进入那段历史的场景,换位思考,看到历史的局限性,看到在当时条件下这个人、这件事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看到其主观动机与客观条件、客观结果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所谓“走出历史”,就是不要为历史细节和对人物、事件的感情所迷惑和制约,缺乏大视野、是非观,凭个人好恶来评价历史,将历史作为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甚至像北齐史学家魏收那样写“秽史”,对历史人物“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
作者武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