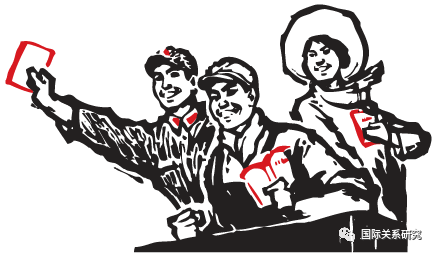
编者按
作者刘胜湘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邬超为江南社会学院助教,原标题为《美国情报与安全预警机制论析》,原文全文载《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六期。
美国安全预警机制是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安全预警机制在“9·11”事件中的迟钝反应及在伊拉克战争前的过激反应,充分暴露了美国情报安全体系的种种弊病和不足,美国国家安全预警能力也饱受批评和质疑。根据“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2002年起美国开始对情报与安全预警系统进行重组。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总监、国家反恐中心等一系列机构的建立标志着美国新安全预警机制的形成。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着力调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重点关注网络安全情报体制的建设,促进国家安全预警机制的整合发展。2017年年初,新上任的“商人总统”特朗普试图对奥巴马政府的情报安全战略作出全面调整,但由于特朗普本人对情报机构高度不信任及受到“通俄门”事件的影响,以至于总统与情报机构间关系陷入紧张状态。从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在情报与国家安全领域的政策主张并不十分明晰,其能否摆脱现有情报与安全体制运行模式的惯性,或是回归传统主流,都有待继续观察。

迄今为止,美国已经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层级最多的安全预警机制。目前,国内学界较多地关注美国情报系统、反恐情报预警体系的改革历程和经验启示,少数军事理论学者的著述涉及美国军事预警系统的建设现状和发展动向,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军事预警与战略预警的理论界限。美国学者及智库则侧重于论述美国情报系统的机构职能、运作模式,如杰弗瑞·理查尔森(Jeffrey T.Richelson)的《美国情报界》梳理了美国各情报机构的组织架构及其主要情报职能,包括对情报机构的管理和指导。也有不少美国学者重点论述全球反恐背景下美国情报系统的问题、改革和评价。本文在借鉴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基于情报视角下的美国应急、反恐、军事和战略预警系统的历史沿革、现实动向和经验启示。
任何情报组织都无法做到全面而精准地掌控所有可能发生的安全危机,这就使得基于情报活动的安全预警实践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安全预警”的概念正式形成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核威慑,核子武器不仅彻底改变了战争的传统形态,而且使美国逐渐意识到建设系统性安全预警机制的重要意义。欧洲冲突预防中心认为,构成“预警”的三要素分别是信息收集与信息分析、预警信号及可能的应对。美国中情局将“安全预警”定义为对即将发生的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进行预先报警。美国前国防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则从情报工作具体实践的角度指出,“预警本身就是一项技能,它要求我们的情报人员能够充分地了解并掌握潜在敌对势力的态度、原则及其实力、历史、文化与偏见等相关内容”。狭义的安全预警仅仅是指向特定对象发出预警信号的过程,而广义的安全预警内涵则要丰富得多,包括情报监控、危机预警和应急预案三个阶段。与安全情报的4种类型相对应,美国的安全危机预警分为应急安全预警、反恐安全预警、军事安全预警和战略安全预警。

纵观美国国家安全预警机制的发展历程,“情报”与“改革”一直都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美国明确以安全情报和预警系统为依托,着力加强和完善安全预警机制的建设,以应对各式各样的安全威胁和快速变化的安全环境。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和发展,美国已经在国家安全预警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中相当丰富的有益经验值得借鉴,诸多失败的教训也要引以为戒。
(一)应急预警机制的启示
其一,美国应急预警的领导体制完善,采用以各级政府为主导的三级预警响应模式,这既确保了联邦政府在应急安全管理中强有力的领导,也能够有效实现各级应急管理机构在应急预警响应方面的协调配合和无缝衔接。作为最高级别的应急管理部门,国土安全部主要负责联邦级别的预警政策制定和宏观指导,同时提供应急预警所需的人力、财政和技术等资源,其下属的联邦应急管理局负责应急核心能力的建设和维护,并代表联邦政府领导、协调和整合包括州政府、地方政府在内的所有应急管理协作者,确保各级政府之间高效率、无壁垒的应急预警合作。州政府应急管理机构主要作为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纵向应急协作的重要渠道,与上级、下级政府相关部门达成协调机制,以此解决应急管理过程中各级政府应急管理机构之间的跨界协作问题和组织依存关系。地方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在联邦、州两级应急管理机构的指导下负责具体实施各项应急预警措施,这足以保证在紧急事态发展超出地方政府的应急预警能力时,联邦及州政府能够迅速介入并加以应对。

其二,美国应急预警的运行机制灵活,能够不断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需求。战争时期的美国应急预警机制主要侧重于防范战争和战时国防动员;而非战争时期,美国应急预警机制的侧重点会自动转移到国内的社会公共危机和自然灾害领域。随着不断的改革和发展,美国的应急预警机制不仅逐步完成了从被动反应向积极防御的过渡,而且还实现了由单一应急风险领域向综合应急风险领域的转变。
其三,法律是美国应急预警机制的有力保障。从1950年的《灾害救助与紧急援助法》到1976年的《全国紧急状态法》;从1988年的《斯塔福法案》到2002年的《国土安全法》,再到2006年的《应急管理改革法》,历届美国政府都会根据不同时期的应急安全需求来制定或修订相关的应急法案,应急安全立法为美国的应急预警机制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不仅如此,不断修订和改进的《国家应急预案(框架)》对应急预警的决策程序、实施过程、应急管理机构的职责和权限等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其四,美国应急预警机制的教训。“9·11”事件后,为了配合全球反恐的战略需要,美国应急预警机制开始执行重“防恐反恐”而轻“防灾救灾”的预警政策,这种人为的倾斜使得美国在应对一些重大突发的自然灾害时表现得措手不及,最终导致不可避免的灾难性后果。对某一应急风险领域的过度关注往往会造成应急管理资源分配失衡的问题,而对其他领域的紧急事态又会缺乏能动反应和预防措施,其结果只能是对应急预警机制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应该努力避免采取“厚此薄彼”的应急管理政策理念。
(二)反恐预警机制的启示
其一,反恐预警分级明确。科学的分级预警制度有助于美国社会各界及时识别不同程度的恐怖威胁,并根据不同的预警级别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来提高反恐应急能力。然而,采用5级预警的国土安全警报系统本身存在结构性缺陷,难以引导公众通过不同颜色来区分不同等级的恐怖威胁,也缺乏相应的反恐应急预案。在反恐预警的现实应用中,这样的反恐分级预警很难发挥实质性作用。因此,美国取消了颜色分级预警,以更为简便的三级制警报系统取而代之。

其二,反恐预警立法先行。“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迅速启动反恐立法程序,先后通过和颁布了一系列的反恐安全法案。如2001年10月通过的《美国爱国者法案》扩展了美国情报界的反恐权力;2002年5月出台的《加强边境安全与签证入境改革法》允许联邦机构通过分享入境者的签证信息掌握移民的动向,以此来获取恐怖分子的个人信息;2004年12月颁布的《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预防法案》促进了反恐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反恐情报的共享。反恐预警离不开顶层立法的支持,反恐立法是反恐预警机制得以正常运行并发挥实效的基本保障。
其三,反恐预警机构调整快速、及时。根据相关反恐法案,美国在第一时间对反恐情报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不仅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国家反恐中心等综合性的联邦反恐机构,而且还对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原有的情报机构进行重大的改组。同时,还将涉及反恐领域的非情报部门也纳入到国家反恐预警体制下,例如能源部、财政部、海关署等职能部门。整合后的美国情报机构以防恐、反恐为重点,这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反恐安全预警工作的效率。
其四,反恐预警情报共享。美国各联邦情报机构都负有反恐的职责,然而想要形成众情报机构齐力反恐的合力绝非易事。“9·11”事件证明了由中央情报主任负责协调和汇总反恐情报的预警机制是极其失败的,由于反恐情报无法实现顺畅的跨部门交流和共享,反恐情报呈现碎片化和分散化。因此,美国重新确立了领导联邦情报工作的真正首脑——国家情报总监。国家情报总监使美国情报界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直接依托下属的国际反恐中心、国家情报委员会实施对反恐预警工作的领导,促进不同情报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情报共享。
最后,美国反恐预警机制的不足。美国已有的反恐情报预警机制尚不能有效应对“独狼式”恐袭威胁,对国际或境内恐怖组织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散播极端思想、招募人员、技能培训和经费资助等反应迟缓,无法实现有效的恐怖威胁鉴别。同时,对一些为恐怖组织提供生存空间、资源或资助的国家政权存在预警威慑不足的问题,对在出现权力真空的边缘地带发展起来的恐怖势力缺乏必要的反恐预警阻断机制。
(三)军事预警机制的启示
其一,美国军事安全预警机制主要依托高新科学技术。美国五角大楼的决策者总是能够根据军事安全预警需求的变化,利用最前沿的高新科技对军事预警系统进行换代升级。例如,以高、低轨道卫星兼备的天基红外预警系统升级原有的国防支援卫星系统,美国的全球军事预警能力又一次得以大幅提升。以更先进的相控阵雷达和数据链系统对空中预警系统进行更新换代,使其具备更早期、更精确的预警和探测跟踪能力。经过高新科技武装的军事预警系统能够对任何军事威胁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使得美国往往能够掌控军事斗争的制高点和主动权。但是,过度依赖技术手段导致其他手段在军事预警应用中的不足,实现各种军事预警手段适当的平衡才能确保军事预警机制的协调运作。

其二,不同层级的军事预警系统互为补充,相互协调。在军事预警的系统设计方面,远程预警与近程预警互为补充,天基预警与陆基预警紧密配合。最新的多轨道天基红外预警卫星系统基本上实现了对重点区域和主要敌手弹道导弹发射的全覆盖探测;陆基预警中不同探测距离的雷达系统实现了对美国本土及整个北美地区的交叉重叠式预警;再辅以先进的空中预警系统对北美东西海岸的警戒监视预警,共同构建起全高度、全天候的陆海空天一体化军事预警系统。此外,美国各军事预警系统依托数据信息平台实现彼此交接整合,形成了集合型、综合化的全球军事安全预警体系,通过促成相关的军事预警系统之间的综合预警集成,进而满足美军各军兵种联合作战和协同作战的预警需求。
(四)战略预警机制的启示
其一,美国战略预警机制既立足于阶段性战略重点,又兼顾到长远性战略需求。从阶段目标来看,美国战略预警工作的重点是评估和监测国际安全环境的发展动态,协同军事预警机制对危害美国安全和利益的重大现实威胁进行有效识别,发出早期预警,并以此支援美国的全球战略行动。从长远目标来看,美国战略预警始终是以遏制、削弱甚至摧毁战略竞争对手,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根本使命和目标。这显示出美国战略预警机制重视推动阶段性预警与全局性预警相结合、战略预警实效与战略预警规划相统一,确保战略预警机制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其他国家应该从统筹战略全局出发,根据自身的具体国情、所处的安全环境、所持的安全观念,逐步推进战略安全预警体系的建设实施。

其二,美国战略预警是一个综合性、动态性预警系统。美国战略预警并非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预警机制,而是注重与其他预警系统的融合式发展。战略预警与军事预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两者彼此融合,相互促进,有效地避免了重复预警和预警漏洞。战略预警还能有效地与反恐预警互相配合,紧密协作,实现预警情报的共享。不仅如此,美国还不断地以最新的技术手段对战略预警系统的组织领导、运行模式和探测能力进行革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战略安全环境和战略安全需求。
其三,大国崛起预警凸显美国重视维持对其他大国的战略优势,同时也显示美国仍然没有摒弃“先发制人”的冷战对抗思维。美国将战略预警的矛头指向真实存在或潜在的主要对手,这种明确的战略指向性凸显出美国十分重视获取并保持相对于其主要对手的战略优势,通过采取各种预防性措施来遏制和削弱战略对手。然而,这种针对新兴崛起国家的战略预警机制实质上是冷战安全观的延续,不仅无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安全利益,而且会进一步加剧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战略对抗,最终导致战略预警适得其反。
总之,经过近70年的改革和发展,美国已经建立一套覆盖应急安全、反恐安全、军事安全和战略安全四大领域的安全预警机制。该预警机制以预警情报为前提,通过情报传递使预警情报为预警决策和执行提供可靠的依据。美国的安全预警机制庞大却不臃肿,复杂却不凌乱,科学的领导体制、完善的运行机制、先行的预警立法、先进的预警手段使得美国能够机动灵活地根据安全环境和安全形势的变化进行动态化的安全危机预警,并不断提高应对各种安全危机的预警能力。可以预见的是,美国未来仍将致力于打造综合均衡、灵活高效的安全预警机制。
(图片来源自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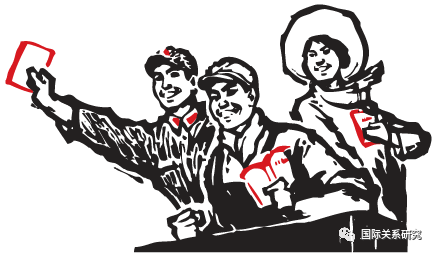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