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颖走后不久,司马颙也离开洛阳回长安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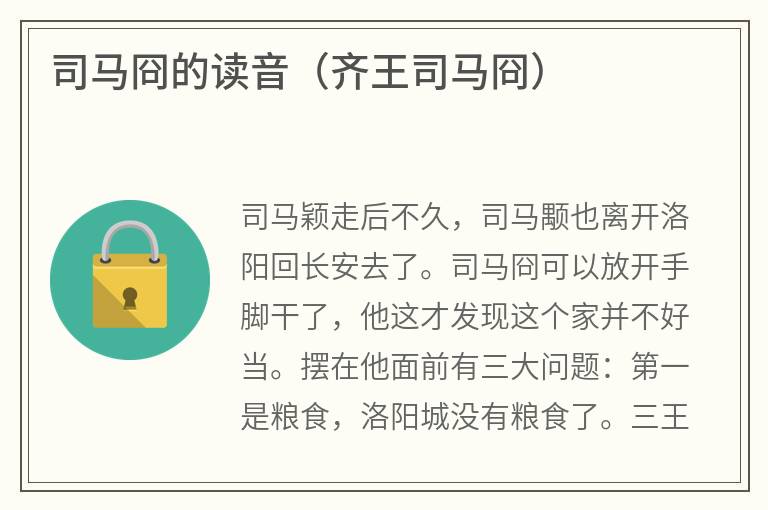
司马冏的读音(齐王司马冏)
司马冏可以放开手脚干了,他这才发现这个家并不好当。
摆在他面前有三大问题:
第一是粮食,洛阳城没有粮食了。三王会京都,几十万的士兵盘踞洛阳城三个月,把洛阳城的粮食全部耗光,再不解决,就要发生大饥荒了。
第二是赏赐,前面的各项赏赐都是针对宗室的,其他人怎么赏却没有定。倒是司马颖回到邺城,给卢志等人申请了赏赐,朝廷也批了,但是其他人呢?司马冏和司马颖一路杀过来,许多人都投奔他们,甚至当司马冏进了洛阳城还源源不断有人带着部队过来,司马冏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都照单全收了,但是怎么赏呢?司马冏这时候有点理解司马伦为什么大肆封赏了,因为大家都眼巴巴看着你呢,你吃肉,总得让大家喝点汤吧。
第三是没人,当年清理司马伦余毒,朝廷的许多官职都空了,机构运转需要人,他必须招揽人才。
司马冏作为当年老齐王司马攸最喜欢的儿子,还是比较有能力的。
针对第一个问题,缺粮那就找粮食,哪里有粮食?南方有粮食,那就从南方运。
尚书台仓部有个小官陈敏自告奋勇去运,司马冏当即任命他为合肥度支,全权办理漕运。
针对第二个赏赐的问题,司马冏不同于司马伦没有威信,全靠好处拉拢。他是从许昌一刀一枪打进洛阳城的,所以用不着滥发奖赏去讨好他们,于是他对自己手下葛旟(yú)、路秀、卫毅、刘真、韩泰等都封为县公,并称小五公,视为心腹使用,其他的就算了。
第三个问题的解决也可视同第二个问题的延伸,现在朝廷缺人,需要提拔人才,如果你有能力,可以安排官职。
当然司马冏也要先安排世家大族。琅琊王氏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王戎为尚书令,王衍和河南尹。
金谷二十四友中的人才也被他启用,例如西晋著名畅销书作家左思,这会他已经创造了洛阳纸贵那个成语,天下闻名,贾谧被杀之后,一直隐居避祸,司马冏把他拉过来就在他手下担任秘书工作。
另外两个二十四友成员刘舆刘琨兄弟因为和司马伦走得太近这时候已经在狱中了,司马冏赦免他们,委任刘舆为中书侍郎,委任刘琨为尚书左丞。
但是对二十四中陆机陆云兄弟司马冏却不喜欢,指控陆机当年为司马伦写过禅位诏书,打算处死他,司马颖出面求情,这才得以赦免,两兄弟感激司马颖,前往邺城投靠,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
除了现成的,司马冏还真是目光炯炯,发掘出许多人才,这些人走得司马冏还要远,在后来历史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试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刘殷,司马冏聘刘殷为军咨祭酒,其实就是军师祭酒,因为避司马师的名讳,改成了军咨,祭酒是首席之意,就是首席军师,当年郭嘉在曹操手下就是这个职务。
刘殷的名气在当时不在郭嘉之下,当年司马冏的爸爸老齐王司马攸和征南大将军羊祜都请过他,刘殷以生病为由拒绝,杨骏就曾经试图聘请他,他以老母年高为由拒绝,司马伦篡位的时候,孙秀也试图聘请他,刘殷吓得跑到了雁门。
这一次司马冏聘请,他答应了,司马冏很是得意问他:“为什么我爸爸请您不来,这次我一请就来。”他明里问,暗里是在炫耀,期望得到的回答显然是一通马屁猛拍。
刘殷的话说得很漂亮:“前面都是尧舜,他们能容人,所以我敢用匹夫之身抗千乘之尊,现在您杀伐在握,我若再抗命,恐怕就要有杀身之祸了。”潜台词就是我惹不起你,我怕得起你啊。
刘殷比郭嘉长寿得多,后来这些王爷们都死了,他又到匈奴人的朝廷里当大官,最后善终,在那个乱糟糟的世界里,如果不是足够的聪明,不会有这么完美的结局。
第二个曹摅(shū),司马冏聘他为洛阳令。他是《晋书·能吏传》上的人,治理地方卓有成效,他在临淄做县令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把囚犯全部放回家让他们和家人团聚,和他们约定,过了年全部回来,后来这些囚徒全都如约归来,一个跑的也没有。李世民身为皇帝竟然照抄了整个做法,用来装点自己仁慈的人设,在后世引起很大的争论。
第三个是苟晞,司马冏任命他为参军。他将在后来的纷争中大显身手,被称为晋朝之韩信、白起,本领可见一斑。
第四个江统,两年前他已经写完了一篇文章,上奏给朝廷,朝廷没有当回事,十年之后,等到狼烟四起,五胡乱华之际,大家才想起来他,纷纷感叹:“江统早预见了这一切啊。”那篇文章叫《徙戎论》,就是建议朝廷把氐人等少数民族全部迁走。现代人看来,他这观点过于偏激,不去反思西晋的苛刻统治,而把一切都推到边疆民族的反抗上去,他写出来的时候,张华还在主政,他在幽州和边疆民族打过交道,自然对这种论调不以为然。但后来西晋皇族覆灭时,看到自己悲惨的结局,许多人就把这篇文章当成了自己错过的灵丹妙药,也错把江统当做是开了天眼的人,其实如果真的按照他的计划执行了,激化矛盾,西晋将会更早覆灭。
江统本质上是个被过誉的文人,所提出来的不过是书生之见。
真正有先见之明的是司马冏聘请的另一个人张翰。他是东吴名士,为人放荡不羁爱自由,被称为江东阮籍,东吴灭国之后,他一直隐居,后来在苏州遇见了一个琴技高超的贺循,两人一见如故,言谈甚欢,贺循要去洛阳,他也就跟着到了洛阳,这会被司马冏聘请,也就当了几个月的官,秋风起的时候,他忽然想吃家乡的鲈鱼、莼羹,当即就辞官回去了。从此创造了一个鲈鱼莼羹的成语典故。
鲈鱼莼羹当然只是一个借口,更深层次的原因张翰是预感到洛阳已经成为是非之地,早晚要生祸患。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