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都在重读《古文观止》卷二左传选文,并作一些补充注释的工作。工作量很大,没日没夜一字一句地读、想、琢磨和咀嚼。
卷二共十六篇文章,我以为更比卷一要难。按照《东周列国志》蔡元放的评点说,卷二全部是外交专对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外交部的外交公文。蔡元放在《东周列国全志读法》中说“出使专对,圣人也说是一件难事。惟《列国志》中,应对之法最多,其中好话歹话,用软用硬,种种机巧,无所不备。子弟读了,便使胸中平添无数应对之法,真是有益子弟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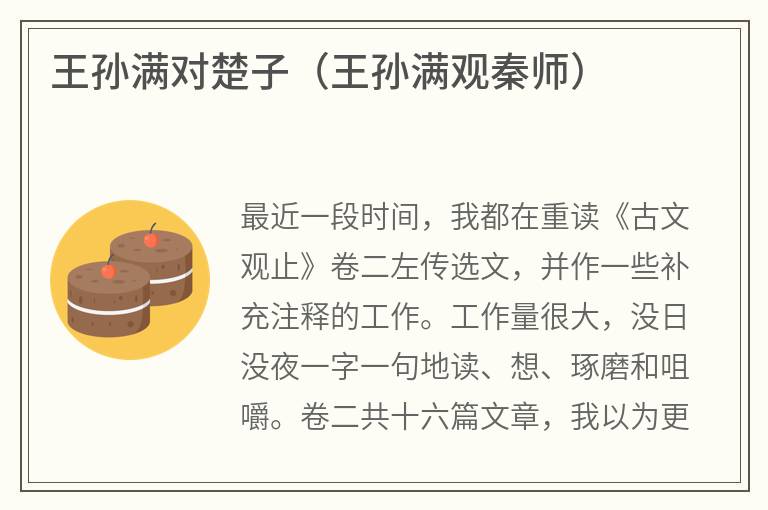
王孙满对楚子(王孙满观秦师)
大家如果认真读卷二,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人物:
有强词夺理,没理也硬要讲出几分理来的晋国人吕相,事见“吕相绝秦”;
有弱国面对强国,极尽委婉之能事,但又暗藏锋芒,最终达成己国愿望的郑国人子家、子产,以及姜戎人驹支,事见“郑子家告赵宣子”、“驹支不屈于晋”、“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子产坏晋馆垣”、“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有打仗失败去行贿求和的齐国人宾媚人,事见“齐国佐不辱命”;
有力谏夫差不能放了勾践,却被夫差拒绝的伍子胥,事见“吴许越成”;
有天下共主周王室受到挑衅,连蒙带骗吓跑楚王的王孙满,事见“王孙满对楚子”;
有高级战俘被交换回国前,被对方国君试探的晋国人知罃,事见“楚归晋知罃”;
当然,还有勇怼权臣的晏子,事见“晏子不死君难”;有妙谏昏君的子革,事见“子革对灵王”。
上述文中的人物,哪一个不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任务?当然也有少量失败的。倘若细细琢磨这些成功与失败的典型,反观今日各国之外交,不过是几千年前的翻版而已。大家可以在心里面想一想:晋国像今天哪个强国?郑国像今天哪个弱国?齐国、楚国、秦国,又都像哪个国家?
书归正传。
话说这次重读,发现了一些容易忽略的问题,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铤而走险,急何能择?
李学勤《春秋左传正义》P571:杜预注“铤,疾走貌。言急则欲荫茠(xiū,同“休”)於楚,如鹿赴险。”孔颖达疏“铤文连走,故为疾走貌。”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P536:此言小国之人若为鹿,则将如鹿之急不择路,赴险犯难矣。
杜预和杨伯峻的说法是:鹿遇危险,仓促之间疾走而奔赴险地。只是,就文章本身而言,郑子家的话是说,你晋国不罩我,我就跑去投靠楚国。楚国是险地吗?楚国难道不是另外一个能够罩住郑国的地方吗?倘若楚国是险地,那岂不是等于说晋国也是险地?
另外,按情理来说,鹿遇到危险,第一反应难道不是疾走离开险地吗?意思是说,遇险之处就是险地,鹿疾走,本能反应是离险,而不是赴险。但杜杨为什么都说“如鹿赴险”呢?有没有可能他们的意思是:郑子家对赵宣子说,我们郑国还是愿意接受你们晋国的庇护的,但倘若你们逼急了我们,情急之下,我们也会不管不顾地贸然做出决定。不管楚国如何蛮夷不堪,不顾郑国今后会不会被楚国给吃得连渣都不剩,我们也要去投靠楚国这块“险地”以赢得暂时性的安全庇护?
因此,“铤而走险”到底是“急切之间离开险地”呢?还是“急切之间奔赴险地”呢?
二、倾覆我国家
在“吕相绝秦”一文中,有一句是“倾覆我国家”。其中的“国家”,在之前的解读中,我顺手就译成了“国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此次重读,我对出现的“国家”二字有了一丝疑惑。上古文言文中,鲜有称“国家”的,要么是单音词,如“秦”、“齐”、“鲁”、“晋”等;要么是双音词,如“秦国”、“齐国”等。何以此处冒出“国家”二字呢?
坊间诸版本皆译“国家”为“国家”,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还是草率为之呢?
检索可知,上古时期,诸侯的封地为“国”,大夫的食邑为“家”。《春秋左传正义》桓公二年: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立诸侯也),诸侯立家(卿大夫称家臣),卿置侧室(侧室,众子也,得立此一官)。
上古所说的“国”,并不是我们今天中国、美国的“国”。彼时,周王室的周天子是整个世界的王,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既已拥有整个天下,当然需要治理。为了便于治理,周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份,分封给上古圣贤的后代(比如公爵国虞舜后裔陈国、公爵国商汤后裔宋国)、周王室的成员(比如周武王的同母兄弟,周公旦的侯爵国鲁国,周成王弟弟姬叔虞的侯爵国晋国)、重要的功臣(如姜太公的侯爵国齐国)和重要的方国(如夏商已经存在的子爵国楚国)。这些被分封的贵族就是诸侯,而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及政权,就是“国”。与今之联合国不同的是,分封之后,周王室仍保有最好的土地,也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只是后来,周王室渐次衰败了。
众诸侯在拥有“国”之后,把“国”分成许多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所拥有的土地及政权,就叫做“家”。这就是“子产论尹何为邑”中的“邑”,实际上就是子皮的“家邑”,或曰“采邑”。众所周知的春秋战国分界点,就是晋国被三个卿大夫给分成三“家”了,是为三“家”分晋。这三“家”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家庭”。
儒家格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为“自身”,“家”为“卿大夫之家邑”或“采邑”,“国”为“诸侯之国”,“天下”为“周王室之天下”。至于今天的“国家”连用,专指“国”而不指“家”,明显是汉语的偏正结构,虽连用,仅取其中一义耳。
此处,我觉得应该既言“国”又言“家”。但如何翻译呢?
往下看,我们发现,文章后一段还有一句是“倾覆我社稷”。大家知道,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古时候由君主代表臣民祭祀土神和古神,故此,土神和谷神就有了等同于君主的含义,而君主即国家的代表,因此,后来就用社稷来代表国家。
显然,前一段说的“倾覆我国家”和后一段说的“倾覆我社稷”是对文,即“国家”和“社稷”是相等的。国是指晋国国君的封地,家是晋国大夫的采邑,实际的意思是“国家和家邑”,类似于“社稷”是“土神和谷神”。
但翻译的时候,不能翻译成“国家和家邑”,翻译成“国家”又让人误解古之“国家”二字就等同于今之“国家”二字,故译为“我们晋国”比较合适。
是不是合适,有待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三、衣服附在吾身
在“子产论尹何为邑”一文中,有一句是“衣服附在吾身”。坊间版本皆译为“衣服穿在我身上”,之前我也没有留意到“衣服”二字。
大家知道,“衣服”在现代文中,是双音词。但在古代,“衣”是单音词,说文曰“衣者,人所倚以蔽体者也。上曰衣,下曰常。”其本义是上衣,后逐渐成为“服装”的通称,合上衣下裳而言。
而“服”字呢,说文曰“用也”,广韵曰“衣服”,但用法则如“以讼受服”,或“车服以庸”。鲜有“衣”和“服”连用的。“服”有“穿着”、“穿戴”的意思,比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朝服衣冠,窥镜”;还比如《汉书王莽传》中的“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
其实,只从单字而言,“衣”、“服”和“附”三个字均可解作动词“穿”。但显然,根据语法,“衣”不能是动词,因为它是主语。那么,“服”和“附”呢,要么“服”作谓语动词,要么“附”作谓语动词,要么“服附”二字皆作谓语动词。
有没有可能“衣”和“服”作同义连文呢?是有可能,只是这么做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因此,我选择认为这句话该译为“衣服穿着附在我身上”。我不确定这样对不对,但直觉告诉我,“衣服”连用在此处,甚是可疑。如果有人能指点一二,我将不胜感激。
这次重读《古文观止》卷二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此次事了,我近一段时间都不想再读了,实在是太费精神了。由此我也想到,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门,其工作是多么繁重啊。连圣人都觉得难的,大约就是好话歹话说尽,软硬手段用尽,对方仍一意孤行。倘若因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发文,平息了一场外交部纠纷,甚或一场战事,那真是善莫大焉。
仔细读了《古文观止》卷二左传选文,再读当今天下各国间的新闻,心中自能衡量各国应对得失,好不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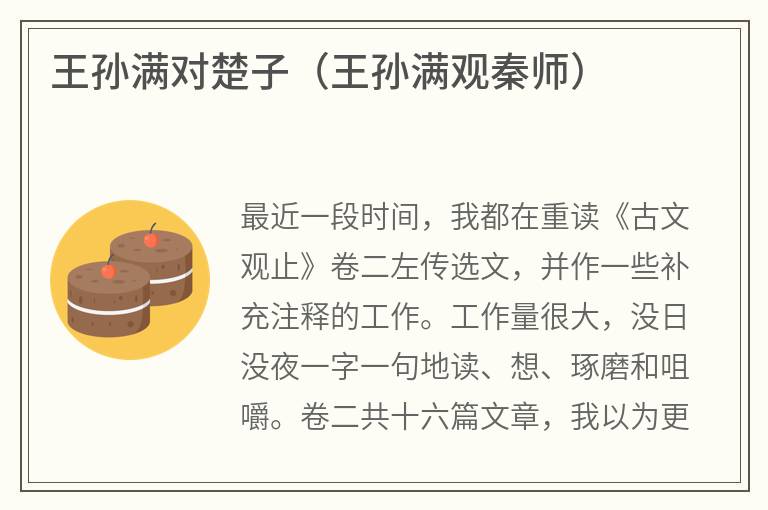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