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寂静无声,所有人都很默契地没来打扰我们。
严谨玉侧身躺在床外侧,我缩在他怀里,心疼地扒开衣服,替他吹吹伤口。

借你金口玉言意思是什么(金口玉言意思是什么生肖)
「疼吗?」
严谨玉摇头,声音干涩,「湛湛一吹就不疼了。」
他奔波数日,明显没有睡好,还经历一场恶战,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又被我激得伤心欲绝,此刻刚缓过劲儿,一句话也不多说,只知道盯着我看,只有在我问话的时候,答上一句,哪还有昔日朝堂上唇枪舌剑的威风。
我眼睛酸巴巴的,小心谨慎地给他上药,埋怨道:「你一个文臣,整天打打杀杀的,不成体统。」
以往他不知这样骂过我多少次,如今我回敬过去,严谨玉竟温和地看着我,「公主教训的是。」
嗐,这话真顺耳。
我同他讲起我在驿站的事儿,夸到小丫头聪明能干,想带她回京,严谨玉就淡淡听着,偶尔乖乖附和几句。
直到我感叹又要麻烦小丫头洗被子的时候,严谨玉冷了脸说,「被王年碰过了,扔掉吧。」
我出门在外,反倒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好歹是慕将军的一番心意,扔掉不合适吧。」
严谨玉一开始不解,随后明白了什么,蓦地僵住脸,「你以为东西是他送的?」
我一愣,「是小丫头说的——」
忽然住了嘴,小丫头当时只说是「公子」派人送来的,我下意识以为是慕将军,再一看严谨玉吃飞醋已经吃到了天上,忽然明白过来。
这货心疼我,又怕我拒绝他的好意,便趁着晚上偷偷跑来送东西。小丫头哪认识他呀,左边一个公子,右边一个公子,反正都是她不认识的男人。
我笑眯眯仰头去亲这个打翻了醋坛子的男人。
两人几日未见,又互相解开了心结,相思一触便是无比热烈,我脸颊发烫,正欲说话,忽闻见新换过的被子上清新的皂粉味儿,有点腻。
我皱眉,严谨玉发现不对,紧张道:「怎么了?」
我摆摆手示意他不要担心,随即撑起身子越过他趴在床沿上,哇地吐了。
严谨玉被我吓了一跳,天还不亮就找来了大夫。
大夫上手一摸,眉眼一舒,嘴角一咧,捋着山羊胡摇头晃脑道:「老夫医不得这个病,告知家人,准备喜事吧。」
老爷子这话说得大喘气,我一度以为要准备后事了,严谨玉吓得脸色惨白,直到他说完,还怔在原地。
他那个通晓十八般谋略的脑子俨然宕机,一脸焦急地问大夫,「谁还能治?」
老爷子摇头,「此病,九个月后,不药自愈。」
严谨玉如遭雷击,愣在当场,很久才回过味来,一双眼睛晶亮亮的,缓慢挪到我身上,「湛湛……你……」
他终不再是僵着一张脸的刻板样子,唇角压抑不住地扬起,呆愣愣地上前走两步,想碰又不敢碰的模样。
我轻轻踢他一脚,嘴角难掩笑意,「都怪你,孩子还得跟着颠簸回去。」
严谨玉小心翼翼地托住我的脚,放进被子里,继而坐在床边抱着我,小心翼翼地,生怕将我碰碎了,「怪我……都怪我……差点酿成大错……我……我……」
我看着他语无伦次的模样,扑哧笑了,吧唧亲了他一口,「严谨玉!」
「嗯?」
「我现在是母凭子贵,你以后得惯着我。」
「好。」
「严谨玉,你脸疼不疼?」
「为何这么问?」
「你当年第一次见我,说了什么?」
【并不是所有人都要惯着你。】
「臣说的没错,不是所有人,但往后臣会惯着公主。」
「严谨玉!你狡辩!」
「微臣不敢……」
番外:
王年抄家的时候,睡卧里一共搜出二十多个金夜壶,父皇气得当场踢翻了桌子,下令将王年的尸体挂在瞿洲城墙外,面向通州的方向,挂满一个月。
姝吉作为证人,要跟着回京城。
我极少看见父皇私底下这般严肃,着一身明黄龙袍,紧绷着脸坐在府衙主位上,一本正经地捋着稀疏的胡子,颇有当朝天子的威严。
姝吉被带进来时,吓了一跳,「黄……黄老爷……」
旁边的慕将军恰到好处的帮腔作势,双手抱拳举在耳侧,拱手道:「无礼!此乃当今圣上!还不速速下跪!」
姝吉扑通一声,「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父皇轻咳一声,嘴角掀起又硬拗下去,「朕——听闻王年无恶不作,便微服私访来了瞿洲。如今王年等人伏法,你需一同回京举证,朕——念你身世曲折,又检举有功,特准许你日后安居京城,朕……」
我听得犯困,睡眼惺忪地悄悄凑到严谨玉耳边,迷迷糊糊问道:「御史大人呀,父皇说了几个朕了?一定要以此来强调自己身份吗?」
父皇也太幼稚了。
严谨玉任我倚靠在他肩膀上,低声道:「刚才是第三个,圣上在兴头上,没个一盏茶的工夫,怕是消停不了,你困了我便送你回去。」
我困得脑袋点在他胸膛上,「这种荒唐事,御史大人不管吗?」
严谨玉托起我的下巴,望着我惺忪睡眼,「小女子的事儿,臣是不管的。」
我一听,瞌睡虫突然消失不见,睁大眼睛,「我想吃冰酪!」
严谨玉与我对视很久,才缓缓道:「自家小女子的事儿,臣还是管得了的。不许。」
我噘着嘴,这是我不知道第几次跟他求冰酪吃,可严谨玉看得严,一口都不许我碰。
我委屈的指着肚子,小声道:「其实不是我,是他想吃……」
严谨玉无动于衷,「子孙孝敬尊长,不利于你身子的东西,他便是馋,也得忍着。」
我被他堵得没话说,叹息一声,「哎……孩儿呀,为娘熬过了你爹的折磨,日后就换你了……」
那馋虫被勾起,怎么也抹不下去,我窝在严谨玉怀里左右扭动,寻不出个舒服的坐姿来。
严谨玉低头,叹息一声,「祖宗,你消停些……我……总泡冷水也吃不消的。」
我一愣,猛地将脸伏进他颈下,生怕被别人瞧见我红透了的脸皮。我被王年惊着,这一胎险些不稳,有些事,最苦的还是严谨玉。
我唇角弯了弯,忽然抱着严谨玉的胳膊,泪汪汪地抬起头来,「御史大人,万一……万一是个姑娘呢?」
严谨玉被我带偏,竟然很认真思考起这个问题,我趁热打铁,「我肚子里的小姑娘告诉我,她就吃一口……爹爹答不答应嘛?」
严谨玉轻咳一声,移开目光,半晌道:「那便只吃一口。」
于是从那时起,我就盼着肚子里能生出个姑娘来。
回京的路上,父皇一扫心中阴霾,开始抓姝吉过来喋喋不休,「朕当年见过一个小宫女,被人推到井里淹死了,还有被药毒死的,被人发现的时候浑身发青,你这么蠢,朕断言,你进去就是个死,你就说朕说的对不对吧?」
姝吉欲哭无泪,点头如捣蒜,「圣上所言甚是。」
「你之前还说朕吹牛,朕可是实话实说。」
「民女愚昧,有眼不识泰山……」
到后来,父皇把姝吉念叨烦了,她抱着父皇的大腿,泪汪汪道:「求圣上把我丢去坐牢吧,我有罪!请您按律法处置我。」
回京之后,意外得知严老御史也回京了,当初大婚之后,我在庄严肃穆的老爷子面前坐立不安,后来与严谨玉发生了龃龉,便没再去。
前不久严老御史回了趟老宅,如今人在京中,正把好消息告诉他。
回京第二日,我和严谨玉回了严家。
彼时我尚未显怀,坐在严谨玉旁边,低着头不敢看老爷子。
「你说什么?」老爷子问严谨玉。
严谨玉坐姿端正,一板一眼道:「湛湛有了身孕。」
老爷子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对着严谨玉低沉道:「你跟我去祠堂!」对我说话的时候温和了一点,「公主吃菜,老臣有几句话要嘱咐谨玉。」
我忐忑不安地看了严谨玉一眼,他给我夹了菜,小声道:「乖,我去去就来。」
我知道祠堂一般是进不去的,也不是什么大喜的日子,难道严谨玉犯了错……要挨手板或家棍?严家家法森严,他……他旧伤未愈,可不能再添新伤了!
我腾地站起来,问了丫鬟祠堂的方向。一路匆匆追过去,祠堂门外,我忽然停住,严谨玉正跪在里头,腰板挺直,老爷子铁青着脸,我进也不是出也不是。
当初我执意嫁给严谨玉,未曾尊重过严老御史,他对我不满意实属正常,可严谨玉不能跪着呀……
随后,我便听到严老爷子气得骂他,「你个混账,南巡那样大的事,你竟不知收敛……路上让公主怀上了,你有没有想过她一个柔柔弱弱的姑娘家受不受得住!君子发乎情止乎礼,我教你的都喂了狗了?」
严谨玉低着头,「父亲教训的是,儿子知错。」
「我听闻公主在通州被歹人挟持,必然受了惊吓,如今可是大好了?我瞧她席间吃得甚少,你上点心,别整日盯着皇帝那些破事,他一把年纪了还让儿孙辈替他操心,我呸!」
老爷子和我父皇真是积怨已久。
「夫人,您怎么站在这儿,此处风大,快进去吧。」严府的下人都认识我,此刻好心提醒,不料里头两位都听到了。
我十分尴尬,两只脚一前一后跨进门里,在门口站定,惴惴不安地看着老爷子。
老爷子轻咳一声,冷着脸道:「你先起来吧。」
严谨玉谢过老爷子,站起身子向我走来,握住我的手,「不是让你在前厅好好吃饭么?手冷成这样,瞎跑什么。」
我越过严谨玉的肩头,生怕老爷子再罚严谨玉,扯出一个甜甜的笑,「爹爹,我带了几壶梅子酒来,您尝尝?」
老爷子蓦地一怔,脸上浮现出几分不自然来,「那……那便尝尝……」
我没看错的话,老爷子笑了。
老天爷,严谨玉的性子竟然随了个十成十,都是吃软不吃硬。我明白后,席间处事便得心应手起来,一口一个爹爹的喊他,把老爷子哄得眉开眼笑,最后喝醉了被小厮搀出去的,边走还边笑,「丫头啊,以后常来看看爹爹。」
我喝不得酒,全是严谨玉替我,如今他微醺,两眼朦胧,软倒在我肩上,「湛湛,我从未后悔娶你。」
「谁信你呢……」我推了推他,推不动,「你胸中有雄韬伟略,若不是我要你做驸马,你便是前途无量的人。」
严谨玉蹭着我的头发,热气和酒香吐在我耳畔,缓缓道:「我不争功名,有些事,私底下做也是一样的。」
若非他喝醉了酒,这些事他是绝不对我说的。
我其实隐约明白一些事儿,父皇对这桩婚事乐见其成,有些大事,却还是委任严谨玉来做的,明面上他人看不见,自然无法论功行赏,严谨玉碍于身份,无法掌权,将来父皇百年之后,皇兄之间的争斗便波及不到严谨玉身上,严谨玉太平,我便一生顺遂。
单看前不久回京后,严谨玉参平南伯府的折子一道接着一道,气势冷冽,狠辣无情,很快,定了逆臣平南伯秋后问斩。
父皇是白白得了个死心塌地的谋臣,为他鞠躬尽瘁毫无怨言啊。
可谓一箭双雕的好计策。
严谨玉说,他不争功名。
更不如说,他爱我,所以为了我,他放弃了功名。
严谨玉白白吃了这么大一亏,我必然不会善罢甘休,是以转天,我进宫,打劫了父皇。
「你给钱!」
柔妃娘娘端着汤盅与我擦身而过,飞快地向院子里逃去。刚端上的汤,她一口咬定凉了,再去热热。
父皇头摇得像拨浪鼓,「没钱……一分没有……」
我一掌拍在桌子上,「你白白占了我家谨玉那么大便宜,官我们不要了,你给钱!赏大笔的银子!」
父皇胡子抖了抖,「这……湛湛啊……严谨玉他自愿……」
「他老实!我也老实?」我叉腰,抬脚垫在凳子上,「南巡多危险的事儿啊,我家谨玉身上的伤一条条的,现在都没好,你说这话还有没有良心!」
父皇吓得赶忙扶我坐下,「湛湛啊,你还怀着身子……别激动别激动……」
父皇身边的公公走进来,低声道:「圣上,严老御史和严御史在御书房等您呢。」
柔妃适时地端着汤盅再次出现,欣喜地唤人,「哎哟,快来人啊,来人啊!圣上吃好了,恭送圣上。」
柔妃这次将我和父皇一并锁在了大门外。
父皇:「……」
他现今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回走着,「怎么都来了……湛湛,你能不能领严谨玉回去?」
我面无表情道:「给钱。」
父皇怜惜地挑起自己掺了白的头发,哀戚道:「湛湛啊,父皇老了……在你不知不觉中……」
「说什么都不好使,把钱给我我就走。」
后来,御书房里又爆发出了激烈的对骂。
严老御史和父皇争得面红耳赤。
我被严谨玉牵着,坐在一旁,捧了碗热茶小口抿着。这种小场面我和严谨玉都司空见惯了,实在没有劝架的必要。
「朕把女儿嫁过去,就是要你!家宅不宁!」父皇指着严老御史,气得满面红光。
严老御史龇牙咧嘴,暴跳如雷,「你失算了!人家现在一口一个爹爹的叫我!不知比在你家里乖多少!」说完扭头企图得到我的支持。
我捂着茶杯,甜甜喊他,「爹爹!」
严老御史笑开了花,「哎!」
父皇气得咬牙切齿,「湛湛!父皇呢?父皇呢?」
我扭头,也甜甜喊道:「父皇!」
父皇顿时神气十足。
末尾啊,我从父皇和老爷子手里拿到了双份的红包,离开争执不休的御书房,领着严谨玉高高兴兴回家过日子去了。
番外(严谨玉篇):
十岁那年,我第一次在御花园里见到宋湛。
一个粉团儿般的小人儿,因为一只兔子哭闹不止。皇宫的人因为她闹翻了天,她是个被惯坏的孩子,与我接触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她发现了我,本来泪眼斑驳的她眨了眨眼睛,对着我伸出手,「哥哥,抱。」
她似乎对谁都不设防,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皇宫里,我很难相信她能平安长大。不知不觉,心软了一些,嘴上却不饶她。
「因一个人,搅得皇宫鸡犬不宁,实非一国公主应有作风。」
我出言告诫,本是好意,她却不领情,给了我一脚。
这个小丫头,真是不可理喻。
我不屑于跟一个小丫头作对,可后来,她盯死了我。
每每随父亲进宫述职,我总能碰见她,她总是喊我「喂」,生气的时候,喊我「严谨玉」,她觉得我事事循规蹈矩,企图以一己之力纠正我。
可严家的孩子,自小被付与沉甸甸的责任,哪里有时间同她玩乐。公主就是公主,食百姓俸禄,却能高枕无忧。
严家在京城的口碑不太好,因为父亲太过耿直,我出门在外,难免遭人白眼和讥讽。
十四岁那年,我被人堵在巷子里,惨遭毒打。父亲不许我与人动手,要我秉持君子风范,因此即便我能将他们吊起来打,也只好乖乖站在原地,任人欺凌。
宋湛那日经过巷子口,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瞧见我,又旁若无人地转过头去,彼时她出落得十分标志,娇媚动人,京中不乏苦等她及笄的少年。
我知道,她不是见死不救,而是为我保留体面。
我原以为此事就此揭过,后来京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宋湛把侯府和其他几家的公子哥儿打了,严重到需接骨大夫挨个上门的地步,我心里一惊,那几个正是把我堵在巷子里的人,一个不落。
宋湛的名声彻底毁了,一时间成了人人畏惧的恶女。
我后来找到她,问为什么,她轻蔑地看着我,「看他们不顺眼,打就打了,还需要原因吗?」
她就像个炸毛的刺猬,浑身是刺。
后来,我慢慢长大,入朝为官。
那几个公子哥儿似乎恨上了宋湛,明里暗里羞辱她,我私下里用过一些手段对付他们,可架不住宋湛明面上的报复,几次甚至到了要他们命的程度。
其实她不需要出手,我来就行。
我几番出言劝阻,尽是被她冷眼瞪回来。
「严谨玉,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她总是笑着问我。
「圣上为公主的婚事忧心已久,公主难道一点也不在意自己的名声?」我凝眉,有些恨铁不成钢。
宋湛一听,噢了一声,「不然你娶我?」
她看似开玩笑,我心里却一突。
她和我一起长大,我了解她的脾性,偏执、任性、不听劝阻,可以说,她像一朵灿烂盛放的花儿,明媚娇艳,却带着刺儿,严家不是好土,如果嫁过来,我无法想象之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
可我也知道她护短,正如她自己说的,严谨玉只有她可以欺负,其他人统统滚蛋。我想问问她眼里的短,是什么意思,亲人?朋友?还是心悦之人?
我对她说,「你尽管试试。」
我真是疯了,宋湛是个与严家格格不入的人,圣上问我时,我却没有拒绝,我那时心里便想着,宋湛因为替我报仇败坏了名声,我娶她理所应当,却忽略了心里一闪而过的窃喜。我从不与女子接触,以往那些大家闺秀红着脸站在远处看我,便让我想起母亲,她的人生算不得顺遂,永远坐在小小的隔窗下,看着外面的天,末了埋没在严家一成不变的枯燥里,直到死去。
宋湛是不一样的……鲜活又明艳。
她被我的挑衅激怒,不久便请了圣旨来,得意扬扬地对我说,「你恭恭敬敬到我府上磕三个响头,我便放过你。」
我没有理她,确切地说,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何要反悔?说到底,我已经存了一些小小的算计。
大婚之夜,宋湛便开始挑衅我的理智。
我在洞房外,听见她对侍女说,「婚订了还可再退,结了可以合离,再不济可以休夫,若是严谨玉待我不好,走便是了。」
她倒想得通透,可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圣上在酒里下药的事我是真不知道,被宋湛撺掇着,稀里糊涂的春宵一度,我开始懊悔自责。这些年我对她的感情,并不全是厌恶,一场醉酒,让我看清了压抑多年、自欺欺人的心思。
我是向往光明灿烂的人,而她恰恰是这种人。
这样自私与卑劣的小心思,我不敢让宋湛知道,我也不想放她走。
后来,我发现她是个嘴硬心软的人,我因朝政忙得脚不沾地,深夜回房,她总能替我留个门,点一盏小灯。我冷落了她,她会跟我抱怨,会耍小性子,温存之时,却像妖精般诱人,我变得不像自己,几次上朝,圣上喊我,我都没听见。
她愿意陪我去严家,在意父亲对她的态度。可那日在席间,看到她束手束脚,手足无措,我后悔了,也害怕了,我想起了母亲,小心谨慎地过一辈子。宋湛不可以。我要她好好待在公主府,严家不必再来。
说话的时候,我惹怒了她,叫她会错了意,她气跑了,恰逢圣上传我入宫,有些话,当下没有解释出来,便没有更好的机会了。我想,误会就误会吧,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宋湛没两天,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松了口气。
她一来找我,我心神便不自觉为她牵动。
后来她在巷子里,把平南伯府的公子打了,我又气又怕,圣上将她养得很好,不知险恶,我则是圣上为她精心挑选的驸马。可那一刻,我好怕自己护不住她。她不知道平南伯是什么人,亦不知道圣上为了拔除这颗钉子费了多少心计,用过多少手段。她就那样把人打了,我气她莽撞无知,可她红着眼,委屈地跟我说,谁都不许欺负我的时候,心莫名地软了。
其实不怪她,她知道为我好就够了。
我说,总有别的法子。
对付平南伯的事,交给我来。
后来南面几股势力开始不安分,时机成熟,圣上准备南巡。
忙起来的时候,索性住在宫中,方便与圣上商议政事。
她似乎埋怨我没有陪她,端着满满一罐核桃仁儿跑进宫里,后来我尝过,回味甘甜,不多时便吃得见了底。我对着小罐哑然失笑,她便好好待在京城罢,倘若南巡平安回来,我会叫她明白我的心意。
严于律己多年,到底是不适应对心爱之人说一些肉麻情话。我做什么都快,唯独在倾诉衷肠这样的事上,慢得很。连一句「我心悦你」,都无比困难。
我觉得需要离开一段时间,理清思绪,随圣上南巡就是个很好的机会,为了避开她,我与圣上合谋演了出戏,差点将她骗过。
可在城外听见她的声音时,我像个被发现的逃兵,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心意。原来人的自制力,在情爱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
她娇娇软软地抱着我的时候,哭哭啼啼对我撒娇的时候,甚至生气瞪着眼叫我严谨玉,我都觉得她无比惹人喜爱。我喜欢逗她,看着她被我说得手足无措、面红耳赤,便心动难抑。
我忘却了父亲的教诲,沉迷温存无法自拔,我觉得有个孩子挺好,至少她不会再想合离的事儿。
可后来,我发现自己一发不可收拾。
我为官多年,清正廉洁,正道公允,这些为人称颂的品质,在宋湛身陷危境时,全部化作齑粉。案子要查,宋湛我也要保。无论查不查得清,我不敢赌圣上的心意。宋湛在民间积怨已久,圣上亦是帝王,安知不会为了平息民愤,将她推上去。
世间太多冤假错案,断不清,办不明。
我不要宋湛做万千里的一个。
我听见府衙外有人喊着处死公主。
好几回,都是同一个人藏在那儿,真是该死。
我忍无可忍,提剑出去,杀了他。
这是我第一次违背公道,我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人。
我一意孤行地利用职权之便扣下证据,既然缺了银子,我便将它补上,我要宋湛毫发无损地从案子里走出来。
正如我对宋湛说的,「有时候,掩盖比澄清更容易。」
后来平南伯府被牵扯出来,背后更多势力不足为外人道。圣上拿着我伪造假证的证据,坐在桌前,昏黄的烛光照不出他的表情。
他说,「严谨玉,你可知罪?」
「知。」
「那便留你一命,将功补过。」
「……朕要湛湛,永不窥得世间丑恶。」
「圣上所愿,亦是臣之所愿。」
平南伯府背后是谁,又是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将罪名扣在湛湛头上,她无须知道,未来数十年,我和圣上,会慢慢收拾。
后来,我听闻噩耗,王年去了驿站。
那一刻我骇得神魂俱散,等我回神,已经站在血泊里,周围横七竖八的全是尸体。她歇斯底里的喊叫让我慌了神,进屋便看见王年正图谋不轨,我给了他一剑,掀开他,抱紧了我日思夜想的湛湛。
我害怕到浑身颤抖,如果她出了事,我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她说要离开我。
我们之间终是藏了太多误会,小到我的一句话,大到她的清白,我通通需要解释。
「我爱你」三个字总是太单薄了。
在嘴边绕了许多回,终是变成万语千言,全部讲给了她听。
我想她明白了。
我,严谨玉,爱她入骨,至死不渝。
直到她任我抱住,我哭了,失而复得的喜悦击垮了我心底的担忧和不安,老天爷待我不薄,我们有了孩子,我很难想象将来会有一个女儿,跟她母亲一样活泼讨喜;或者是个儿子,眉眼像她,性子像我。
无论怎样都好,这辈子陪在宋湛身边的,只能是我。
产后小番外:
我生肚子里那两个时,费了好大一番力气。
产婆说我骨架娇小,又是罕见的双生儿,生产时不亚于鬼门关走一遭。
当时我疼得满身是汗,一波又一波的绞痛自小腹紧密的传遍全身,我已经哭不出声。
产婆脸色不好,「都这么长时间了,才看见头。公主,您加把劲儿啊。」
我倒是想加把劲儿,将严谨玉的胳膊都抠出了血,严谨玉面如死灰地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喊我「湛湛」。
他也没想到,我这一胎,藏了俩。
一儿一女。
产婆抱着一双儿女,满脸堆笑的对我和严谨玉道:「公主驸马有福,是龙凤胎。」
严谨玉脸色白得吓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生孩子。
我有气无力地埋怨他,「御史大人可真厉害,一下子便儿女双全了。」
严谨玉满脸后怕,「湛湛,不生了,以后都不叫你生了。」
产婆见我俩都不理她,抱着孩子找父皇报喜去了,屋里只剩我俩。
「你文采好,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严谨玉想了想,「明喧,婉婉。」
一个动,一个静,他大概是想让两个中和一下。
后来,那两个也确实承了他们爹的意愿,蓬勃生长。
严家小公子严明喧,成了遍京城最能闹腾的公子哥儿,人都说,刚正不阿的严御史养出个纨绔来,整日里嚷着惩恶扬善,却回回被他爹提着领子回去打。
严家嫡女严婉婉,活生生像她爹的翻版,整日里不苟言笑,是京里有名的冷美人。
是日,刘大人携夫人和眼眶乌黑的爱子找上门来,我一瞧便知是明喧的杰作,当即派了人去唤严谨玉。
两个孩子一对质,才明白刘家公子近日不知从哪儿惯了个调戏丫头的毛病,言语间对婉婉颇不尊重,明喧一气之下,给了他一拳头。
我生了孩子后,脾气好了不少,刘夫人瞧我好欺负,嚷嚷道:「那也不能打人啊!」
刘大人胡子一吹,「正……正是!」
明喧多少还是怕严谨玉的,缩着脖子不说话。婉婉则跟他爹一样,沉着脸,面无表情。
严谨玉破天荒没有对明喧出手,反倒一字一句问道:「尊夫人此言差矣,令郎逞口舌之快,可曾顾及过小女的感受?」
我冷哼一声,「本公主觉得,驸马所言极是。」
刘大人被我一点,才察觉自己是在跟一家子皇亲国戚说话,顿时心虚不已。
刘夫人在气头上,「我们不过动了动嘴,您家可是动手啊!」
刘大人去拉她,被她甩开,叉腰撒泼道:「皇亲国戚也不能不讲道理!」
婉婉忽地站起身,走到明喧跟前。
「姐!你别害怕!我给你出气——」
「咚!」
婉婉一拳头打在明喧眼睛上,砸出个乌青来。
那力道我瞧着都疼,严谨玉和没事人一样,我都怀疑他和婉婉串通好了。
明喧哭唧唧地嚎叫,「姐!你打我干什么啊!」
婉婉冷着脸扭头看着刘大人一家,面不改色道:「够了吗?」
刘大人见闹得这般尴尬,点头道:「够了够了……」
严谨玉紧接着道:「既如此,咱们来说说动嘴的事儿。」
论嘴上官司,当今朝中,无人能胜严谨玉。
我可是生平头一回看到严谨玉以势压人,捂着嘴笑得浑身打战。
刘大人一听,吓得脸色刷白,「哎……御史大人言重了,不过是小孩子玩闹……」
明喧这会儿也反应过来,气得跳脚,「你等着!本公子明日定要把你调戏姑娘的丰功伟绩发扬光大!让全京城都知道!」
末尾,刘大人带着妻子理直气壮地来,灰头土脸地走。
明喧委屈吧啦地来找我,「娘……喧儿痛……要娘吹吹……」
严谨玉忍无可忍,提着领子一把将他丢出去,冷声道:「回去将『丰功伟绩』默一千遍,弄明白意思再来见我。」
严明喧一脸难以置信,「爹!我是在反讽啊!您上个月还拿这个讽刺别人呢!」
严谨玉不理他,砰关上了门。
一番热闹看得我乐不可支,严谨玉走过来抱住我,「公主笑够了吗?」
我上气不接下气,「御史大人好生威武,不战而屈人之兵,湛湛好喜欢。」
严谨玉脸色稍霁,抱着我准备小憩一番。
我知道他是丢下公事匆匆赶回来的,疲惫全写在脸上,顿时有些心疼,其实我完全可以蛮不讲理地将刘大人一家扫地出门。可严谨玉喜欢讲理,渐渐地,我便甚少动用自己的方式了。
「严谨玉,以后你若忙着,便着人知会一声,我学着处理。」
严谨玉看着我,眼底温柔而平静,「不,湛湛,严家这般热闹,我很欢喜。」
严谨玉大我七岁,许多年过去,岁月没有在严谨玉脸上留下一点痕迹,他举手投足间,反倒愈加沉稳冷静,叫我移不开眼。
我心脏怦怦直跳,脸一红,嘟哝道:「怎么年纪越大越会撩拨人呢?」
严谨玉一顿,沉吟道:「公主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微臣失察,让公主失望了。容臣将功补过。」
他一把抱起我来,我吓得手忙脚乱攀住他脖子,「我……我不是在说你老啊!」
严谨玉淡淡觑我一眼,「噢。」
「也没有说你不行的意思。」我连忙解释。
「公主金口玉言,说什么都晚了。」
——完——
文章名称:《谨衣玉食》
主页小说都是各处搜来的,途径比较杂,有写文章名称和作者名字的会标注,等不及更新的也可自行搜索观看哈,如有侵权,请联系我删除哦。不常在线,不能及时回复消息还请等等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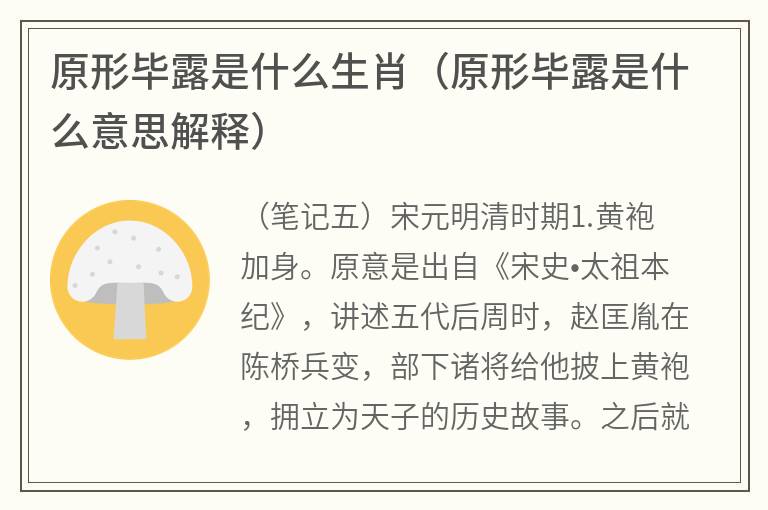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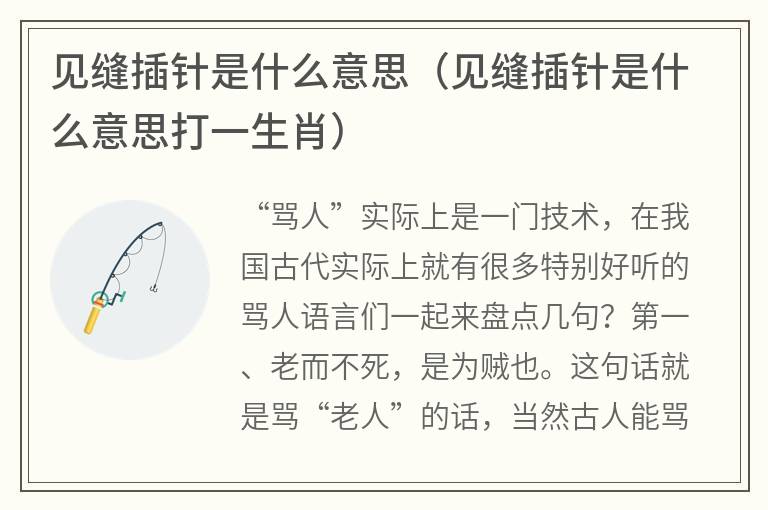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