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妓女是社会所认定的无贞无德的薄幸花草,名妓画家最初也仅被认为是善画的妓女,而非画家。因此,无论是游离于社会伦理外的职业身份,还是难以逆转的性格缺点,皆是名妓画家与普通画家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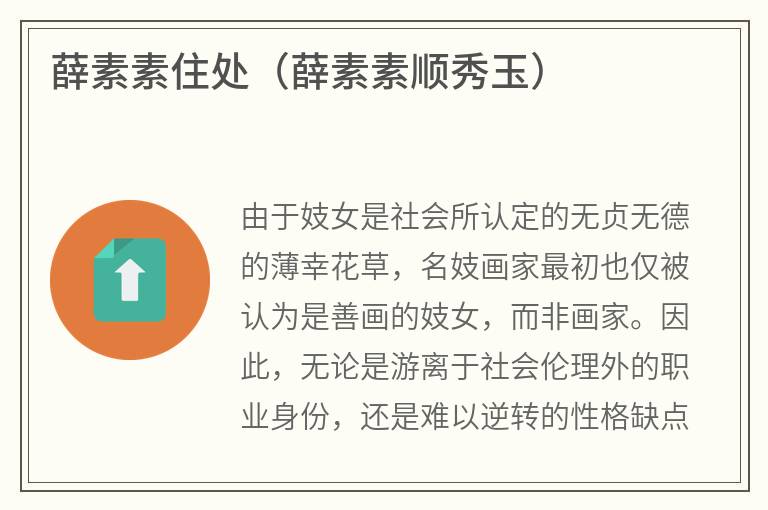
薛素素住处(薛素素顺秀玉)
但也正因这样的身份,让晚明的名妓画家们脱离了古代社会对女性生活的约束,跨立于看似不相容的女性私人世界与男性公共世界之间,承载着这一性别层面的自由,名妓画家打破了传统的性别意识与刻板印象,调和了文人画的风雅意趣与女性的感性意趣,具备着跨越性别审美情趣且独具一格的绘画艺术风貌。
晚明时期的青楼名妓,需要通过学习文人化的生活、交往方式,从而进入男性文士的生活中,进而增加自己从良的机会。因此身处青楼文化下的名妓群体对文士有着多方面的依赖,不得不选择在衣饰、打扮、生活乃至审美上对文士进行讨好与依附。
在名妓的绘画方面亦是如此,名妓画家们通过在学画过程中摹习文人画作,接受文人墨客的指点,来掌握文人画的笔墨技法与情趣,进而表现出对文人画审美情趣的研习与继承。
纵观晚明名妓画家的传世绘画作品,从题材选择到笔墨表现,不难看出名妓画家们皆以在画中展现文人士气为荣,追求脱离女性的闺阁气质,对文人化的艺术风格有着不懈地追求。
在花鸟画方面,以梅、兰、竹、菊四种花卉为母题的四君子,是名妓画家在花鸟画作中最常使用的题材,其中又以象征着圣洁素雅的兰花最受名妓画家们的喜爱。
如以画兰而闻名的马守真,墨兰兼具文人的野趣与女性的柔美风韵,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马守真《兰竹图》折扇上写满的题跋看,其风格鲜明的兰花深受文士们的热烈追捧。
由于马守真在文士间巨大的影响力,晚明名妓画家间逐渐形成了画兰之风,但与名妓画家对兰花的创作热情不同,四君子中的竹,通常仅在名妓画家的笔下与兰花或石头组合出现,多是用以衬景的细竹。
晚明时期,董其昌通过提出“士气”与“南北宗论”的理论,将文人画与院体画完全分离,在画坛大力提倡追求自然天趣的文人画。
早年的《兰竹石图》中兰花采用双钩白描,转折较硬;后方的细竹以墨笔画出,竹叶以浓墨轻点而成,略显呆板;最后方的矮石皴擦兼备,从画面中对墨色的大量运用,不难看出马守真早期画作中摹习文人画笔墨的努力。
在马守真中年创作的《兰竹湖石图》中,以墨笔画兰竹,后方湖石皴擦简淡,下方苔草信笔点染,笔墨粗放,线条流畅,兰草杂而不乱,墨竹穿插得当,飘逸而不失章法,展现出高超的文人画笔墨技法。
从马守真的画作变化中不难看出,名妓画家自最初学画就已开始对文人画的笔墨韵味进行摹习,并随着画技提高越发清晰地展现出文人画的笔墨技巧与意趣。
尽管名妓画家们在晚明青楼文化的熏陶下,深受文人书画的滋养,奠定了画作中文人化的笔墨基础,但随着名妓性情的变化、个人的成长,以及在士妓交往中境遇、心态与情感的改变,名妓画家在绘画中逐渐展示出区别于文人意趣的一面,或是在笔墨中融入女性情趣,或是以感性浓烈的画面展现自我浓郁的情感。
总之,晚明名妓画家以非凡的笔墨才能和独特的才情表现,以画言情,极具浪漫情怀,展现出了男性文人画未能呈现的细腻情感。
名妓画家在追随文人化笔墨表现的过程中,逐渐开拓出全新的,以展现身为女性的才情意趣为目的的笔墨形式,形成了兼具文人士气与女性柔美气质的独特风格。
《设色灵芝兰竹图》在笔墨上以工写结合的方式画成,兰花以双钩浅设色为主,墨笔竹草点缀。
画中九丛兰花坡石各具意象,同时又紧密相连,墨笔兰竹与岸石小草点染随性,颇有文人气韵,双钩的兰花则用笔细致,又不失随意,独具风格,婉转的叶片以浓墨细笔流畅画出,敷以浅色,生动又不失天趣。
马守真在画卷最后一丛兰花中,独具匠心的将最左侧的叶片与其他伸展的长叶区分,画以向上挺拔的姿态,并在中间多次转折,在最高处又向右侧弯转斜出,宛若一名优雅的女性舞者挥袖起舞的姿态,自然生动,饱含天趣,展现出融合于画中的柔美而不失逸气的独特女性情趣。
由于名妓身份的特殊,境遇多变,因此名妓画家在画作中展现出的情感心态也是丰富而多变。其中,最为常见的情感表达是对从良后幸福家庭生活的希冀。
画面由梅花、水仙、瘦石组成,瘦石伫立在最前方,石后的水仙向上方四散,开得正盛,梅花枝干被石头遮挡,如同从石上长出一般,枝干曲折蜿蜒,顿挫有致,点点梅花错落其间,水仙以白描双钩画成,向上伸展,充满朝气,梅花错落有致,枝干以墨笔侧锋擦出,曲折有力,瘦石先以墨笔勾勒后淡墨渲染,再以浓墨点染皴擦,厚重坚实,画面以简练坚定的笔法画出,既有蓬勃朝气又不失似水柔情,笔法秀美而不失逸气。
结合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另一幅画面风格相似的《湖石水仙图》,亦是将水仙置于巨石背后,用坚硬的巨石对比出水仙的娇柔,不难看出薛素素不愿以风尘身份终老,对于从良与婚姻生活的坚持与执念。
名妓离开风尘从良后,面对的是传统的家妾身份与闺阁生活,相对于以往长期生活的市井街道,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变化,但因从良心切,名妓在从良后基本都选择规避外人,展现出家庭的一面。
明代中期,王阳明融合传统儒家及禅道精神,提出了更符合时代追求的阳明心学,确立本心的地位,并展示着其以自我本心为导向的美学思想。
这一美学思想在晚明时期发展为文人画独抒性灵的美学宗旨,进而打破了过去理学的局限,标榜在画中展现最真实浓郁的主观感情与自主独立意识。如徐渭的《水墨牡丹图》,完全舍弃形似,以大写意笔墨点染花头枝叶,以墨代色,花瓣内深外浅变化丰富,笔意潇洒自如,画面狂放不羁,点点墨块表达着画家性情中的最为自得不拘的一面。
再如文徵明的《兰竹图卷》,画有近十组兰竹石的组合,兰花、兰叶以淡墨画出,婉转自然,墨色浓淡适宜,运笔流畅丰富。墨竹皆以浓墨侧锋点画而成,潇洒劲健,背景草石以干笔枯墨勾画皴擦,再辅以荆棘溪流穿插其间,萧疏幽冷的环境映衬出画中兰竹的清雅幽淡,表现出文徵明最为真实的高洁性格与作为文人的安逸雅致之情。
两者的画面表现虽大相径庭,但无不都体现着画家自身最为真实的性格与情感,显现了晚明时期阳明心学对文人画的深刻影响。
名妓画家在对文人画的吸收学习中也同样继承了独抒性灵这一美学思想,且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在画面中蕴含着更加浓烈、真挚、并且展现真我的情感意识。
此画作于顾眉在秦淮畔边经营眉楼之日,正是画家际遇最盛之时,而画中兰花盛气的形象也无不在印证着画家的傲岸之气。两段兰花皆以浓墨勾画而成,生机盎然,地面以枯笔皴擦,辅以浓墨点染草石。
其中一段兰花右侧被石所遮挡,石头以枯笔勾出,中间留白,苍劲老辣,与后方繁密的兰花形象对比鲜明,另一段兰花独特的裁取边角之景,但仍不失生机。
随风飘扬的兰花生机勃勃,笔墨飘逸不失坚韧,兰叶粗细相宜,画面中饱满的自信张扬的情感与洒脱不羁的笔墨,无疑是顾眉在遭际绝佳之时,张扬性情的真实展现。
与此同时,顾眉在构图上也是独具匠心,分别通过石头的遮挡以及不完整的兰花形象,表达着自我的不完整,展现出作为名妓希望从良的个人情感。
但无论顾眉在画中展现的是身处青楼巅峰的张扬自信,还是作为名妓而自发地对从良的希冀,皆是借文人独抒性灵的美学思想,将自己的真挚的真我性情凝结于画中,借此展现出浓烈而真实的情感。
不同于文人画中以男性视角出发的情感,名妓画家们多从个人生活出发,结合作为女性的特殊审美与心灵感悟,在画中忠实地表达着内心的独特情怀与性情,展现出对至真至纯美学精神意义的追求。
如李因的两幅《荷鸳图》通过其中所蕴含着的不同感情,真实展现出画家内在的心理变化与感情发展。作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荷鸳图》轴,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面由右侧高挑的荷花与下方的雄鸳组成。
精致白描的荷花与浓墨渲染的荷叶之间对比鲜明,画面笔墨秀美,背景大片空白,下方有少许的水纹,孤独的雄鸳与低垂破败的荷叶使画面显现出鲜明的萧索之态。
李因在画中展现出的萧败态势与崇祯年间时局的动荡不无关系,面对曾经人声喧嚣的城镇市井化为兵戈抢攘之地,在混乱时局中难免不为夫君的生活感到担忧。画中孤独的雄鸳与萧索的景色皆表现出李因在乱世下对世间的无奈,对生活的忧虑,以及对夫君的祈愿。
名妓画家借脱胎于文人画的笔墨,以及直抒性灵的画面情感,在绘画艺术中进一步融入自我浓烈真挚、至真至纯的情感表达与精神意义。
相较传统文人画更为含蓄婉约的画面表现,晚明青楼名妓的绘画艺术中饱含着真我精神,从而为晚明的女性绘画开拓出了全新的绘画情感新天地。
尽管名妓绘画常被看作文人画系统中不起眼的附庸,实际上却是饱含着名妓画家独立的情感与审美鉴赏价值。
名妓画家从文人画系统中汲取文人潇洒的笔墨风格与寄兴的精神内涵,进而在画中融入私人的、感性的情感韵味与画面趣味,大胆地展现自我感性意识,追求至真至纯的美学精神,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文人画的画面风貌,可以说,名妓绘画将女性情感融入传统文人画系统,为明代画坛融入了独特的生机,促进明代绘画丰富多样的表现力。
此外,名妓绘画中蕴含的独特情感,真实展现出了女性在晚明乱世生活中的苦辣酸甜,侧面揭示出晚明时期市井社会中的女性生活最为真实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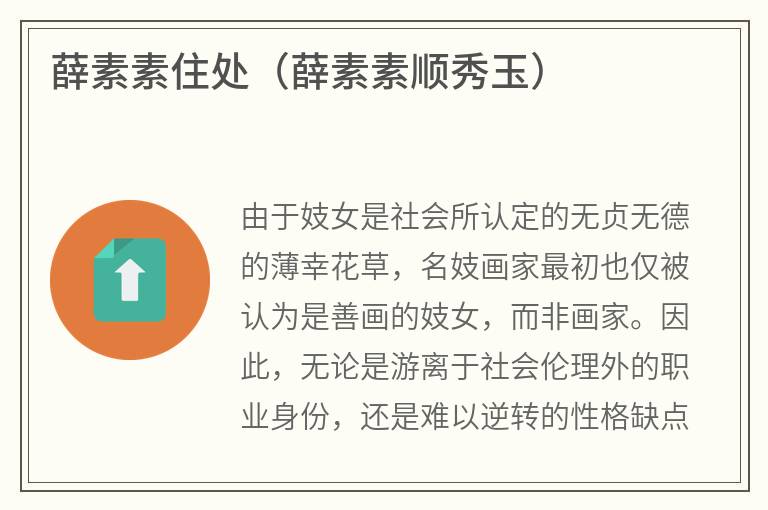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