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珍珍
关键词:哈德逊河画派审美理想自然心灵介入

赫德岛(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哈德逊河画派(HudsonRiverSchool)是19世纪(活跃于1830年至1880年)的美国风景画派,也是美国艺术史上第一个独立画派。该画派以托马斯·科尔(ThomasCole)、亚瑟·布朗·杜兰德(AsherBrownDurand)、费雷德里克·爱德文·丘奇(FredericEdwinChurch)等为代表,致力于描绘美洲的自然风光,因早期主要描绘哈德逊河沿岸风景,故被后人称为“哈德逊河画派”。自然景观是该派画家的主要题材。他们对自然的描绘,蕴含着一个宏大的审美理想,即通过艺术呈现新大陆的原始荒野,激发观者的审美体验、情感共鸣,以审美洞察人与自然、上帝间的原始关系,肯定个体原初、无限的创造力,而这都隐藏于该画派多样、新颖的艺术形式中。
感知荒野的多样与无限
哈德逊河画派的画家们乐于将个体感官体验引向丰富的自然荒野中。在他们眼里,美国荒野是最有价值的描绘对象,他们以写实的风景画及关于自然的心得笔谈,描绘着对其的思考,这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19世纪初的美国在文化上依旧是欧洲的学徒。绝大多数的美国画家都有着旅欧学画的经历,追随、模仿着欧洲的绘画风格与题材,如华盛顿·阿尔斯顿(WashingtonAllston)的《约翰·金博士》(Dr.JohnKing,1814)、《为伯沙撒的盛宴而学习》(StudyforBelshazzar’sFeast,1817),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West)的《维纳斯哀悼死去的阿道尼斯》(TheDeathofGeneralWolfe,1819)等,都能明显看出是对当时欧洲绘画重人物肖像、重宗教历史的模仿,缺乏民族特色。英国杂志嘲讽道:“试问四海之内……又有几人观看美国戏剧?抑或欣赏美国绘画、雕塑?”〔1〕这让美国学者备感焦急,爱默生指出如今美国处处“都依赖英国,很少有(自己的)一首诗、一个版面、一份报纸”,〔2〕“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3〕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急需独立的艺术风格与题材。
事实上,美国通过学习欧洲文明来复兴民族艺术之路是徒劳的。美国早期绘画(即历史画)难以根植于美洲土壤,“它在人民中没有根基”。〔4〕历史画需要艺术家、观众具有坚实的人文修养和历史沉淀,这都是建国不过百年的美国所缺乏的,因而不会引起民众共情。1855年,一篇题为《艺术常识》的社论言明了这一事实:“让我们记住,绘画的主题……是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你对它们没有爱,你就不可能对代表它们的画作有真切的感受……我们爱自然和美——我们钦佩在作品中演绎它们的艺术家。”〔5〕在美国,有别于欧洲文明的原始荒野才是促其实现文化、艺术独立的真正倚仗。
受泛神论与宗教世俗化影响,他们普遍认为心灵与自然都“是由上帝的意志决定的”〔6〕,有着不言自明的原始关联。丰富多样、有机再生的原始荒野是上帝意志的可见形式,也是心灵创造力的可感图像,而这些已被欧洲文明所丢弃。1835年,科尔在《美国风景随笔》(EssayonAmericanScenery)中写道:“在文明的欧洲,风景的原始特征早已被破坏或修改……但自然仍占主导地位……因为自然之手……以比人类之手所触及的任何事物更深邃的情感,影响心灵。在它们之中,随之而来的联想是关于创造者上帝的。”〔7〕因此,他自豪地指出美洲荒野“比欧洲文明的任何成就都更为古老”〔8〕,因为它的原始性正将心灵引向造物主的意志。1836年,爱默生在《自然》(Nature)中,又重申了原始荒野脱离历史传统却饱含启示的精神价值。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一种并非传统……拥有并非他们的历史,而是对我们富有启示的宗教呢?大自然的生命洪流环绕并贯穿着我们的身躯。”〔9〕它指向原初心灵如上帝般的创造力。“自然美在人的心灵中改造它自己,不是为了毫无结果的沉思,而是为了新的创造。”〔10〕这意味着美国自然独特的荒野面貌,不仅是实现国家文化独立的突破口,更蕴含着重要的审美目的:在对荒野的深入感知中,激发心灵原初的创造冲动,促其回归与自然、上帝的原初联系。
受欧洲浪漫主义、爱默生的影响,他们将诗意感知运用于美洲荒野,在直觉、联想中扩展对其的体验,发现被忽略的形式。在画作中,他们设法呈现荒野微妙的色彩层次,吸引观者注意常因光线角度、距离重量等因素忽略的细节,甚至看似丑陋的枯枝杂草、毫无生气的石头也被他们囊括进画作里,以此丰富观者体验。就像科尔的《吉尼斯风景》(GeneseeScenery,1847)与杜兰德的《在林中》(Inthewoods,1855),他们细致地描绘倒下的枯枝及其断裂的截面、每根树枝扭曲的形状、树皮上的斑驳,甚至树叶摆动,尤其是《在林中》,松针尖锐的触感、苔藓潮湿的气味等代表原始自然的蛮荒气都得以有形呈现。细看科尔的《吉尼斯风景》,还能体会到画家对自然色彩的敏锐捕捉。远处的山谷、丛林甚至天空因处于背阴面而呈现灰调,作为前景的瀑布、枯枝因沐浴阳光,则呈现出黄棕色的质感。而被阳光直射的自然面,科尔则大大加强了色泽的透明度,使其具有白调的光泽感。更为用心的是,两幅画作的布局都有意设计低矮歪倒、不会阻碍观者视野的自然前景,从而清除观者与画作的距离与障碍。观者不是抽离在外的审视自然,而是人在其间的亲密接触,以此确保“我们同可感知的事物打交道”〔11〕不受阻碍。这种对荒野多样形式的探索成为画家们的共同意识。
亚瑟·布朗·杜兰德在林中布面油彩154×122厘米1855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而为了感知荒野更多样、新颖的一面,他们积极走出画室,走入人迹罕至的山川丛林,将心灵感知具身化为一次次行动,在行动中,让荒野景观去激发心灵的创造力。他们是“徒步旅行者和登山者,对其而言,绘画是一种运动艺术”〔12〕:科尔曾徒步数百英里、穿越过数十座未开发的山脉,杜兰德曾去过卡茨基尔山、伯克郡、缅因州及北美东北部的诸多地区,乔治·宾汉(GeorgeBingham)则深入科罗拉多州、加利福尼亚州等未开发的山川河流,丘奇甚至穿越了美洲大陆,足迹远至南美、南极……悬崖峭壁、原始森林、火山极地、热带雨林等罕见奇观激起了画家们心灵多样的情感体验,他们掏出锡制的管状颜料,直接作画,将其付诸于笔端,成就了西方美术史上罕见的荒野系列。〔13〕而这些画作在纽约、波士顿、费城等画廊一经展出,立刻便被哄抢一空。事实证明,别样、新颖的自然荒野能够唤起民众的情感共鸣。
深化对荒野的感知,除了发掘其审美广度,也在探索其审美长度。自然无限、创生的本性足以达到持续刺激心灵的意图。对自然无限性的洞见,出现在地质学的研究中。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科学技术与绘画艺术同时迅猛发展,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等学科的出现,正以其专业知识,介入未开化的自然。有趣的是,自然科学并没有消减艺术家们对自然的浪漫想象,反而增强了他们在自然中感受创造力的信念。在这里,不得不提及地质学家莱尔(CharlesLyell)所做的突出贡献,他的地质研究为艺术家们无限延展了地理时间,以科学的方式证实了当下的荒野化石是创世的印记、天赐的财富。如希区柯克(Hitchcock)所言:“地质证明他(上帝)是不变的,在过去的漫长时间里……地质学为上帝的仁慈提供了许多奇特的证据。”〔14〕这让浪漫的诗人、画家兴奋异常:对美洲处女地的浪漫想象,便是在探索原初的创造秘密,便能感知心灵原初的创作冲动。地质发现满足了艺术家们对自然无限感知的欲望,也正因此,莱尔在19世纪的美国文艺界非常受欢迎。〔15〕爱默生在《日晷》(Dials)中提及了莱尔访美讲座的盛况,画家们则在他的启发下创作了诸多表现美洲地质面貌的画作,如科尔的《埃特纳火山》(MountEtna,1842)、杰西裴·弗朗西斯·克罗普赛(JasperFrancisCropsey)的《美国瀑布,尼亚加拉州》(AmericanFalls,Niagara,1855)等。
相较于无机、固定的地质构造都能展现自然的无限,有机生长的自然植物则更能显出自然动态变化的过程,实现对心灵的不断滋养。受柯勒律治、歌德等欧洲浪漫派影响,画家们普遍接受植物是有机的(organic),它与人的生命历程可相互类比。科尔则以组图的形式将个体心路历程与自然四季意象相捆绑,在周期性的变化中延伸着自然的审美长度,也实现着对心灵、生命、文化的思索。在《童年》(TheVoyageofLifeChildhood,1842)中,“清晨的玫瑰色光线、繁茂的花草是早期生活快乐的象征”,〔16〕童年的孩子就像春天的暖阳,自带天使般的光环,有着富足的创造灵感。而到了《青年》(TheVoyageofLifeYouth,1842)、《成年》(TheVoyageofLifeManhood,1840),原初的想象力、创造力逐渐远去,在对其的找寻中,个体既收获创造的喜悦,也品尝着失败的滋味,就像夏天繁盛的草木与骄阳,秋天阴冷的气候及衰败的草木。直至《老年》(TheVoyageofLifeOldAge,1842),天使又重回心灵,引领生命实现救赎,获得圆满,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新系列的最初事实”。他们珍视在原初荒野中,生命所展现的无限更新、富有宗教般救赎的力量,因为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更大的可能性”,上帝“在我心中”。“在自然界,每时每刻都是新的,过去总是被吞没,被忘却……除了生命,变迁,奋发的精神,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17〕生命的价值就在永无止境的创造中。
创造诗意的理想自然
随着对自然持续、全面的感知,心灵无限的创造力被逐渐激活。在充满创造力的心灵面前,自然便不是描摹对象,而是创造的载体,它是精神的形态而不是物的枝蔓。这是19世纪的艺术家们宏大的审美构想:在感知自然的同时,完成着对它的诗意洞见与二次创造。爱默生指出“在风景画里,画家应当提示一种比我们所了解的还要美好的创造”,“因为它表现了一种对他有益的思想”,“他将会重视这种对自然的表现,而不是自然本身”。〔18〕科尔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自然中的真实是指——自我实现、圆满……去创造事物,创造它们的对象和目的”,“是对自然所建议的原则的执行”。〔19〕从这个意义而言,他们与其说是想恢复心灵与自然、上帝的原初关联,不如说是对上帝造物过程的创造性重构,是对心灵体验的不断更新。心灵活动无限接近上帝造物时的思想动态,这便是创造的过程。
而缺乏对该画派深层体认的观者,或许会认为他们的画作不过是一些过时的、对自然细致入微的写实模仿,尤其是随着现代摄影、照相技术(航拍、广角镜头等)的广泛应用,再无需画家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去寻觅、观察自然细节。〔20〕从物理真实的角度考虑,哈德逊河画派还不如普通的家庭照片更能记录美洲的自然风光,因而有些观者认为该画派的成功得益于摄影技术还未普及,这显然是对该画派的误读。如弗莱克斯纳(JamesThomasFlexner)所言:“哈德逊河画派的审美并不寻求我们今天所说的摄影复制。”〔21〕该画派要寻求的是与心灵相符的“精神”自然,它隐秘于画家的精巧构思中。
在构图上,哈德逊河画派努力营造一种和谐整一感。画家们对自然细节的写实处理最终在画作上呈现出和谐的关联,并且细节与整体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艺术操作,而是一种内在情感将它们紧密整合在一起。这不是主观臆断,吉福德(SanfordRobinsonGifford)就明确指出画作应具有“统一的必要元素”,以此给观者留下单一情绪,而“在哈德逊河画派和透光派的各种画作中,都可以识别出这种和谐的统一或合理的总体感觉”。〔22〕画家们在对自然零散且持续的经验中,寻求统一性,发现单一的情感特质,这似乎是对杜威“整一经验”的图像说明,就像在《艺术即经验》中,杜威说过“使得一个经验变得完整和整一的审美性质是情感性的”。〔23〕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相较于杜威在经验层面发掘情感特质、促成经验完满,画家们则更希望能超越自然多样、连续的表象形式,达到形而上的本质同一、上帝造物般的精神完满。换句话说,该画派受爱默生的超验思想影响,看中的是能够推动自然意象超越自身经验物性、洞见精神的诗性崇高感。
选择崇高作为心灵的推动力量,画家们不是盲目的。就词源而言,崇高一词的拉丁文是sublimis,源于两个词根“抵达”(sub)和“门楣”(shawl),意为人的视线在空间上超越自身高度,它的转义指向超越性〔24〕,这非常契合他对心灵不断更新、创造自然的情感期待。他们对心灵的创造力充满信心,使其不会如伯克(EdmundBurke)般,将崇高与痛苦、恐惧等负面情绪或可怕、可憎的事物相捆绑。在画家眼里,在富有创造力的心灵面前,自然不是可怕、有害的,“人要比他看到的自己更加伟大,而宇宙也不像人想象的那样恢宏”。〔25〕他们重塑了自然所带来的崇高体验,将其与喜悦、宁静、沉思等有益状态相联系,就像科尔在给杜兰德的信中所写,“一种宁静祥和的精神笼罩着大地。这是和平、精神性的、吸引人的崇高”,是“沉思的崇高”。〔26〕
在画作中,他们常常选取“云”作为构图中心,去营造高远、愉悦的崇高情感,比如马丁·约翰逊·赫德(MartinJohnsonHeade)的《纽伯里波特草甸》(Newburyportmeadows,c1872—c1878)、《佐治湖畔》(LakeGeorge,1862)等,都是描绘“云”的典型。在《草甸》中,赫德刻意压低了地表基线并选择平坦无垠的草地,让画面至少三分之二都被毫无树木、山峦阻隔的云层占据。在辽阔的天地间,地面以其微弱的占比,仿佛顷刻间就要被云层吞没,而在画作的左上方,也正有浓密的乌云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但有趣的是,观者丝毫不会生出暴风雨来临的紧张、压迫感,因为透过云层的阳光正宁静地拂过每一寸青草,为草地镀上一层暖黄。乌云并没有让地面蒙上一层深灰,草地反而呈现出如春日般温暖、静谧的色泽,草地上低洼处的积水透着草甸的倒影,水面丝毫没有风雨来临前的波澜,这些处理让气象学家惊呼画家们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而这恰恰说明,画家们自始至终所遵照的便不是自然的物性真实,而是在创造的自然中所蕴含的情感真实:在远观辽阔的天地时,内心油然而生的平和与欢愉。
赫德通过一抹阳光,消解了暴风雨等景观可能带来的恐惧,使画面营造出直抵心灵的暖意,这也是该画派传递崇高感的常用方式,像丘奇的《芒特迪瑟特岛海岸风景》(Coastscenemountdesert,1863)、克罗普赛(JasperFrancisCropsey)的《日落,鹰崖,新罕布什尔州》(Sunset,eaglecliff,newHampshire,1867)等,便是以“太阳”作为核心意象,让整个画作笼罩在辉光中。无论是初升的太阳,还是夕阳的余晖,“太阳”都是画作的圆心,普照着自然万物。在《海岸风景》中,朝阳耀眼的光线给予了灰黑色的礁石一层透亮的光晕,仿佛可穿透厚重的岩层。《日落》中的夕阳将断崖、枯树等残败之物都染上了浓密的橘色,而橘色正是最暖的色彩,它代表富足和喜悦,这或许就是对爱默生说的“面对自然,他胸中便会涌起一股狂喜,尽管他有自己的悲哀”〔27〕,最好的注脚。
费雷德里克·爱德文·丘奇芒特迪瑟特岛海岸风景布面油彩92×122厘米1863美国沃兹沃思艺术博物馆藏
由于对太阳、光线及其与云层、断崖等关系的执著关注,哈德逊河画派在其发展后期也被称为“透光派”(Luminism)。Luminism的词根lūmin,译为“光”,Luminism表示与光线相关的绘画艺术,因而也有学者将其译为“辉光派”“光线主义”等,本文之所以未参考前人译法,是因为“透光”一词最能体现该画派真正的艺术风格及喜爱“光线”的本质原因。先说艺术风格,透光派对于光线的运用集中于“透”而非“亮”上。他们让阳光照射于画作中的某一事物(如山崖、礁石、云朵等),并以其穿透力使得事物原先的阴、暗本色瞬间被光线击穿,呈现出透明的质感。也就是说,透光派要表现的不是事物被光线照亮,而是被光线穿透〔28〕,这在与同时期的法国风景画派,即巴比松画派(Barbizonschool,1830—1880)的比照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巴比松画派的代表柯罗(JeanBaptisteCamilleCorot)、纳西斯·迪亚兹(NarcisseDiaz),在其作品《草木葱茏的半岛》(Woodedpeninsula,1865—1868)、《枫丹白露森林中的一片阳光明媚的空地》(AsunlitclearingintheforestatFontainebleau,1868)都描绘了阳光下的自然景色,却很难看到画家对光线穿透力的运用。画作中,阳光普照着自然万物,其色调呈现出均衡感。而上文提及的赫德的《纽伯里波特草甸》、丘奇的《芒特迪瑟特岛海岸风景》则能明显看到在阳光穿透乌云或礁石处,光亮度显著高于别处,近似透明,强抓眼球,甚至连克罗普赛那幅描绘夕阳的《日落》,光线也丝毫没有失去了穿透力,同样能够感受到照射于“鹰崖”崖间的光线明显更通透,几近于天空般明亮。而画面上那些不仔细观察都难觅的云朵,更因阳光的透射,完全贯穿了“太阳”的色泽。这都足以说明他们对光的透视情有独钟,而究其原因,源于他们对自然美的本质理解。
云与太阳既是激发心灵崇高感的意象,也是实现画作透视目的的载体,它的双重性暗示着哈德逊河画派的美学逻辑:在创造的自然中,通过激发心灵的崇高感,从而洞悉心灵与自然的本质同一。受新柏拉图主义、爱默生等影响,他们普遍认同多样的自然形式最终都会指向同一本质,即无限的心灵,因为“整个宇宙都是灵魂的客观外化,是属于心灵的,真善美统一在灵魂中”。〔29〕相应地,由无限心灵所创造的自然也必能体现这一“精神”本性,真善美都融于自然中。画家们理想化地消解了柏拉图的诗哲之争,将哲人的使命转为自己的创思目标。科尔在评论中写道:“真善美的构思和再现是诗人的首要目标,画家也应如此。”〔30〕杜兰德在《书信》中也表示艺术的本质体现为对自然真理性的描摹。这说明画家们对自然的创构隐藏着巨大的审美理想:洞见自然或心灵的本性。
而“透视”便是他们的洞见手段。受爱默生影响,他们认为当心灵洞察到真善美的本性时,具体事物都会褪去形式、颜色的包裹,“所有低级的、属于自我的一切都消失了”。凭借“透视”,有形有质的物质世界(theworldofmatter)会转变为无形无质的意义世界(theworldofmeaning),〔31〕自然或心灵本性是通透的。于是,画家便以光的透视,以近乎透明的自然事物去呈现这一洞见状态,在诗意的透视中创造出理想化的“精神”自然。但事实上,理想的光线难以透析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里,自然的命运不是诗意的,充满着尘世事功。
人工介入后的自然命运
科尔曾痛苦地感慨道,美国人需要的是物质而不是思想,他是对的。〔32〕哈德逊河画派创造的诗意自然及其倡导的抽象观念,很难与工业快速发展、物质欲望不断增长的时代相适应。在19世纪的美国,随着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人们不断感受着商品经济、技术生产所带来的便利,重实用、重事功的扬基人(Yankee)似乎更愿意接受物质满足,而不是去荒野探求自然精神,就连科尔也不得不承认“有教养的人在社会中所发挥的能力,这仍然比荒野更重要”。〔33〕诗意自然并没有为物质生活、机器生产预留位置,而美国快速迈入技术文明的步伐却在实际中破坏着自然的诗意。对此,托克维尔敏锐地觉察到,他说:“一个人在穿过这些绚丽荒野时所感受到的一切,就像在弥尔顿的《天堂》中一样,是一种安静的钦佩,一种温和的忧郁感,以及对文明生活的模糊厌恶,一种原始的本能……事实就像已经发生一样确定。再过几年,这些密不透风的森林将会消失。”〔34〕数年后,这一预言得到印证。据记载,为修建铁路,每天约有12.5万英尺的木料用于采矿铺路,每年净消耗10.8万根绳索和4000万英尺的木材……而这些物料都出自于加利福尼亚“取之不尽”的原始丛林。〔35〕此外,为了出行便捷或减少修路成本,人们举起斧头、开山劈树,破坏原始地貌,为其强行嫁接铁路、桥梁、公路等人工景观,人类正成为美国荒野的终结者。〔36〕从原始荒野、诗性自然到工业景观,自然因人类工具的介入而发生破坏性剧变,他们推平了曾引以为豪、视为上帝恩赐的丛林山川,推平了辛苦建立起的艺术风格,更推平了民众基于自然而来的精神信仰。这让哈德逊河画派陷入沉思,其思考的核心便是人类对原始自然的介入问题。
对此,画家们的态度是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故不妨从他们创构诗意自然这一共同基点出发,逐步展开其对人类介入自然的多种倾向。在诗意自然中,他们将人类的介入方式主要框定为审美静观。作为传统美学概念,“静观”在古希腊时期便已出现。毕达哥拉斯说过:“人生就好比一场体育竞赛,有人像摔跤者那样在搏斗,有人像小贩那样在叫卖,但是最好的还是向旁观者的那些人。”他所言的“旁观者”,在塔塔尔凯维奇看来,就是具有审美态度的人,看重的是无功利的美感经验。〔37〕随后,康德则更为详细地论述了审美经验的静观内涵。康德认为只有观者与鉴赏物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才会产生愉悦感,才能产生审美体验。他说:“我们只想知道,是否单是对象的这一表象在我心中就会伴随有愉悦,哪怕就这个表象的对象之实存而言我会是无所谓的。”〔38〕这就意味着,审美体验不涉及个人欲望,例如当静观者欣赏原始森林时,想到的不是如何铺成铁轨为自己提供方便,因为对美的感知与对象的实存性毫无关系,它与以实用、功利等为目的的行为相分离。但这并不是说,审美静观与介入相矛盾。相反,作为审美经验,静观本身便是一种介入形式,“是一种不欲占有对象的、超脱的、敬虔的心态”,如学者所言:“一种审美经验必然既是静观的也是参与的。”〔39〕
这在哈德逊河画派的作品中能感受到。在其看来,自然美源于个人的审美静观,而不是有目的的“寻觅”或物欲的满足,这也成为哈德逊河画派的共识。在该画派的大部分作品中,并未出现人的身影(如上文提到的科尔的《埃特纳火山》、克罗普赛的《美国瀑布,尼亚加拉州》等),观者对作品的审美知觉使其进入作品世界,进入到自然静谧、整一的诗意风貌中。在这里,人类是对自然的静观者、朝圣者,他们能凭借感官去体验自然,引发共鸣。自然是人类的伊甸园,是原始创造力的有力证明,会对心灵起到净化、升华作用。而即使画作中出现了人的踪迹,人对自然也依旧保持静观,就像在《眺望大海》(AlfredThompsonBricher,lookingouttosea)、《曼斯菲尔德山素描》(SanfordRobinsonGifford,Asketchofmansfieldmountain,c1858)中,个体驻足于自然奇观前,瞭望那宽广的海面、巍峨的山脉,其内心感受到油然而生的崇高、平静之感。换句话说,画中人的存在烘托了自然的美学价值,个体心灵仿佛是受到自然的情感召唤,从而不自觉地走入其间。静观是人类介入自然的诗意姿态,也是哈德逊河画派思考介入问题的基准。
不过,与康德将审美与实用、功利截然二分不同,哈德逊河画派并不拒绝生活经验的介入、人对自然的物用参与。他们认为日常经验、自然物用有助于产生个体的静观冲动,及至摆脱经验物性,达到心灵无限的创造力。或许是因为,此时人们的物欲、经验还不具备破坏自然诗意的可能,又或许是因其对心灵力量足够自信,他们愿意将物性经验囊括进诗意自然中,《在卡斯卡皮迪亚河钓鲑鱼》(Salmonfishingonthecascapediacriver)、《由密苏里来的毛皮商》(FurTradersDescendingtheMissouri,1851)、《佐治湖畔》(Lakegeorge,1862)等作品就描绘了悠闲的渔民、晚归的船夫及运输货物的商人。画作依旧具有透亮的光线、宁静的湖面和高远的云层等该画派显著的意象特征,并且依旧没有让人成为构图的中心或主角,即便在《商人》中,看似商人居于画作的中心位置,也有只黑猫与人作伴,仿佛在说人与动物平等的栖息于自然的怀抱中。人作为自然的有机部分,就像石头、树木、湖水一样出现在风景画中,接受着自然的教养。这就是他们的态度:自然物用是滋养心灵的馈赠,人类的劳作行为可将其与整个自然相关联,“让人经过类比的方法领悟物质与精神的联系”。〔40〕在这种情况下,画家们没有排斥生活经验对自然的物性介入。
乔治·加勒伯·宾汉由密苏里来的毛皮商布面油彩73.7×92.7厘米1845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但很快,历史便给了哈德逊河画派一个奇妙的讽刺:在科学技术与自然精神同时发展的19世纪美国,对物用自然的认可使得个体欲望获得了合法甚至神圣化的光环。人类开始肆无忌惮地介入自然,满足自身的物欲,当机器生产、工业产物进入原始自然后,原先的自然景观便惨遭摧残。不过,哈德逊河画派是乐观的,他们寄希望于心灵无限的力量,就像感知原初自然、创造诗意自然一样,认为人类也能在蒸汽火车、铁轨公路间,恢复心灵与自然的原初统一,“把人工和违背自然的东西重新归于自然”。〔41〕铁路纵横、商场林立与田园乡村、丛林湖泊并没有实质差异,都不过是佐证心灵价值的事实依据,不会改变自然的精神事实。于是,画家也把它们融进了画作里。克罗普赛(JasperFrancisCropsey)的《斯塔鲁卡高架桥》(StarruccaViaduct),乔治·英尼斯(GeorgeInness)的《特拉华水峡》(DelawareWaterGap)以及杜兰德的《(文明的)进程》(Progress)都包含了工业文明下的新事物,并毫无违和感的融入在充满诗意的自然中,尤其是《斯塔鲁卡高架桥》,火车横穿整个画面的中心,车头冒出的蒸汽与天空上的云层融为一体,象征着工业文明与自然理想实现了平衡。
但细看画作,便能感觉到这种平衡暗含着画家们对工业文明的不信任感。画作中的公路、火车头、高架桥、大坝几乎都分辨不清,模糊地隐藏于自然景色的包围中。从构图的比重而言,画家们都对原始景观做了大占比的处理,像在《(文明的)进程》中,画面左侧、上方甚至右上方都被原初自然所占满:被闪电击毁的树木、满山谷的落叶,蔚蓝的天空,透亮的阳光,甚至是丛林里攀岩的印第安人,都展示着上帝创造的古老自然。而仅有画面的右下角,拥挤的安排着进步时代的新事物:人工的花园、汽船、密集的人群……仿佛随时可被裁去,都不会影响任何感官体验。而该画作《(文明的)进程》以为题,则显得有些讽刺,甚至隐隐流露出对工业机器进入荒野的反感,就像当时的研究者所说:“最近,蒸汽和美术勉强相识。现实和理想一起抽过烟斗。铁马和飞马肩并肩,并驾齐驱,像训练有素的一对一样,齐刷刷地喘着气。这种结合会有什么结果,天知道!”〔42〕画家们既有将工业生产经验融入诗意自然的乐观心态,同时也流露着对机器进入荒野的质疑与反感,这种矛盾的姿态源于哈德逊河画派折中的审美意识。他们不像叔本华那样,是彻底的静观论者,批判科技理性对文化的戕害,主张审美静观可以“使我们摆脱了意志的催迫”〔43〕;也不像杜威那样,想要彻底改变“静观”传统,将生活经验与审美经验相联系,在经验层面恢复个体对自然整一的审美体验;更不像马克思那样,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从生活实践处追问道德精神价值。他们既希望个体通过审美静观顿悟自然的精神性,又想凭借心灵的本质力量为物性生产提供依据。这样,人既可以享受科技便捷,又不会丢失精神信仰,而这过于理想化了。
心灵的力量并非是无限的,在现实自然面前,它无力扭转工业生产对自然文化内涵、个体精神信仰的摧残,只能发出对其无声的控诉。科尔的画作便是最好的例证。1836年科尔创造了《初秋,观卡茨基尔山》(ViewontheCatskill—EarlyAutumn,1836—1837)。六年后,他又重返故地,以同一视角绘制了另一版本《卡茨基尔山间的河流》(RiverintheCatskills,1843)。两图一比照,便会发现原先前景中茂密、翠绿的树木不见踪迹,左下角刚刚成长起的小树,也仅留下被锯断后的木墩,地上掉满了“无用”的枝丫。“这两幅图展示了从理想到现实的更务实的相遇,从神话时代到人类时代的一些进步。对科尔来说,现实充满了辛酸。”〔44〕而他的帝国组图更体现着这份辛酸。在该系列最后一幅《帝国历程:毁灭》(TheCourseofEmpire,1836)中,画面前景被一个将要毁灭一切的人所占据,他以前倾姿态将观者领入战斗,电闪雷鸣、火光四起,房屋桥梁瞬间坍塌,人类建造的辉煌毁于一旦。他将其对机器生产的反感转化为电光火石的诅咒,因为它们毁灭了自然的诗意。他说:“不是我想让他(杜兰德)痛苦,而是想让他和我一起对所有崇尚金钱的功利主义者进行诅咒。”〔45〕这预示着哈德逊河画派关于人类诗意介入自然荒野,维持审美静观理想的溃败。“一个暂时结合了自然和文明的理想,最终注定要转变成一种以机器和技术形式著称的美国艺术。”〔46〕
〔1〕SydneySmith.“ReviewofSeybert’sAnnalsoftheUnitedStates,”TheEdinburghReview,vol.33(1820),p.79.
〔2〕TheJournalsandMiscellaneousNotebooksofRalphWaldoEmerson,volIV.EdsWilliamH.Gilman,RalphH.Orthetal.,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0-1982:297.
〔3〕吉欧·波尔泰编,赵一凡等译《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2页。
〔4〕OliverW.Larkin,SamuelF.B.MorseandAmericanDemocraticArt(BostonandToronto:Little,Brown,1954),p.31.
〔5〕TheCrayon,I,No.6(February7,1855),81.
〔6〕同〔3〕,第26页。
〔7〕ThomasCole,“EssayonAmericanScenery”(1835),inJohnMcCoubrey,ed.,AmericanArt,1700–1960,SourcesandDocumentsintheHistoryofArtSeries(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65),p.102.
〔8〕DavidSchuyler.SanctifiedLandscape:Writers,Artists,andtheHudsonRiverValley,1820-1909,p.9.
〔9〕同〔3〕,第6页。
〔10〕同〔3〕,第19页。
〔11〕同上。
〔12〕JamesThomasFlexner.ThatWilderImage:ThePaintingofAmerica’sNativeSchoolfromThomasColetoWinslowHomer.NewYork:DoverPublications,1970,p.90.
〔13〕NicholasGuardiano.AestheticTranscendentalisminEmerson,Peirce,andNineteenth-CenturyAmericanLandscapePainting.London:TheRowman&LittlefieldPublishingGroup,Inc.2017:21.
〔14〕EdwardHitchcock,ElementaryGeology.NewYork:DaytonandNewman,1842,pp.275-276.
〔15〕BarbaraNovak,NatureandCulture:AmericanLandscapeandPainting,1825-1875,p.50.
〔16〕Ibid.,p.47.
〔17〕同〔3〕,第447,455—456页。
〔18〕同〔3〕,第477页。
〔19〕ThomasCole,“ThoughtsandOccurrences,”undatedentryofc.1842,NewYorkStateLibrary,Albany;photostat,New-YorkHistoricalSociety;microfilm,ArchivesofAmericanArt.QuotedinLouisL.Noble,TheCourseofEmpire,VoyageofLifeandOtherPicturesofThomasCole,N.A.NewYork:Cornish,Lamport&Co.,1853,p.335.
〔20〕参见NicholasGuardiano.AestheticTranscendentalisminEmerson,Peirce,andNineteenth-CenturyAmericanLandscapePainting.London:TheRowman&LittlefieldPublishingGroup,Inc.2017:27.
〔21〕JamesThomasFlexner.ThatWilderImage:ThePaintingofAmerica’sNativeSchoolfromThomasColetoWinslowHomer.NewYork:DoverPublications,1970,p.63.
〔22〕NicholasGuardiano.AesthetictranscendentalisminEmerson,Peirce,andnineteenth-centuryAmericanlandscapepainting,p.94.
〔23〕杜威著,傅统先译《艺术即经验》,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8页。
〔24〕陈榕《西方文论关键词:崇高》,《外国文学》2016年第6期,第93—111页。
〔25〕同〔3〕,第31页。
〔26〕Cole,quotedinLouisLegrandNoble,TheLifeandWorksofThomasCole.Cambridge,MA:TheBelknapPress,1964,p.162.
〔27〕同〔3〕,第9页。
〔28〕参见孟宪平《透光风格:一种美国绘画风格的学术史考察》,《美术》2011年第3期,第121—125页。
〔29〕同〔3〕,第33,425页。
〔30〕LouisLegrandNoble,TheLifeandWorksofThomasCole.Cambridge,MA:TheBelknapPress,1964,p.82.
〔31〕彭峰《完美的自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32〕BarbaraNovak.AmericanPaintingoftheNineteenthCentury:Realism,Idealism,andtheAmericanExperience[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49.
〔33〕ThomasCole,“EssayonAmericanScenery,”inMcCoubrey,AmericanArt,1700-1960,p.100.
〔34〕DenisdeRougemont,LoveintheWesternWorld(NewYork:DoubledayAnchor,1959),p.23.
〔35〕HenryJames,WilliamWetmoreStoryandHisFriends(2vols.,1903;2vols.in1,NewYork:DaCapoPress,1969),2:4.
〔36〕参见BarbaraNovak,NatureandCulture:AmericanLandscapeandPainting,1825-1875,p.135.
〔37〕塔塔尔凯维奇著,刘文谭译《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19页。
〔38〕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判断力批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39〕郭勇健《论审美经验中的身体参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73—79,128页。
〔40〕同〔3〕,第29页。
〔41〕同〔3〕,第504页。
〔42〕WoodcutfromdrawingbyPorteCrayon(D.H.Strother)inHarper’sNewMonthlyMagazine19(1859):1,reproducedinHuth,NatureandtheAmerican,p.85.
〔43〕同〔39〕。
〔44〕BarbaraNovak,NatureandCulture:AmericanLandscapeandPainting,1825-1875,pp.140-142.
〔45〕LouisL.Noble,TheCourseofEmpire,VoyageofLifeandOtherPicturesofThomasCole,N.A.NewYork:Cornish,Lamport&Co.,1853,pp.217-218.
〔46〕KennethMaddox.IntruderintoEden:IconographicSignificanceoftheTraininNineteenth-CenturyAmericanLandscape.Ph.D.diss.Ph.D.diss.inprogress,ColumbiaUniversity,writtenundertheauthor’sdirection.
李珍珍复旦大学中文系、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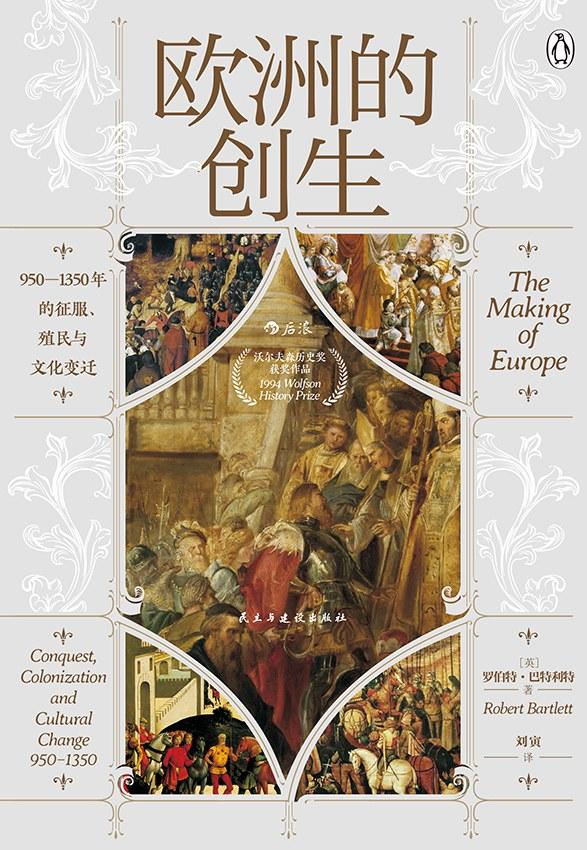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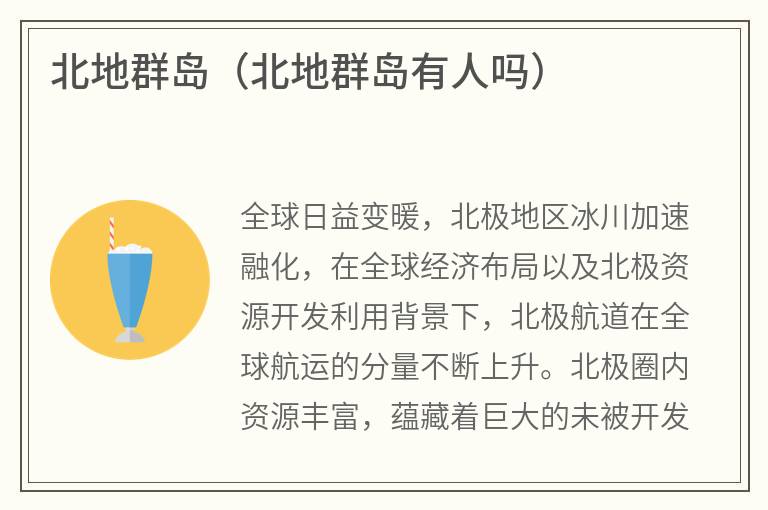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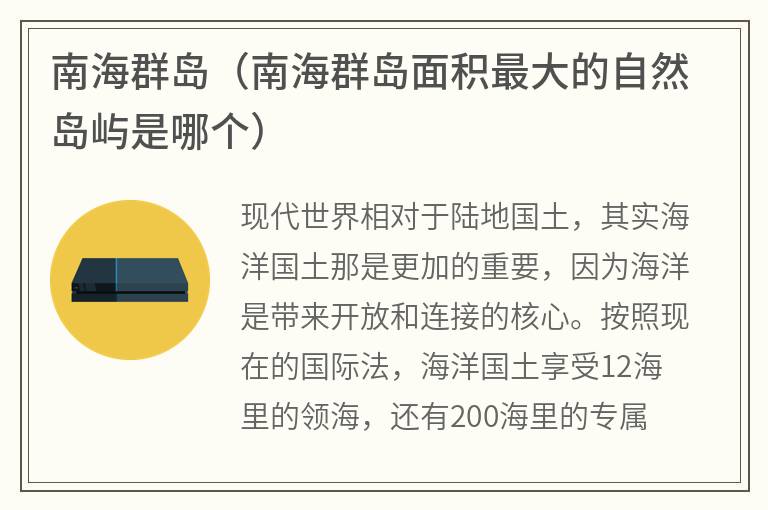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