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地区有没有过“罗子国”?
张一湖
世传有两个“罗子国”,一个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存在于今湖北宜城地区的罗子国,一个是相传于春秋战国时期存在于洞庭湖南面的罗子国。我们暂且将相传存在于洞庭湖区的罗子国称作“后罗子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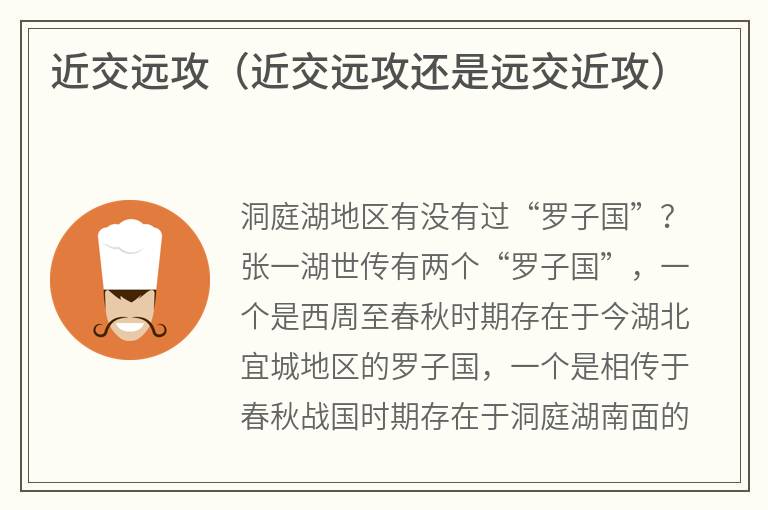
近交远攻(近交远攻还是远交近攻)
明《嘉靖湘阴县志》称:“周成王分封,地属楚,至文王徙为罗国。秦废封建,改国为县。”是说自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罗子国遗民至湘江流域,这里即成为“罗国”,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改“罗子国”为罗县,其间共468年,“罗子国”一直存在于洞庭湖以南地区,湘阴县境也一直隶属“罗子国”。
上述说法符合历史真实么?对于这个问题,看来大家都是一头雾水,而且都在一头雾水中人云亦云,却很少有人去怀疑这个“从天而降”的“后罗子国”是否真的曾经存在。
笔者从接触湘阴历史资料开始,特别是在阅读湘阴历代县志之后,就对这个说法有了怀疑,并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搜集证据,试图解开这个谜团。
当然还是从罗子国的历史说起。
一、罗子国的来龙去脉
(一)罗子国的起源
“罗”族传说为祝融氏吴回的孙子陆终的第六子季连所创,是芈部落穴熊的一个分支,和楚同宗。关于罗子国的起源地,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罗族”起源于“罗地”,而这个“罗地”指的是今河南省罗山县一带,罗人首先居住于此,商朝中叶被迫西迁到今甘肃正宁县。周武王因其参加灭商时有功,封罗为子爵,成为周的属国,后随楚国迁徙到宜城(今湖北宜城)。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罗人的祖上是为天子掌管鸟兽的官。《礼记·郊特牲》记载:
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罗氏致鹿与女,而诏客告也,以戒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国。”
一般认为,这里所说的“大罗氏”就是罗人的祖先,原本居住在甘肃正宁附近,后来跟随楚国的先祖一起迁居到湖北宜城。
以上两种说法,前一种说法“罗”人是因地而得姓,后一种说法是因职官而得姓。两种说法相同的部分是说罗子国的先民都曾居住在甘肃正宁附近,而后从甘肃正宁迁徙到湖北宜城附近。不同之处是关于起源部分。如果罗氏是因居住地而得姓,那么其发源地便是河南罗地无疑。如果罗氏是因职官而得姓,那么便有两种可能:一是罗氏原本就居住在甘肃正宁附近,与河南“罗地”没有关系;二是罗氏原本居住在河南,因为得了职官之后,便以职官为姓,于是将居住地也改称为“罗”。
笔者认为,根据《礼记》的记载,罗氏是因职官而得姓,这一点当更为可信。至于发源地,笔者总认为发源于河南、中间迁往甘肃正宁的说法稍稍牵强了一些,倾向于罗氏原本发源于甘肃正宁地区的说法。罗氏与楚同宗,楚之先祖起先也居住在甘肃境内,不闻居住河南某地。后楚、罗结伴南迁,来到湖北境内。
(二)楚罗之战
由于在周成王分封时得到名位太低、封地太少,楚国历代君主对此深感不满,心怀怨愤,而且也从来没有把成王说的“子男之田”放在心上。此后,经历了400多年的发展,到了楚武王时代,楚国已经占领了江汉间的大部分地区,疆域非常宽广,国力非常雄厚。楚武王不满足自己的名位,更不满足局促于江汉“南蛮”地区、继续遭受中原各国的歧视,于是,他要求称王,并以此为借口向汉水以北进兵。他首先召集汉水附近的诸侯小国开会,让大家尊他为王,谁不顺从就打谁。这样,楚国就开始了对汉水流域各诸侯小国的频繁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并在公元前722年灭掉权国之后,正式打开了北上中原地区的通道。
公元前701年,楚国莫敖屈瑕(楚武王之子,屈姓始祖)出兵以武力招降汉水流域的贰、轸两个小国。该地区另一小国郧国起兵反抗楚军,将军队驻扎在一个名叫“蒲骚”的地方,并联合随、绞、州、蓼共五个国家的军队,准备共同抗击楚军。屈瑕手下将领斗廉夜袭郧师,在蒲骚将郧军打败,其它几个小国的军队一哄而散,望风而逃,于是,屈瑕成功招降了贰、轸两个小国。第二年,屈瑕又领兵攻打心怀不轨的绞国。绞国军队不敢迎战,婴城自守。屈瑕用计诱使绞国军队出城,将其打败,逼迫绞国订立城下之盟。
《史记·楚世家》记载了楚国这一时期对小国的征伐活动:“楚强,陵江汉小国,小国皆畏之。”楚国不断欺凌、降服江汉间小国,让这一地区的小国们惶惶不可终日。《春秋左传》记载:
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従之。绞人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
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使伯嘉谍之,三巡数之。(《春秋左传·桓公十二年》)
可见,楚国在伐绞之战中分军渡过彭水、逼近罗国的举动,刺激了罗国的神经,让罗国十分惊恐。罗国准备抵抗楚国军队的进攻,并派出侦查人员反复侦探楚军的情况。
与其他小国相比,罗国更接近楚国。楚武王原本的策略是“近交远攻”,即对临近诸侯国采取外交手段,稳住它们,以解除楚军进军中原的后顾之忧。这一次,楚国察觉到了罗国的“不安分”,于是决定除掉这个腹心之患。在伐绞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699年,楚武王派屈瑕统率楚国大军伐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楚国伐罗之战。《春秋左传》详细记录了这次战役: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
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1]
从楚武王夫人邓曼“知楚师之尽行也”的话里可以看出,这一战,楚国派出了自己全部的精锐部队。可见楚武王对于此战的重视和志在必得的决心与信心。指挥这一战役的主帅是楚国的莫傲(楚国当时最高的官职,权力比后来的“令尹”还要大)、战功卓著的大将屈瑕。然而,由于屈瑕骄狂轻敌,而罗国则早已厉兵秣马,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联合了卢戎作为援军。所以,这次战役的结果是出人意料地以楚军大败、罗国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伐罗之战,是楚武王、楚文王时期乃至此后数百年间楚国最为严重的一次军事失败。这次失败对于楚国而言是非常惨痛的,而且对楚武王本人的打击更是非常之大的。第一,经过楚武王亲自组织训练、在当时的天下称得上数一数二的强大的楚国军队全部出动,却被小小的罗国和卢戎打得大败,溃不成军!第二,楚武王痛失了大臣和爱将屈瑕,而且这位大臣和爱将就是他的亲生儿子!第三,为了安抚众将,楚武王不得不承认“孤之罪也”,主动承担失败的责任。可想而知,楚武王对于小小的罗国应该有多么的痛恨!
东周庄王七年,公元前690年(一说公元前691年以前),在楚武王去世之前不久,楚武王亲率大军踏平罗国,并将其灭亡,报了一箭之仇。
(三)罗国遗民的迁徙
文献说,楚国灭罗之后,楚文王为了避免罗国遗民再生事端,就将其迁居到湖北枝江地区。后来又因为这一地区太过靠近楚国的都城郢都(在今湖北荆州地区),于是干脆将其驱赶过长江,远放洞庭湖以南地区居住。有迹象表明,罗子国遗民首先来到今汨罗江口,然后,溯汨罗江流域而上,分布至今平江、汨罗、屈原、湘阴等地。
二、“后罗子国”真的存在过么?
1995年版《湘阴县志》引历代史志称:
公元前689年春,楚文王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县县北),再徙罗子国遗民至湘水之南。自此,县境属罗子国地。
秦代废分封,设郡县,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改罗子国为罗县,隶长沙郡。
按此说法,从公元前689年到公元前221年的468年间,“罗子国”一直存在于湘江流域以南、以汨罗江为中心、包括今湘阴、汨罗、屈原等地在内的这片地区。这,可能么?
笔者认为不可能。
(一)楚武王、楚文王时期国的“灭国为县”运动与“后罗子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问题。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都介绍秦国的郡县制。其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县制的正是楚武王。公元前722年,楚武王为了打通通向“中国”的通道,在经过精心的军事和外交准备之后,出兵攻打权国,将其一举灭亡。楚武王灭亡权国之后,为了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管辖之下,一劳永逸地占有这个地方,便创造性地将其地设置为楚国的一个县,而这个县,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县。所以,权县也被称作“中华第一县”。
从楚武王灭权为县开始,楚国就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国为县”运动。据称,楚国在800年间(但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从楚武王开始的约四五百年内)灭国65个,其中有史可稽灭国为县的就达20个。楚国的灭国为县运动,基本的模式是:1、将战败国灭亡,使其国家不复存在;2、在该地设立县治,由楚王派遣官吏管理;3、将被灭亡国家的贵族、人民迁出,使其成为“遗民”(即“亡国奴”),迁往别处居住。
在楚武王向北扩张的初期,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主要是为了避免过分刺激中原各大国,常常采取“剿抚并用”的手法,将一些不听话的国家打败,摧毁其政权,然后扶植傀儡政权,让其“复国”,使之听命于自己。但是,到了楚武王后期和楚文王时期,楚国就没有那么“温柔”了,一般都是一棒子打死,不留任何死灰复燃的机会。楚国灭亡罗子国在公元前690年,比灭亡权国晚了32年。这时,楚武王已经公然称王,楚国早就不玩让小国“死而复活”的猫捉老鼠式的游戏了。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楚国对其它小国都一脚踩死,却反而会对与自己结下血海深仇的罗国爱心泛滥、网开一面么?楚国会让这个已经沦为“亡国奴”的仇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树起“罗子国”的旗帜、而且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468年?
(二)楚国对洞庭湖地区实施管辖与“后罗子国”存在的时间问题。
楚国对洞庭湖地区实施正式管辖是在公元前396年之后的事情,而此时距离楚武王灭罗、楚文王迁罗已经过去了将近300年。虽然由于熊渠“伐杨越”,到楚文王时代,洞庭湖地区已在楚国的政治影响之下,但楚国并未对其实施具体管辖。楚文王能将罗子国遗民迁徙到这里来么?所以,罗子国遗民何时到的洞庭以南,还是一个值得考证的问题。或者楚文王当初只是将罗子国遗民向着长江、洞庭湖以南地区一赶了事、任其自生自灭?果真如此,罗子国遗民在此“化外之地”私下树起一面“罗子国”的旗帜、建立起“非法政权组织”也许有几分可能。但问题是,楚文王会允许罗子国遗民这样做么?罗子国遗民又敢于这样做么?
即便说历史上真有罗子国遗民在此私下树起了非法的“罗子国”的旗号,那么,在吴起变法、楚国对洞庭湖及其以南地区实行正式管辖之后,“罗子国”的旗帜还能继续高高飘扬么?而历代史志竟说秦始皇时期始将“罗子国”改为“罗县”,这又怎么可能?这又怎么可能呢?!
还有一点,罗子国本是一个小国,以那个年代的人口水平,一共能有几万人就不错了。楚国灭罗之后,只是将其贵族、统治层(当然还包括这些贵族的奴隶)迁出,不见得要将其居民全部迁出,所以,成为“遗民”的人只是原罗子国民的一部分,这部分人到底能有多少呢?他们几经迁徙,必定有一部分留在了途经之地,比如枝江,剩下的人来到洞庭湖地区,能够建立起一个国家吗?
(三)早期史籍上没有任何关于存在过“后罗子国”的原始记载。
今天能够看到关于“后罗子国”的记载,只是在历代《湘阴县志》等地方志里,而且没有任何出处和根据。《左传》关于“罗国”的记载到屈瑕兵败便戛然而止,《廿四史》则干脆没有“罗国”、“罗子国”的痕迹。假如在洞庭湖以南地区曾经存在一个“罗子国”,而且据说这个“罗子国”还很大,有的资料甚至称其为“当时汨罗江流域方圆5000平方公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什么从先秦史籍到《廿四史》会没有任何记载呢?
(四)考古发现
1957年,湖南省博物馆在汨罗罗水与汨水会流处南岸之小洲上发掘出“罗子国城遗址”,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490米,南北400米,出土有春秋战国时期文物,与罗国子民迁此筑城之历史和城址吻合,定为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年的这一文物发掘发现,被作为“罗子国”曾经在汨罗江流域存在的铁板钉钉的证据。但是,这一发现却是按照“按图索骥”的思路去做的。就是首先确定有一个“罗子国”,然后去找,结果一找就着!
然而,就在2015年年底,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古罗城遗址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考古调查和试掘。考古人员就古罗城遗址考古调查、试掘工作进行了汇报。发掘结果表明,罗城遗址内虽然存在春秋时期的遗存,但城址的修建始于战国时期(即比通常所说罗子国遗民来到洞庭湖地区的时间晚了几百年),汉六朝时期城址继续沿用,六朝时期利用战国古城的东、南城墙兴建了一个包含东西两个并列城圈的小城。考古人员认为,罗城遗址并不是所谓“罗子国”的都城,而是一处战国时期的楚城,极有可能是出土简牍和文献记载中的“罗”县城遗址。
这样一来,“罗子国”都城是没有了,“罗子国”的存在自然也就更加缥缈了。遗憾的是,历史专家和考古人员也没有去怀疑这个“后罗子国”是否曾经存在。
(五)有关记载逻辑混乱,谬误百出。
相关文献口口声声说楚国“灭罗”,将“罗子国遗民”迁出。既已“灭罗”,为什么还能有“罗子国”?罗子国民既已成为“遗民”(即“亡国奴”),“罗子国”又怎么会继续存在?如果罗国存在,为什么要称其民为“遗民”(亡国奴)?
一批被放逐的、人数不确定的“遗民”(亡国奴)一来到汨罗江畔,这里立刻就成了“罗子国”!湘阴县境也立刻就归属了!这些说语法逻辑混乱,显然不能作为历史的依据。
综上所述,笔者大胆提出一个结论——湖之南地区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什么“罗子国”!千百年来大家口头笔下的“后罗子国”,其实是不太认真、不太严谨的史家们慵懒地推测出来的,是个“伪罗子国”。
三、关于“县境属罗”的正确说法
那么,罗子国遗民来到洞庭湖地区居住发展的情形究竟如何呢?笔者试做一个推演:
楚文王时期,楚国迁都于郢。楚文王不想让罗子国的遗民居住在郢都附近,于是决定将其再次迁走。迁到哪里呢?此时整个长江到汉水之间都是楚国非常稳固的疆域,只有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地区,楚国虽然不直接管辖,但是那里也没有什么值得顾忌的政权组织,而且这个地方地广人稀,正好可以让罗子国遗民去居住。于是,楚文王灵机一动:干脆让这群家伙走远点!
就这样,罗子国遗民来到了洞庭湖地区。为了安全,这些“遗民”首先顺着汨罗江溯流而上,来到今平江境内。作为“亡国奴”,罗子国遗民仍时时怀念自己的祖国,所以,他们仍以罗为姓,并将他们新的居住地称作“罗”,将流经住地的这条河流起名叫“罗水”(汨罗江的支流)。
《史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因而“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罗子国遗民自北方来,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而且经过血腥的战乱和连年的迁徙,现在终于有了一块安生的地方,所以格外珍惜。他们在当地辛勤耕耘,与人和谐相处,逐渐赢得了当地民众的信赖,影响越来越大。由于他们甘心臣服于楚国,所以,到了战国时期,楚国也就顺水推舟,在汨罗江畔设立罗县,给罗人居住。自此,“罗水”、“罗地”、“罗城”的叫法逐步流传到整个洞庭湖南岸地区。
湘阴立县,县境自益阳、罗、湘西三县划出。后来,罗县又被并入湘阴。故关于湘阴与罗的关系,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湘阴县境的一部分曾经属于罗县,而不是县境曾属罗,更不是曾属“罗子国”。
[1]《春秋左传·桓公十三年》。
编辑:子禾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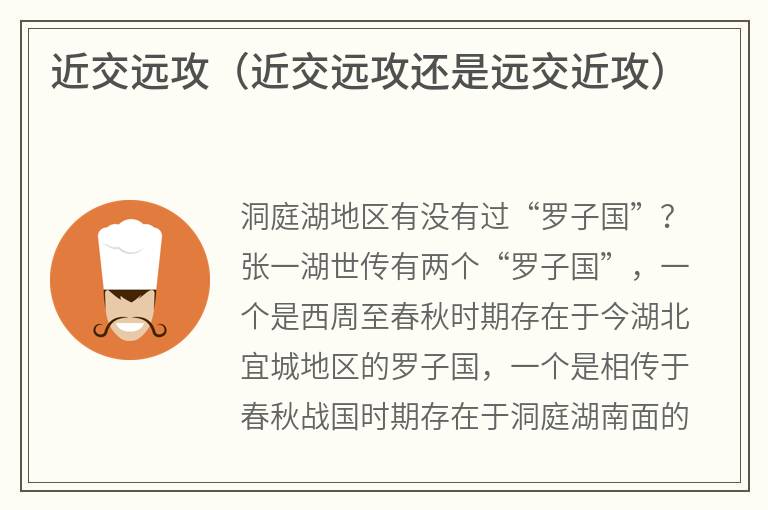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