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6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全球繁荣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Prosperity(IGP)举办了“亚洲的性别与繁荣 (Gender and Prosperity in Asia)”系列讲座。这一系列共有六期,由中心副讲师何嫄组织策划,既有涵盖亚洲女性整体经济和残障状况的专题演讲,也有针对特定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缅甸的国别讨论,旨在促进亚洲女性之间,以及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理解与连结。在第五期讲座中,韩国“SHARE(性权利和生殖正义中心)”的联合创始人,“生殖正义联合行动Joint Action for Reproductive Justice”的联合主席,酷儿女性主义者Na Young(那英)围绕“韩国女性主义运动的问题和背景”进行了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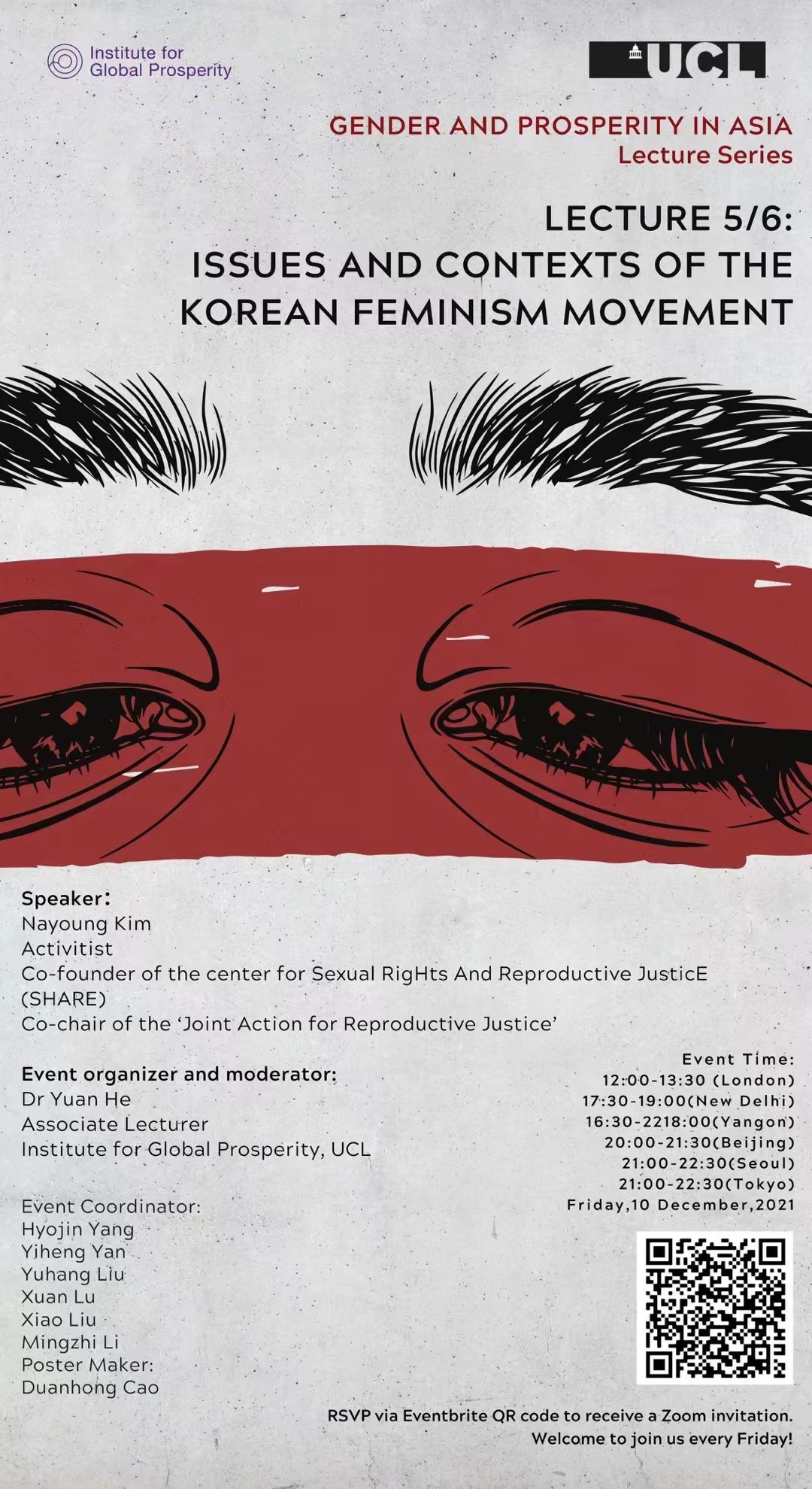
自2010年堕胎问题在韩国成为社会议题以来,那英一直致力于终止怀孕的非罪化。她于2017年发起了“生殖正义联合行动”,并在2019年与其他的活动人士、律师、医生和研究人员成立了性权利和生殖正义中心。2019年,她与Sunhye Kim 和 Yurim Lee等人一起在《健康与人权杂志》上发表了《生殖正义运动在挑战韩国堕胎禁令中的作用》。那英的主要兴趣是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同性恋行动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生殖正义运动和全球行动主义。

韩国“SHARE(性权利和生殖正义中心)”的联合创始人,“生殖正义联合行动Joint Action for Reproductive Justice”的联合主席,酷儿女性主义者Na Young(那英)
韩国的女性主义运动与反女性主义运动
在活动的开始,那英首先指出:在过去的六年内,韩国围绕#MeToo、消除网络性暴力、终止怀孕非刑罪化等议题展开了大规模集会和一系列女性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带来了具有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重大变化。此外,韩国社会也兴起了诸如“逃离束身衣(escape the corset)”和坚持“不结婚、不做爱、不约会、不生孩子”的“4B”运动等女性主义主张。
但近年来这些运动同时也遭到了大规模反对。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期间,韩国男性对射箭项目金牌获得者安山发起攻击,认为安山是仇恨男性的女性主义者,要求她道歉并退回金牌。这些男性认为安山是女性主义者的理由是她有一头短发,且断言她在Instagram上使用的一些词汇是在嘲笑男性。
过去几年内,这种荒唐的集体攻击急剧增加。在安山事件中,韩国射箭协会挺身而出,以明确而坚决的态度阻止了这些男性的无理要求。但仍有一些公司乃至政府机构承认了此类指控并为之道歉。在安山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阴谋论在韩国社会大肆扩散,它宣称女性主义者在广告中加入了特定的手势,以嘲弄韩国男性。韩国男性投诉了在广告中使用这种手势的公司和政府机构,还获得了这些公司和政府机构的道歉。他们还敦促游戏公司终止一位身穿标有“女孩不需要王子”T恤的女配音演员的合同,攻击某些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妇女组织的女明星等等。
问题在于,韩国的政治家们正积极地利用并增强上述群体的反女性主义逻辑。在明年的总统大选前,韩国两大政党都遵循反女性主义逻辑,借此来确保他们的支持率。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观察男女权力关系的不同,比较女性主义运动与反对运动的影响力,或通过判断时下最为重要的性别议题,来正确理解过去几年内韩国的性别运动进程。为了准确分析性别问题背后的原因以及女性主义运动的未来方向,我们必须了解韩国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历史及其背景所带来的影响。
妇女和女性主义运动与韩国的政治和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
那英强调,韩国妇女和女性主义运动与政治和经济变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1987年6月民主化运动前后,韩国成立了非政府组织形式的妇女组织,并颁布了确保妇女权利的法律。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妇女组织以大学为中心,展开了各种以性别政治为基础的活动,许多女性主义运动以文化运动为形式开始活跃。与此同时,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韩国也加入了这个全球的浪潮。
然而,1997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对韩国女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资产泡沫消失,国家接近破产状态。由于韩国当时欠下了大量的国际债务且无力偿还,不得不求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干预,韩国的经济与劳动力结构被改变,不仅是经济,国内教育和社会也受到了重要影响。
在大量韩国人失业,人人挣扎于生存的情况下,过去反对军事独裁的政治力量首次上台掌权。同时,自1998年的金大中政府,政府开始依循国际人权规范建立社会制度。这一改变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一方面,它表明了韩国政府不会停留在过去,将遵循国际民主化的标准;但另一方面,在许多人因大规模重组而失去工作、经济上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又被视作缓解社会混乱的种种手段。
这一改变的模糊与矛盾之处,在妇女人权的制度措施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落实了1997年和1998年的经济重组计划后,许多妇女失去了工作,在裁员浪潮中首当其冲。从那时起,许多女性就失去了有保障的工作,被迫以非正式员工的身份工作。
另一方面,韩国妇女事务总统委员会于1998年成立,在2001年更名为性别平等部。2005年,经过妇女的长期斗争,《民法》废除了以丈夫和父亲为当家人的户主制度(Hoju system)。这一制度的废除,标志着韩国妇女运动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成就。然而,伴随着经济和新自由主义而来的这些这改变,造成了极其矛盾的局面。一部分人产生幻觉,认为韩国社会已经实现了制度性的性别平等,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人权得到了提高,但事实并非如此。
随着韩国走上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道路,“女性只要有能力就能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功”的神话广为传播。政府主导的制度化变革变成了主导力量,影响超过了基层的运动。越来越多的女性信奉“贤能政治”(meritocracy)的神话,在新自由的框架下相互竞争;同时,她们对妇女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趣大大降低。从2000年代中期到2010年代初,许多大学里的女性主义社团、俱乐部与相关媒体都逐渐消失。直到2015年,韩国女性主义运动才再次崛起。
2015年以后韩国女性主义运动的走向和背景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那英指出,为了更好地理解2015年后的韩国女性主义运动,我们有必要对其走向和背景进行分析。首先,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变革之后,经济主体的改变对韩国社会的性别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改革发生以前,韩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由男性家长来“养家糊口”。所以,如果男人得到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就能提供终身雇佣保障。此外,大多数工作都属于男性工人,虽然妇女也外出挣钱,但她们的收入仅为“补贴”家用。男性和女性在工作保障、晋升和工资方面有着巨大差距。由于男性在社会上更为重要,所以父母为了教育儿子,经常会让女儿受较少的教育,并且让她们从十几岁开始就从事低薪工作。
在经历了1997年的结构调整后,妇女的工作地位变得更为恶劣。但问题是,以前能够找到安稳工作的男性也处于非常不稳定的境地。每个人都被迫去从事不固定且缺少保障的工作。因此,在男性过去的经济地位和性别地位发生变化的同时,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转变。为了使人们能更好地适应新自由主义制度,韩国的教育制度也迎来了改革。过去,只有毕业于优秀大学的男性才有优势,但在新自由主义变革之后,韩国社会继续塑造贤能主义的神话,强调只要个人有能力,可以考出尽可能多的证书并获得成功。
这些变化堪称引发了一场关于改变性别和性的地位的斗争。男性作为稳定家庭收入支柱的经济优势和权力地位遭到了动摇;女性则得到了虚假承诺:只要有能力就能成功,这与性别无关。
事实上,在2000年代,女孩的学术成就远远超过了男孩。过去,女性无法上学,受教育程度较低,缺少与男子平等竞争的机会。因此,在女孩获得更高的学术成就后,韩国社会产生了“性别平等已经实现”的幻觉。然而,在现实中,男性就业率维持稳定,没有明显的变化,而女性就业率则保持在男性就业率的一半以下。直到2017年,女性的失业率依旧远远高于1999年。但社会却一直将男性视为青年失业的代表群体,还让女性误认为是自己抢走了本属于男性的工作。
在2015年,韩国女性在社交媒体上打出“我是女性主义者”(I am a Feminist)的标签,这一运动促使更多韩国女性打破这种幻觉,并真诚地谈论社会的不平等现状。引发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一名少年在推特上表示自己因为讨厌韩国女性和韩国女性主义者,所以要加入ISIS。之后,这位名叫金根的男性果真前往叙利亚加入了ISIS。然而,一位著名的男性专栏作家发表了标题为“加入ISIS的金根是一个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愚蠢的女性主义”的文章,描述了这一情况。
这在女性中引发了巨大的愤怒,并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标签话题行动,许多女性在推特和社交网络打出标签,宣称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许多女性分享了她们的故事:她们曾认为自己可以在平等的机会下凭借自身能力获得成功,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与此同时,一种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传染病也引发了新的舆论漩涡。在MERS流行初期,一名男性用户在某大型网络社区上发帖称:“MERS在韩国爆发的原因是因为两名女性在中东进行豪华旅行后回国。”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目睹了网上的舆论后,韩国的女性用户开始积极回应不实指控。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聚集在一起,女性用户对调模仿了“共享MERS爆发信息”的MERS Gallery分区,将“MERS Gallery”与女性主义小说《伊加利亚的女儿们》的名字结合在一起,组成了名为 “Megalia ”的网络社区。这部小说所讲述的,是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地位被颠覆的世界。
此后,女性用户发起了一场名为“镜像”的反击,通过改变男性试图歧视和丑化女性的话语中的主体性别来回击男性。在现实中,男性的言语是虚假的煽动,而在镜像反击中,女性的言语则描述着真实的情境。通过这一策略,女性展示了未被揭示的严肃现实。这个网络社区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因为女性的焦虑和愤怒已经达到了极点。
与此同时,控制女性的性和身体的企图仍在继续,将韩国的低生育率归咎于女性。韩国卫生和福利部下属的研究机构建议通过对独居者征收更多的税,来应对国内的低出生率。韩国政府还公布了一张地图,显示全国各地区的育龄女性人数。
曾经风靡全球的鸟叔Psy在《江南Style》中有这样的歌词:一个看起来很安静,但玩的时候很会玩的女人。在社会地位的变化中,男性要求女性接受这样的信息即女性应该顺从,但也能参与性玩乐。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男人想要继续在性方面占据统治地位。 “逃离束身衣”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过去,很多女性认为,为了在新自由主义的竞争中取得成功,她们应该适应这男性制定的性规范(sexuality norm),甚至将外表视作自身能力的一部分。然而,在2015年后,许多女性开始摆脱这种虚构的范式,“逃离束身衣”运动受到了许多年轻女性的青睐。
2015年后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这些运动主要由网络社区和社交网络发起。过去,运动的主要由学生运动组织、工会、政治团体、社会运动团体来主导;但在2000年后,影响力更大的网络社区和社交网络成为了动员的主要形式。
网络舆论的主要特点是根据事件来迅速传播信息,且拥有更广阔的传播范围。相较于社会运动组织或学术机构,网络舆论的语言更简洁、更直接,人们可以更容易地参与进来这些人也更加倾向于关注自己的直接利益而不是社会结构中。
此外,近年来的网络文化因为基于社交网络或特定社群,很容易被煽动,假新闻或夸大的事实会迅速传播。当一些开始只是为了好玩的煽动性言论,在熟人圈中得到传播后,它可能会突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议题。许多针对女性主义的反击就属于煽动性事件。近几年网络动员在女性主义者中引发了很多争论,一些煽动性信息制造了反挫的机会;人们在关注这些轰动性信息的同时,却忽略了其背后的实际内容。
另一方面,#MeToo运动、消除网络性暴力运动和终止怀孕非罪化运动则是通过线上组织与线下活动的相互协同来推进。韩国的政治变化和女性的经历影响了这一进程。韩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尤其在2000年代,韩国每隔4年就会举行大规模集会。政治变革在短期内就会发生,许多人都参与了例如弹劾总统等重要的历史变革。但是也有许多女性在集会上经历了性骚扰或没有受到尊重。在这些政治变革中,女性的诉求没有得到重视。因此,在2016年弹劾前总统朴槿惠的集会上,女性主义者组织了一个名为Femizone的团体,并发布了女性主义宣言。女性主义者表示,我们将驱逐继承独裁之父的当权者,建构起一个有女性主义观念的新民主。我们也强调,不应该再局限于制度民主,而是施行一种能有效消除对社会少数群体的歧视、不平等和污名化的女性主义政治。
不幸的是,又一位男性政治家成为了总统。文在寅总统在选举时宣称,他将成为一位女性主义总统,但实际上,在执政时期,他没有履行成为女性主义总统的承诺。伴随着国内的政治变化, #MeToo运动在韩国展开。首次在电视上露面并公开发言的女性检察官徐智贤在接受采访时揭露了现实结构:即使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针对女性的暴力仍在继续。之后,与文在寅总统同属一个政治集团的政客安熙正被爆出曾多次性侵他的秘书。此后,#MeToo运动继续在韩国的文化艺术界、国会、企业、媒体、学校等领域内蔓延。韩国的移民女性也发出控诉,指出对移民女性的性侵犯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目的是利用移民女性的生产劳动和生育劳动来维持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MeToo”运动之后还发生了数次反对网络性暴力和非法拍摄的大规模集会,揭露了韩国社会内关于性别和性的等级与暴力。
在这一浪潮中,终止怀孕非罪的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它重要意义在于实现了终止怀孕的完全非罪化,而不是在特定条件下将终止怀孕合法化。我们提出了生殖正义,摆脱了“胎儿生命权”与“妇女决定权”的二元框架。我们揭露了过去为了经济发展而强力控制生育的国家矛盾。在《母婴保健法》中规定,国家将残疾作为合法堕胎的条件,目的是为了只选择具有生产能力的人口。因此,我们提出了“如果终止怀孕是一种犯罪,那么罪犯就是国家。”通过诉诸生殖正义的框架说服了宪法法官,法院在2019年裁定惩罚终止怀孕是违宪行为。
但是,正如我在开头所述,反女性主义团体以及试图利用反女性主义运动获取支持率的政客正在成为严肃的威胁。据统计,20至30岁的韩国男性的主流观点认为,文在寅政府是一个女性友好的政府,他们因此转而支持反对党。然而,社会统计数据表明,韩国的真正的问题是年轻一代有很强的经济和社会焦虑。Ta们最大焦虑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无法找到稳定居所,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实际问题。但政客们非但没有对这些问题负责,反而利用了当前的反女性主义势头。他们扮演起了年轻男性的代言人,表示“我们也要考虑男性的损失”。他们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反女性主义的势头。
韩国女性主义运动在未来应该如何行动?
那英在第四部分展望了韩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未来。过去几年内,韩国的女性主义运动有了国际知名度,女性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受到关注,也对其他国家的女性主义者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之所以在介绍韩国女性主义运动时,强调历史、政治、经济背景,是因为区域背景是很重要的。如果缺少对区域背景的了解,女性主义者们将会认为世界上的妇女都在经历类似的问题,无法在抽象的共鸣之外建立团结。而在了解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和环境后,女性主义者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女性主义运动的各个方面及其差异,找到具体的团结点,并进行批判性分析。或许,这一系列讲座的初衷,也是为了针对不同社会提供具体的理解。
韩国女性主义运动与全球女性主义浪潮同步共振。但同时,韩国社会特有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在运动过程中性别与性的等级(gender-sexuality hierarchy)变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所要求的贤能主背景等因素都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些因素导致了韩国女性主义运动的特殊形式。
对于有些运动的口号。那英认为,我们很难说女性主义的目的是成为一个成功的女人。这样的口号再次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贤能理念,而不是继续与社会上的结构性歧视作斗争。举例而言,“逃离束身衣”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该运动摆脱了对女性的性控制和固有性别角色。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女性被困在“女性通过变得与男性相似就能成功”的信念之中,我认为那就不是女性主义实践。
女性主义者必须积极揭露性别和性控制背后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并带来结构性变革。以#MeToo运动为例,这一问题反复出现的原因是,韩国社会的经济资源和权力仍然集中于男性。这种结构性力量能够控制女性,并对女性实施暴力侵害。因此,女性主义者需要改变以男性导演为中心,给予他们权力和补助金的文艺界结构;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劳动结构,改变移民政策。此外,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异性恋和血缘关系中心的家庭制度。只有坚持这些改变,#MeToo运动的意义才能超越承认受害者或惩罚施暴者,带来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变革。然而,韩国政府对#MeToo运动的回应仍然仅限于惩罚肇事者,为受害者建立一个报告系统,并为受害者提供保护。
作为对比,终止怀孕非罪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不局限于某个议程,而是通过女性主义来挑战结构性问题。事实上,早在2010年,韩国就曾出现过为女性争取怀孕和生育自主权的运动,我也从那时起就参与其中。但是,在2016年该运动迎来复苏后,我们指出国家的所作所为并非是为了保护胎儿生命或限制女性的自主权,揭露了国家在惩罚堕胎罪的同时,为了落实人口政策所实施的不义与暴力行为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残疾人和穷人被强制进行堕胎或绝育;未婚女性生下的孩子,或与黑人男发生关系后生下的孩子被强行送到国外收养。国际领养是韩国政府的另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提出终止怀孕非罪的要求的同时揭露这些问题,我们强调了以下事实:终止怀孕问题不仅仅是女性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同时改变社会结构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在一个终止怀孕非罪的社会中,我们所要求的不是“惩罚或允许”的二元框架,而是如何从现在开始消除不公,确保实际的性权利和生育权利。在这个变革过程中,我们同时思考如何将这些权利与教育、劳动、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各种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与此同时,随着问题组成发生变化,我们将会拥有更多可联合的力量、建立更多的社会联系,在更多领域引发改革。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可以成为一个政治主体,提出与生活各方面,如残疾、种族和阶级都息息相关的问题,而不是被性别割裂。女性主义是一场引起系统变革的运动。那英和SHARE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为生殖正义而行动的活动家正积极地将气候正义、边境控制、移民政策、债务问题、酷儿运动以及残障运动的要求,与生殖正义运动联系起来。那英最后表示:在未来,当我们与各国女性主义运动交汇时,希望我们能理解彼此的政治背景和变化,发出重要的团结之声,共同推动系统性的变革。
(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顾问、原“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组织负责人,北京为平妇权益机构共同发起人冯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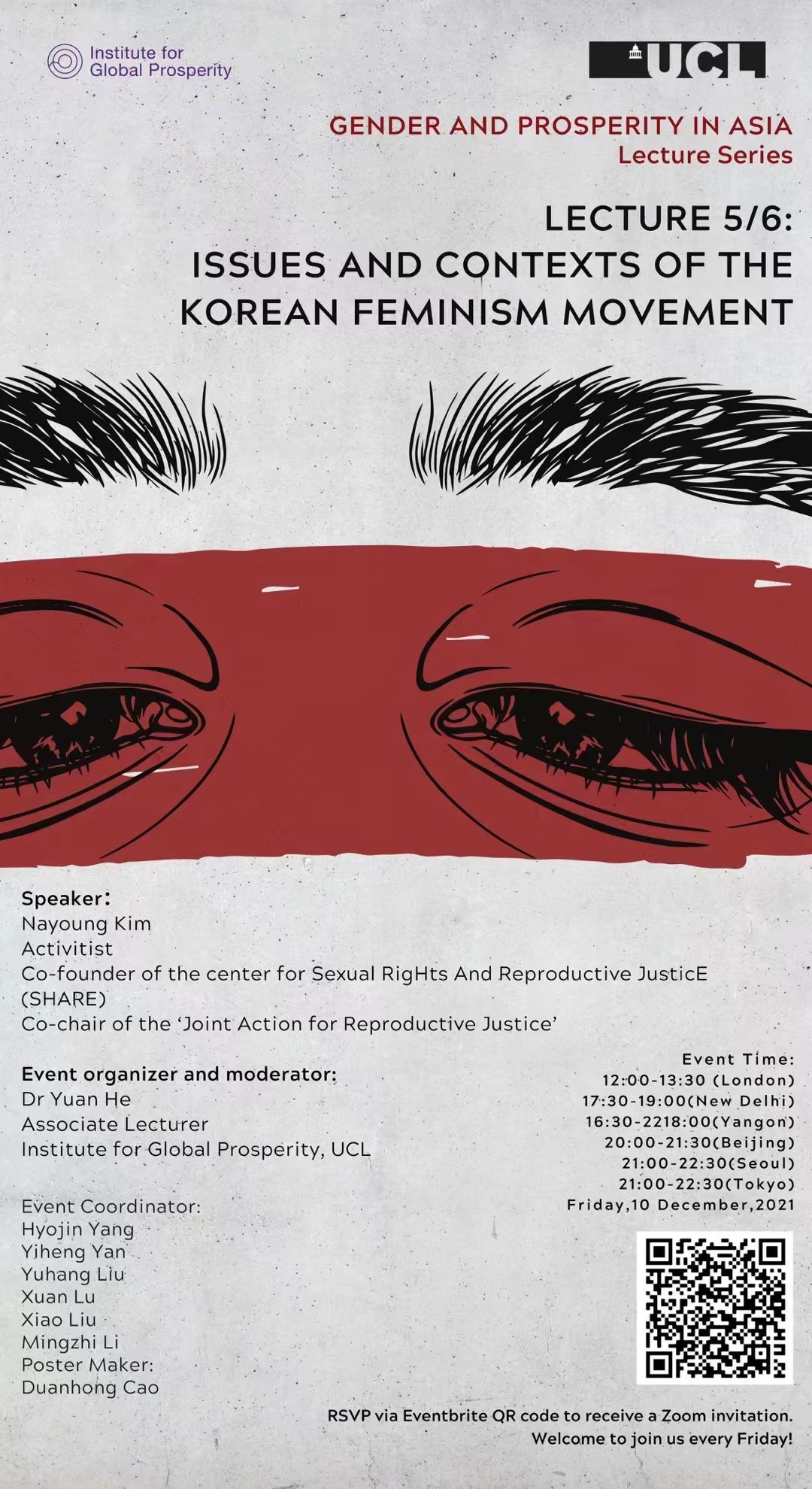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