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什么?这个本质论问题已经历史化了。卡勒说,文学是什么?这要看是谁问了这问题。面对一个5岁的孩子,回答可以很干脆,而文学专业人士之间,则说来话长。事实上,他忘了一点,这还要看是在哪儿、在何时提出这问题。比如30年前,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1]中,王晓明如是说 :“每当看见‘文学现象’这四个字,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文本’,那由具体的作品和评论著作共同构成的文本。这当然不错,文本正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不是惟一的部分,在它身前身后,还围着一大群也佩戴‘文学’徽章的事物。它们有的面目清楚,轮廓鲜明,譬如出版机构、作家社团;有的却身无定形,飘飘忽忽,譬如读者反应、文学规范。它们从各个方面围住文学文本,向它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在许多时候,这些影响是如此深入,你单是为了看清楚文本自身的意义,也不得不先花力气去辨识它们。”而如今,看到这么一段话,太多年轻同行会对其中的苦口婆心大惑不解;即便是过来人,对当年那个不言自明的大前提变得心存疑虑的,估计也不在少数,“文本正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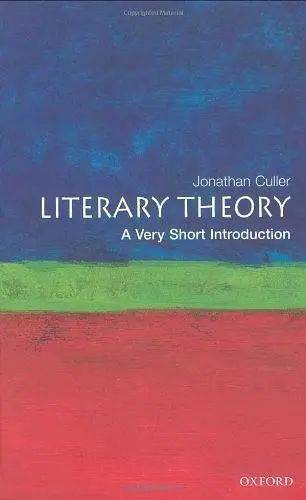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我们确实已经跑得够远了,在文学的认知上,尤其是在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的路上。
这条路上,收获有目共睹。在我看来,“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就是文学研究“历史化”结出的硕果。因为其动力和感召力之一便是, 在世纪之交反思“纯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定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与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现代变革、与20世纪中国、与中国革命这一最大“政治”之间的深刻关联;在近年有关文学史写作的竞争场域里,标举五四文学革命以降的“新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艺”及“当代文学”这一脉的主导地位及其合法性,以及现当代文学发展道路与其书写的历史必然性;并在高度认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特别紧密而紧要的前提下,试图突破政治与文学的“笼统而抽象”的固化认知,力求深入地摸索社会历史在每个阶段的具体现实,以及一百多年来社会变迁的连续性过程;从而 通过对具体历史情境中社会“内在肌理”的把握,来更新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体认,乃至重新认识当下中国的“政治”与“文学”。
与此同时,“历史化”的路上,问题也暴露了不少。突出表征之一就是,特别追求细部具体和局部真实,满足于“满地碎银子”,“历史化”堕入了愈演愈烈的“碎片化”:这不仅指诸多研究之间各司其事、各是其是,而且指不少成果内部,铺陈了背景材料、零星所获一堆,也并非没有心得妙悟,但千言万语“只盘带,不射门”,甚至最终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或者只为“慢镜头”播放式的“小历史”叙事而陶醉,而这也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时段和区域不断细分,研究论题越来越琐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二是历史观上,以“民族的、地方的、女性的或者族群”的“身份政治”取代甚至拒绝类似政治经济学范式或“阶级政治”那样的总体思考和宏大叙述。
由此看来,“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又还是应对文学研究历史化危机的纠偏之举,是“历史化”进路上的升级换代工程。因为,这一研究思路正是出于对“碎片化”的警惕与反省,而理直气壮地追求“大历史”叙事——既区别于“革命叙事”“救亡叙事”,又区别于“现代叙事”“启蒙叙事”,而最好是能综合了“革命”与“现代”、“救亡”与“启蒙”,又更贴合百年中国的新历史叙事; 之所以要竭尽所能打开历史的褶皱,也并不是为了简单还原史实及其细节,更不是回到琐碎历史的汪洋大海,而是为了重构历史的整体感,新建有关现当代中国的大历史判断。因而此研究取向,以“社会史视野”名之,实质上,一是为了凸显上述这种“整”和“大”的诉求,二是为了与原来的“政治”与“政治史”既拉开距离,又若即若离;况且对于文学实践来说,再也没有比社会结构和长时段社会变迁这样的视野,显得更加整体而宏大的参照系了。换言之,“现当代文学研究”如今强调是放在“社会史视野下”云云,“社会”与“社会史”,确乎一类概称,至于是否取径于“社会学”或“社会史”来进行研究,大可不必太过较真[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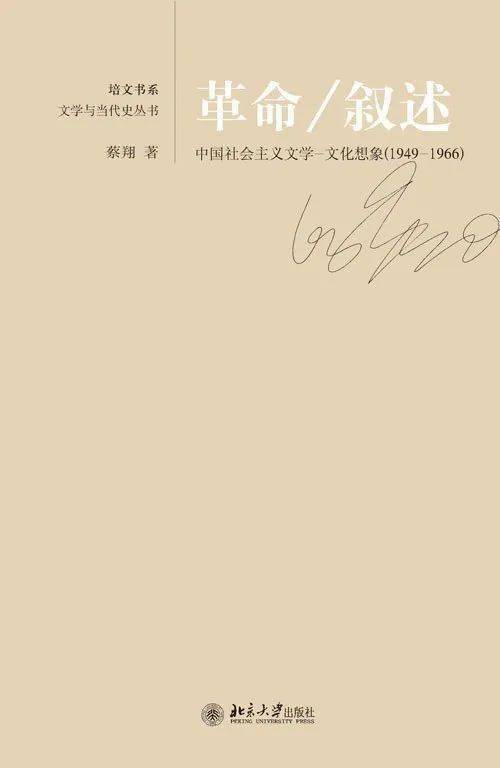
蔡翔《革命/叙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基于研究主体的意识与视野,尤其是“态度的同一性”,“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相互激发、共振,有渐成一股潮流之势。扩大而言,在洪子诚有力地论证了是“当代文学”生产了“现代文学”,从而使当代文学真正地学科化以来,在以蔡翔的《革命/叙述》一书为标志,“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学研究开始直接正面地“思想”起来以后,整个(现)当代文学界里“左”的一翼越来越活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学人。研究的意向性也已经汇聚成了高度统一的学术愿景,不少个案的工作非常具有生长性,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博学”的精神状态和学术姿态,更是令人钦佩,让人不由地对当代学术有了更高的期许。但是期望越大、责任越重。在理念与行动、声势与实绩之间,毋庸讳言,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那种让同道奔走相告,也让对手肃然起敬的研究成果和实质推进,还是相当稀缺。要求再严格一点的话, 即便是“社会史视野”取向的研究,有些也是令人遗憾地,未能同他们警惕的“碎片化”真正区隔,一不留神就难免“细节肥大症”,材料上“危险的增补”不断,而核心的原创观点却总是延宕,“捅不破窗户纸”。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当然是因为,这难题实在太难。正如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前无古人一样,伴随这一历史进程的文学也是在探索与挫折中前行;而且根据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不同步、会错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面对人类此前一系列文学艺术高峰,面对资产阶级文学的“文化霸权”,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艺等等,存在与否?如何存活?怎么在竞争中发展?有过哪些经验和教训?所有这些,都是问题,也都是难题。多年前为研读赵树理,我曾经慨叹,这要靠“靠不住的自己”在论述中完成那“未完成的文学实践”,实在是难!就此而言,尽最大可能去占有各种历史资料,把活生生的现当代文学实践放之于活生生的社会历史语境,在对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高度互动、相互生产的历史现场的考辨与考察之中,努力发现作家作品与彼时彼地社会现实的具体性之间的真切关联,进而发现乃至发明现当代文学真正创造性所在,或起码形成必要的同情性理解。——这在原则上是毫无问题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事情越难,越得有个抓手,难题越积越多,势必要换入口。所以,“文本正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话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在策略上,势必要对“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也来一个历史化,搞清楚了当年为什么强调语境化之后,也不妨索性后撤一步。再找寻新的抓手或入口,“文本”则肯定首当其冲。这个“文本”,可以是泛化的文本概念,包括现当代中国的各类文学实践与试验,也包括所有非典型、未成形的文学样态,但其核心内涵还是,“由具体的作品和评论著作共同构成的文本”,特别是在重新强调文本的开始。 事实上,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这在各派理论的文学认知中都是常识。在视文学为“镜”者的眼中,是文学作品映现了世界,这个世界即便是虚构的,也总是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而这种真实既可体现为文本里的人物、故事和场景等,也可解读为作品创生时那个世界的真实。 在视文学为“灯”者的眼中,是文学作品表现了作家的丰富心灵,作品里有作家全部的思想探索和情感体验,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一个也不能少。而在文学流程论者看来,文学作品就更重要了,作品既是作家创造力的文字结晶,也是读者接受的文本依凭,作品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中介,却也未必不是造成误解的根源,但最终,作品还是解读论争惟一可靠的枢纽,也是文学作为社会交往系统而存在的基本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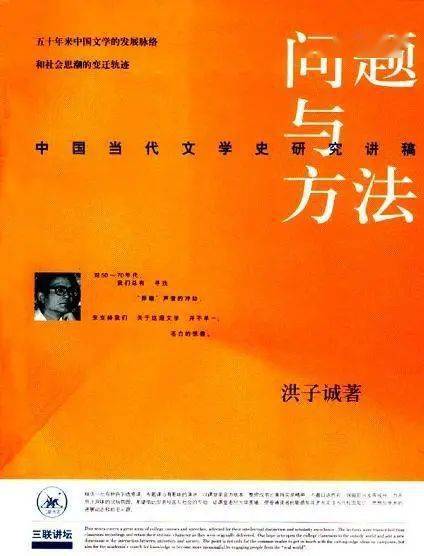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当然,文学确实不只是作家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作家”和“作品”也尤其有必要扩大内涵或重新定义,但还是不得不说,在当下的文学研究界,作家创作的作品文本的重要性,实在是被严重低估。用成系统的理论话语套文本者有之,用成规模的外围材料释文本者有之,而借文本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者,那就更多;而且看起来都还是以引一点原文、也阐发几句的样子来进行。然而,真正将文学作品看成是具有自身完整性和生命力的文本,尊重乃至敬重文本者,又有几人?
值得庆幸,还是有的。这里以我国台湾学者赵刚为例。赵刚是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近年来却以其“对陈映真研究的巨大贡献”,“为我们作了一个作家研究的示范,让我们知道:在战后这一个极端扭曲的台湾社会里,像陈映真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青春的乌托帮幻想与政治整肃的巨大恐惧下,曲折地发展出他的小说写作的独特方式,以及籍由小说所折射出来的思想的轨迹;随后,在越战之后,他又如何发展出一套第三世界想象,并籍着另一种小说,思考台湾知识分子的位置及其潜在问题”。其实最初,赵刚所进行的也是我们似曾相识的工作流程:“首先,从阅读中抽绎出一些‘主旨’或核心概念或提问。然后,‘命题作文’,按照主旨/概念把各篇小说中的相关‘资料’找出;然后编织成一个首尾一贯的论文。”好就好在赵刚及时有了反省并付诸于行动,最终,“和我之前所设想的大不相同,因为我把‘素材’(也就是相关的小说)严格地保护在各篇小说的独特的历史空间中,而不让它被概念所分割、析离、重整。……我打定主意下笨功夫,写每篇小说的读后心得。那就得再读一遍、两遍,然后写出我的心得。既然每篇都要‘写’,我就不自觉地‘正襟危坐’起来了,如琢如磨,眉批、加注,打问号……”如此摸索形成了他的方法论。这里,有研究者面对研究对象的谦逊,有读者面对文本的敬畏。“每一篇小说都是一个有机体”,“我希望保留每一篇小说的历史性与有机性”,“让自己比较柔软地在对象所规定的历史情境中优哉游哉,不要想当然,不要先入为主,解读的眼睛不要死盯着,要让对象自己走过来、浮出来。”“这里并没有什么神秘主义的意思,因为靠的是笨功夫。”[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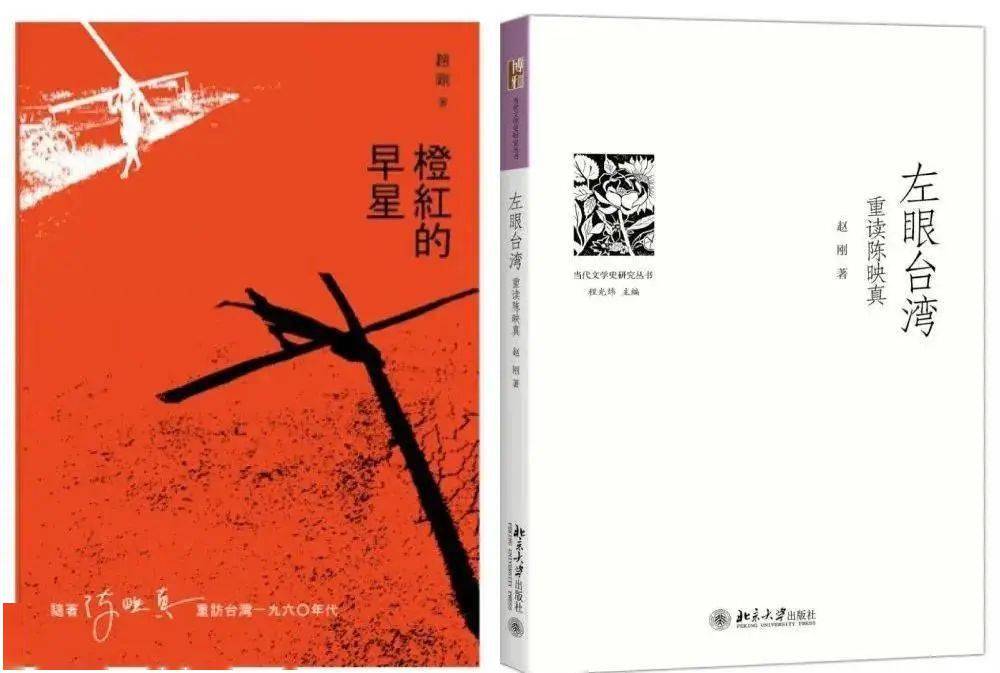
赵刚《橙红色的早星》人间出版社2013年版/《左眼台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赵刚将其“功夫”称为“篇解”。“篇解”而能对陈映真及台湾左翼思想研究有如许推进,这与个人的禀赋才华等当然相关。而且,研究对象如陈映真,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实用性与介入性,身体力行发挥文学实践的政治功能;研究主体如赵刚,正宗社会学出身,专业的社会科学训练;研究目标“终究在思想”,“把小说放回它所由之产生的原有时代的政治社会中,去体会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自己身存的历史环境与课题”,种种这些因素,都在这一成功案例中起到了作用。不过,赵刚在方法上高度重视作家作品、聚精会神研读文本,更毫无疑问地具有示范性。虽然他所针对的,其实是也十分普遍的“理论先行”,而不是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甚至赵刚同样是很强调“历史化”的。但是,为了反思文学研究在“历史化”过程中轻忽以至轻慢作品文本的倾向,援引赵刚的陈映真研究为例,强调“以文本为本”的重要性、优先性,还是非常适切的,而且应该还更能鼓舞人心、增强信心。
这是因为,无论知识立场还是问题意识,抑或文学认知、研究旨趣,“社会史视野”取向的同道中都可以有赵刚,也应该有“赵刚”;这是因为, “以文本为本”高度重视文本及其阅读,与“社会史视野”特别强调历史化语境,看似出入不小,而实质上二者共享的价值远大于差异。其一,事物的意义不在其本质,文学作品也不存在一个固化的意义;意义取决于关系,因而作品文本的意义处在其上下文之中,由语境决定;语境没有限定,所以意义也不可能终结。因此其二,把文本语境化乃至“永远地历史化”,这都没有错,甚至还不妨把这逻辑延伸至所谓“纯文学”,只不过“纯文学”视野中的文本语境是“空”的,是将作品文本与抽象的普遍性相联系,于是语境有也等于没有,于是无论什么文学,都一概虚化成了统一的“人性”“国民性”“现代性”“人民性”,或者“美”“反讽”“形式自律”。这个名单可以很长,也可以“后来居上”或者“五十步笑百步”,但总是概念化,不具体。所以其三,只有把作品放在其创生的社会语境里,放在作家创作历程的语境里,放在读者阅读反应和期待视野的语境里,放在作品所属文类和文学史谱系的语境里,总之一句话,只有把文本放在具体、生动、合理的语境之中,文学作品才能获得有效的、特殊性的理解,也才能“还魂”为活泼、充实的生命,乃至还原其本来的面目。事实上,我还更愿意换个简单直白的说法,即:才能把文本真的读通、读懂,进而才有可能读好、读透文学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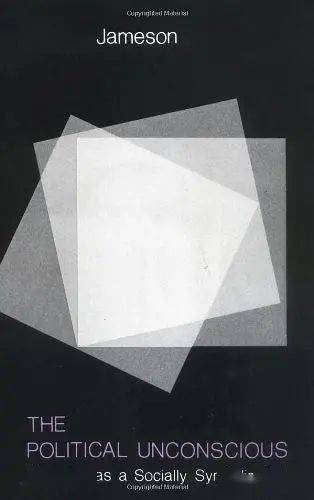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事实上,这便已经涉及二者的差异,或毋宁说是,在共同的、广义的历史化或社会史视野之下,“以文本为本”的独到之处和启示所在。也许看起来只是个工作方式的问题。“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 何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于特别诡谲、峻急、多变的历史年代,许多作家作品是在与所处时代贴身肉搏中创生(乃至方生未生)的,所以,不通过巨量史料的掌握以想象性还原那饱满的“现场”及“瞬间”,不在态度、情感及“感觉结构”上与作家作品同呼吸共命运,那怎么行?但也就是在这里,必须提请注意:在赵刚们“以文本为本”的思路和做法里,那些都是“诗外”功夫,都是后台工作,是锻造自己成为合格研究主体必备的准备阶段;而在工作的前台,却是当然应当专注于“诗”,应当全神贯注于文本,对作品进行专业的文学性阅读;因而工作成果的呈现上,文学研究也就自然应当区别于历史研究,不再是史料或史学素养的直接展示,而是基于“历史化”而充分“语境化”地打开乃至穿透了作品文本。
这意味着工作方式和程序不同的背后,也确实有思想观念上的原因。限于篇幅,我们最后从理论的高度聚焦一个问题: “文本”的“语境”在哪里?“语境”首先就在“文本”里。文本构成文本自身的“第一语境”,这不是文字游戏,这道理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做过充分论述,我只是从底层逻辑强调其更基本的方面。 文学是社会的交往行为,文学价值的实现有赖于作家创作与读者阅读两端的有效互动与配合;所以,一方面,作家在作品里总是预设了一个与“理想读者”共享的、不言自明的“世界”乃至“世界观”,另一方面,后来的“真实读者”为了打开文本、读懂作品,总是经常地需要通过“注释”来理解“语境”,需要打开“社会史视野”。在此意义上,“社会史视野”不是外在的,更不是外来的,而其实是“以文本为本”必然内生的需求,也是打开文本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行动。

铁凝《哦,香雪》原刊,《青年文学》(1982)
且以我较为熟悉的铁凝《哦,香雪》为例。这篇小说在1982年的历史情境中诞生时,文中那个“塑料铅笔盒”对于香雪的吸引力及其象征性,在作家和她所期待的读者心目中,都是毋庸多言的;这也决定了当时对文本的基本理解。时过境迁,“塑料铅笔盒”象征的“现代化”意味,对于后来的读者不再不证自明,甚至在其象征的光环脱落 之后,塑料铅笔盒还不得不面对跟凤娇们的“发卡”如何区隔、跟父亲手工做的“小木盒”孰轻孰重等方面的质疑;这样的重读,既以对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史图景的总体把握为基础,又因文本关键性的驱动而促发史料“二度激活”;事实上,这“二度激活”的“社会史视野”,因其深刻嵌入在文本之中,所以才更具生产性。也因此才有可能看到,对以上重读的重读已经正在发生:小说里有个重要名词,“公社”,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是比“塑料铅笔盒”更难吃透的,因为这背后,有香雪们更深厚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而在小说文本里,“公社”引发了主人公踏上“火车”去拿鸡蛋换塑料铅笔盒的英雄主义行为,又同样决定了英雄主角最后的回归,尤其是作家对这回归的最高赞美。总之,在这样的视野下,《哦,香雪》既讲出了一个“现代”主体诞生的启蒙故事,又讲“好”(?)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凯旋在新时期开启时刻的故事……
那么请问,这样的视野与方法,是“社会史视野”还是“以文本为本”?这样的解读,是“革命叙事”还是“现代叙事”?显然我的建议是,不妨也来反问一句:这种二元对立的选择题,是从哪儿来的呢?
文学“文本”之中,自有“历史”的“镜与灯”,由此“内曜”,方为文学性阅读与研究。

注释
[1]《今天》杂志1991年第三、四期合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本文是与《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程凯、何浩、刘卓、萨支山四位笔谈的对话,文中对他们的引用不一一注明。
[3]详见赵刚《左眼台湾》,尤其“自序”及吕正惠、陈光兴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保马
微信号|POURMARX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