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中期至战国的中原地区,由于诸侯、卿大夫等各级贵族均拥有制作青铜器的能力,生产效率又得到显著提高,故青铜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式多样。从西周青铜器艺术直接发展而来的极富区域性的青铜器艺术此时已完全形成,娴熟的造型处理、多样的装饰题材、高超的表面加工又造就了其富丽、清新的时代特征。以下就此期青铜器艺术形制和纹饰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器物造型娴熟,并开始向日常实用器皿转化
春秋中期至战国的青铜器,已由浑厚转为轻盈灵巧,在造型的处理上,达到了娴熟的程度。以鼎的造型为例,虽然蹄足、附耳、带盖的形制特点在上一阶段就已出现,但此时才广为流行。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鼎的双耳曲折外张,从而与鼎腹和蹄足的曲线相呼应,看起来更为协调美观。盛酒器中的壶,腹部不再是之前不甚美观的垂腹造型,已变得圆鼓高胀,不仅增加了容量,又使壶体更为耐看。部分壶盖上的莲瓣形装饰、馨龙捉手以及咋舌的双虎底座,更强化了这种美观的效果。

山西新绛釆集的附耳无盖鼎,外壁釆用了先进的失蜡法铸造工艺,比之先前通过传统泥范法制作的镂空装饰更为玲珑剔透。竄中部出现的直壁、敦的盖逐步圆隆进而与器身一致、喜好用深盘的豆而不用浅盘的铺等又均是出于器物容量的实际考虑。用于冰镇酒食的鉴的出现,说明青铜器的造型和功能已经完全适应不断提高的生活需求。
由于社会的变革,传统礼制的解体,使青铜器开始逐步转向日常生活领域。以拟形的青铜器为例,商周时期模拟鸟兽形貌的青铜器多为从属于礼仪活动的容器,此时依然有部分鸟兽形尊,不仅造型生动,且纹饰精美,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的鸟尊其铭文为“子乍弄鸟”,已是供贵族把玩的弄器,而多数的鸟兽形器已不再做成容器,它们或作为独立的摆件,或成为器物的支架、鑿、耳、盖钮等,更加凸显了观赏和实用的功能。此外,对于战国末期出现的一部分造型简约、装饰朴素的传统容器,它们作为日常实用器物的可能性更大。
纯装饰性的蟠蜻纹、蟠虺纹的普遍流行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器上流行的环带纹、窃曲纹、垂鳞纹、瓦纹、重环纹等此时已基本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由先前的交龙纹、窃曲纹演化而来的盘绕纠结、雕镂工整、组织严谨的蟠螭纹或蟠虺纹,从而确立了一种全新的装饰风格。螭是一种无角的小龙,《说文解字》:“螭,若龙而黄也。……或云无角曰螭。”蟠螭纹由两条以上的小龙相互交绕构成一个图案单元,通过横向和纵向的交错连接,构成较为复杂的装饰图案。

龙的身躯相对较粗,表面或有几何形纹,结构多为S形或C形。龙头多为侧面,上唇翻卷,也有少数作正面的,还有作双头形的等等。有些蟠螭纹仅有盘绕的躯体,但又夹有牛头纹或兽面纹。虺是一种小蛇,《国语吴语》:“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韦昭注曰:“虺小蛇大”。蟠虺纹即为一种纠结盘绕的小蛇纹,结构与蟠螭纹相似,但躯体更为细小,头部仅用圈点纹表现,有些因头部和身躯过度简化,演变为由点和曲线组成的云气纹。蟠螭纹和蟠虺纹多以编索纹和贝纹作分界,围绕器壁作二方或四方连续式分布。它们虽为动物题材纹饰,却与商周时期神秘、威严的动物纹明显不同,由于形象的简洁和结构的繁复,从而更具纯粹的装饰韵味。
除蟠螭纹和蟠虺纹外,此时还有各种动物纹和几何纹。兽面纹多蜕变成衔环的铺首,点缀了器物的环耳。几何纹中的回纹、卷云纹、斜线纹等多填充器物多余的装饰面,虽在装饰的手法上近于商周青铜器的几何纹,但更突岀观赏性。
新式装饰题材的涌现和多种装饰工艺的兼用并施
以描绘宴乐、狩猎、战争、射弋、釆桑等情景的人物画像纹,自春秋晚期出现,盛行于战国早、中期,多装饰于壶、鉴、匯、铜等器物的表面,釆用了铸镶或线刻两种工艺手段。这种纹饰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青铜器装饰题材,显得格外清新自然,不禁令人耳目一新。前文所举的上海博物馆藏的铜豆上,就有用红铜铸镶的狩猎纹,手持长矛、长剑的猎手穿梭于各种飞禽猛兽之间,描绘出生动紧张的狩猎场面。在这幅图画中,人不再是动物的附庸,而一跃成为自然界的主宰,表明当时的观念己逐步摆脱神秘主义的困扰,更加强调自身的主体性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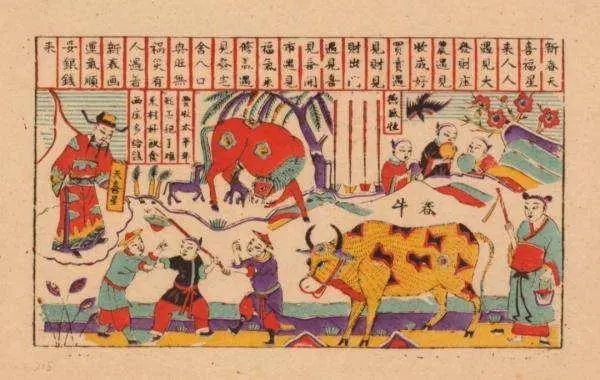
同馆所藏的铜凱其内、外壁有用细线条刻划的建筑、人物、车马、飞倉走兽的形象,人物或宴饮、或击钟、或起舞、或弋射、或驾车、或炊煮,鸟兽泰然自若地漫步于人和建筑周围,一幅安逸祥和的日常生活场景跃然于器上。故宫博物院藏的宴乐狩猎攻战纹壶,全器画面分三层展开:第一层(壶颈部)为釆桑和射礼画面,有桑树、“躬桑"的后妃和挽弓搭箭的人;第二层(壶腹上半部)为宫室宴飨、弋射、捕鱼画面,有建筑、家具、酒器、钟磬、舟船和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第三层(壶腹下半部)为水陆攻战画面,有城池、云梯和攻守的双方,还有两艘激战正酣的战船,其场面因有无头士兵的形象而被渲染得极为血腥。
人物画像纹表现的乃是日常的礼仪、生产、生活、战争等场景,其内容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而其分栏的构图以及对亭台、楼阁、人物、舟车、器具等的剪影式描绘,均是汉代画像艺术的渊薮。除人物画像纹外,战国时期出现的花叶纹,既是中国青铜时代少有的可确认为植物题材的纹饰,又是人们审美领域进一步拓展的明证。此时的青铜器艺术,因在造型上取得了娴熟的技巧,故而开始关注表面装饰对器物艺术效果的影响。部分器物的表面釆用了陞金、错金银、铸镶红铜、镶嵌绿松石等表面加工工艺,色彩斑甥,更显富丽华美。其虽为少数,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蟠螭纹和蟠虺纹繁密精细的装饰之风,又弥补了因素面器物的流行而产生的单调和乏味?

此时的青铜器铭文,长篇纪事体的较少见,但章法和布局多追求规整统一。铭文的制作,早期多铸文,后发展为刻文。铭文的内容,春秋中晚期的尚有颂扬先祖、祈福家族兴旺之类的语句,战国之后多''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器上记有督造机构名、职官名和制器者名字。春秋中晚期晋国的铜器铭文较为纷杂,或笔画细劲多方折、布局散漫,或继承西周笔意,以曲笔为主,中段丰满,末端尖锐,这种字体发展到极至就成为蝌蚪文。
栾书缶上光彩夺目的错金篆书是此时的杰出代表,其文字圆润秀劲,布局规整,光彩夺目,别具特色。战国时期著名的“平山三器”上的刻铭,文字极多,排列齐整,字形修长细劲,每字竖道往往引长下垂,末端尖锐。此时的青铜器铭文艺术,由于多位于器物的外表面,故无论其章法布局、字形结构还是剔刻、鑲嵌的工艺处理,均极力展现文字的形式美和装饰美,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
春秋中期至战国的青铜器艺术,造型娴熟,蟠螭纹和蟠虺纹繁复细密,人物画像纹新颖别致,表面装饰工艺丰富多彩,铭文极具艺术性,整体上均给人以富丽清新的审美感受。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