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日济南警方通报的发布,“阿里女员工疑被侵害事件”也有了新的进展。而近年来,围绕职场性别霸凌、骚扰与不平等的讨论也屡见媒体。但另一方面,在公共言论场上,诸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完美受害人”论调,也常出现有关性别议题的讨论中。虽然本次事件仍有争议,但无论事实走向何方,重新审视与澄清职场中的性别议题尤为必要。
本文希望通过推介关于中国城市职场性别政治的社会学研究,推动相关议题的深入讨论。当代中国女性的职场生涯、工作环境与劳动过程,近二十年来已经得到了不少社会学者的关注。这些研究覆盖了不同类型的女性群体,包括经历了“国企下岗潮”的大龄女性职工、作为乡城流动人口的“打工妹”以及从事城市新兴服务行业的年轻女性群体等。而本文所要介绍的民族志作品“Gender, Sexuality and Power in Chinese Companies:Beauties at Work”(《“白领丽人”在职场:中国企业中的性别政治》)则聚焦于当代中国城市白领职场中的性别政治。作者是海外中国学者,任职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刘捷玉教授。2008年,作者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入江苏省一家国企背景的外贸企业参与观察,开展为期六个月的田野调查,并在随后八年内对受访者进行了追访,并对其他类型企业(金融、IT、房地产、电信等)的职场白领进行了访谈。研究揭示了21世纪以来,拥有良好教育背景与事业上进心、被誉为“精英”与“中产阶级”的女性都市白领们,在职场中所面临形色不一、制度化的性别区隔。

“白领丽人”:新时代、新女性
“白领丽人”(White-collar beauties)一词指的是集中于城市第三产业就业、拥有相对体面社会地位、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女性。该词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是“白领”的职业身份。在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看来,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职业与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了“白领”群体的兴起。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传统的制造业“蓝领”工人与农场主等“旧”中产阶级为聚集于城市服务业的“新”中产阶级所取代。而在中国,“白领”群体兴起于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计划体制下各行业“单位”快速退出而为市场体制下各类“企业”所取代。不同父母辈的“职工”/“工人”身份,“白领”身份意味着摆脱体力劳动,在社会分层中占据相对占优的社会地位。
而“丽人”一词则暗示了她们性别化(sexualized)的身份。在中文中,甚至缺乏一个指代“男白领”群体的词汇(Liu,2016:17)。20世纪90年代,“白领丽人”被中国媒体用来称呼在外资企业就业的中国女性。她们被外界冠以“工作舒适、收入高薪、聪明自信、工作快节奏以及生活高消费”等想象。21世纪以来,随着企业发展与职业扩散,这个标签被用来指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脑力劳动的城市女性。在社会话语中,“白领丽人”意味着“能力出众、衣着优雅、外表迷人、头脑聪明”的女性专业人员。按照罗丽莎(Rofel,2007)在《欲望中国》(Desiring China)书中对“欲望”(desire)概念的解释,“白领丽人”话语引发的是年轻一代中国女性对“青春、智慧和美丽”的身份渴望,从而摆脱上计划体制时期以中性化或男性化出现的女性形象,以及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被认为是“缺乏能力、没文化、作为包袱”的女工身份(关于其父母一辈人的生命历程分析,可参阅刘捷玉教授2007年出版的另一部作品“Gender and Work in Urban China:Women Workers of the Unlucky Generation”《下岗女工的生命历程: 中国单位体制中的性别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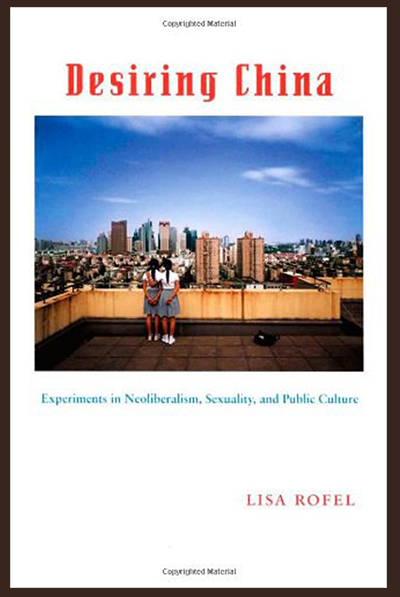
《欲望中国》(Desiring China)
此外,该欲望表达还包含了新时代女性对消费取向的城市生活憧憬,以及对效率理性取向的事业职业追求(Liu,2016:18)。由于“白领丽人”们大多出生于80年代,来自城镇地区,并于21世纪初期进入职场。她们拥有相似的代际身份特征: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红利——得到了来自家庭的资源倾斜与父母的身心投入。这也是为何他们往往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拥有追逐自我职业事业发展的机遇。
当女性面临物化:职场中的性别文化
对比其经历过政治运动、文化冲击与经济重组的父母一辈而言,“白领丽人”们无疑是“幸运的一代”。但即使如此,在职场中的女性白领们依然因其性别身份而面临着歧视、凝视与无视,体现在职场的性别文化中。
职场性别文化是职场劳动控制与组织劳资关系的构成部分。其中这一机制通过对女性“物化”的形式加以实现。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Martha Nussbaum(1995)和Rae Langton(2009)区分了“物化”(objectifcation)的几个特征:
1)工具化(Instrumentality)。客体被视作实现目标的工具。
2)自主性的否定(Denial of autonomy)。客体被视为不能自决。
3)惰性(Inertness)。客体被视为缺乏主观能动性。
4)可替代性(Fungibility)。客体可以被替代。
5)可侵犯性(Violability/ Ownership)。客体被视为可以侵犯的。
6)可占有性。(Ownership)客体被视为可以被占有、交易与交换。
7)主体性的否定(Denial of subjectivity)。否定客体的情感需求。
8)身体还原(Reduction to body)。对客体的评价停留在身体之上。
9)外观还原(Reduction to appearance)。对客体的评价与其样貌结合起来/以貌取人。
10)沉默化(Silencing)。客体的发言权被否决。
问题是,哪些组织文化与制度构成了物化女性的基础?在“Sex in work(工作中的性)”一章中,作者指出,维系职场的层级控制的两种性别文化:男性气质主导(masculine domination)与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e control)背后,通过对女性的物化加以实现。
首先是企业对女性的外貌要求。在服务业企业中,业务涉及业务销售、商务合作和公共关系部门在招募女性时,有意选拔样貌出众、女性。但“美貌”是一件主观的判断。作者发现,对于女性的“好看”判断,在人力资源部门看来非常具象化:例如“皮肤白皙,身材苗条,五官端正”。但涉及到对男性“好看”的评价则没有一个具体标准,更多是含糊地要求“高大、干净得体”(Liu,2016:90)。这种外界“凝视”下形成的审美要求,促使女性员工对自身身体的规训与焦虑,日常需要通过护肤、整容、塑形来维持身体。虽然“美貌”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女性提高个人魅力,在事业发展上占据优势,这也是哈基姆(Hakim,2010)所认为女性拥有的“情色资本”(erotic capital)。虽然在个体层面上,女性地位会因为她们的“美貌”而所有提高,但是在集体层面中女性社会地位并不会因此而提升,反而固化了职场乃至社会中男性主导的性别文化。一名受访女员工这样说道:
“通常人们认为一个女人如果很漂亮,头脑就简单。即使漂亮的成功女性完全得益于她的努力,人们也会把她的成功归因于靠外表上位。这样一来,如果女性有意利用她们的外貌来获得成功的话,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强化女性在社会中“装饰性角色”的印象对女性地位的整体性提高没有任何帮助。但相比下,男性较少面临这样的顾忌,外界只会称赞他不仅能力突出,而且很帅。”(Liu,2016:101)
对女性的外貌追求不仅仅是为了在商业活动过程中追求企业形象的提升,也包含了对组织内部的管理作用。在调查中,企业男经理向作者暗示:女性员工的存在可以“减轻男员工工作压力”(Liu,2011:p89)。无独有偶,2015年,某互联网企业也被曝光招聘一个新职位“程序员鼓励师”,要求“颜值要对程序员有足够的震撼力”,从而“激发团队又猛又持久地工作”。
但对于组织而言,存在着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企业不鼓励女性在企业内部展现性征(sexuality)。例如,在入职手册中,作者观察到企业对男女日常着装的规定差异:对于男性而言,着装原则取决于是否“正式”,“男性不允许留胡子、穿短裤、背心或无袖衬衫”,但对于女性而言,着装原则取决于是否合乎“性道德”,“女性不允许穿无袖衣服、短裙、露脐装、低胸和紧身衣服”(Liu,2016:p75)。但另一方面,在特定时刻,女白领被调度起来展示其“性征”(sexuality)。例如,在企业内部组织的男子篮球比赛中,女性被动员起来充当“篮球宝贝”。这一过程,拉拉队员的着装被暗示要衣着性感以“吸引大家眼球”。事实上,在篮球比赛中,作者也观察到观众(往往是男性)的议论焦点在于拉拉队员的身体,相关话题更是成为随后几周的办公室谈资(Liu,2016:83-86)。
无论是样貌和着装要求上的性别差异,还是对性别的特定要求,反映了企业组织内部的性别文化。从企业文化取向上,性征(sexuality)在组织内部受到了严格控制。而在管理实践取向上,性征则被调度起来,用于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内部管理。
对女性而言,建构自己的专业化形象与摆脱“先入为主”的态度,去性化(desexualized)的性别实践成为了她们的策略。例如在日常装扮上,受访的一名女销售指出(Liu,2016:p105),如果服装过于女性化,人们只会强调其女性身份而非职业身份。其次,如果着装过于“暴露”或“性感”,更是容易引起对其专业能力乃至道德身份的非议与质疑。因此去性化的服装是维系“女白领”专业性的关键要素。更重要的是,“去性化”的着装在女白领看来可以减少职场性骚扰风险——相比之下,男性不会因此问题而引起顾虑。
性骚扰的背后:性化的权力与制度
在中国社会,社会关系在商业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国企业特别重视客户关系的发展与维护。对此,企业常常借用餐饮(上酒桌)、娱乐(唱k)与休闲活动(桑拿)来维系客户关系。女性在客户关系维护过程中的作用与模式是制度化的。
女性在酒桌上扮演了何种作用?在作者调查过程中,一名受访女员工比喻尤为精妙:餐桌上的女性就如同菜肴中的“调料”,起到了气氛点缀的作用。而女性“敬酒”以及被“劝酒”才是宴请中必备的仪式。例如有观点谈到:
“如果我们女性说自己不能喝,男客户更来劲了:他们会说你是不是在骗人?坚持要你喝上一杯,甚至有的客户会怂恿说,小姑娘要不我们这样吧:你喝一杯,我陪你喝三杯,如何?”(Liu,2016:p94)
尽管“能喝”并非是男性的专利,但在特定的劝酒、陪酒文化下,女性喝酒成为了同侪压力的产物,因为压力不仅仅来自外界的客户,还来自上级同事。如果坚持拒绝喝酒,可能会被冠以“失礼”、“不给面子”、“不懂事”标签,并在随后受到批评与指责。
吃饭喝酒只是客户日常维系的第一步,饭后的“节目”同样离不开女性参与。唱K已经成为商务活动中常见的仪式,女性往往被要求与客户同唱以及跳舞,这一过程容易遭遇行为不轨的肢体接触(Liu,2016:p96)。类似模式化的商务活动不仅令人疲惫,而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性别歧视、性别骚扰到性侵犯也给予女性带来心理压力——不仅仅是花费时间精力适应这种男性主导的商务文化,而更来自外界基于“刻板印象”对女性的道德评价,使其极易名誉受损。频繁的商业活动使企业里从事销售业务的女白领们容易遭受来自男友的猜疑。不止一名受访的男性员工指出,在择偶中,他们更倾向于找从事老师或护士等女性化职业的女朋友,而不愿选择女销售。
性骚扰常见于这些性化(sexualized)商务活动与办公日常中。在餐桌上,男性劝女性喝酒之外的一个乐趣是讲“黄色段子”,对象则是在场的女性。在职场里,如果一个男性员工擅长讲“黄色段子”,则往往被管理层认为是一名能提供欢乐、制造气氛的“破冰者”。而男性领导把讲“黄色段子”作为展现风趣、制造气氛的方式。面对餐桌、职场乃至日常的“黄色段子”,女性应对最有效的策略莫过于微笑并沉默以待。因为如果一个女性参与到“开黄腔”的游戏中去,反而会有损其“名誉”。很多时候这种“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一些男性看来,并不认为是“性骚扰”的表现。但事实上,正因为“笑话”的制造背后存在着不平等的商业关系与层级关系,女性只能沉默。如果“黄腔”来自同级的男同事,女性反而可以采取言语反击来表达自身的抗拒立场。
其次是拥抱亲吻等肢体接触和性暗示。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中的女性职工同样面临着上级类似的骚扰与侵犯风险。但她们能采用的抗争策略极为有限(Liu,2007)。而在今天市场经济中,虽然女性可以选择“用脚投票”,但各行业的组织内部依然缺乏处理性歧视、性骚扰与性侵犯的机制,这也是为何近年Metoo运动在中国倍受。
性骚扰的背后,交织着性别文化与组织制度的权力不平等。以上行为与过程巩固了男性的权力象征,并转化为工作场所中的权力。当性骚扰成为常态后。女性不得不内化与合理化相关行为。一名女性经理认为,如果女下属不能适应(这些场景),那么最好的建议莫过于换一份工作(Liu,2016:p97)。尤其是对于销售行业而言,拒绝客户意味着失去业务的机会。其次,当无法依靠组织来维护权益的时候,反而强化了这样一种期望:即自己应该自力更生。如果无法躲避骚扰,那只能是女性自己的能力问题,从而使使性别等级制度不断被固化与“自然化”。

反思职场的性别政治
为什么在大众看来“能力出众、衣着优雅、外表迷人、头脑聪明”的“白领丽人”职场生涯中,依然得面对不平等、性骚扰与性侵犯等问题?作者认为,无论是根植于权力不对等的性骚扰,还是组织内部的性别文化,本质上都是制度化了的性别歧视——把女性置于从属性、依附性的客体地位。虽然“白领丽人”一词也在今天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相反更多被“职业女性”一词予以代替,这种公共话语的“去性化”固然可以理解为进步。但是,在男性为主的部分职业行业中,类似“美女官员”、“美女学者”等称谓,依然在公开或私下被使用于称呼相关从业女性。或许在个体看来,“美女”只是一种恭维,但是无形中却消解了女性的专业能力的认可,同时也是一种对职业女性角色的物化。这种根深蒂固、没有被意识到的性别观念不断再生产出不平等的性别文化。
面对职业发展的性别天花板与职场性别文化,作者观察到女白领们能采取的三种策略:第一,发展副业,重新定义事业上的成功;第二,把重心从追求“事业成功”到回归家庭;第三“用脚投票”换工作(Liu,2016:64-69)。但可以发现的是,以上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职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这也是为何作者在十年前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在2021年的今天都观察到相似的案例。
在成书之际,作者指出了一些可能会变革职场性别文化的因素。例如,以规章制度为基础的现代组织与强调“关系”的职场文化之间存在内在张力,这使得“职场中的(性别)关系”与“职场(性别)关系”存在互为竞争的关系。其次,在代际变迁下,随着“90后”“00后”走入职场,更新一代的女性在破除性别的制度障碍上拥有更大的能动性。作为独生女,她们得到了父母的关爱与重视。这种成长经历与家庭支持带来了全新的女性主义,例如更具有自主性的婚恋观念,也迫使市场与国家重视女性群体的诉求。而近年来,女性主义观点的传播与实践,则从外不断冲企业的性别文化,在“阿里女员工疑被侵害事件”后,阿里内部也很快形成《6000名阿里人关于807事件的联合倡议》,阿里官方回应则宣布成立反职场陋习小组,推动反性骚扰的机制化工作,防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酒桌陋习、低俗玩笑等在工作场合让员工感到不适的方式。”
相比于性别不平等文化背后形塑因素的复杂性,性骚扰与性侵犯问题更容易通过政策干预加以预防。性骚扰等问题在西方社会被正视也不过近半个世纪的事情(McLaughlin et al.,2012),但目前也发展出相对完善的应对机制。例如在大学等专业化组织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流程,包含了不当行为的明确界定、相关政策的定期宣传教育、程序化的申述渠道与调查手段、惩戒措施等等。一方面,制度所形成的“震慑力”可以降低性骚扰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以上政策干预机制也可以防止“误伤”。这对于中国各行业组织而言都有参考意义。
结语
正如波伏娃的名言:“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性别歧视与职场性骚扰也并非根植于生理性别(sex)中的生物本能,而是来自后天的社会性别(gender)建构。“白领丽人”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在于突破这些建构的性别歧视,更深层次在于跳出“男性凝视”(male gaze)的陷阱。一个充满性别偏见、刻板与不平等的社会,无论是女性、男性以及性少数群体都是受害者,破除以上问题不能只依靠女性,更是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感谢刘捷玉教授对本文写作细节的解答。对观点理解不当纰漏之处,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1.Langton, R. (2009).Sexual solipsism: Philosophical essays on pornography and object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Liu, Jieyu (2007) Gender and Work in Urban China: Women Workers of the Unlucky Generation. Abingdon: Routledge.
3.Liu, Jieyu (2016) Gender, Sexuality and Power in Chinese Companies: Beauties at Work.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4.McLaughlin, H., Uggen, C., & Blackstone, A. (2012). Sexual Harassment, Workplace Authority, and the Paradox of Pow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7(4), 625–647.
5.Nussbaum, M. C. (1995). Objectification.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24(4), 249-291.
6.Rofel, L. (2007).Desiring Ch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7.Tang, L. (2018). Review: Jieyu Liu, Gender, Sexuality and Power in Chinese Companies: Beauties at Work.International Sociology,33(5), 593–595.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