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武人有着怎样的社会地位?
为何会出现忠而复叛的现象?是否真的像宋太祖所说的武人是社会动乱的乱源?
五代是否真的“重武轻文”?宋初是否真的“重文抑武”?
在宋史专家柳立言领衔编著的新书《五代武人之文》中,这些问题都能找到相应的答案。本书将如剥茧抽丝、老吏断案般,循循导引,揭秘藏在墓志碑文里的五代武人的宦海浮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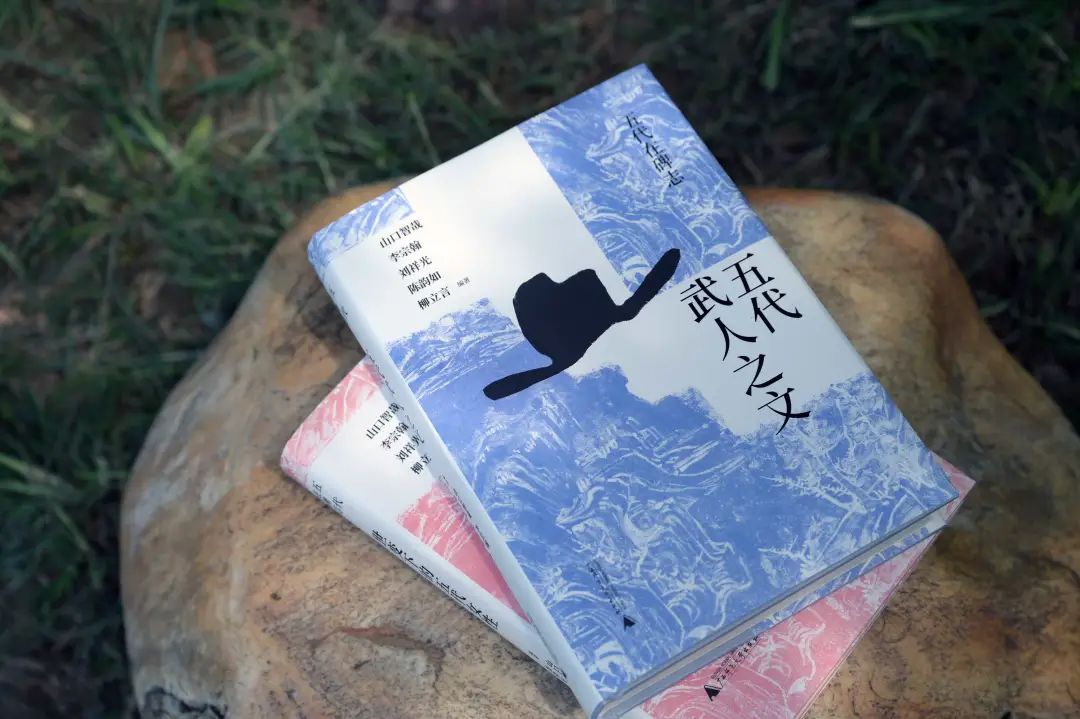
柳立言在书中表示,本书的图书特点是完全利用武人的墓志和碑铭,不是去否定学人已发现的部分真相,而是发掘更多的真相。书中从文人如何书写武人、武人之文事与武功、武人之后代和转型三个方面增加我们对武人的了解,分析解读五代武人的家庭结构、仕宦经历、上升通道、观念信仰等,探讨并重新评估了武人在五代至宋初的历史角色和地位。
此外,作者还提出了一系列颇富启发性的议题,如:认为武人对“致治” 有一定的贡献,而不只是宋太祖所说的“致乱”;武人品德和信仰是否符合儒家的严苛标准;等等。可以说,本书是从五代之“武”追溯宋代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源流,并透过石碑和石刻这类“文”的表现加以阐释的划时代成就。
武人是五代社会动乱的乱源吗?
与南方诸国相比,北方的五代(梁、唐、晋、汉、周)一直被学人认定是乱世,而主要的乱源是武人。无可否认,这是真相,但只是部分而非全部的真相。要发掘更多甚至更重要的真相,理应利用墓志碑铭,一则因为它们是许多国史传记的前身,二则它们对墓主家人、仕历和婚姻的记载,远多于正史。不难发现,不少在朝廷或在地方上足以致乱或致治的武人,凭着武功起家之后,他们的家人和后代都兼学文武,有些学习文事,有些学习武功,有些兼习两者。他们也兼仕文武,有些是文官,有些是武官,有些先后兼任。有时他们也兼治文武,有些在文事有治绩,有些在军事,有些兼得鱼与熊掌。当然,他们也文武通婚,与文人气味相投和利益一致。两个问题油然而生:其一,武人在五代和宋初的历史角色和地位,是否必须重估?甚至连宋代在历史分期如“唐宋变革”的角色也要重估。其二,利用墓志碑铭作为论据,应如何克服“隐恶扬善”“以虚为实”或“这些不过是墓志题中应有之义”的疑虑?
对五代武人,三位专门研究军政的老、中、青学人的观点如下:
王赓武(Wang Gungwu)的名著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及其中文版《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至少经过一次修订和两次重刊(1963、2007、2014、2015),但对武人的评价不变。王氏没有否认五代道德混淆、无法无天和紊乱脱序,但认为这些描述无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而“新的探索应摆脱儒家的先入为主(Confucian preconceptions),……那是苛严和缺乏同情心的”。于是,王氏只探讨军权,主要是天子亲军的重建和争雄,但至少留下五个尚待探讨的疑问:
一、五代武人真的不能符合儒家的价值标准吗?他们被大量选入真宗朝编撰的《册府元龟》受到赞扬,那些编撰者不正是儒臣吗?他们难道没有采用儒家规范作为选录的标准吗?
二、五代武人不乏允文允武堪称“儒将”的人,他们为何不能符合儒家标准?
三、一般武人,即使出身绿林也要遵守帮规,他们成为朝廷命官之后,是否仍要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或“武士之道”(以下有时简称“武德”)?如是,与传统的武德有何异同?如《左传》“武有七德”列举用武所要符合的七种条件——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是否仍为五代用武者(当然包括武人)所遵从?例如西蜀的多位节度使,“或以他职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务(治理地方镇所),专事聚敛,政事不治,民无所诉”,蜀主乃以东川为武德军,“取武有七德以为军号”,作为武人鉴戒;宋仁宗朝的知谏院张方平也说:“武有七德,安民为本”,以安民为七德之首。事实上七德不但见于宋代的诏令、奏议,还见于基层读物《小学绀珠》。此外,宋太祖以杀降为“不武”之甚,把白起逐出位于武学的武成王庙,这个出自武人之口的武德,难道不符合儒家标准?
四、研究权力是否应兼顾军与民?拜制度所赐,如诸司使副既可到军队任职,亦可到地方担任刺史至节度使,大量武人乃成为地方首长,集合管军与治民(含财和刑等)两权于一身。所以,探讨权力结构,不能只看武人的武功而不顾他们的民事。
五、新史学应否兼顾高层与基层?我们一方面应探讨新的权力结构“在政治上”(如中央与藩镇的关系)有没有减少还是增加了无法无天和紊乱失序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应同情百姓,追究新的权力结构“在社会上”有无改善庶民的生活。
一言以蔽之,只要探讨武人是谁和他们的吏治,便能检讨“儒士之道”与“武士之道”有何交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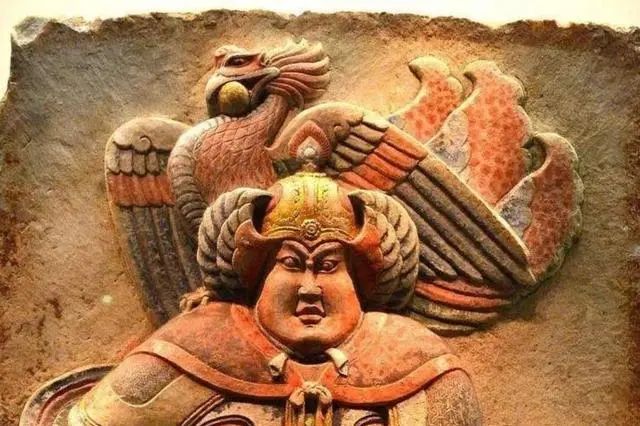
黄宽重《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1990)可能代表直至今日的主流看法。
他说五代“军人干政,兵变迭生,武人不仅成为政局递嬗的主导力量,更是政权转移、政治败坏的重要因素”。类似意见也常见于教科书,如高明士和甘怀真等人编著的《隋唐五代史》(2006增订本),认为五代政局的特质之一是“暴虐残杀成性”,其“政治风气的败坏,实为中国史罕见。……殆因五代政权主要建立在军事将领之手,而这批武夫悍将的横行暴虐,较诸唐末大混乱不遑多让,遂使黄河流域之民众,疾苦日甚。以致白骨蔽地,荆棘弥望,百姓有如生活在水深火热之困境中,其惨况实难以想象与形容”。《剑桥中国史》第五册上篇(2009)第一章《五代》有点旧酒新瓶,读者不如直接阅读陶懋炳《五代史略》(1985)、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1990)和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1991),后两书居然不在剑桥书目之中;较新的著作亦无多大进境。
方震华(Fang Cheng-hua)认为文治与武功难以并存,而武人难行文治。他的“The Price of Orthodoxy: Issues of Legitimacy in the Later Liang and Later Tang”(《正统王朝的代价——后梁与后唐的政权合理化问题》,2005)与王赓武的意见稍有不同,以为后梁为了寻求正统,政治领袖愈来愈拥抱儒家的价值系统(increasingly embracing the Confucian value system),“也间接造成这些武人统治者的文儒化”,结果却是灾难连连,如“后梁末帝重视文治,却缺乏统兵的能力,终为李存勖所灭”。本来以武取胜的“李存勖在灭梁后暂停军事扩张,致力模仿唐代皇帝的形象,……执掌大权的郭崇韬则努力重建由世族领导的文人政府,而这两点都成为其政权快速灭亡的原因”,这岂不是以文误国?在专书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D.875-1063)(2009),方氏以三页的篇幅讨论武人形象的改变,如与文士交流和学文,一些子孙亦允文允武,但总的来说,武人“缺乏一个道德传统,足以抗衡行之已久的儒学(Confucianism),……武人风格不能产生一个价值系统,能够将军事行动法理化/正统化”,又认为“武臣的统治对庶民带来严重的苦痛,进一步破坏武人的道德形象”,似乎又重复了王赓武的说法。
无论如何,“重视文治”的后梁末帝在位约十一年(913—923),于五代最长,远过仅四年(923—926)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和后来任何一位君主,不管他们是重文还是重武,那又如何能够推论,谓重文是王朝短祚的原因呢?在位次长的是约八年的后唐明宗(926—933,欧阳修误以为最长),被《旧五代史》称许为“力行于王化,政皆中道,时亦小康,近代已来,亦可宗也”,毫无疑问是因为他能兼重文治和武功(见本册《沙陀王朝武人刺史卖剑买牛》),故也实在推论不出文治是短祚之因和文武不能兼治兼得。
今人可能被古人误导,或不加细想,把他们的“论点”误作“论据”,或对武人过于严苛,例如要求他们十项全能,只要有一二项失足,便全盘否定。我们先看古人对五代武人的论点或观点,以下列三个最为重要,然后逐一检视。

针对武人之贪残害民,宋太祖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史·文苑传》说:“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两说都被学人视为宋代重文轻武的由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武人不能文治。
针对武人不遵法制,《宋史·刑法志》说:“时天下甫定,刑典弛废,吏不明习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
针对武人鲜能识书或吏治,太祖“谓侍臣曰:‘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左右不知所对”。
如所说属实,那五代的武德既难以符合儒家的要求,也不构成自成一格的价值系统。在统治阶级里,即使是中高层的武臣,也普遍没有文识,欠缺道德,不守法制,鲜能吏治,祸国殃民。他们是“致乱”之源,根本谈不到“致治”,故宋太祖要把他们的治权移交文臣。既然如此,学人甚少探讨武人之治,更不会追究他们是否治乱相若,甚至治多于乱了。
然而,这些观点大可商榷。首先看它们的性质:就史学三论来说,它们仅是“论点”,不是“论据”,用它们来“推论”五代武人不能文治,就好像我们推论秦桧是奸臣,证据是古人说他是奸臣,那当然是流于人云亦云的。我们最好列举事实(fact)或事件(event)作为直接论据,再引用古人和今人较有凭据的论点作为辅佐证据。不管出自古代名人或现代大师,欠缺凭据的观点和论点,最好不要用作直接证据,更不能用作最重要的证据(本册《不远鬼神文武皆然》)。
论点又分“专论”和“泛论”(generalization或概括性评论),前者针对个案,后者针对众案。以偏概全或以小见大时,必须留意个案的“代表性”;以全概偏或以大见小时,也必须留意其“涵盖度”。且看一个批评五代吏治的泛论:魏泰(活跃于神宗至徽宗)自谓其《东轩笔录》乃“姑录其实以示子孙而已,异时有补史氏之阙,或讥以见闻之殊者,吾皆无憾”,亦即魏氏所记有时与众不同,但均是实录。
今人亦认为,“总的来说,在宋人笔记之中,它还是史料价值较高的一种”,应大致可信。魏泰说:“五代任官,不权轻重,凡曹、掾、簿、尉,有龌龊无能,以至昏耄不任驱策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一直到了“范文正公仲淹,乞令天下选人,用三员保任,方得为县令,当时推行其言,自是县令得人,民政稍稍举矣”。不知这些为数众多,且最接近人民的基层官吏,是文人还是武人居多?难道文人不是致乱之源?假如到了范仲淹之世,才“民政稍稍举”,那五代末年与北宋初期恐怕是五十步笑百步。这种泛论,应相信哪些部分?无论是学生或老师,都应分清哪些是论点,哪些是论据,不要把缺乏论据的论点当作论据,以讹传讹。
其次看这些观点的提供者,最重要的当然是宋太祖,以过来人说过来事,又是皇帝,谁敢不信。其实不尽然,太祖的布衣交兼儿女亲家王审琦家族就不是他所说的“方镇残虐,民受其祸”和少读书不通治道。审琦为节帅,以不事聚敛和尊重旧制赢得《宋史》的赞美,说他“政成下蔡,……卓乎可称”。王氏以武功起家之后,子弟文武兼习、兼仕和通婚,有些更能兼治,于民事和军事均有治绩,其姻家刘氏家族也是如此(本册《不远鬼神文武皆然》)。
这种文武兼资用(capitalization)的情况,早见于五代初年。梁太祖朱温甫即位便公开表扬“文武材”,鼎鼎大名的武将牛存节家族,及其同样鼎鼎有名以治理河南建立不世功业的姻家张全义家族,还有中层的萧氏家族,莫不文武兼学、兼仕、兼治和通婚(本册《六代婚宦书与剑》)。到了五代末年,后周两位皇帝尤其重视吏治,在诏撰的两个《屏盗碑》里,表扬两位武人文武兼资,是与皇帝“共理”天下的“良二千石”(本册《武人在地之光》及《一所悬命》)。事实上宋太宗亦勤习诗词、书法和法律,追求允文允武和出将入相的传统武德。太祖既是过来人,岂会不知,他只说同行的坏话(部分真相)不说好话(其他真相),当然有政治目的,我们不要中了这位武人的心计。
事实上,针对太祖因武臣残虐而将其治权移交文臣的说法,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朝臣提出更多的解释或真相。如贾昌朝在仁宗庆历二年(1042)上奏说:“太祖初有天下,鉴唐末五代方镇武臣土兵(native土著,不是士兵)牙校之盛,尽收其权,当时以为万世之利。及太宗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及西夏反,宋人屡战屡败,“此削方镇兵权过甚之弊也。……此用亲旧恩幸之弊也”;随即指出,“太祖监\[鉴\]方镇过盛,虽朘削武臣之权,然边将一时赏罚及用财集事,则皆听其自专,有功则必赏,有败则必诛,此所谓驭将之道也”。
由此可知两点:其一,太祖要夺去武人治权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削弱有着强烈地缘(即土)和亲缘关系,而且“过盛”的武人势力,务使方镇无力挑战中央,简单说就是“削藩”,关键应是“权力”多于“治乱”。其二,削权之后,太祖和太宗仍然重用为数不少的旧将,并把军中的刑赏和地方的部分财富“听其自专”,而且一任十多年,成为所谓祖宗驭将之法,如“结之以恩,丰之以财;小其名而重其权,少其兵而久其任”。在此,太祖和太宗最重要的考虑,在如何驭之,而非轻之或抑之,故在“小其名”和“少其兵”之后,便可“重其权”(充分授权)和“久其任”了(本册《一所悬命》)。
最后,看这些论点的内容是否完全符合事实。就道德来说,儒家之最高要求应是忠义,而欧阳修《新五代史》说:“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总计十八人之中,只有李遐和孙晟是文人,武、文比例是16∶2,武人大胜文人。我们可以不同意欧公的界定,但他至少拿出数据来(参本册《数目字会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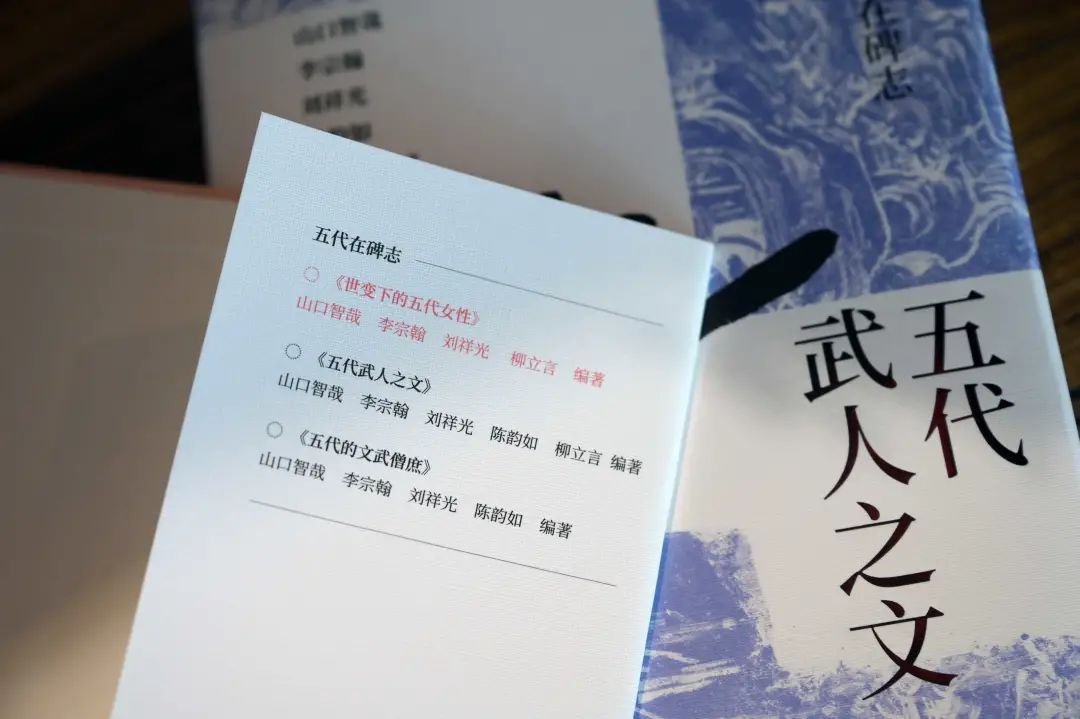
更值得注意的是武成王庙的配享。能够入祀者足以作为武臣之典范,即使不能自成一个价值系统,也相当符合儒臣的要求了。太祖即位后三年(963),看到白起在七十二贤之列,以其“杀已降,不武之甚”,涂抹其像,并下诏由三位文臣检讨入祀之资格,结果一共退去二十三人,补入二十三人,其中三人是五代武将。重订之后,就国祚与人数之比例来看,第一高的是魏晋南北朝,第二高竟是五代,第三隋唐,第四汉代,第五春秋战国。无论是质和量,五代堪充典范的武人不差于其他朝代。
就法律来说,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2006)第十章《立法成就与司法制度的变化》劈头就说:“对于五代时期刑法变化的研究,还存在不少错误的观点,甚至将这些观点写入高校教材之中,影响颇大。”在立法上,他认为“五代时期的法律不过是唐后期的继续,是沿袭而来的,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因而要说倒退变重,无论如何也算不到五代时期”。在司法上,他也承认“军事执法机构仍是武人掌管,使得整个五代时期执法官员素质比较低下的情况难以改变”,似乎有所倒退。有趣的是,连宏在《五代法律制度考》(2007)所举的司法例子竟是好坏参半。被百姓叫好的,如后唐庄宗、出卖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和后晋安重荣等,都是武人;被叫坏的却有文人,如后汉宰相苏逢吉要将贼人和四邻同保“全族”处斩等。可见在五代法治好的一面,武人实有份;在差的一面,文人也有份(本册《才兼文武是否墓志应有之义》)。
其实,从法律文化的角度言,五代庶民对“非典”司法的感受,跟士大夫,尤其是后世的士大夫,有时并不一样,喊好或多于叫坏。此外,武人若经济有成,受益的是大众,司法失败,受害的毕竟是小众(第一册《冤家聚头文武合》)。无论如何,武人在单一项目失手,不足以抹杀其他项目的贡献。
就吏治来说,纵使五代乏善可陈,也没有多少官逼民反的事例。最严重的一次是后梁末期(920)的毋乙和董乙起事,很快就被敉平,跟唐代王黄之乱、宋代方腊之乱和明代李自成之乱不能相提并论,或见五代武人治郡不比唐宋明的文人差太多,至少没有招致国破家亡。
吏治之优劣也反映在经济之发展,杜文玉《五代十国经济史》(2011)的结论说:“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北方的经济状况不如南方那样繁荣,但是早在后梁统治时期有些地区就已经使经济有所恢复,比如(三位武人)张全义治理下的洛阳地区、韩建的华州、成汭的荆南等。此外,后唐明宗统治时期,史学界公认是北方的小康时期。尤其后周建立以来,采取了各种措施,大力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已经使北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唐代末期。”可见在武人主政之下,五代的吏治自始至终都有可观之处,否则何来复元、小康与超越?
这些真相有没有反映在墓志里?章红梅的发现让我们既喜又惊。她花了长达九年的时间完成《五代石刻校注》(2017),共收五代拓片224件和十国121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她完全没有提到的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2012)约103件。让我们高兴的是,她再次发现五代有黑暗的一面,反映墓志没有一味隐恶。章氏自谓墓志可补史之阙略和正史传记之讹谬,在她笔下,五代是“血腥分裂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凋败的时期之一。……中原地区,武人专政,……轻视文治,崇尚武功,……与北方重武轻文相较,南方君臣多能礼待文士儒生,积极提倡文教”。让我们吃惊的是,章氏校注了约345件墓志碑铭之后,竟然完全没有看到或提到五代光明的一面,她还是以“血腥”“凋败”和“重武轻文”作为五代的特点。
其实,她所说的南方诸国,创业君王无一不是武人,可见武人及其后代亦未尝不能“礼待文士儒生,积极提倡文教”。章氏在无意之中也替北方提出一个重文的证据,说修史之时,“为了弥补图籍的不足,北方各小朝廷扩大搜罗范围,南方诸国割据势力所辖典籍也在采集之中”。如是,还能说北方漠视文化吗?个人相信,只要凭着常识和心平气静地阅读五代224件以墓志为主的拓片,是很难推论五代是“最黑暗、最凋败的时期之一”或“轻视文治,崇尚武功”的。不说别的,那些墓志的作者全是文人,其文笔之精彩与学养之高深,毫不输于唐志和宋志的作者,难道他们不是出自五代的教育和文化环境吗?由此可知,成见和误解绝对影响研究者的判断和视野。

本册的特点是完全利用武人的墓志和碑铭,不是去否定学人已发现的部分真相,而是发掘更多的真相,从四方面增加我们对武人的了解。
第一,文人如何书写武人。正史传记的重要史源就是墓志碑铭,后者的一个特点是隐恶扬善和虚实相间,故我们首先分析墓志的笔法,并提出若干研究的方法,或可避免误解误读。
第二,武人之文事(或作文治、吏治、民事等,随重点而用)。武功与文事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少武人出身布衣,对民间疾苦的感受和关怀往往超过书斋里的文人,他们成为地方首长后,往往与文士合作,建设地方。他们是否对“致治”有一定的贡献,而不是只有宋太祖所说的“致乱”?
第三,武人之品德和信仰。与文人相较,有时大同小异,双方不乏交流的平台和媒介,如经营佛事和与文化僧交游。有时更是武胜于文,如欧阳修认为武人至少在死节和死事的表现上超越文人。他们是否能够符合儒家的严苛标准?
第四,武人之后代和转型。安史之乱产生一批新的武人,如河朔三镇;王黄起事和后梁、后唐统一北方,又产生一批新人;五代约五十三年亦足以产生新一代的武人。武二代或三代有何重要特征?假如文武兼习、兼仕和通婚是普遍情况,是新兴势力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后,为了维护其统治阶级和阶层的地位而采用的普遍手段,那么宋代的“重文轻武”应如何理解?
推荐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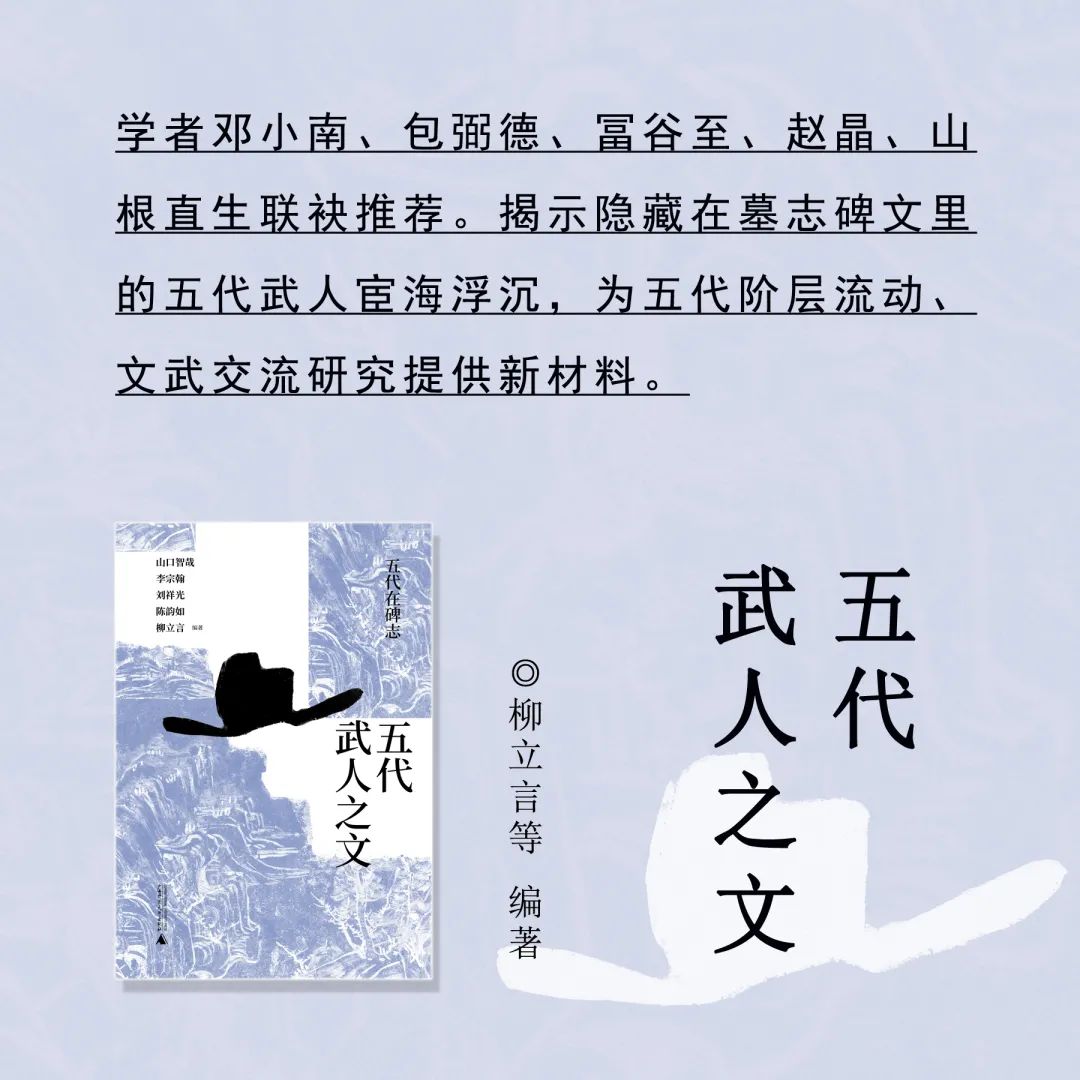
宋史研究专家柳立言领衔编著,历史学界学者邓小南、包弼德、冨谷至、赵晶、山根直生联袂推荐。
本书利用墓志碑铭发掘出的有效信息,是研究五代社会史及阶层流动、文武交流不可或缺的史料、史观。书中分析解读了五代武人的家庭结构、仕宦经历、上升通道、观念信仰等,探讨并重新评估了武人在五代至宋初的历史角色和地位,增加了我们对五代文武间的交流和武人的乱与治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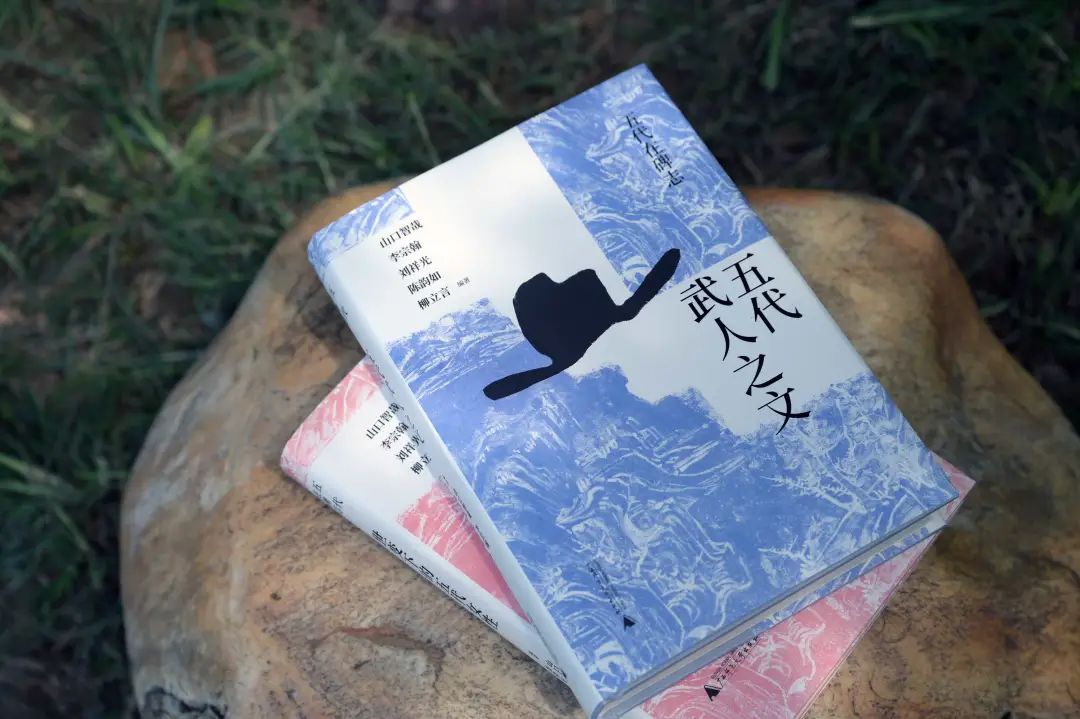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