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自《资中筠自选集·感时忧世》,作于2006年)
我们国家近二十多年来,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有些领域进展迅猛,有些领域相对滞后。当然,走在最前面的是物质层面的经济发展。在这里面,民营企业的发展势不可挡,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增长迅速,而相对说来,其地位的确立却是经历了缓慢曲折的过程,最近几年发生了质的变化。曾几何时,提“私有”尚属“敏感问题”,而现在经过多年的争论,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终于写入宪法。一方面是企业的权利和地位得到保障,用通俗的话说,可以放手赚钱;另一方面,财富分配不均、严重的两极分化为朝野所关注。另外,除了传统的弱势群体的需求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的社会需求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公民”及其与公益事业的关系提上日程,适逢其时,出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CSR)这样的新名词。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几个层次:首先,当然是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同样是赚钱,对社会和民众的利益有大有小,有的行业本身甚至危害社会;其次,合法经营、合法纳税;再次,保障本单位职工的权益,也就是首先对本单位职工负责,至少应满足现有的劳动法规的要求。以上几条我认为是对企业最起码的要求,对民营、国营都适用。反过来说,就是不搞假冒伪劣、不欺骗坑害消费者、不偷税漏税、不行贿受贿、不经营有害行业(如赌博、有害青少年身心的网吧等)、不肆意污染环境、不拖欠工资、不虐待员工、不违反安全生产规则,等等。就我国的现实而言,要做到这些已经不容易,我无法统计,完全尽到这些起码的责任的企业占多大比例。
但是,现在讲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停留在这些最起码的要求上,而主要是指企业在实现自身的经营和利润以外,关注社会需求,为社会公益做出自己的贡献。本来,每一个公民都对社会负有责任,单单把企业突出出来,首先,当然是因为大量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集中在企业手中,他们处于强势,责任与能力应相适应。其次,如何使用财富,对社会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包括社会稳定、普通百姓的生活,乃至社会风气。
试以近百年前的美国为例:当时在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情况下,社会财富总量急剧增加,而且大量财富向少数财团聚集,出现了举国侧目的富豪家族,同时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尖锐化。于是对待财富就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富人一掷千金,穷奢极侈,以炫富为荣,无视底层百姓的呻吟。当时像芝加哥、纽约等先发达城市,豪门盛宴是一种时尚,奇装异服的化妆舞会规模达几百人,一夜消费额相当于一个工人一生的劳动。一时之间,这些富豪也颇为风光,成为记者追捧的对象;另一种富人,以卡耐基、塞奇夫人等为代表,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看到就在同一城市,那些居住在污秽破烂的贫民窟中的劳动者,全家人在条件恶劣的血汗工厂里日夜苦干,难求温饱,意识到这样的社会难以为继,自己既然有幸成功致富,就对改变这种情况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也是一掷千金,不过是用在公益事业上。这种捐赠不是盲目的、零散的,而是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可以取得最佳社会效果的领域,并且以自己经营企业的知识和经验,或聘用具备这类能力的精英来管理公益机构。
对美国说来幸运的是,后一种富豪的行为压倒了浮华之风,引领了百年的社会风气。从卡耐基到比尔·盖茨一脉相承,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公益捐赠文化”。并没有法律规定什么人或什么规模的企业必须作公益捐赠,但是美国成功的企业,或有点名气的企业家如果不做公益捐赠,自己都会感到说不过去,更不用说富豪榜上有名的了。如今,全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价值观,掌握财富的人固然有权过常人望尘莫及的奢华生活,但是为他们赢得尊敬和荣誉的,也是他们自己从中得到真正满足的,绝不是超常的高消费,而是对社会公益的贡献,而且其贡献一般与其财富相适应。
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企业,并非单纯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进行捐献,而是具备在各种社会需求中做出明智的判断的眼光,选择覆盖面广、现实需求与社会长远发展相结合的那些领域进行捐赠。所以,教育和医疗健康领域几乎是各国公益捐赠普遍的重点。其长远意义不言自明。另外,掌握巨大财富的企业和企业家引领社会风气,公益捐赠固然是很重要的途径,还会在企业内部自觉倡导某种伦理观念。例如美国大卫与露西·帕卡德基金会提出一套要求领导阶层与员工共同遵守的守则:
正直(对周围同事和捐赠对象都开诚布公)、尊重一切人、相信个人的创意、讲求效率(善于抓住难得的足以做出突出成绩的机会,以长远的目光来选择支持的领域)、有宏大思考的能力(能够下决心对独一无二的、足以产生长远影响的项目进行大笔捐资)。
硅谷社区基金会提出的“硅谷文化”若干条,其中有:
●我们相信将所得返回社区至关重要;
●我们像社区的投资者一样思想和行动〔这句话意思是指,无偿的捐赠与有偿的投资要一样积极、认真〕;
●我们在做出付出的决定时有极强的独立性;
●我们的联系超越硅谷以外……;
●我们的潜力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还有不少大公司,先从在本单位进行人性化管理做起,善待员工,在企业内部倡导某种伦理和行为准则,同时鼓励员工在其所居住的区域进行志愿活动和公益性捐赠。总之,有了CSR这个概念,就可以创造出许多途径,以财富的力量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
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求生存,缺乏平等竞争的条件。在20世纪前半期发展起来的民营工商业、金融业,尽管力量薄弱、处境艰难,但还是涌现出了一批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企业和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对倡导现代理念,对促进科技、文化、教育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也带有中国特色,与反帝反封建联系起来。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宗旨,发展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外御列强的压迫,内促中国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对赈灾、扶贫,特别是对教育进行捐赠也是自认为义不容辞的经常任务。一旦国家有难,出现不少毁家纾难的感人事例。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在抗战爆发后,国府南迁之际,停止了公司的业务,把全部船只无偿提供国民政府运军队和物资到大后方,在关键时刻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一般说来,这部分被统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及其代表人物(包括书业、报业等文化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也是反对奢侈浮华,主张勤俭创业,推崇知识,鼓励子弟自立自强,不做纨绔子弟。公益理念也可以从企业内部做起。例如笔者少时直接有过接触的天津东亚毛纺厂,其创办人是著名企业家宋棐卿,不但生产了当时最优质的国产毛线,堪与英国的进口毛线一争高下,而且在经济极不景气、民不聊生的40年代末,带头在厂内实行合理的工时工资、职工福利、培训等制度,并建立职工子弟小学,本单位职工子弟一律免费上学,同时也对外招生。由于其师资力量强,教学制度先进,外面的学生也踊跃报名,我的两个妹妹就上过那家小学。
不论是外国的企业家还是过去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家,对社会的责任感都出自主人翁感,认识到自己的事业是与全社会的稳定和兴旺息息相关的。社会如果发生大动荡,或是崩溃,企业自然无法生存。在社会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时,无非是两条路:或者底层百姓揭竿而起,或者掌握主动的阶层自觉进行改革,实行渐变。在极“左”的年代,一切改良的措施,包括公益、慈善事业,都被批判为“麻痹工人斗志”的“欺骗手段”。记得“文革”中,上述东亚毛纺厂善待职工的做法曾专门作为资本家的“伪善”加以批判,称该企业为“文明监狱”。
在这方面经过了历史的反复和断裂,时至今日,在又一轮财富的积累、新的社会矛盾呈尖锐化的形势下,显然我们只能尽可能选择和平改良而避免暴力动乱。处于矛盾一端的先富起来的群体,自然对缓解矛盾,进一步推动社会健康的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自己,也为他人。毋庸讳言,在方今中国的国情中,无论是缓解社会矛盾、保障平民的生活福利,还是制定政策法规以促进公益慈善事业,主要责任仍在政府。中国企业与企业家的处境不能与美国相比,其能力和责任自不相同。但是本文主题是企业的责任,政府方面不在讨论范围,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企业家作过分的苛求。
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自觉地提出CSR这一概念,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本着这一理念在做着真正的公益事业,是足以令人欣慰的。此处用“真正的”字样,是区别于一些笔者认为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公益事业,至少其出发的理念与CSR有一定的距离。最常见的误区是把公益捐赠与软性广告混为一谈,捐赠者的目的是为自己的企业和产品打知名度,甚至公开提出交换条件。其条件五花八门,归根结底是有利于推销企业。即使就一时一事而言,客观结果对捐赠对象有利,也不足为训。如果成为一种模式,不但无助于发扬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反足以腐蚀真正的公益事业和公益理念。当前在我国,此类做法之所以流行,并且不以为怪,除了“资产者”方面的问题外,与现行体制、不健全的法规分不开。目前,自愿捐赠的渠道并不畅通。绝大多数有公募资格的公益基金会还是“官办”或脱胎于“官办”的,它们在全国或各地向企业集资,操作公益项目,取得不少成绩,但由于是“官办”,就免不了权力带来的种种弊病。就全社会而言,总是求大于供,有时捐赠方就可能不纯粹出于自愿,而集资方急于完成任务,免不了凭借某种权势和许诺一定的条件。这样,公益捐赠中包含着某种胁迫和利诱的成分,也成为一种权钱交易。也许在目前的过渡时期,这是权宜之计,但是为了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应该在较短的时间内逐步扭转这种方向。我们期待出现的局面是:一方面,企业界的CSR意识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体制和法规进一步完善,方便任何有志者进行自愿、独立的捐赠,这样反过来又促进CSR的普及,可望出现集思广益、百花齐放的公益事业,满足形形色色的社会需求。
有鉴于我国的特定条件,有志于公益捐赠的企业和企业家还不可能像国外那样,随时自己成立独立的各类规模和主题的基金会,同时也还缺乏足够的专业人才进行管理和操作。比较方便的办法是,与自己信得过的现存的公益组织合作。“全国企业社会责任网络”(NGOCB-CSRN)的建立刚好可以在供需双方之间建立起桥梁。这种合作既可以满足捐赠者“自愿”、“独立”的原则,还可以对接受方雪中送炭,同时保证专业、规范的操作。在目前我国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我乐观其成,故欣然应约命笔,略抒己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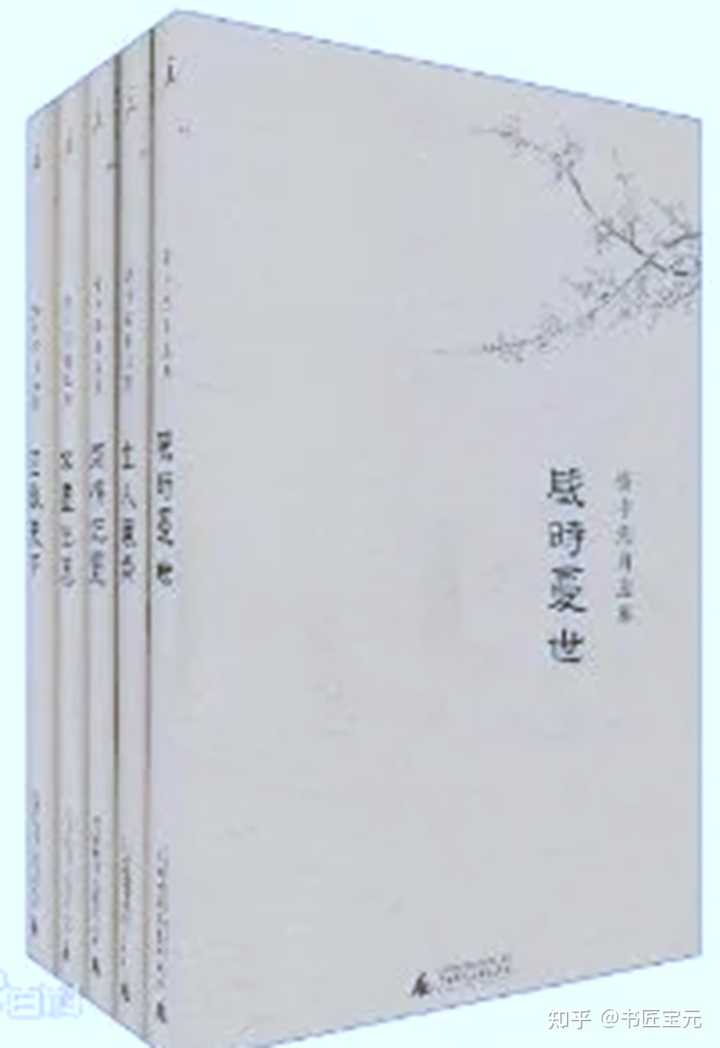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