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
领袖观点| 行业报告 | 行业头条 |
本文来源于《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在此次讲座中,陈教授以身边实际的事件为例,解释了为什么民间金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同时表达了对于“人之初,性本善”的坚信,以及相信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如果有办法让自己继续遵纪守法,没几个人会选择抢劫偷盗。
同时,陈教授也强调“领薪日贷款”等高利贷金融有它特殊的需求和社会意义。许多中低收入群体是正规银行、正规金融机构都不会服务的对象。他们的信用评级要么很低,要么就没有信用数据,唯一愿意给他们提供服务的是高利贷机构,因为那些高利贷机构愿意承担风险,愿意接受信用评级低的人。
“此外,如果把这些高利贷业务都禁止,那就把这些中低收入群体的“做好人”路子都堵了。一旦碰到青黄不接或者发生意外灾害,这些老百姓就会被逼上绝路、走向犯罪。民间金融不只是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也更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其实,民间金融就是与正规金融相对应,是指未受到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所控制的金融活动。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赊贷业。《国语·晋语八》叔向论忧德不忧贫时说,栾书的儿子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极),假贷行贿",就是说放债取利是其增殖财富的一种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金融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其规模日渐增大。与此同时,国家对“非法集资”的打击也逐渐升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行政取缔到创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非法集资”类犯罪的罪名,其惩治手段不可谓不严厉,惩罚范围不可谓不宽泛,然而其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对于民间借贷的界定和合法性,吴晓灵教授曾在中国国际金融博物馆主办的“江湖”沙龙上有过如下表述:
“民间借贷从来都是合法的,合同法保护民间借贷,个人和个人之间是可以借贷的。但是有一个利率的上限,如果高于基准利率的四倍,不受法律保护,并不是非法。最近看到报纸上说贷款利率下限是放开了,什么时候放开上限,其实没有上限,只是说超过了四倍以后不受法律保护,这个事情我希望能够解释。”
“企业之间本来也应该是允许借贷的,这也是民间借贷,商业信用早于银行信用,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很多国有企业靠在银行能够得到贷款的便利,当贷款的二传手,跟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国企也在当二传手。然后把这个钱借到了社会上,治理整顿经济从过热到冷却之后出了很多的风险。在95年的之后人民银行立了一条企业之间不许借贷,那是特定情况下出现的。因而企业之间的借贷是商业信用,也是对的。但打击的是什么呢?打击的是说不是一对一的借贷,而是你向很多人去借钱,司法解释是有的。超过多少金额,超过多少个人以后就叫非法集资,民间借贷从来都是合法的。”

“大家其实想知道,我能不能够靠借贷为生呢?来做贷款买卖呢?我们推的小额贷款公司其实就是这样,你可以以借贷为生,注册一个贷款公司,但是它的红线是不允许吸收存款。玩自己的钱可以,玩一两个机构给你批发的钱是可以的,但是不许去玩社会公众的钱。”
但是,虽然民间金融是合法的,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是,并不是就放任其发展,近日,吴晓灵教授在接受《21世纪》的采访时,强调对于民间金融要加强监管:
“金融是负外部性很强的行业,必须有市场准入。通过牌照管理等方式将金融活动的负外部性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针对小规模金融活动,在法律规定的一定范围内,可有条件的豁免监管。比如私募基金就是在豁免条款下进行自律管理。”
“但总体来说,金融是一个强外部性行业,并且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必须要从严监管,保证社会的平稳运行与健康发展。”
摘录
今天,我们谈金融怎么可以减少犯罪、促进社会和谐。你可能觉得奇怪,金融市场怎么能降低犯罪行为呢?
如果把我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的四年算进来,我一共在耶鲁工作了22年。多年以来,总有一些关于耶鲁校园周围发生抢劫的报道,尽管这些年已经改善很多,犯罪率在减少,但还是偶尔会发生。两年前,一位叫斯密的年轻人在傍晚时分拦路抢劫,被抓获后,他供认说:“我有一份工作,但要到月底才发工资。可是,我这个月18号就没有钱了,还有12天怎么过呢?跟朋友借钱借不到,又没有银行愿意给我贷款,我靠什么活下去呢?只好去抢了!”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斯密未必想违法抢劫,只是到月中青黄不接,没钱过日子了,被逼得无路可走。而金融本来可以给斯密这样的人提供类似“过桥贷款”这样的支持,因为他12天后就有月工资,只是现在没钱。所谓“过桥贷款”就是给他一些钱,让他度过未来12天这个“桥”,也就是让他把未来的部分收入转移到今天花。好处是让他不必去抢劫,可以继续做好人!
一、领薪日贷款的故事
实际上,在美国,有专门针对斯密这种“青黄不接”挑战的贷款业务,叫做“领薪日贷款”(payday loans),只是美国50个州中有15个州法律禁止,很多社区也自己立规禁止这种贷款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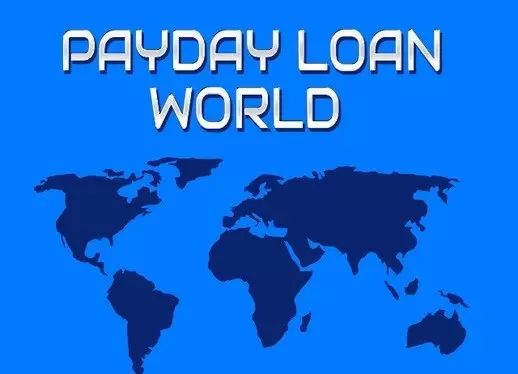
领薪日贷款大致是这样运作的:斯密18号没钱了,还有12天才领到月薪,但是没关系,他可以带上近几个月的工资单、个人支票和最近的银行账户单,到“领薪日贷款”公司,写上350美元的个人支票,把签名日写成月底的领薪日,然后他就能借走300美元。
由于中间要付50美元费用,如果把这个算成利息成本,那么,每年利息就要超过400%,成了绝对的“高利贷”!正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这看起来似乎是乘人之短挤榨借款人,所以,美国的许多州和社区就禁止这些“高利贷”公司存在。
所以,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像斯密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就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去偷盗或者干脆抢银行。
那么,斯密抢劫背后的逻辑到底有多普遍呢?是不是能得到大样本数据的支持呢?芝加哥大学茂斯教授对加利福尼亚州的1300个社区做了系统研究,因为这些社区有的允许“领薪日贷款”业务,有的是严格禁止。
结果她发现,在1996年后的7年里,一旦碰到自然灾害冲击,两类社区都会经历个人破产率的增加,抢劫、偷盗案发率、酗酒发生率、夫妻吵架率、救护车呼叫率等指标也都会上升,但是,允许“领薪日贷款”等高利贷业务的社区里,情况要显著好很多,抢劫、偷盗、夫妻吵架的增加程度要少很多,那里的社会秩序要更加稳定!
她的研究表明,由于金融帮助老百姓摊平突发冲击带来的影响,让短暂的收入短缺不至于造成“无米下锅”,所以,金融工具使这些斯密们可以继续做遵纪守法的好人,而不是被迫走上犯罪!
二、高利贷带来的好处
在美国,大多数州还是允许“领薪日贷款”等高利贷机构合法经营的,所以,金融降低生存压力的好处在大多数地方还是能够享受到。根据一个研究机构统计,一年大约有4000多万美国人使用“领薪日贷款”,占全美国人口15%,每年“领薪日贷款”总额超过400亿美元。这些使用“领薪日贷款”的美国人,平均一年借8次左右!他们对高利贷的依赖可想而知。
从这些数字,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没有“领薪日贷款”去帮忙,这4000多万美国人中,有多少会被逼上抢劫、偷盗之路呢?所以,立法者可以出于好心去禁止高利贷,但是,倒霉的是老百姓社会,因为那会导致很多人走投无路、走向犯罪。
1985年到2002年之间,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参议员叫“菲利普·格拉姆”,他出生在乔治亚州,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残疾、没收入,他母亲靠同时做两份工作,才勉强做到既照顾残疾丈夫,又抚养三个孩子。但是,家境艰难,收入风险太高,没有正规银行愿意给他母亲贷款买房子。到最后,为了让一家人住上自己的房子,他母亲唯一的选择就是借高利贷买房。

所以,就有了格拉姆参议员的名言:“如果次级贷款早就被禁止,如果高利贷机构早就被禁止,那么,我母亲就不可能在我们兄妹三个都很小的时候买到自己的家!有了高利贷,我母亲至少可以让我们住自己的家!”
如果监管者为了自己的方便而禁止民间金融、禁止高利贷,那么,千千万万个低收入家庭就永远买不上房子,受害的是中低收入老百姓,而且社会也不得安宁。从这些故事和数据可以看到,金融虽然在一般意义上是解决跨期价值交换的问题,而在具体场景下,这种跨期收入配置可以起到稳定个人和家庭的生存状况的作用,尤其让你即使碰到突发冲击、意外挑战,也能很平稳地生活。或者即使不碰到意外冲击,也能像格拉姆参议员说的那样,让收入低、贷款风险确实大的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到自己的房子,享受其它生活品。
那么,为什么民间金融在中国被禁止那么多年呢?在监管便利和社会收益之间,以前的选择似乎是偏重监管便利。
三、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要点
第一,“人之初,性本善”。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如果有办法让自己继续遵纪守法,没几个人会选择抢劫偷盗的。
第二,“领薪日贷款”等高利贷金融有它特殊的需求和社会意义。许多中低收入群体是正规银行、正规金融机构都不会服务的对象。他们的信用评级要么很低,要么就没有信用数据,唯一愿意给他们提供服务的是高利贷机构,因为那些高利贷机构愿意承担风险,愿意接受信用评级低的人。
第三,如果把这些高利贷业务都禁止,那就把这些中低收入群体的“做好人”路子都堵了。一旦碰到青黄不接或者发生意外灾害,这些老百姓就会被逼上绝路、走向犯罪。民间金融不只是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也更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本文为作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
说到底,“民间金融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市场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对金融抑制下扭曲的信贷市场的一种纠偏机制。其既包括不具有系统性金融风险、无须纳入金融法调整的民间借贷等应然意义上的民间金融活动,又包含具有强烈系统性金融风险却游离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准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等金融活动。”
“中长期改革目标还应当是改变金融抑制的现状,促进金融自由化,开放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大力发展地方性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并实现利率市场化,以真正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间资本逾越法律界限进入监管空白地带的动机,防止民间金融危局的再次发生。”(观点来源:北京大学法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刘子平)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