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张茜
9月28日,Lisa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三张幕后照片,以疯马秀内部的猩红色沙发为背景,并配文“Can’t wait for this to finally happen!”(等不及,这终于要发生了)。随着法国当地时间28日晚的首场演出结束,网络上释出了Lisa幕后与舞者的合照,演出造型也随之曝光。
一时间,互联网再度沸腾起来。
在此前,其实并没有任何现场影像或照片释出,但声称是绝密独家的Lisa脱衣舞彩排视频,已经在网络上被倒卖无数次,求片卖片,好不热闹。但对于真的会花一两块钱去买这种“绝密独家”的人来说,可能有点遗憾,拿到手的只是一些被换了名头的高糊演唱会直拍和盗录视频。
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认定Lisa的自甘堕落,还有她丢亚洲女性脸面的罪责,假视频也不是很必要。
她自出道以来的任何照片、舞台、服饰、造型,乃至私人生活,都已经成为了审判素材和荡妇明证。“铁刘海”不再,是初心已失;露出臀部线条的舞台服,是“泰妞”迎合欧美;长期增肌锻炼所致的大腿肌肉,是丰臀嫌疑。
一言以蔽之,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人类想象力的丰富和无穷。
9月初,知名韩国女团BLACKPINK成员Lisa,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剪影海报,配文“嘘……即将到来”,宣布她将登上巴黎疯马夜总会的舞台。

Lisa发布的剪影海报
9月6日,疯马秀作出了确认,在官网放出简短的文字预告,称Lisa将变身“疯马女郎”(Crazy Girl),于9月28日、29日和30日,进行5场演出,演绎原创的歌舞表演,包括经典曲目“But I am a Good Girl”和“Crisis?What Crisis!?!”。
消息轻易突破了K-Pop粉圈,引得舆论哗然。一边是声称“Lisa背刺东亚女性”,一边喊着跳舞自由,少管女人”,一场围绕“Lisa应不应该去疯马秀跳艳舞”的互联网口水仗,以“腥风血雨”之姿,持续了近一个月,热度至今不减。
对具体在争论什么完全没有兴趣的路人,下意识的反应是,Lisa甚至都不是中国人,这吵得也太莫名其妙了。
的确,一位在泰国出生,在韩国出道,在欧美市场爆红,手握7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K-pop女爱豆,将登上以脱衣艳舞著称的巴黎疯马秀舞台,却唯独在中文互联网上激起了泼天的愤怒。
乍听之下,反常到令人难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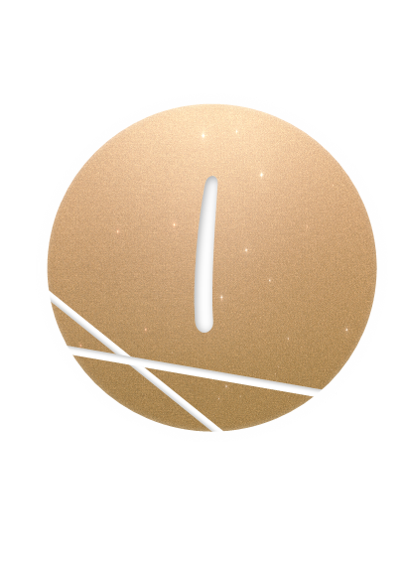
疯马诱惑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争议,关于疯马秀,我们需要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补充一些背景知识。
疯马夜总会(Le Crazy Horse de Paris),是一家在欧美享有盛誉的卡贝莱歌舞厅,以纯正法式风格的艳舞著称,位于巴黎的乔治五世大街,由阿兰·贝尔纳丁于1951年创办。
1968年,全裸表演在法国合法化之后,“疯马”成为巴黎的“脱衣舞圣殿”。

Le Crazy Horse de Paris
2005年,贝尔纳丁家族将该夜总会出售。新股东和管理层接手后,在夜总会总监安德蕾·戴森伯格的负责下,开始邀请知名艺人在夜总会进行脱衣舞表演。
第一位登台表演的“客串明星”便是蒂塔·万提斯(Dita Von Teese)。这位全球最著名的脱衣舞明星,被认为“以其标志性的香槟浴和闪耀奢华的脱衣舞服装,让脱衣舞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重新回到了聚光灯下。”

Dita Von Teese
至于现代脱衣舞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的巴黎。它源于一种名为“依芙特的就寝仪式”的表演,演出者是一名年轻女性,表演内容是表演者在寻找跳蚤的同时,慢慢脱去一件件衣物,最后也没找到跳蚤。
发展到现在,脱衣舞和脱衣舞之间,也存在鄙视链。
法国人作为现代脱衣舞秀的发明者,非常看不上拉斯维加斯的脱衣舞俱乐部那种“全部露给我看”的美式风格。
法国人安德蕾·戴森伯格面对美国记者,如此评价她心中的美式脱衣舞:“她们只是在盲目地满足男人的幻想和要求,因此失去了某种自我。”
在她心中,疯马秀则是“非常有灵性”,她表示“一切都与暗示有关,一切都在想象中。那确实是在展示,但你又永远不会真的看到。比较像是用水彩装点人体,而不是用灯光打亮。”
夸夸其谈之下,也不难看出疯马秀的某种规范。疯马女郎的身体要在遮掩与展示、调情与挑逗、自我与被欲求之间有所平衡,主仆角色灵活流动。这种通过对视觉效果的掌握,操弄身体元素,来延续观赏情趣的表演秀,作为“一种技艺表现”,在疯马夜总会,达到了近乎规范化的程度。
这里的规范化,指向的是一套严苛的身体标准。这也是在这次争议中,被高亮出来用于批判的物化女性“明证”。
疯马女孩都修习过古典芭蕾。她们的身高必须在186cm到193cm之间,双乳乳头间的距离不能超过26.67cm,肚脐到阴部的距离不能超过12.7cm。她们每周必须量一次体重,身上不能有刺青,也不能做医美手术。
她们的身份对大众完全保密:每个人都有舞台化名,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绝不对外公开。虽然她们登台时身上唯一的衣着可能只有一些小小的彩色灯串,但她们永远不会完全裸露,脚上也一定穿着高跟鞋。
高跟鞋用于凸显腿部线条,“穿上它以后,走路会变得不一样。动作也会变得不一样。加了一点人工技巧进去之后,整个诱惑游戏就可以顺利展开。如果是完全裸体的话,观众反而会睡着。”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整套关于脱衣舞秀的诱惑论述与实践,产生于一个身体禁忌相对宽松的国家。

作为一个孕育了存在主义的国家,法国人会拍一部《臀部不为人知的秘籍》的纪录片,来讨论身体部位用什么方式形塑了文明;也会用“她的屁股真会唱歌呢!”和“当假屁股横行世界,且让我歌颂正直无欺的真屁股!”来赞美臀部;法国人也用波伏娃的背面全裸照,作为庆祝波伏娃一百周年诞辰的封面。
然而,回到东亚社会,脱衣舞秀却是另一回事了。在社会伦理上,它是有违社会风气的“淫秽表演”;根据职业划分,它一般被归入性产业之列,甚至更笼统地划归为“娼妓问题”,从来没被当作一个独立现象得到过广泛讨论。
这样的认知框架里,具体到Lisa应不应该出演疯马秀的口水仗上,问题就呈现为情色象征、偶像身份、女性主义理论和自由意志的大乱斗,只分回合,难计胜负。

艳舞自由?
9月8日,在ELLE法国更新的一篇文章中,疯马总监安德蕾·德森伯格透露,早在7月,BLACKPINK于法国国家竞技场举行演唱会期间,Lisa已经秘密排练疯马表演多次。
“作为‘Totally Crazy’演出的一部分,Lisa将穿上多种服装,与剧团一起表演多个节目。”
至于疯马秀邀请Lisa的原因,疯马总监则表示:“希望吸引年轻且依然充满女性魅力的新客户群”,并称“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明天的受众……因为疯马已经成为自信、自由、充满好奇心、热爱自己的女性的象征。我认为,Lisa的决定也传达了相同的信息。”
也就是说,疯马秀邀请Lisa,作为一项商业策略,瞄准的其实是K-POP偶像身后异常活跃的粉丝群体构成的潜在市场——作为参考,BLACKPINK的粉丝性别占比,女粉为88%,男粉12%。
另一边,考虑到BLACKPINK的未来发展前景不明,4位成员都将踏上单飞之路。以舞蹈和说唱见长的Lisa登上疯马秀,对于更为鼓励爱豆保持“温良恭俭让”清纯女神形象的K-POP产业来说,无疑算得上惹人注目的“破格一跳”。
如果只看商业层面,以争取年轻人市场和最大曝光度为目的的跨界合作,不分行业、不分国家,大家都在玩,显得无可指摘。
事实上,争议的焦点远离了这一跨界合作的商业性质,指向的是价值层面的话语之争。疯马秀的象征意义和Lisa的K-POP女性偶像身份之间,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视频剪影中的Lisa
为了在价值上更接近全球年轻有闲一代女性,疯马秀采取的话语策略,是搭流行文化和身份政治商业化的快车。借女明星们的性感迷人和星光闪烁,把自己的品牌价值,和展现身为女性的内在自豪感关联起来,是一条十分讨巧的谋生之路。
近些年,疯马没落,亟需变革,将品牌内核从“礼赞魅力与诱惑”的法式色情集大成者,更新为一个鼓励女性作为主体,用奢华艳舞进行自我欣赏、自我肯定、自我赋权的舞台。
在《法式诱惑》一书中,作者把这种精明策略总结为:“疯马夜总会的舞女是掌控自己命运的霸主。”
但是,这种无助于女性权利伸张的消费主义话语收编,其实是新自由主义式耍流氓。一定程度上,消费主义试图染指所有严肃价值的厚脸皮公关策略,已经帮助我们完成了对“好词”的快速脱敏。
脱衣舞俱乐部的总监鼓励粉丝把脱衣舞秀和“女性力量”挂钩理解。但抛开这种营销策略,人们依然有理由,不把性感迷人的星光闪烁和展现女性内在自豪感关联起来。
美国专栏作家阿里尔·利维(Ariel Levy)的一句话,非常适合引用在这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性感风趣、聪明能干的话,就用不着装扮成脱衣舞女郎的样子,或者让自己变得像男人一样,抑或迫使自己成为任何跟浑然天成的自我不相符的样子。”
当欧美身份政治乘着商业化的大潮,在鼓励个体基于多元主义的“性别身份”消费各类文化制品,为主体性积极证成,但真正的进步难觅行踪的时候,在全球文化版图上,远离欧美文化圈的东亚受众,皱着眉头,厌恶任何以“自由”和“开化”为名的跨文化说教。

争议中经常出场的,是上野千鹤子那句话:“强调女性具有能动性、自愿选择成为性客体,是性产业的陈词滥调。因为女性的能动性可以为男性的性欲免责。”
这当然不是巧合。
因为东亚女性在公共交往和社交权利上,最主流的诉求一直是“反性化”——和欧美不同,“我们”拒绝承认女性的优势地位来自于做一个性感尤物。
我们借助对性别的“去差异化”,来强调一种平等对待的地位:“妇女能顶半边天”。这种路径,不同于欧美社会,后者鼓励女性重新定义何为女性气质,进而构建其主体性。
具体到日常情景中,在不关涉社交主题的场合,人们最好不要对女性作出强行欣赏或者贬低一番的低劣姿态,于现代人而言,这是最基本的礼貌问题。
然而现实是不一样的,在一个时时刻刻致力于性化、客体化女性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中,我们无法天真地大谈特谈“情色资本”的颠覆意义,因为这个概念成立的理论前提,是性应该构成一个能够被单独讨论的议题,独立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这也是理解“Lisa背刺东亚女性”论的逻辑起点。

“背刺东亚女性”
9月15日,据韩媒报道,Lisa拒绝了YG的第二份价值500亿韩元的续约合同,当天,YG Entertainment的股价大跌9%,创下自去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在大众的认知中,她作为K-POP女爱豆,被粉丝真金实银捧到了全球流行文化新星位置,如今褪去了曾经在镜头前惊慌失措的青涩乖乖女模样,成为了可以影响YG股价涨跌,在唱跳事业和个人发展上,手握绝对议价权的优势女性。

Lisa
粉丝眼中,此刻的Lisa,拥有近乎无限的选择余地。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她选择了在奢牌满地的巴黎,把自己陈置在“性客体”的魅惑灯光下。借用罗兰·巴特对脱衣舞的解构式解读,这在抽象意义上,属于把身着高定舞台服和昂贵饰品的自己,主动纳入奢华之物的范畴。
于是,在反对者的理解中,5场艳舞秀,2300张入场券(疯马秀最大客容量为460个座位),象征着她主动邀请他者,把自己当作一件纯粹的奢华之物来看待。她在社交媒体说出的“你没有被邀请”,更是点燃反对者的怒火。
借助一点点想象力的发挥,亚洲女性登上代表白男权势的舞台,形成了一种后殖民主义风格的叙事:“欧陆白男玩味远东猎物”。长期被置于性偏见和劣势处境中的亚洲女性,在只有Lisa到场的疯马秀上,再次丧失了“我们”极力伸张捍卫的主体性。
无论Lisa最终在疯马秀以怎样的形式表演,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反对她的人,在观念上认定,在后殖民霸权语境下,伪装成“鼓励女性用穿最少的衣服,实现自我赋权”的男凝色情文化,支配了这位头脑简单的漂亮女性,又一次选择了主动扭曲自己的自由意志,投其所好完成五场自降身份的取悦。

Blackpink与LV三公子的合照
由此,跳艳舞被赋予了接受“第二性”的从属地位、自我毁灭主体性的象征意味。
在这套逻辑中,Lisa不仅是粉丝用“零花钱”砸出来的爱豆,她作为K-POP产业粉丝票选的流行文化偶像,被郑重其事地赋予了代表“亚洲女性”的国际形象和主体地位的抽象责任。
在反对者眼中,这顶高帽决定了,疯马秀当然不只是跳艳舞,她以展示自身“情色资本”的玩票方式,一边取悦白男审美,一边背刺东亚女性。

“向下的自由”
此外,基于对追星文化的想象,对Lisa的声讨,还指向了“带坏未成年人”,尤其是“会让未成年的小妹妹,觉得跳脱衣舞从此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为此感到揪心扼腕的人们,代入的是在《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中出现的问题:
“怎样做才能把一个更值得活的世界交给妹妹们?”

思考乘着想象的翅膀,“底层失足女性”受剥削而无人在意的悲情场面,和流行文化偶像下海大跳艳舞的堕落影像之间,被强行关联了起来,而在道德直觉上,后者导致前者,后者加重前者。
一个轻易可达的结论是:Lisa去疯马秀的行为,在客观上,会鼓励年少无知的“妹妹们”接受下海被吃、自暴自弃的自由。
所以,这才出现了那句反复重申的呐喊:“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
如果前述背刺论的完成,还讲求一点点结构主义理论功底,和逻辑上自圆其说的能力。从这里开始,诉诸道德恐慌的滑坡论证势不可挡,也把争论带向了一地鸡毛的弥散状态。
学者丁瑜的《她身之欲》,是一本关于“娼妓问题”的质性研究巨作。她访谈了23位工种各异的“小姐”,以研究者的身份短暂与她们同吃同住,了解她们的生活。
每一位“小姐”都给出了为什么自己会选择从事这份工作的答案,贫困、教育机会的缺乏、对流动和城市生活的渴望、家庭冲突、不愉快的婚姻等等,每一个答案都不那么轻松。
但没有一个“小姐”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我追星,我喜欢的明星在夜间节目上跳甩臀抖胸舞,我想模仿她,在众多的模仿路径中,我觉得相比买一个同款牛仔短裤或者吊带裙,做“小姐”是更能让我感受到追星骄傲的生活方式。
不管具体涉及什么问题,到处可见“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获得高赞。
但这个向下是相对谁的向下,怎样算向下,向上的自由又指什么?这句话对自由和自由意志的预设和理解,是基于对哪种危险的感知和焦虑?它自身又释放着何种专断气息?
统统无人回答。
我的理解中,这句话背后,表现出对复杂现实的拒绝,徒有性别平权坦途的天真愿望——永远向上。对流行文化明星向下的批判,背后的心理逻辑是对“偶像指引人们向上”的暗许。
然而,没人告诉我们的是,一旦走出习惯用感性曲解现实的玫瑰色泡泡,每个人要面对的复杂问题就是:
对于大写的“人”来说,残忍的真相是,自始至终,不论是声称历史指定的个体,还是粉丝票选的偶像,在一个讲求人格和尊严平等、自我负责的时代,那些看起来熠熠生辉的人物,明星、政客、学者、教皇,他们在价值进步的意义上,根本不具备可以引导他人的特权地位和超人能力。
“怎样做才能把一个更值得活的世界交给妹妹们?”
如此傲慢的提问方式,是在表达一种真诚的迷茫还是“婆性”(上野千鹤子用词)风格的自恋呢?
Blackpink
对于清楚所谓独立而自我负责的人生,这个问题或许根本不成立。
站立在如春日薄冰的现实之上,我们作出选择,我们承担后果、孤独、痛苦和责任。如果能意识到,从小到大被父母提醒“你只能靠自己”是一种成长创伤,那没有道理看不出把性别进步的责任,寄托在唱跳爱豆身上,是多么虚无的上纲上线。
这个一地鸡毛的争议事件,如果揭示了什么紧迫问题,不是Lisa去法国跳艳舞,不是东亚中产女性的地位滑落,更不是想象中失足女性的任人欺凌。对于此时此刻,紧迫的问题,是对观念的狂热崇拜,正在与尊重他人的日益缺乏沆瀣一气,相辅相成,挤压每一个人可能的思考和生活空间。
尊重事实,尊重经验性的常识,尊重他人的智识,尊重与我不同者也具备自我决定、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但唯独不应该抱持教条主义的单一道德法则和行为准则。
所有捍卫个人选择、消除个人发展限制的权利理念,都应当警惕其僵化为审判教条,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底线。
参考文献:
伊莱恩·西奥利诺,《法式诱惑》
马蒂尔德·拉雷尔,《去他的父权制》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
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
韩炳哲,《爱欲之死》
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望》
理查德·乔伊斯,《道德的演化》
上野千鹤子、铃木凉美,《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
丁瑜,《她身之欲》
约书亚·L.彻尼斯,《一种思想及其时代:以赛亚·伯林政治思想发展》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编辑 | 阿树
排版 | 风间澈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