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建设健康城市的行动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思考,是21世纪的中国在促进人类健康发展方面提出的一种新要求,它表明中国在建设健康城市的理念、行动和目标方面已经达到了一种更为自觉的阶段。
城市,从它开始成为人类社会交往的结点或枢纽的那天起,就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其形态和功能,以适应社会和人类生存发展变化的需要。因此,排除人类无法预见的大自然灾难,就人类历史的一般发展来说,任何一个城市的产生、发展或退化、衰败,都不是某个具体的事件或单一的因素可以解释的,城市的存在和变化与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和谐程度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城市的健康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是不可分割的。
普遍地说,城市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构成形态,城市与社会关系是具有共同内涵的两个词,它们之间似乎并不需要构成新的相关性来进行交流。但是就城市的特殊性而言,城市相对于周围地区的集中性,枢纽性,依赖性和控制性,使得城市构成了自身特殊的,区别于周围地区,特别是区别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关系。于是,城市既面临着一个协调自身内部社会关系的使命,又面临着必须与周围更大的社会关系协调的使命。城市的健康,实际上是指城市自身的和谐关系,而健康城市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则是指城市自身的和谐与周围社会的和谐关系。虽然本质上都是一种“和谐”,但表现在不同的层次,就具有了不同的特性。要认清这种不同,就需要理解健康与和谐的关系。
“健康”是检验和谐的尺度
如何理解与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是当代中国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名人或伟人曾经用“大同”、“无差别境界”等概念来定位理想社会,但这些理想最终之所以只能成为空想,主要是因其本身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自人类社会从原始状态进入社会分工状态以后,人与人之间在智慧能力、资源占有等许多方面的不同,都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可克服的先天差异和后天差距,要想在消灭这种差距的前提下去建立理想社会,在理论上缺乏科学性,在实际上属于乌托邦。
但是,和谐社会的提出,首先在理论上是科学的。因为和谐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找差异之间的配合,消除差异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切有机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一个完整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需要各种不同的分工,会出现各种差异。理想的社会不是要消灭合理的差异,而是要协调差异之间的关系,在健康发展中共同感受幸福。
当今社会,一切科技、生产和文化的发展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保障全体人民生活的幸福才是目的。和谐社会的科学定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逐步成为人类理想社会的现实目标。党的十六届六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开篇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把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和向往的和谐社会概念引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并赋予崭新的含义,使几千年来人们追求的理想社会第一次成为拥有13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生动实践。” 今天,“和谐”正在由一般美学的概念和文学的形容词上升为人类理想社会追求的真理。
真理的价值在于它的预见性和指导性。正因此在没有实现真理之前,真理的真伪就成为人类认识的难题,于是人们提出了真理的检验问题。那么,什么是检验“和谐的尺度”呢?
在“和谐社会”的大目标下,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建构和谐社区、和谐单位、和谐企业、和谐家庭、和谐班组的口号。当所有的决策和行动都被冠上“和谐”的头衔时,对和谐的检验自然也就成了问题。对人体来说,和谐是通过健康来表现的,和谐的身心会促进人体的健康,反过来,疾病缠身则表明身心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和谐。同样,对社会来说,和谐也是通过健康来表现的。如果一个社会失序动荡、冲突激烈、关系紧张、社会病症很多,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不健康的,表明其内在充满着不和谐。
尽管健康城市运动一开始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但在当今世界,其内涵和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了卫生的范畴。在“健康”问题上,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日趋发展,传统的定式思维已经被打破。环境因素、药物滥用、行为与生活方式、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等等,都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关于健康的概念以及影响健康的种种因素。因此,对“健康”概念的定义和对“健康”问题的研究,已远远超出了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的范畴。
正如个体的健康需要肌体均衡的发展一样,城市的健康也需要社会均衡的发展。经济学的木桶理论,曾经比较形象地阐明了一个系统必须均衡发展的真理,社会发展更是这样。以一个城市为例,如果这个城市的GDP年年增长,但公共资源短缺,公平正义失落,诚信关怀缺失,理想信念滑坡,那么单纯依靠经济发展或强化政治的手段都是不能促使城市健康发展的。
总之,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来看,建设健康城市的实践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当建设健康城市运动让人们直接感受到健康的结果时,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就不再是遥远的目标而是包含在其自身的内涵中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健康”是检验和谐的尺度。
建设健康城市是构建和谐社会承上启下的关键点
健康作为一种生命现象,必然要表现自己特有的运动和发展形态。如果说“生命在于运动”表述了生命存在的一般规律,那么“健康的生命在于和谐的运动”就揭示了生命发展的具体规律。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生活领域,健康的生命个体,总是会通过自身和谐关系的渗透力由点向面(周围的环境)扩散开去,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和谐的张力”。一颗生命的种子在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后,就会长成参天大树,并通过开花结果播撒后代,让自己的周围形成适宜于自身生命发展的树林。相应地,动物世界的形成,人类世界由个人到家族乃至到城镇、国家的形成也具有这样的规律。生命世界的生存竞争,可以被理解为自然对不同物种自身和谐张力的考验和筛选。
在中国,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王者治国经典的是儒家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它从根本上表述了以人为本的“和谐张力”在社会治理上应该得到运用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古希腊也有相应的表现,因为在古希腊,哲学有最高智慧之学的美名,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即:如果哲学家能成为王者或王者本身就是哲学家,那么国家就一定能够得到最佳的治理。这个想法的形成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单个人的作用在整体社会中的影响是非常渺小的,因此个人是不可能也没有力量去影响整个社会的;但是权力可以将个人的作用提升到支配社会的绝对高度,只有借助权力,个人的影响力才可能成为社会的影响力。在这方面,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就是典型,他一生都在致力于这样的寻找,但其结果正如中国的孔子一样,两者皆以失败而告终。
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任何试图通过个人的修养或智慧及其所营造的和谐环境去影响整个社会的实践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圣人成不了王者,而王者也难以成为圣人。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权力的获得和运用从来都不是实现理想的途径,相反是争斗欺诈的利益战场。圣人追求的和谐关系在尔虞我诈的权利争斗中无法生存,因此通常只能退隐山林、市井或朝野。
随着科学进步与民主制度的建立,现代社会越来越要求执政者“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决策者用好权的最高境界,就是要构建全社会和谐的大环境。如此,执政者“以人为本”的理念才可能得到真正的体现,从而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建设健康城市,对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个个人来说,就是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的大环境;对整个社会来说,它则是一个放大的个体,并且承担着与周围城市、乡村和国际交往中和谐关系构建的使命。因此,建设健康城市,是构建和谐社会承上启下的关键点,也是促进全人类健康发展的大本营。
来源:《健康城市理论与实践》,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健康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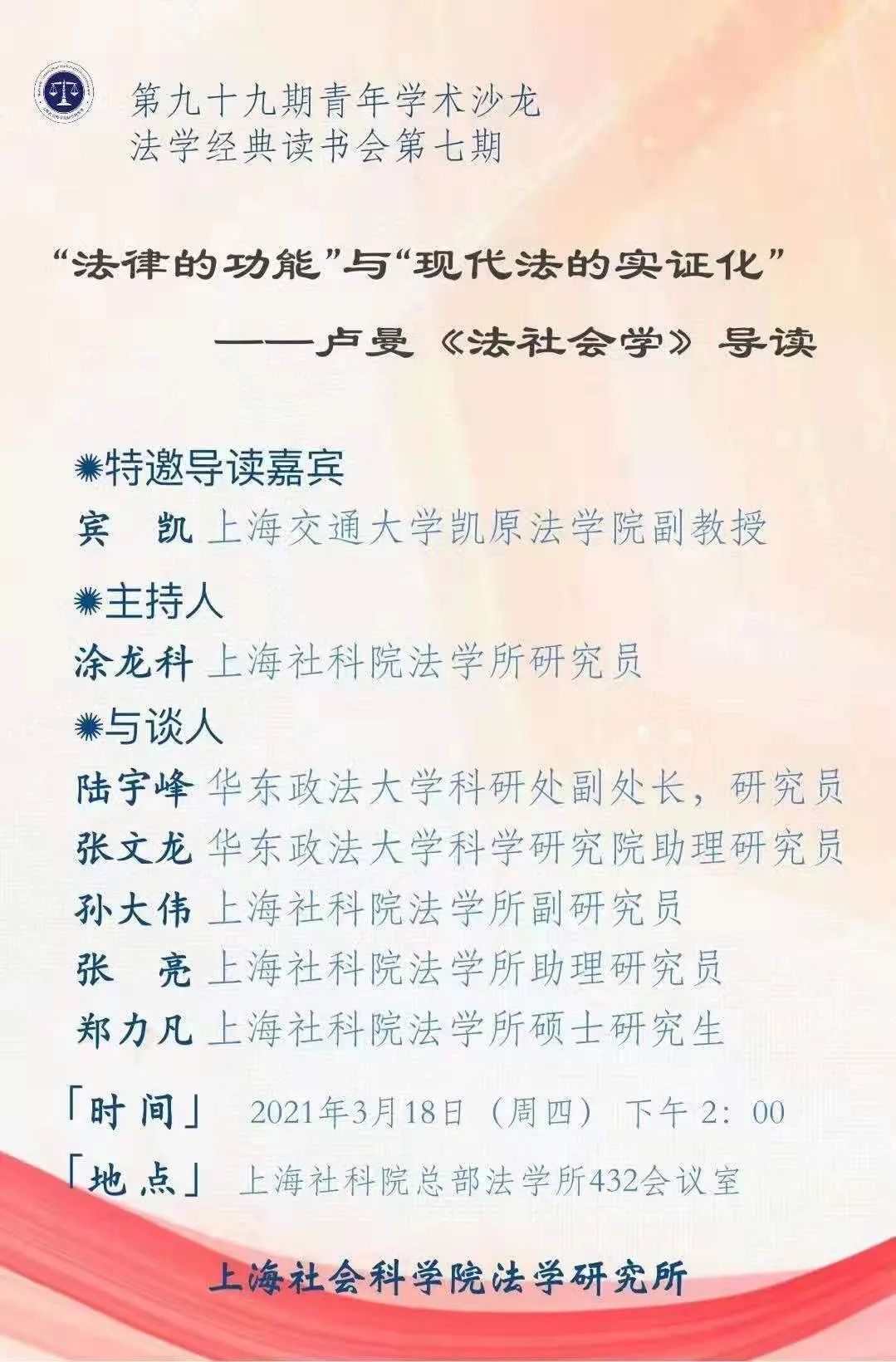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