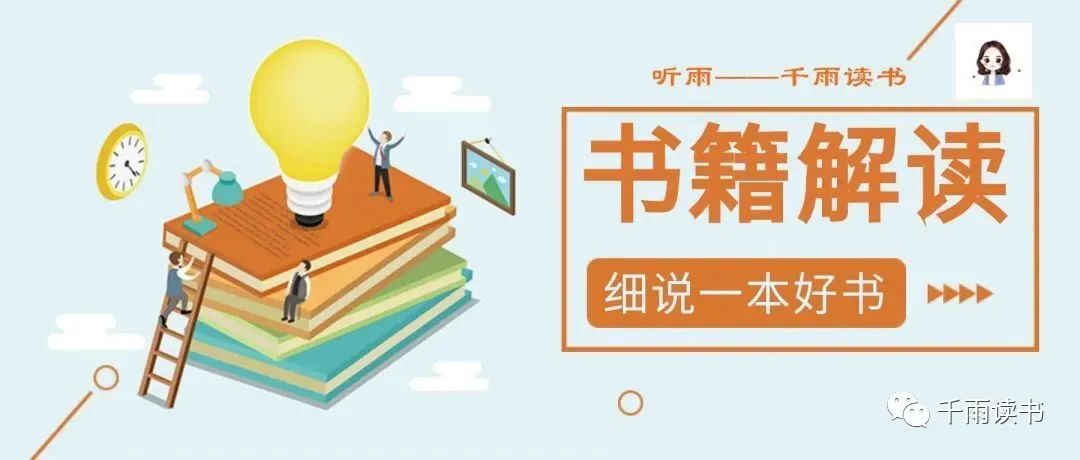
几千年来的农业文明,导致中国人对星象、气象、季节、节气等方面格外关注,因而逐渐形成了“天的观念”,以及古代中国大行齐道的“天下”之说;而“国家”和“民族”的概念,皆为近代产物。
足见中国人的“天命思想”,根深蒂固;即便在当下,中国人的脑子里仍旧保留着强烈的天命观。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一书的阐释是:中国人总想把控自己的生活,视“天时、地利、人和”为最佳时机,故无论成败,均会联想到天数、气数、命运、时运等因素;比如,中国人盖房子,大都会关注“风水”,其中关联的不仅是建筑和环境的问题,重要的是还牵扯了人的命运。
本书作者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翟学伟,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期致力于社会学本土化研究,曾两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

书中内容基于对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史和本土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对可操作化的落地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诣在找到一套具有中国社会运行规则与特点的理论模型。
由于受西方社会学视角、理论、概念和方法的影响,致使中国社科研究领域有关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作品鲜见于世,这也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成了当年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重要“结晶”的原因所在。
因此,翟学伟教授秉着对“中国人、中国研究的反省、批判及出路”的思考,扎根于本土研究。
他一方面以西方社会学研究经验为参照,摒弃“糟粕”,撷取“精华”;另一方面突破长久以来囿于西方社会学研究框架的束缚,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并将中国本土化研究的经验,糅合到一个统一而整体的逻辑分析框架中,以此构建出一套经得起推敲的中国本土化研究的概念、理论和方法。

中国本土化研究的探讨和出路
翟学伟教授在研究中发现,很多中国本土概念并非一定要靠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来说明;因为,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结合文化性叙述和典型故事,来表达其内涵或意义的。
如何理解?
比如,对于某些较难定义的概念,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作品中找到其孕化路径,这些概念其实早已被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或在儒家思想中反复使用过,如“孝”“人情”“关系”“面子”“缘”“恩”“义”“礼”等等。
由此可见,想要定义这些概念不但困难,甚至还会遇到一定义就会出问题的情况,如是否进入了西方的概念?是否挤干了本土文化的内涵?是否用西式思维来看待中式现象……
因为,现代学科研究对于“定义概念”本身,一直存在争议。
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曾指出,社会学家都想通过运用定义性概念,来讨论各种被精确定义的事件;但是,经验世界的性质,却使得这一愿望无法实现,由于概念所解释的实际情况本身就存在转化与变动,故而无法给予明确的分类。
换言之,经验世界的本质,就是定义性概念的绊脚石。
翟学伟教授则从另一角度看问题,认为“敏感化概念”可以用来把握动而不定的经验世界,以及某些社会事件的过程与评价,并推导出一种社会学理论;只是要注意这种理论体系或扩张之法,既不是非此即彼,也并不是非得如此。
基于此,我们才可能发展出一个以本土方法进行的本土研究,即从“面子、人情、报、关系”等一系列难以定义的本土概念中,建立一个明晰的学术概念。
比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许烺光的“情境”、梁漱溟的“伦理本位”、杨国枢的“社会取向”等等;足以说明,这些概念皆源于本土文化的某一重要或核心问题的概括,是可以被精确定义的。
由此可见,本土化研究的出路,既非直接套用西方现成定义的理论,也非投机取巧地进行二元对比,更非添加到传统文化中去试图“化”西方理论;而是一边全面了解西方学术思想,一边坦然面对自己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进而重整“行装”,然后一步步向前。

解析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重要特征
书中说,假如借用西方的人格量表,来理解或概括中国人的性格和交往特征,那一定是不准确的,得到的答案,也只是简单的分值高低而已。
事实上,“脸面”一词,才是真正可以用来概括、描述和分析中国人性格和社会关系的概念,只要稍微分析其内涵,就会触及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关键点;只是这个概念大多源于感受和感悟,而非源自清晰地分析和研究。
因为,涉及这些概念的人更多的是文学者,而非社会学家,导致其含义难以明确和界定;加之概念自身的复杂性,使得大多数研究只能停留在现象描述、归纳陈述和实证研究上;由于缺少对理论探索和框架性的把握,很多经验研究也就无法触及其根本意义,甚至还会出现研究方向的偏差。
好比“面子”这个概念,只要是中国人,又或是接触过中国人的人,都可以真切感受到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心理现象。
玄之又玄的是,“面子”难以被精确定义,只因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为了创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模型,翟学伟教授将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提出的“面子是中国人性格上的第一特征”理论,结合林语堂关于“面子是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 (即面子、命运、恩惠)中力量最强大的一个,很多中国人为面子而活”的观点,进行了一番探讨。
那么,“脸面”和“面子”又有何区别?
对此,人类学家胡先晋先生,从学理上分别给予了学术性的定义,即“脸面”和“面子”为两种不同的心理和行为,“脸面”涉及的是中国人的道德品质,“面子”指的是由社会成就而获得的声誉。
翟学伟教授却表示,这些定义并不能解释清楚二者真正的区别与联系所在——光是从语义上理解,就会发现其内涵不过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又或是一种面部本身的丰富变化来指代复杂的心理与行为。
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做人重心大多落在“关系”二字上,脸面观自然也就落在了“面子”的资源上,而非“脸”的资源上;换言之,中国人总把面子和人情相提并论,而非把脸和人情相联系。
概括地说,中国人人际交往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重情轻理,人情、面子相互交融;其二,在关系格局上,惯用特殊主义手法;其三,讲究形式主义,注重礼尚往来。

中国人情社会的情、理、法平衡观
据上文,中国社会是一个讲人情、面子的社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开始使用“人情”与“面子”这两个概念。
然而,大部分学者都对二者含义、彼此关系,以及在中国社会所发挥的作用等等,尚缺乏理论推演的逻辑整合,也就很难获得中国社会关系的真正解释。
关键在于,中国人运作关系的策略和思路,与西方理论的旨趣和指向存在诸多不同。
因此,翟学伟教授提出了一个预设,即把中国社会设想成“情理合一”的社会,以窥探中国人的处世原则,只有采用这种既不偏向理性,也不偏向非理性的做法,才能在两者之间做出平衡与调和。
例如,中国先秦时的“情”,是指人之常情和性情,与当下所讲的“人情”完全不同;孔子有言:“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足见早期儒家所讲的“人情”,与现代心理学所讲的情绪和感情没有多大区别,原意均是指人的天然或自发感情,即如《礼记·礼运》所形容的:“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由于儒家思想对人伦的规范和影响,后人对“人情”的演变逐渐变味,人情内涵也从心理学认识,向社会学认识产生了严重的转化。
随着时间推移,儒家产生了一套所谓的“做人规则”的“礼”,以及“天理”“人情”之说;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社会对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不做二元对立的划分,其实是期望社会个体在做人办事时,两者均不偏废。
这一点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对做人、做事的判断,并非从理性和逻辑的角度思考,而是从具体情境和个别性上考虑。
举例来说,我国学者在研究传统法律时发现,“情理法兼顾”或“合情合理合法”这两个常用语,是能够表达出一个十足的中国式观念。
通俗地说,能以情、理、法“三位一体”的方式消除冲突,才是最理想的法律。
而三者中任一者,均不能作完整意义上的“法”来理解;这也表明,当情与理处于二元对立时,任何一种理都会受到情的干扰。
但因有儒家文化“礼”的制约,中国人总能在情与理之间,找到可以回旋的余地和平衡。
如此人情社会,皆可谓“人人心里有杆称” ;这种独具特色的社会平衡观,其含义主要体现在主观感受的分寸把握上,也即一种假设“人心本善的良心”上的心理掂量,而非出于真正的客观尺度。

结语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的人情交往,存在隐晦性利益交换的一面,其主因是由“报恩”所促成;因为,在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中,没有“伯乐”就没有“千里马”;“恩情”的本质,就在于个人通过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为他人解决了人生难题,致使受益者产生理应持有的感激和回报。
实际上,中国人的人情交换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为“恩情”范畴的“感恩戴德型”;二为“人情投资型”,通常叫作“送人情”或“送礼”;三为一般性的“礼尚往来型”。
故而在中国人眼里,有交换关系或恩惠关系才有人情关系,没有交换关系就没有人情关系。
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是家庭链条上摆脱不了的分子,因而在言行举止、为人处世、事业功名、做官掌权等问题上,不仅涉及个人,还涉及整个家族沾光的期待。
可见在情理社会里,人情是在报和欠的过程中获得权力,是交换所得的结果;而面子,是在关系的关联中获得权力,是无交换的结果。
所以,不管人情和面子无论如何运作,其结果都是通过与他人建立特殊关系,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回报。
一言以蔽之,与西方社会注重的理性和契约关系不同的是,中国人情社会的本质,就在于中国人乐于借助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正式的社会支持,还有庇护或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往大方向看,个人可借助所处的共同体,在相互支撑和交换中实现个人由共同体走向国家之路,最终通过此通道进入官僚体制,使共同体与国家结构紧密关联,形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景象。
用翟学伟教授的话来总结,想要讲清楚中国的问题,就要用中国的理论方式找到一条出路,并非总用观念文化来说事,而是把人和文化要素一起放到背景中去观察,如此才是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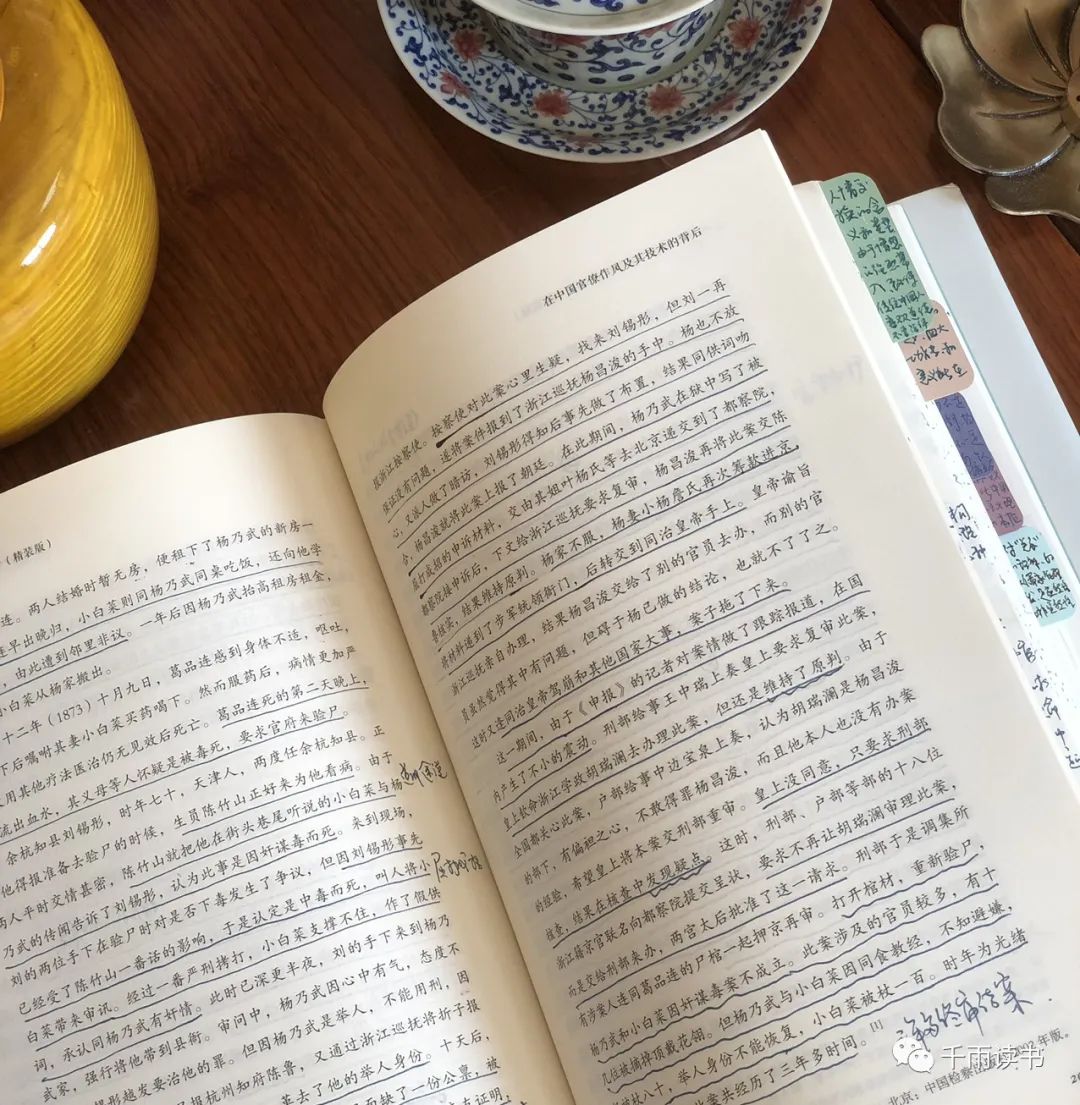
END

秋冬文艺抒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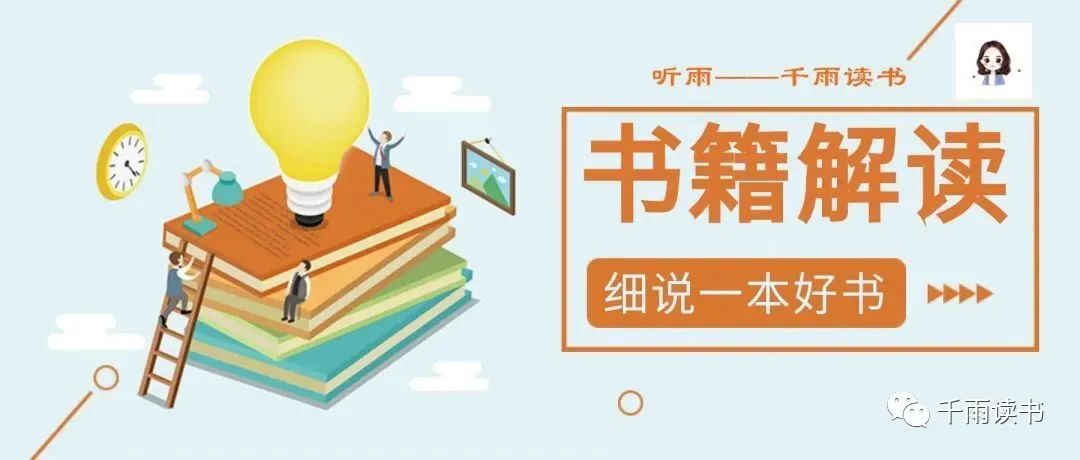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