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00年六月的一天,虽然不断有海风吹来,但古城海康(今雷州)的天气依旧有些闷热。这天,被流放到海康的秦观换了一身新衣,在简陋的家中踱着方步,好像在等待某个重要人物的到来。
忽然,门口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秦观大步走出屋子,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在一个年轻人的陪伴下向他走来。“苏公!”看见来者,秦观三步并作两步迎了上去。“少游!”
见了秦观,来者先是一愣,随即也加快脚步急忙走上前去,眼中流露出久别重逢的喜悦,也隐隐有些不敢相认的吃惊。来看望秦观的这两位远客,不是别人,正是苏轼和他的儿子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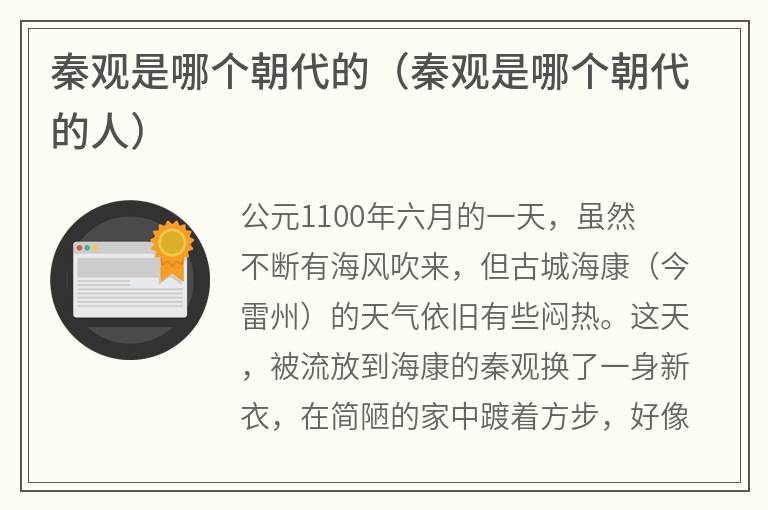
秦观是哪个朝代的(秦观是哪个朝代的人)
苏轼比秦观大整整十二岁,他与秦观是师生,是同僚,也是精神上的知己。秦观因苏轼的举荐走上仕途,同时也因与苏轼的亲密关系,多年来一直与苏轼在宦海中共同浮沉,苏轼受重用时他得以升官,苏轼失意时他也跟着被贬。数年前,在旧党失势的大潮中,苏轼被贬到最为偏僻遥远的儋州当官,不久,秦观也被流放到海康。
在海康时,秦观不过半百之年,虽不再年轻,但也算不上垂暮之年。可是,或许是他心思太重,天性不及苏轼旷达,又抑或是他身体太过羸弱,因此觉得自己命不久矣,此生会在孤苦中死于海康。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还会在哲宗驾崩、徽宗继位后收到北归的诏令,更没想到还有机会在生前与恩师再见一面。时隔多年后再次相见,这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感慨万千。来不及寒暄,秦观立即将苏轼和苏过请进屋里就座。屋舍寒酸,桌上仅有两杯热腾腾的茶水和一些极为简单的点心。秦观和苏轼各坐一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有无限的话想说,但一时竟不知该从何说起。
时光荏苒,回首往事,他们相识已有近三十年的光景。想当年他们初相识,苏轼正从密州移知徐州,已是名扬全国的文坛巨匠,仕途上虽因新党把权无法在朝廷施展才能,但在地方上担任太守,倒也过得惬意逍遥。而此时的秦观,还是个初出茅庐、不满三十的青年人。他十分倾慕苏轼的才华与为人,曾在熟人的引荐下专程到徐州拜谒苏轼,还为苏轼写下一篇《别子瞻》,其中有“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徐州英伟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区域”之句,可见对苏轼的崇敬之情。
当然,秦观也不是泛泛之辈,他出生于江苏高邮城东的武宁乡,祖父曾当过南康太守,父亲也是个读书人,家中有“蔽庐数间”“薄田百亩”,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是书香门第、小康之家,因而得以从小饱读儒家经典。
年轻时的秦观豪爽洒脱,游历江南各地,四处结交朋友,也和多数读书人一样满怀济世情怀。他的诗词也写得极好,如他早年创作的《行香子·树绕村庄》:
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
远远围墙,隐隐茅堂。飏青旗、流水桥旁。偶然乘兴、步过东冈。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
整首词语言朴素自然,寥寥数语就将春日里草长莺飞的村庄景象写得十分传神,清新之气扑面而来。
秦观的文才很受老乡孙觉、僧人参寥子等人的赏识,而孙觉、参寥子又都是当时的名士,与黄庭坚、王安石、苏轼等有交往,正因为这层关系,秦观得以与苏轼这位大文豪结识。
公元1077年,苏轼刚到徐州当太守不足半年,就遇黄河河堤决口,浩浩荡荡的黄河水朝徐州方向涌来,苏轼临危不乱,镇定指挥徐州百姓抗击洪水,备受百姓爱戴。洪水退去后,苏轼主持在城东门筑黄楼,取“土实胜水”之意,并邀秦观为之作赋。
《黄楼赋》之于秦观,相当于呈给苏轼的一份拜师礼。文章写成后,苏轼看了大为赞赏,直夸秦观有“有屈、宋之才”。因苏轼的夸赞和推举,一介布衣的秦观得以在文坛崭露头角,成为与黄庭坚、晁补之等人齐名的文坛新秀。
而秦观与苏轼的深入交往则是在两人相识的次年,秦观去越州探望祖父和叔父,恰逢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于是乘坐苏轼的官船一同南下,途中他与苏轼一道游山玩水、探访各地,俩人性情相投,一路上相谈甚欢,彼此间亦师亦友的关系,也从那时起得以悄然建立。
这一时期的秦观因无牵无挂,生活过得无拘无束,故而曾惹下一些风流韵事,如他最为出名的《满庭芳·山抹微云》一词,据说就是那年在越州时为一歌妓所作: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词中所写的这位女子,是秦观在游历越州时于太守席上见到的一位佳人——一个是年轻潇洒、风流倜傥的公子,一个是色艺双绝、多情妩媚的美人,三杯两盏薄酒过后,俩人便暗生情愫,这便有了“多少蓬莱旧事”“青楼薄幸名存”这两句。然而,欢愉毕竟短暂,分别却是必然。在秦观离开越州时,这位佳人匆匆赶来相送,但兰舟渐远,只剩一人在船上黯然伤神,一人在岸上“空惹啼痕”。
《满庭芳·山抹微云》一词写得真切感人,曾盛极一时,被时人广为传唱。它之所以能被口口相传,一是因为秦观感情之“真”,二是因为他的词艺之高——不说别的,仅开篇的“山抹微云,天连衰草”八字,就像一副工致的对联,雅俗共赏,而句中一个“抹”字别开生面,写出了越州山水如画的韵致,不能不说笔法的精妙高超。
这首词传开后,秦观在词坛的名声更盛了,还因此得了“山抹微云君”的雅称,连一向看不起“艳词”的苏东坡也觉得“山抹微云,天连衰草”一句写得甚好,因此戏称秦观为“山抹微云秦学士”。
不过,苏东坡毕竟是老师,在众人都夸赞秦观时,他却认为这首词总体虽好,里面有些句子却未免黏腻低俗,因此在再见秦观时说:“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吓得秦观急忙解释:“某虽不学,亦不如是。”意思是我虽然学问浅薄,但也不至于像柳永那样。苏轼却继续追问:“‘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问得秦观哑口无言。(见清代王弈清《历代词话》)
不过,秦观毕竟不是柳永,即便《满庭芳·山抹微云》被苏轼归为“艳词”,他此生所作的“艳词”也并不多,但每首词一旦写出,便是词中珠玑,不可多得。如流传甚广的经典词作《鹊桥仙》便是如此: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借牛郎织女的故事写人间悲欢离合的诗词为数不少,而秦观的《鹊桥仙》能成为其中经典,不仅是因为词写得美,更因其立意高远,所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一句才能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公元1079年,因为“乌台诗案”,苏轼突然下狱,而后被贬黄州数年。此间,秦观因两次应试接连落榜,朝中又无人举荐,只得暂且退居故乡,以诗书自娱。
虽然秦观的词风与苏轼迥然不同,但苏轼却偏爱这个比他小十几岁的门生。在黄州期间他自身难保,因此只能在心中为秦观的处境默默叹息。而公元1084年,当他收到诏令终于可以离开黄州时,刚一离开黄州,他就跑到江宁向王安石求情,希望这位昔日在政治上叱咤风云、如今虽隐退但仍不失影响力的前任宰相能提携秦观,以提高他在文坛的知名度。此时,王安石与苏轼已冰释前嫌,他十分慷慨,毫不吝啬地称赞秦观的诗歌“清新似鲍、谢”。
因有王安石与苏轼这两位大人物的赞许和鼓励,秦观决心再度赴京应试,并于公元1085年如愿考中进士,被授予定海主簿一职。
可以说,如果不是苏轼,或许秦观在两次科举考试失利后,也会像他父亲一样守着家中百亩薄田度日,当个简单的文人。然而,因为苏轼的惜才,因为他的一再鼓励和大力推荐,秦观走上了仕途——这一年,他三十六岁,经多年努力终于考中进士是喜,而年华蹉跎,十年寒窗苦读却只换得主簿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官职,又令他稍稍感到失落。
但人生总是充满未知性与戏剧性,谁又知道进士及第是好事还是坏事?在秦观考中进士后不久,因神宗驾崩,垂帘听政的高太后起用司马光等旧党,在这一风云变幻之际,苏轼因旧党重新得势而东山再起,在短时间内连连擢升,在恩师的举荐下,初入官场的秦观也好运连连,很快从主簿升为太学博士,而后又担任秘书省正字。
被调回京城当官,又在短时间内步步高升,令不谙世事的秦观以为从此就可平步青云,于是有些轻浮地写下了“更无舟楫碍,从此百川通”的天真话。他显然不知道政治从来都波谲云诡,得势与失势都是转眼的事。
太平日子没过几年,司马光死后,元祐党争便拉开了序幕,以程颐为首的洛党、苏轼为首的蜀党和刘挚为首的朔党因抱有不同政见而互相攻讦,致使朝政陷入混乱。在剧烈的党争中,秦观曾写《朋党论》提醒圣上善辩朋党、任用君子之党,后又写了《财用》《用人》等充满雄辩色彩的文章,对新党旧党的过错作了客观、公允的批驳。尽管秦观本身想尽量超脱于党争之外,可因为他出自苏门,他的文章不仅没能使他和恩师苏轼从党争中脱身,反而使他自己四面受敌,陷入了复杂的政治旋涡中。
在随后的短短数年,秦观屡遭诋毁,先因被指“素号薄徒,恶行非一”被罢去太学博士之位,后来又因被指与青楼女子过从甚密、行为不检而丢了秘书省正字的官职。接二连三的打击令他对仕途沮丧,此时他的内心,诚如《虞美人·碧桃天上栽和露》一词所写的那般愁苦: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乱山深处水潆回。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
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
这首词表面是写山间一株无人欣赏的碧桃,实际写的却是才华得不到赏识与施展的自己。“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不正是他孤芳自赏的写照吗?
秦观敏感而多情、率真而正直,同时也显得有些过于脆弱、单纯与悲观。这样的性格或许只适合当一个单纯的文人,因为自古官场险恶,要在官场如鱼得水,就得有八面玲珑、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本领,但这些本领秦观几乎都不具备。
就说他被罢去正字一事——换作他人,在“行为不检”成为被对手攻讦的原因时,理应检视自身行为、小心处世,但秦观却意气用事,不仅不避嫌,反而因为官场失意常常醉卧青楼以解忧怀,这就注定了他在官场无法自适的命运。
可以说,秦观在汴京过得较为如意的几年,与恩师苏轼的举荐与庇护有很大的关系。他第一次入京为官是因为受到苏轼的大力举荐,后来得以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这三个苏轼门生同时供职史馆,也是因为苏轼被诏回京后再次举荐的结果。
公元1091年到公元1094年供职史馆的这段岁月,秦观得以与志同道合的同门师友共事、闲来把酒言欢,又有恩师苏轼的庇护,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为如意的一段时光。而世人将秦观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也是始于此时。
可惜,政治动荡的风波从未停息,公元1094年,随着哲宗亲政起用新党,苏轼等一众旧党被一竿子打翻,在政治上与老师站在同一阵营的秦观,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厄运连连,屡遭贬谪,直到公元1100年他与苏轼在海康见面,覆盖在他头顶的阴云才稍稍被风吹散,露出了一点希望之光。
而在多年的失意生涯中,因为无法像苏轼那般达观,秦观一直生活得郁郁寡欢,性情转为沉郁。无法把控自己命运的他,只好借助诗词来抒发内心不尽的苦闷,或如《好事近·梦中作》一词所写的那般,只能从梦境中寻求暂时的解脱: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
北。这是公元1095年,秦观被贬监处州盐税时所作。一天晚上,他梦见春天来了,春雨过后,春花怒放,满山春色,林间有黄鹂婉转的鸣叫,天上有奇幻的飞云,而在这一片明媚的春光中,他孤身一人“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
这是一个轻盈的梦,然而“醉卧”两字充分展现了词人想忘却世间烦恼的内心世界,而这种渴望,恰恰是因为现实太过沉重苦闷,所以只能在虚幻的梦境中寻求解脱。正如秦观的好友黄庭坚所说,在明媚春光中醉卧古藤下的词句,是忧伤的断肠人所写的断肠句。
《好事近·梦中作》一词在当时被广为传唱,当时苏轼已被贬到遥远的惠州当官,一个友人曾向他详细讲述秦观的处境,在讲到这首词时,苏轼不禁哀伤落泪。
不久,秦观因被人诬告写佛书,再被降罪,还被削去官职,遭流放湖南郴州(见《宋史文苑传》)。无端获罪的秦观深感凄苦,在奔赴郴州途中,他曾夜泊湘江,想起当年屈原、贾谊等人因怀才不遇而行吟江畔,在感慨之余写下了《临江仙·千里潇湘挼蓝浦》一词:
千里潇湘挼蓝浦,兰桡昔日曾经。月高风定露华清。微波澄不动,冷浸一天星。
独倚危樯情悄悄,遥闻妃瑟泠泠。新声含尽古今情。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湘江的夜色清冷,寒气逼人,正如他所处的官场,没有一丝暖意;而湘妃幽怨的瑟声,一如他此刻寂寞清冷的心境。初到郴州时,秦观在一个凄苦的春日写下了充满失意与幽怨的《踏莎行·雾失楼台》: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那浓雾遮挡的是他人生的渡口,那杜鹃啼叫的是他内心不尽的哀愁。桃源如在云端遥不可及,而友人从远方寄来的安慰信件,更增添了他思乡、思故人的愁绪。《踏莎行·雾失楼台》整首词哀婉凄切,以至于清初诗人王渔阳在《花草蒙拾》中这样点评:“高山流水之悲,千载而下,令人腹痛。”到郴州后,秦观又曾作另一伤心词作《点绛唇·桃源》: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
醉酒的人驾一叶小舟随波而行,不知不觉来到一片世外桃源,然而因无法了断尘缘,仍为名利所纠缠,最终错失桃源,又回到了现实中。但桃源之外是什么呢?——是一片“烟水茫茫”,夕阳的余晖冷冷地映照在水中,面前是无数的山,不尽的水,那通往桃源的路,已全然记不得了。
这首词写的不是梦境,却比梦境更恍惚迷离。那夕阳下茫茫一片的不是水面,而是词人的人生,曾经误入的桃源再也回不去,而此时的他只能驾一叶扁舟在江水间飘荡,茫然不知何往。
这些平淡中充满幽怨的词,如一曲曲哀歌,是秦观对人生发出的一声声无力的叹息。
这些叹息都是无力的,因为在命运面前,个人总是无力的。秦观因无力而生出悲观,因悲观而生出绝望。此时的他已经对一贬再贬的宦途生涯心灰意冷,不抱希望,而他压抑在心中的苦闷,则化成悲哀融入他的血液,深入他的灵魂。
公元1099年,一间简陋的房舍内传出几声咳嗽。不久,屋内亮起了一盏油灯,昏暗的灯火在风中摇曳,将桌前单薄瘦削的身影照在墙上,形成一个幢幢黑影,使得屋里更加昏暗了。
这个不眠之人便是秦观。这一年他刚满五十岁,但多年来遭受的一连串打击令他身心俱疲,他看上去满脸愁容,表情清苦,身体也十分虚弱。
夜不能寐,于他而言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自从五年前被贬官,他就忧思成疾,整晚整晚地难以入睡。他想知道自己的人生究竟为什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却又苦苦寻不到答案,只好在日复一日的悲哀中消磨时光,令自己变得形销骨立。
而这一晚,他似乎比往日更加心事重重。在桌前呆坐许久后,他在桌上铺开纸,用笔写下了这么几行诗句:
婴衅徙穷荒,茹哀与世辞。官来录我橐,吏来验我尸。藤束木皮棺,槁葬路傍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
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闺。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时。修途缭山海,岂免从阇维。荼毒复荼毒,彼苍那得知。岁冕瘴江急,鸟兽鸣声悲。空蒙寒雨零,惨淡阴风吹。殡宫生苍藓,纸钱挂空枝。无人设薄奠,谁与饭黄缁。亦无挽歌者,空有挽歌辞。
这篇凄怆的文字,已不像往常对人生悲惨遭遇的哀叹,而是秦观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而写下的《自作挽词》。
其实,早在写下这篇《挽词》的数年前,秦观在刚被削去官籍不久后所写的《千秋岁·水边沙外》中,就已隐隐流露出此生不复有希望的绝望情绪: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当时春光正浓,而身处逆境的秦观毫无心情去感受鸟语花香。抬头远望,只见沉沉暮色中几朵云在天上飘浮。当他想起旧日与他一起欢会的友人多已零落,看到暮春时节飞花在风中凋落,他仿佛看见了自己不久后的命运。
创作这首词时,秦观才四十几岁,正当壮年,然而此时的他对仕途、对人生已经绝望。他的哀愁是如此深重,以至于只能用“愁如海”三个字来形容,他已被哀愁淹没,无法自拔。哀莫大于心死。
被流放郴州时,秦观曾到衡阳与时任衡阳太守的孔毅甫见过一面。孔毅甫读了秦观的这首《千秋岁》,大惊道:“盛年之人,为愁苦之言凄怆太甚!”他对秦观好言劝慰,但心里却明白,这个形貌枯槁之人正如西边的落日,已是暮气沉沉,因此在送走秦观后,他叹息道:“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
孔毅甫所料不错,自被流放郴州以来,内心绝望的秦观早已放弃了自己的命运,此生凄苦,他悲观地料定自己将在孤苦中死去,如他在《自作挽词》中所写的那样凄凉无比。
他是如此绝望,以至于不再对什么寄托希望,为自己写好挽词后,就开始默默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想而知,公元1100年,当秦观得知自己在有生之年竟然还有机会复官时内心是怎样的激动,而当他收到苏轼的信件,得知年逾六旬的恩师将在北归途中专程到海康看望他,内心又是怎样的波澜起伏!公元1100年六月的那个夏日,这对师生终于又见面了。
时隔多年未见,再次相见,隔着一张桌子对望的师生二人都唏嘘不已。
前尘往事如梦,当初的欢愉,当初的悲痛,都成了遥远的回忆。如果说这短暂的一生还剩下什么,那就是隔桌而坐的两副苍老的身躯,两张苍老的面孔。此情此景,正如秦观在《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一词中所写的那样: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但是,相聚总是匆匆。不久,苏轼收拾行囊继续北上,秦观也被放还复官,前往横州赴任。到广西藤州时,重新感受到一线生命之光的秦观心情重又变得疏朗,还与同行的人一起游览了光华亭。途中他忽觉口渴,叫人去取水,等水送来时,他微笑着看了一眼,便含笑辞世了。不想“后会”终于无法再实现。公元1100年秦观与苏轼的这次分别,成了这对师生的永别。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