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宫墙之外,我的意中人还在等我回到他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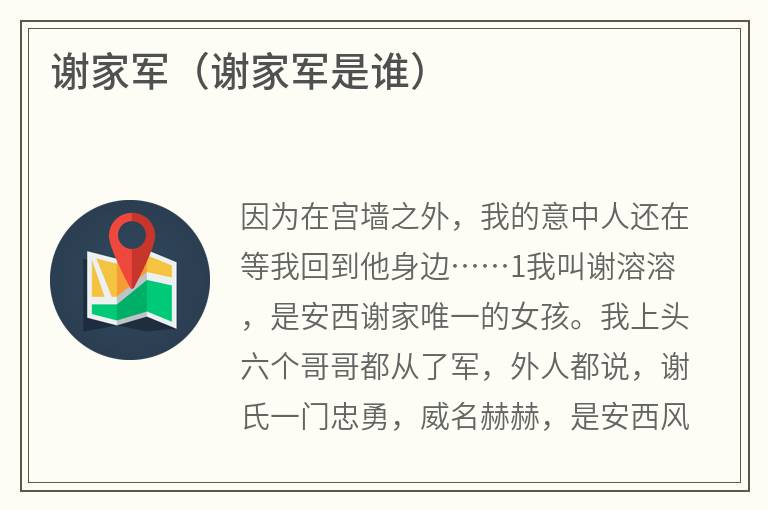
谢家军(谢家军是谁)
1
我叫谢溶溶,是安西谢家唯一的女孩。我上头六个哥哥都从了军,外人都说,谢氏一门忠勇,威名赫赫,是安西风头最劲的家族。
——按我爹的话说,最好别让他知道这是哪个鳖孙说出的话。
“混账东西成日扯淡!朝堂上那帮子人本来就看我们姓谢的不顺眼,这种话说出来,是恨不能把我们老谢家全送去见阎王爷?!”
我爹说这话时,正在校场练兵,热气蒸得嘴巴边起了一串燎泡。
泰和四年的盛夏,我十二岁。我娘没得早,我基本上是家里一帮大男人手忙脚乱里带大的。
后来我爹老和我说,未出襁褓时,他就抱着我打过先锋,这才是谢家风范。
将军一手执枪,一手抱娃,听起来很像军中佳话。
而事实是,那日冲锋时,我那没良心的爹把我往大哥怀里一揣,自个儿在戎狄军中杀了个三进三出,出尽了风头。
至于大哥,一心想夺的先锋功没了,还得绕路骑回大营,差点被人当成逃兵。
待到家里年纪和我最相近的六哥都从了军,我索性就搬到了谢家军中,与父兄们一同生活。校场繁忙,平日里我就住在军医帐中,帮着整理一下草药和常用伤药方子,其中就有一帖专治我爹血热的药。
我爹这个人气性大,上阵打仗他最勇,一练兵就容易瞎激动。今日和我爹一同在校场的是六哥,平日里和我爹打嘴仗总打得有来有回。
也不知道今日是被晒蔫了,还是听厌了,这会儿只埋头练枪法,一杆白杨枪在空中快得残影都看不清。
我没有戏可看,只觉十分无聊,吩咐了近卫去熬解暑汤。等士卒们稍作休息时,我亲自端了一碗汤上前:“爹,今日有外客在呢。”
“齐王来了又如何,强龙不压地头蛇……”
我爹不屑地哼了一声,眼看就要说出更多忤逆犯上的话,我直接把碗怼到他嘴边:“求您莫给大哥添乱了。”
我爹还想挣扎,被我一手按住肩膀,我拿着药碗作势要灌。
他奋力挣扎:“你这小妮,快松手!怎么和你老子说话的?”
我笑吟吟地望着他,手上将力加到五分:“那您喝还是不喝……”
“喝,我喝还不行吗!”
我爹开始龇牙咧嘴,恹恹地接过汤碗,一饮而尽。
——自我九岁后,我爹掰手腕就没再赢过我,也不知道他还在负隅顽抗些什么。
我和我爹正眉刀眼剑时,中军帐中有人出来。大哥走在前面,后面的人坐着轮椅,被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男孩推着。
我难得在军中见到这个年纪的男孩,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这年头安西日子不好过,很多年岁不到的孩子来投军,只为了吃口饱饭,可这男孩年纪还是太小了些。
况且若真是投军的,那男孩的身形也太单薄了些。
只听那坐轮椅的青衣人道:“本王也不欲让谢小将军为难。成华这孩子能不能进谢家军,还要看他自己的造化。”
我爹和我大哥对视了一眼,默契地不发一言。青衣人看了那男孩一眼,他就径直走向校场边放着的武器架,取了把一石弓,走到靶场上。
烈日炎炎,照得男孩脸色煞白,我不禁有些揪心。
“这齐王的养子,看着真是和齐王一样的病恹恹,”六哥不知何时站到了我身侧,摇摇头,“真不知道大哥为什么这么看重齐王。”
六皇子身有顽疾,不能自如行走。更因生母是异族又早逝,比起其他兄弟,早早便被发配到了安西做齐王。
我用衣袖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病恹恹?你十二岁时可开得了一石弓?”
六哥望着那男孩稳稳三箭正中靶心,脸色有点发绿。
谢家军选拔标准极严,唯心性纯善,意志坚定,身强力壮者,方可入营。入营标准,便是能开一石弓,酷暑中奔袭十里不停。
安西的夏日如娃娃的脸,方才还是烈日高照,这会儿却下起了大雨。我随着六哥退到营帐边。射箭完就是奔袭,那男孩脚程不慢,如今已在校场中跑了五里不止,却明显体力不支起来。
望着那在雨水泥泞中踉跄的人影,六哥都面露不忍,齐王却面不改色。
十里结束,那男孩跪倒在泥地里,大口喘着粗气,脊背却挺得笔直。我眼见我爹和大哥神色有些复杂,最终还是松口,让那男孩入了谢家军。
得了准许,那男孩好似并不怎么开心,只是安静地走到齐王身后,习惯性地握住轮椅把手。齐王按住他的手:“既然已经入了谢家军,你不必和本王回王府了。”
声音清越,平静得近乎冷酷。
我皱起眉。可那男孩只是垂下头,并没说什么。淋湿的发梢不停往下滴水,像是被无视的小兽,只是倔强地站着。
齐王也没出声,让侍从上来推轮椅,再没多看那男孩一眼。
等到那青色背影彻底在雨里隐没了踪迹,我走上前,将一块干帕子递给他:“擦擦吧。”
那男孩没看我,也没接帕子,转过身就往雨里走。
六哥眉头一皱就想出声,我按住了他,扬起声音:“有时候,人对着在意的人,才没办法好好道别。可能是怕多看一眼,就不忍心了。”
那男孩转过身,第一次正眼看了我。他往回走了两步,有些犹豫地接过了帕子。
“谢谢。”他说。
我笑着摇摇头,手指往刚刚男孩走的反方向一指:“新兵营在那边,下次可别走错了。”
望着男孩走远,我和六哥对视一眼,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方才我爹和大哥是那副神情。
那男孩话虽少,却带着一丝关外的戎狄口音。近十年来,大赢与戎狄摩擦不断,如今来了个异族男孩,还是齐王亲自送来的,难保不会出什么岔子。
六哥道:“这齐王,也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
2
安西地广人稀,平日里大家伙也没什么爱好,私下里就爱评些什么“军中第一力士”,“北营第一俊男”。
有了各种榜各种第一,就会有拥簇者。拥簇者多了成了小团体,就会有画,有诗文,有杂戏。
军中的过路黄有些短缺,我自告奋勇,去城中买。市集上一路走来,不时能见到敲锣打鼓,卖各种画像的小摊,也有杂戏,在演我大哥戎狄军中杀进杀出的戏码。
安西民风彪悍,比起关中京城,这里不时能看到男男女女,争风喝醋,寻衅斗殴,可谓是文武兼备地追星。
——很适合爱看戏的我。
不过无论榜怎样变,有一个人总是常常位列榜首的。
镇西将军家的大公子,谢珦。去年秋天,皇帝老儿借口镇西将军谢朗守卫安西多年,劳苦功高,将其召回京中。谢氏的其他家眷都一并去了京城,只留下长子谢珦替了他的位子。
我们家虽也姓谢,可祖上没半点根基,比不得镇西将军所在的淮安谢氏有数百年根基。谢将军回京,意为拱卫京师,实则明升暗贬。刘丞相又以谢珦经验不足为由,上书皇帝,夺走了半数兵权。也正是如此,我爹心下颇有怨言。
这一有怨言,打仗就格外狠。对戎狄几个大胜仗下来,我爹也封了平西候,竟是比谢将军还高了些。
我从未亲眼见过谢珦。然而他是六哥最崇拜的人,因此只要一有空,六哥就在我耳边念。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对谢珦有个好印象,有几次被四哥五哥听见了,却不住笑他傻。我们家如今风头正盛,若是再和镇西将军联姻,就能统一安西境内四十万军力。便是谢珦愿意,爹愿意,我也愿意,这事也成不了。
一阵草药的气息随风而来,我仰头一看,不知何时已然到了医馆。
柜台上的伙计正在唾沫横飞地八卦:“你看那齐王府,去年才修好吧,晚上远远望去和个鬼屋似的。往日也不见什么人来往,哪里像个王爷的模样?”
老大夫撇撇嘴:“这都一年多了,老夫一直在这诊病,就没见过府里那位出来过几回。哪像咱们侯爷家的公子们,那才叫真真的好男儿。策马御道的模样,那叫一个俊!”
“要我说小谢将军才是真俊,”挎着菜篮的大婶嚷嚷着,把药包塞进篮子,“平日里一副书生模样就俏得很,可披上战甲更有风采!”
眼看医馆里热火朝天地又快忙起来了,我赶紧上前买了几斤草药,溜之大吉。
今日是休沐,爹难得回了趟谢府,我也一并跟着回了家。这会儿刚过后门,没走多远,就听到远远似乎有人谈话的声音。
我定睛一看,那在花园里的人,正是那日去了军营的齐王。
他正仰头看向我爹。似乎是在僵持。他别过头,催动轮椅往前。
眼看他的轮子就要压到水池边的一丛黄花,我忍不住喊了起来:“大人,且慢!”
不顾二人的脸色,我跑上前,将齐王的轮椅往一边推了推,离我的宝贝药草远一些。
我在军中无聊,常常翻翻医书打发时间。哥哥们练军难免会受伤,我想研制出一种比现在军中更好的伤药。这种在花园里的过路黄,便是其中一味主药。
过路黄常生长于山坡阴面,又喜潮湿,安西干热,难得能寻见,可不能就这样让齐王的轮椅压死了。
“混账,你又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我抬起头,正对上黑着脸的我爹。
看看四周半个侍卫也无,我知道这定然不是一次寻常的拜会。
我爹转身跪下,我也赶紧跟着跪下:“齐王殿下,小女不懂规矩,望你看在她年纪小的份上,莫要同她计较。”
那日我并未留心这位王爷的长相,方才晃眼一见,也没看清眉目,只见一双手落在轮椅的木把手上,像红木碗里新剥好的春笋。
——肚子怎么好像饿了?
“无妨,二位先请起吧,”那双手顿了一顿,敲了敲把手,“将军的提议,本王会考虑的。”
他似乎是要自己推着轮椅走,轮子却被池边的石子卡住了。
我本能地起身去扶。然而方才跪得太急,压到了麻筋,我这起来得急了,重心直接一个不稳……
噗通!
平西侯府后院传来重物落水的声音,水声四溅,惊起一堆墙边的飞鸟。
“爹我没事,不用救我!”
我从水里奋力扑棱起来,和岸上满身是水的齐王面面相觑。
我爹看起来恨不得和我一起投水自尽。
一起陪葬的,自然还有我们老谢家的颜面。
3
那日齐王换了衣服回去,才过了半月,皇帝就下了旨意。
平西侯之女,入齐王府,拜齐王为师。
六哥听闻这件事,惊得直接把饭碗打翻了,站起来就要冲去中军帐找爹。
我拉住他:“陛下已经下旨了,哥你现在去,又能怎样呢?不过是让爹为难罢了。”
六哥看着我,嘴唇都在抖。外边这样红的太阳,他的脸色却是灰白的。
“小七,你不明白,进了齐王府,就没人能护着你了……”
我怎么不明白呢?我是安西谢家唯一的女孩,进了齐王府,就变相阻绝了各大势力与谢家联姻的可能。
只要我父兄还在安西,我可能就要老死在齐王府中。
“六哥,是爹先去找齐王的,”我抓住六哥的手,笑了笑,“他一定有他的理由。”
泰和四年秋,我打包行囊进了齐王府。
这一场师徒戏,双方都心知肚明。因此除了第一天拜师礼,有皇帝的人在场,齐王不得不在,之后我就没怎么见过他。
一开始本着师徒名分,我还照着家里带来的《女诫》,遵循敬慎之道,想着侍奉近前。
然而在我第三次不慎把他的茶杯握碎后,齐王终于忍不住了。
“你的一片诚心,本王明白了,”齐王捏了捏眉心,我注意到他指尖都有点抖,“本王不知道怎么教人,你有空可以多去书阁转转。实在不行,后院池子挺大,你去钓鱼也成,钓完放回去就是了。”
后来我想找那本《女诫》,找了好久都找不到,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齐王府很大,可比不得安西的校场大,也比不得关外的草原大。可王府戒备森严,守卫也不好老放我出去,我只能成日待在府中。
所幸府中的书阁里有很多医书和笔记。我闲来无事,便夜以继日地看。
这里很多书上都有一个人字迹。那人的字画微瘦,落笔如行云,一眼便知是名家教出来的。
我本以为齐王打发我去看书,是为了眼不见为净。可那笔记遍布兵书国策、经史子集,我日复一日地对着,便好像真的有位师父透过字里行间,一句句对我说话。
除了一日三餐,齐王很少出屋子,我进了府大半月,也只知道他喜爱住在高处,且阁楼中的窗户时时都是开着的。
也许是看我实在无聊,齐王让人送了一把钥匙给我。原来后院有一个很大的药圃,本是成华在照看着,他去参了军,如今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药圃就无人照看了。
“谢姑娘既对草药十分热诚,药圃托付给你,本王也就放心了。”
十分热诚,是因为我为着一株药草把谢家的脸面都丢了个尽么…….
我接过钥匙,不禁开始怀疑。
院子就在齐王的住处旁边。有时我抬头看,就能见到一个身影静静待在窗边,头顶是秋日晴朗的天。
一日傍晚,我正在药圃里掘一株野薄荷,只听见后面有陌生的脚步声。
齐王府里下人不多,我想起集市上听过的闹鬼传闻,顿时紧张起来,握紧了手里的药锄。
“你是哪来的小婢女,为何鬼鬼祟祟在我的药圃里?”
我低头一看。这身衣服是旧了些,还沾了土,乍一看确实与婢女无二。
放下药锄,我站起来朝对面人行了个礼:“又见面了,成小公子。”
对面的成华看到我,愣了愣,神色却疑惑起来:“是你。你既是殿下新收的弟子,如今正是傍晚时分,为何你不在近旁侍奉茶食,却在此处挖土?”
——挖土怎么了,惹着你了?
我诚恳道:“是我太笨手笨脚了。”
说话间,我手里被塞了一个帕子,正是上回在军营给他的那块。
成华收回手,脸微微别开:“看你满头大汗的样子,快擦擦。殿下傍晚总要有人煮茶,你随我一起去,还能喝两口。”
我愣了一愣,只感觉他的态度浑然不像下位者对上位者,倒更像是寻常人家的.....兄弟?
我还来不及细想,架不住这个人转身就走。本来我这灰头土脸的样子,并不想一起去,可是说不的机会都没有。我只能一跺脚,抓起药篮去追。
到了齐王的住所,兵士自然退开,他径自上了二楼。我步子比他小,一路走来已是满身大汗,连上楼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才上到二楼,我就听到成华的声音:“今日我回来,集市上有人卖红绳手串,说是保平安的。我如今在军营,有俸禄了,就买了一条。”
我摸了摸手腕上的红绳,有点恍神。
六哥刚入军营的那年,也是这样一个闷热的傍晚。他迎着晚霞,挥舞着红绳踏入家门,非让我把这根红绳戴上。
“以后六哥就有俸禄了,攒攒钱,每年再送你一颗开过光的白玉珠,”他笑得嘚瑟,“等这红绳上串满了九颗,就能保百病不侵。”
“你买这做什么?”齐王叹了口气,“有时间多看两本医书,不比这强?”
“我汉字认得少,那书就和天书一般,”成华理所应当地回,三两下就把那朴素的绳子系到了齐王手上,“哪比得上红绳有效?在我们关外,哪家的娃娃病了,父母都会给他戴上红绳祈福的,很快就好了。”
话说得好意,只是我听着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下一秒,齐王解开了我的疑惑。
他摸着茶杯,淡淡笑了一声,我却觉得背后凉风乍起。
“怎么着,你还想当我爹?”
——第一次见面时,没觉得这孩子这么憨啊!
齐王回头看了眼灰头土脸的我,又看了看满头是汗的成华,又看了眼手上的红绳,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叹了口气。“先喝口茶,歇歇再说。”
我忽然有点想笑。
自进齐王府以来,大多时候齐王总给我一种疏离感。只是这一刻的无奈,让他变回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成华指了指我的手:“殿下都说喝茶了,你还拎着药篮做什么?”
我才回过神,匆忙行礼,将药篮交给了一边的小厮。
齐王看了一眼,眸光微微闪动:“怎么想起采薄荷?”
“秋日闷热,弟子看《肘后急备方》写,薄荷可散风热,逐秽气,”我小心翼翼捧起茶杯,吹了吹,“本想交予厨房,煎一些薄荷水给大家,还没来得及拿过去。”
忙了大半个下午,我还真口渴了。这茶异香四溢,只是太烫,我换着法子试着嘬了好几下,都被烫回去了。
“殿下你看她,像不像……”成华顿了顿,恍然大悟似的说道,“像一只啄不着水的小鸟。”
我才意识到失礼,抬眸望去。
也许是失心疯了,我仿佛瞧见齐王嘴角弯起:“不必着急,无人与你抢的。”
4
那日小插曲后,我在齐王府中的日子又恢复了平静。齐王又恢复了那副疏离的样子,唯有月中月末,成华回来时,才有些新鲜事。
那一年的冬天,我的哥哥们被四处调配,整个谢家军拆得七零八落,连伙房里烧柴的下人都在议论。
我忍了大半月,终于还是去见了齐王。
他倒也没有闭门不见,说的话既坦诚,又冷酷:“朝中有人容不得谢家,本来没有借口,只能把你兄长调到各地。本王若真上了奏章,被有心人视作谋反,那才真是致你父兄于险境。”
他说得对。他是个被发配的王爷,我是个不满及笄的幼女。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我颓然倒在雪地里,他让下人扶我回去休息。
那日之后,我不知怎么就病了,老不好。病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老在想,为什么我爹还不来看我,为什么哥哥们也没来。
也许是药特别苦,有一日我很不争气地哭了起来。送药的大婶不忍心,终于还是把真相告诉了我:
“十日前,小六将军在关外巡视,被蛮子暗算,现在也不知道怎样了。侯爷那日后便没出过军营,日日在军中苦练兵士,怕是就等开春去找蛮子报仇呢。”
我跌跌撞撞地在及膝深的雪里走。
“求殿下,让弟子去见见六哥吧……”
我跪在门外,仰头望去,那披着黑色大氅的身影,安静地靠在窗边,握着一盏茶。
门前的兵士面露不忍,朝我摇了摇头:“七姑娘,回去吧。”
我在家中行七,上头六个哥哥,如今已四散天涯。如今最亲近的六哥生死不明,却只能困在这偌大的齐王府中,不得脱身。
我呆呆地望着楼阁之上的那人。
胸中一阵翻滚的情绪,我也不知是什么,只知道我顾不得尊卑,顾不得禁忌,只是仰头而道:“齐王殿下腿不能行,却独爱眺望远处,又来了安西,不就是不愿此生拘束于高阁之内?可如今为何强拘我于这囚笼之中,致使骨肉分离!”
我的声音传去很远很远。
天上的雪鹅毛似的落下,轻飘飘地落在我的脸上,也落在他的脸上。被风轻飘飘地吹起,落在茫茫的雪地上。
他依然端坐高楼,那样高高在上,那样无悲无喜。
好似那日的笑意,柔软,都只是我的幻觉。
便是垂眼望我的样子,也一如庙里的金身佛像,看似悲悯,不过无情。
我忍不住崩溃大哭,可嗓子早已哑了,哭声都传不出喉咙。
“求求殿下,求殿下了……”
失去所有意识前,我犹自喃喃自语。
那一晚,我的病前所未有的重,连梦里也睡不安稳。梦里我一直在哭,好像有人来到了我身边。
我看不清那人的面容,晃眼间,只觉得有些像成华。
“六哥,我想见六哥…….”
他好像也很无奈,移到我床边:“先好好喝药,你六哥没事……”
我凑在他手边喝了药。他刚想离开,我本能地不愿他走,只是一边哭一边抓住他的衣袖,怎么也不让走。
“成华,”我叫他名字,抽了抽鼻子,又开始掉眼泪,“你哥哥这个人真奇怪,他的笔记都好像比他真实。他的笔记里,那些志向,那些不甘,都那么真实,就好像在对我说话一样。”
那人好像怔在了原地。过了好久,才终于拿着帕子,替我把眼泪擦掉:“乖,先把病养好,才最要紧。”
他的声音很轻,但是很好听,像清越的琴,像落在叶尖的雪。
本来烧得滚烫的大脑,好像也没那么疼了。
我不知何时睡去了。
5
后来大夫和我说,我病了三日,高烧不退,一开始喝不进药。后来喝了药,才渐渐好转。
醒来时,雪停了。我枕边有一封六哥的手书。
原来不让我出齐王府,是老爹的意思。四皇子背后的刘党整了淮安谢氏,又盯上了我们家。我爹好不容易求了齐王,把我送到府中想保住我。奈何刘党本就疑心齐王府是否和谢家勾结,要与刘贵妃的四皇子作对,这一来更是频频在暗中下手。
如今谢家六子重伤,谢家幼女不惜犯上,齐王也不放人,是铁了心要和谢家划清界线。这一来,反而让刘家消停了些。
我病好那日,亲自斟了一壶齐王最爱的顾渚紫笋茶,去向他拜谢。
屋里烧着暖炭,窗前的齐王一身青色常服。夕阳落在红木轮椅上,仿佛镀上一层鎏金边。
“你来了。”
我行礼上前,他抬眼看我,忽然笑了一下。
是真正的笑,不是我的错觉。
也许是玉杯太薄,杯身太烫,我手一抖,又把一个杯子摔了。
——谁见过庙里的金身笑啊,那多惊悚啊。
我赶忙想要附身收拾,齐王直接叫人把我拉住了:“你先坐下吧。”
他又回到了原本的面瘫脸,只是这回声音有点抖。
“这是本王从京中带来的最后一套杯具了……”
“现在确实是悲剧了。”
我积极认错,死不悔改。
齐王又开始捏眉心,我发现这个人好像特别喜欢捏眉心。
泰和五年开春之后,六哥亲自领了一队精兵,去关外敲打了戎狄一次。
戎狄果真消停了些,可明眼人都知道这肯定无法长久。关外连着两年大旱,今年春天又来得特别晚,早就没吃的了。
便不说如今关内谢家军被拆得七零八落,便是谢家军仍在鼎盛之时,戎狄也是要来的。
我在王府中的日子过得平静,朝中腥风血雨,我只埋头钻研医经,改良了好几个杂病方子。
就如同在温水里煮着的鱼,温暖惬意,却也知道末日尽在眼前。
泰和五年秋天,关外天灾。九月,戎狄大军来犯。
失去谢家军镇守的疏勒、毗沙接连陷落。是谢家大公子谢珦将军亲率三万亲兵,才在安西都护府外一百里的焉耆镇,挡住了戎狄的入侵。
若不是我爹依然驻守在此,安西城中早已大乱。齐王准了我在王府门口每日放粥。府里的存粮一日少于一日,流民却一日比一日多。
到最后,连珍贵的紫笋茶,也不过被扔进粥里添几分味道罢了。
西州刺史刘胄的援军,早就应该到了。可是九月等到了九月中,又等到了十月,援军还是没到。
谢珦死的那日,安西下了好大一场雪。
我从未见过他,但我知道,无论什么榜,现在他是当之无愧的榜首了。
齐王靠在窗前,望着远处茫茫的雪,握紧了扶手。
窗外的雪刮了进来,我只感觉身上一阵阵冷得慌,赶忙取了黑色的大氅,上前给他披上。我唤他,师父。
齐王看了我好几眼,沉吟片刻:“谢侯骁勇,小六将军也英名赫赫,必不会有闪失。”
——他原来是在担心我。
谢珦难道不英勇么?传言他苦战半月,在城墙上力竭而死,至死也没辱没淮安谢氏的英名。
最可怕的,从来都是天灾加人祸。
我上前,替他系好大氅,“师父,你说安西会失守吗?”
书阁中有那样多的古书,写过战乱之景,我记得最深的只有一句:
春燕归,巢于林木。
百姓无檐可蔽风雨,归燕无檐可筑春巢。
一笔写尽赤地千里。
我抬眸望他。雪花落在他的眉宇,融成水珠,与他的目光一般莹润。
有史以来第一回,师父拍了拍我的手:“放心,我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
明明他腿不能行,也上不了战场,可我就是信他了。
雪停了,戎狄也退了兵。只是不知道这一场雪后,关外又有多少百姓要流离失所。
果然,还没等我爹彻底安置好流民。泰和六年四月,戎狄再次来犯。太子领兵出征,西州刺史刘胄再次拖延粮草运输,太子于焉耆被掳。
谢珦用命换来的防线,只多守了六个月。
大敌当前,刘党却把安西当作了自家后院的屠宰场,皇子们一个个被送来安西送死。
我身在王府中,日日提心吊胆,一会担心听到父兄噩耗,一会担心齐王也被迫为国献身。
所幸齐王一向身体羸弱,四皇子一党并不将他放在眼里。
太子被掳,帝后亲征,一月后车驾到达安西。城中士气大振,我站在书阁上,望着城内久违的花团锦簇,和平之景,心底不知为何,总感到十分不安。
两日后,消息传来,王军大败。
这一战震惊朝野。戎狄中的西羌部拓跋氏,战出了赫赫威名,以一只精锐狼军数次以少胜多,还在万军中掳走了帝后。
为了追回帝后,我爹和六哥率军追击,不得不进入戎狄的埋伏圈中,以少对多,回来时,两个人身上全是箭矢,生死不明。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军医帐中帮忙。师父终于准了我出王府,我便到了成华所在的营帮忙。
消息是成华和我说的。我只是顿了顿,然后接着替一名小兵剜箭矢。
“狼军用的箭矢是带倒钩的,若是不尽早取出,很容易感染。”
至此,安西境内再无大将可用。四皇子一党不得不重新起用镇西将军谢朗。谢将军一路西进,散落在安西、安北、陇右的谢家军,一呼百应。
谢将军进城那一日,齐王府也久违地来了客人,是个和齐王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
这一回出征,五皇子孟云晗可算大出风头。刘家千算万算,也没算过他们设下的屠宰场中,真出了个杀神。
我不知道他们闭门谈了什么,只知道翌日,我第一次见师父换上了戎装,与五皇子一同驾马而过安西城。
那是泰和六年的盛夏,离我第一次见他,已整整过了两年。
我从未知晓,他还会骑马。坐在特制的马具上,自斑驳的树影下驾马而过,眸光如水,耀眼不可逼视。
我仰头望着,感觉眼眶灼热得生疼。
为什么这一回不藏拙了呢?明明都已经藏了这么多年了啊。
那些笔记里的不甘,志向,埋在心中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这么傻呢?
策马经过我身边的那一瞬,我听到有人对我说,放心。
上了战场,没人能说自己一定能全身而退。谢珦不行,我父兄不行。
可我就是信他了。
后来,世人只知道五皇子亲自督军,只领了五千谢家精兵,就杀得戎狄退败五百里。却不知,熟识安西地势,戎狄情报的六皇子齐王,也是制胜的关键人物。
过了半月,在榻上的我爹和六哥,奇迹般醒转。
又过了三月,五皇子班师回京,沈尚书率文武百官相迎。听闻刘家本还留有后手,哪知四皇子迎接时竟然被气势所摄,一下跪倒在五皇子马前。
泰和六年秋,新皇登基,改年号为初平,封赏救国功臣与各路藩王。
而我只高兴,齐王府中又有足够的紫笋茶了。
我在齐王府又呆了三年。后来回想,那真是我生命中最宁静的时光。
那三年,我们谢家马不停蹄,肃清边关,关内关外百废俱兴。我推着师父的木轮椅,在安西境内画遍了每一株草药。那三年,我将安西境内的药植进行汇总,编撰了新的医书,又根据安西药植的药性,改良了军中已存伤药方,命名为《无垢方》。
直到初平三年,护国公之乱,皇后谢婉被废,淮安谢氏全族流放。
那一年盛夏,我刚满十六岁,皇帝下诏让我入宫选秀。旨意到了安西,我爹捏着圣旨的手都在抖,六哥更是差点当场爆发。
“我谢子颐还轮不到卖妹妹来换一家安宁,大不了就反了。”
面对着明摆着要我入宫为质的旨意,我却一言未发地接下,回了齐王府。
护国公之乱后,齐王府外的兵士增加了数倍不止,名为守卫,实为监视。齐王又恢复了深居简出的日子。
我刚走到阁楼前。
安西的天真不给面子,方才还是艳阳高照,这会儿便下起了大雨。
也许老天爷也爱看戏,离别就要配上凄风苦雨做背景。
雨幕之中我抬头,他依然端坐在高楼上,握着一盏茶。
雨落在我的脸上,也落在他的脸上。
我偏不愿哭。
满地泥水湿泞,我整顿衣裳,安静地俯身下拜。
“求师父,在小七离开那日,不要来。”我的声音穿过雨幕。
安西境内的安宁,是无数将士的鲜血,我父兄的鲜血,师父的心血换来的。
如果师父可以为了百姓,不惜永远被兄弟忌惮;那么我也愿意为了安西,为了谢家和师父拼死守护的百姓,入宫为质。
我仰起头,望着那人微微一笑。
然后我亲眼看见,那白玉般的茶杯碎了开来。
似有鲜血随雨而落。
6
入宫那日,我被封了美人,赐住永宁宫,当夜奉诏侍寝。
我端着一碗解暑汤入殿。只见廷英殿内帷幕翻飞,仿佛鬼影重重。
皇帝似乎已经等了我多时。
“朕似乎从未见过你常服的模样。果然谢家的女儿,戎装英气,宫装也甚美。”
我将碗放到桌上,微微一笑:“陛下对前皇后,也这么说的吗?”
说完不看他僵住的脸色,直接端起碗怼到他嘴边,“夏日闷热,臣妾请您进一碗解暑汤。”
皇帝拧起眉头,我轻轻按住他的肩膀,脸上依然挂着微笑。
他挣了挣,又挣了挣,脸色终于恼怒起来。
“谢溶溶,不要以为你曾经救了朕……”
“原来陛下还记得……”
还记得泰和六年的盛夏,跟随齐王一并出征的成华,披着一身带血的盔甲疾驰回城。
戎狄大军虽已溃败,可狼军凶猛,且退且战,生生耗去了半数谢家精兵。如今安西城中还需谢朗将军坐镇大营,指挥四方,防止戎狄反扑,竟无先锋人选。
还记得那日,我披甲跪在谢朗将军帐中,字字有声。
“我谢家就算只剩了最后一个女儿,也会守住这安西。”
还记得盔甲很热,敌人很多。我手上挥舞的长枪,也变得很重。
可是当我抬头时,万军之中,一眼便见到那被鲜血浸润的眉宇。
即使面对着狼军的箭矢,依然眸光沉静,澄澈如雪。
我狠狠一拍,胯下的马儿吃疼,猛地朝着那狼军冲将而去。长枪一拨,将将把箭矢打落。
本文来自知乎
《娴妃的意中人》已完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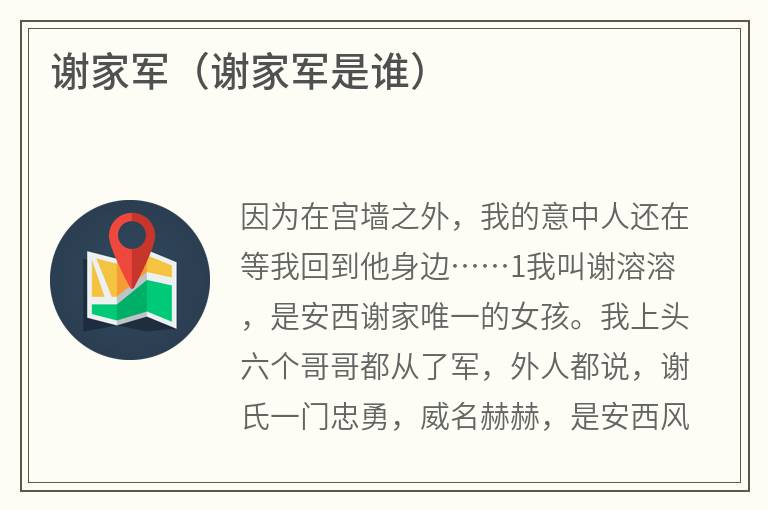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