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唐朝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不仅建立了皇帝与“天可汗”的双重崇高地位,而且有足够的魅力吸引各国首领前来贡拜。
作为当时的一个“超级大国”,唐朝在这10点媲美现代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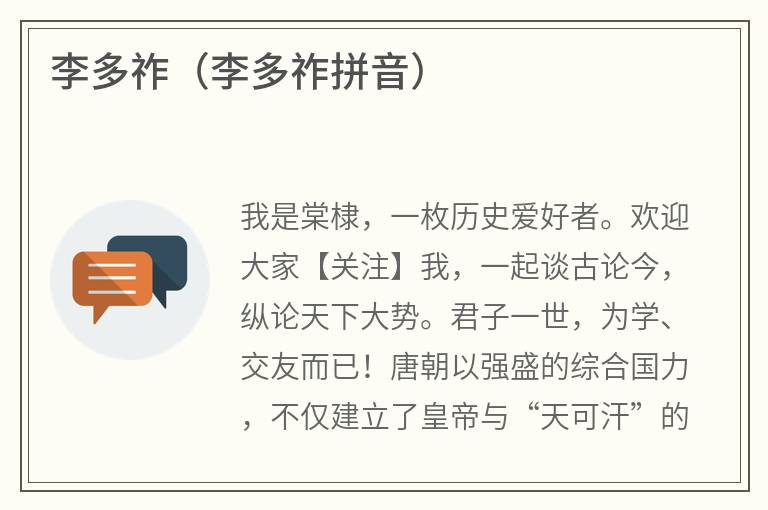
李多祚(李多祚拼音)
唐代是南北朝和隋朝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时期,各民族进入唐境分为被迫内迁和寻求保护两种,因仰慕唐朝经济文化生活先进而零散入境的人也很多。
西域胡人中以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入居最多,在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原州、长安、洛阳等地都有其聚落,从西北辗转到范阳、营州等东北之地的粟特人也很多。西安出土的康法藏、康志达、安万通、安元寿、米继芬、何文哲等人墓志中,都反映了昭武九姓在京师居住的情况。
特别是在长安经商的西域胡人很多,“酒家胡”和侍酒的“胡姬”比比皆是,安史乱后胡商归路断绝,仅长安客省居住者“常有数百人,并部曲、畜产动以千计”,不少为冒充回纥使者的粟特商人。
广州、洪州、敦煌、登州、楚州、洛阳、扬州等城市也是外国人集中的地方。因朝觐、侍卫、求学、传教、行艺、避难而入居长安的西域人也不少。如武德时期疏勒王裴纠来朝,拜为鹰扬大将军,“留不去,遂籍京兆”。
咸亨时期波斯王子卑路斯因国亡求援于唐,入长安授以右武卫将军,随行的波斯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孙有上千人,皆流寓长安。为帮助唐朝平叛入居的柘羯军也多留居中原,于阗国王尉迟胜率五千人赴难,后皆留居长安纳入唐籍。
唐政府对外国人移居中国,曾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制定出专门的优惠政策,规定归化中国的外来者,一方面具状送官府奏闻,一方面所在州镇给衣食并于宽乡附贯安置,另外,还可免去他们的十年赋税。
这对外国移民具有巨大吸引力,是粟特、新罗、大食、波斯等移民社区形成的重要因素,如登州的“新罗坊”,青州的“新罗馆”,敦煌、凉州的“昭武九姓”等。
唐王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州县,都有外国人或异族人担任官职,如京畿道委任的715人次刺史中,异族有76人次,占十分之一强,尚不包括早已同化者。安国人安附国其父朏汗曾任维州刺史、左武卫将军,后迁升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封定襄郡公。
安附国本人为左领军府左郎将,后授上柱国,封驺虞县开国男。他的两个儿子分任右钤卫将军和鲁州刺史,一家三代在唐朝做官。康国商人康谦在唐玄宗时被授予安南都护,后又为试鸿胪卿,专知山南东路驿。
高丽人高仙芝在唐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为唐开拓西域立过大功。另一高丽人王毛仲,也官至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进封霍国公,曾是唐玄宗时皇家禁军的首领。
日本的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50年,改汉名为晁衡,曾任左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等职。龟兹人白孝德,因累立战功,官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鄜坊邠宁节度使,历检校刑部尚书,封昌化郡公。波斯人后代李元谅曾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
越南人姜公辅,在唐德宗时担任翰林学士,曾一度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居宰相。新罗人金允夫、金立之等也都在长安宿卫任官,金云卿曾任兖州司马、淄州长史等。唐朝大胆起用外族和外国人入仕任官,采取“兼容并包”的用人政策,无疑是其国际性眼光的表现。
唐朝前期开疆拓土和后期平叛定难,大都通过提拔与重用各民族“蕃将”。
《新唐书·诸夷蕃将传》列入许多著名人物,出土的“蕃将”墓志也很多,如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执失思力、哥舒翰、白元光等为突厥人,契苾何力、契苾明、仆固怀恩、浑瑊、李光进、李光颜等为铁勒人,泉男生、泉献诚、王毛仲、高仙芝、王思礼、李正己及其子孙李纳、李师古、李师道等为高丽人,黑齿常之为百济人,突地稽、李谨行、李多祚、李怀光等为靺鞨人,论弓仁、论惟贞祖孙为吐蕃人,尉迟胜、尉迟敬穗、尉迟青、尉迟伏阇信等为于阗人。
来自昭武九姓诸国的更多,如安金藏、安禄山、史思明、康日知、李抱玉、李抱真、白孝德、何进滔、何弘敬等。此外,还有出身党项、沙陀、契丹等民族的蕃将。这些在唐朝任职的武将,有的入朝听命中央调遣,有的为边疆都督、都护或节度使,担任一方军事长官。
唐玄宗时以外族将领32人代替汉将,更是将他们作为支撑帝国大厦的重要柱石,肩负着内护京师、外备征御的重任。东突厥汗国的阿史那社尔等,铁勒的薛咄摩支等,契丹的李楷固等,百济的沙吒忠义等,都担任过朝廷禁军高级将领,连西域诸国和新罗、渤海等入侍质子也都配授禁军诸卫郎将。
如蕃王子弟婆罗门(北印度)翟昙金刚、龟兹王子白孝顺,吐火罗(今阿富汗)王那都利第仆罗、于阗王尉迟胜等都在长安朝廷留充侍卫,官至大将军等。许多蕃将及其后裔被唐王朝“处之环卫,委以腹心”,不仅赐姓封王,赐婚尚主,而且陪葬帝陵,官爵世袭。唐代的军事活动,动员了很多外来民族的“降户”或“归化人”,在蕃将率领下防守反击,这是唐朝“羁縻”政策为其国际战略服务的特征。
按《唐六典》记载,盛唐时有70多个国家与唐王朝经常往来,外国人在唐朝居住者众多,难免有违法犯罪现象。
唐朝对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所发生的法律纠纷,有专门的法律规定:
《唐律疏议》解释,化外人,即谓:
这就明确表明,凡是外国人,同一国家侨民之间的案件,唐朝政府尊重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根据他们的俗法断案,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而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侨民在唐境内发生的纠纷案件,则按唐朝法律断案,在法律地位上与汉人完全平等,没有特别的治外法权。
这种涉外立法,分别体现了当代立法的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的原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开元二十五年,又在《关市令》中规定各国蕃客往来中国,根据其装重,在第一道入关口检查后,其余关口再不必重复检查。至于外国商人在边境互市,要由互市官司检验,交易时官司要先与外商核定物价,检查商品,然后交易。
中唐时期,唐政府对海上贸易也采取轻税保护政策,太和八年(834),唐文宗下诏对“南海舶”,“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观察节度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奏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大批外国商人经由陆路海道来到长安、洛阳、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运来香料、药材和珠宝,带走丝绸、陶瓷等物品。刘展反叛,入扬州大肆抢掠,“杀商胡波斯数千人”,可知胡商聚市人数不少。
在长安的许多胡商以经商致富而闻名,如敦煌文书记载:“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骁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侯王。”
史婆陀就是世居长安的粟特人。正因为唐王朝对外商持优惠政策加以保护,有时甚至给予特殊照顾,鼓励交易,每年冬季都要给“蕃客”供应三个月柴炭取暖,所以胡商乐不思蜀,“安居不欲归”。
长安有胡商以十万贯买武则天青泥珠,有商胡以一千万买宝骨,西市成为外商的聚居区,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店肆铺邸,还举质取利放高利贷。
唐文宗时曾责令汉人偿还“蕃客本钱”,不得停滞交易,使外商遭受损失,“方务抚安,须除旧弊,免令受屈”。对于外商的遗产处理,唐廷也是尽力保护,按规定外商死后,官府照管其资产;如满三月无妻子诣官府认领,则没入官库。这都说明唐政府对来华贸易的外商是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的。
当时除不得在边境诸州进行冶炼钢铁,开采矿业以及弓箭兵器等贸易外,其余物资都可以通过正常贸易进出口。但为了防止外商走私关塞偷渡,扰乱国际贸易秩序,杜绝利用秘密婚姻等不正当手段进行贸易,朝廷于开元二十五年、建中元年和开成元年多次诏令:诸丝绫罗锦、珍珠、银铜铁与奴婢买卖等,“不得与诸蕃互市,又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往来,又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
但政府的禁令只是防范走私,并不阻止中外贸易。
异国或异族通婚是打破“华夷之辨”的一个重要表现。贞观二年(628)六月,唐廷敕令:“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唐律令格式中也有类似规定:“诸蕃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并不得将还蕃内。”
这仅仅是指外族男子不能将汉族妻妾带走,并不禁止外族与汉族的通婚,相反,唐律允许外国人入朝常住者,娶妻妾共为婚姻。从出土的唐代墓志可以看出,昭武九姓粟特人安氏、曹氏、何氏、石氏、康氏等与汉族刘氏、韩氏、高氏、罗氏等异族联姻非常普遍。
特别是散居内地者更容易胡汉联姻,如从河西走廊到关洛、太原等地区分布着一连串的粟特移民聚落,长安、蓝田、户县、周至等京畿地区胡汉杂居,通婚嫁娶自属常理。虽然唐朝律令中严格限制偷渡入境者私自与境内妇女结婚,但境外诸族内迁则可以结婚联姻同化。
至于胡汉联姻之外的异族通婚,更是比比皆是,如突厥、粟特、契丹、沙陀等,一直到唐末之后,沙陀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君主的后妃仍有一些出自安氏、米氏、何氏、曹氏等。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记载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时,“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
为了减轻政府供给负担,朝廷下令将检括的四千多胡人遣返回国,不愿归者则入籍为唐人予以安置,结果无一人归返,全部加入神策禁军。
这些人事实上已变为长安居民的一部分,其胡汉联姻已不止一代。即使建中元年(780)唐朝曾一度禁止中原汉人与域外人通婚,但也是针对当时京城侨民通婚过多、仰靠政府供给衣食过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东城老父传》记载元和年间“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少年皆有胡心矣”。
据史书统计,唐高祖19女中有7位嫁给胡族,太宗21女中有8位尚异族驸马,玄宗30女中有5位嫁给胡族大臣。大臣中如裴行俭、张说、唐俭、于休烈、史孝章等人皆是胡汉联姻。还有许多“杂胡”通婚于汉人的事例,如武周时游击将军孙阿贵夫人竹须摩提,乃印度女子等等。
西域与外国文化在唐长安长期流行,并成为时尚。
舞乐最为突出,宫廷十部乐中,除燕乐、清商乐之外,龟兹、西凉、天竺、安国、疏勒、高昌、康国、高丽均为外来乐曲,竖箜篌、琵琶、觱篥(bìlì)、都昙鼓、毛贞鼓、羯鼓等乐器皆为波斯、印度等地传入。软舞曲中的苏合香、回波乐等,健舞曲中的柘枝、胡旋、胡腾、拂菻、阿辽、达摩支等,都是具有外国特色和异族风格的舞蹈,歌舞戏类的拔头、骠国乐、南诏奉圣乐等亦是外邦传入,至于吸收外来乐舞而新创作的霓裳羽衣舞、菩萨蛮舞、醉浑脱等更是中外文化交流互融的结晶。
长安乐府中有许多乐工是外国世家,如来自曹国的琵琶名手曹保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相传,其后还有曹触新、曹者素等。米国的米嘉荣、米和郎父子与米禾稼、米乃槌等都以擅长婆罗门舞蹈见长。
康国的康昆仑、康逎、康洽也是长安的琵琶名手,安国的安叱奴、安万善、安辔新则是舞蹈家。
中宗时一度风行于长安的泼寒胡舞原出自康国,玄宗时流行的柘枝舞原出自石国,演艺者皆为“肌肤如玉鼻如锥”的外国男女。唐长安还盛行来自外国的娱乐,如“婆罗门胡”表演的拂菻幻戏,宫廷和民间都喜欢打的波罗球,以及每年正月十五夜晚“西域灯轮千影合”的游乐活动。
长安画坛上别树一帜的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和康国画家康萨陀等,他们传入印度画法和西域凹凸画派,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称:“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异域传入的绘画技艺对当时中原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人大规模穿戴外国异族服饰,并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这是其他朝代比较少见的现象。
刘肃《大唐新语》卷十记载:
高宗显庆年间虽下诏禁用帷帽,“神龙之末,羃罗始绝”,但“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靓妆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京城长安里“胡着汉帽,汉着胡帽”,非常普遍,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
所以史书称开元以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当时从贵族到士庶皆以穿胡服为时尚,来自波斯、印度妇女的步摇、巾帔等佩饰也流行一时。中唐以后,长安又流行“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唐人还仿效过吐蕃赭面、堆髻的“时世妆”:“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可以说,唐长安是一个兼容外来服饰文化的中心。
至于“胡食”,在长安也比比皆是。东市和长兴坊有专门的毕罗店,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长安:“(开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节。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白居易的《寄胡饼与杨万州》更是众口传知:“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长安里坊“酒家胡”开设的酒店颇有特色,“胡姬”更是有名。
唐人住宅内,从王珙家西域、波斯传来的“自雨亭子”,以及玄宗宫内的自雨亭凉殿,都与《旧唐书·拂菻国传》里记载的一样:“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
街衢上女子骑马是一般民众都能够见到的景致,连贵族妇女亦挥鞭走马。近年来,西安地区考古出土胡装女子骑马俑和胡人三彩俑等文物不胜枚举,正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胡化”状况。
唐朝对宗教传播并不严厉限制,外国诸宗教的僧侣都可以进入唐境,特别是对佛教僧侣开放最大。
众多外国高僧汇集长安,翻译佛典,传播佛法,如唐中宗时义净在长安大荐福寺设翻经院,参加译经的有吐火罗沙门达摩来磨,中印度沙门拔弩,罽(ji)宾沙门达磨难陀,东印度居士伊舍罗、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等。据佛教史书记载,唐代外国僧侣来华非常普遍,有些只知僧名不知国籍。
仅次于佛教的是史称“三夷教”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唐朝对这三个外来宗教僧侣,早期颇为宽容优待,故三教一度在长安等地广为流行。
贞观五年(631),“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同年,唐太宗还允许大秦国景教上德阿罗本携带经典入长安传教,贞观十二年下诏于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21人。武后延载元年(694),摩尼教高僧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到达两京,进行宣教传经。据林悟殊考证,长安有6所祆祠供西域移民作为宗教活动场所,而景教高僧更是进入皇宫宣讲,吸引了许多贵族,景僧伊斯甚至成为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副手。
会昌五年(845)灭佛时,“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32]。可见“三夷教”人数不是寥寥无几。现在西安碑林所留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用古叙利亚文记载了119个景教僧侣,说明唐代景教在中国内地二百多年的传教历程。
唐朝还允许摩尼教于768年在长安及外地建寺传教,统称大云光明寺,其僧大多是粟特人或波斯人,在长安摩尼师的人数也不少。
三夷教是西域移民和外国侨民的精神支柱,也是利用宗教联络团结外来人的中心,唐政府允许三教僧侣入华留居传教,正反映了长安国际性都市的性质。
唐朝经济强大,文化繁荣,对周边诸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于是一批批外国学子泛海越岭到中国留学。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长安国子监增筑学舍和增加学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
此后,来自周边国家的留学生络绎不断,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考证,日本入唐留学生有姓名者为149人,学有成就的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大和长冈、橘逸势、僧空海等。新罗入唐习业的留学生更多,仅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就有216人。
唐政府对留学生给予优待,补助日常生活费用,四季发放被服,允许他们在国子监太学、四门学等一流学校读书。
特别是科举考试入仕方面,为了照顾外国和其他各民族的学生,唐廷特设“宾贡进士”,以示区别。
据严耕望考证,仅新罗人就有23人登宾贡进士科,如金云卿、金夷吾、金可记、崔慎之、崔利贞、朴孝业、李同等,最著名的是崔致远,他12岁离家入唐,经过六年游学,于唐僖宗乾符元年(874)19岁时考取唐宾贡进士后在唐朝入仕做官,官至侍御史、内供奉。
新罗人崔彦为18岁中宾贡进士后,在唐滞留二十余载,直至42岁时才回国。
此外,大食人李彦升,渤海国人高元固、乌炤度、乌光赞等皆以外国留学生身份考中进士。据《唐会要》卷三五“学校”条记载,“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弟入朝就业”,仅太学诸生即有“三千员”。
由于留学生的生活费主要由唐政府负担,所以不允许他们无限期留居中国,超过九年的就要另谋出路了。
各国入唐留学生对国际交往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他们在长安招聘人才,交结其他国家使节,搜集或出资购买书籍,特别是他们将学习了解到的唐文化与典章制度传播于各国,有的新罗、高丽留学生通过唐朝前往西域、印度,有的波斯、中亚、印度留学生则通过唐朝到达日本,更增加了唐帝国的国际色彩。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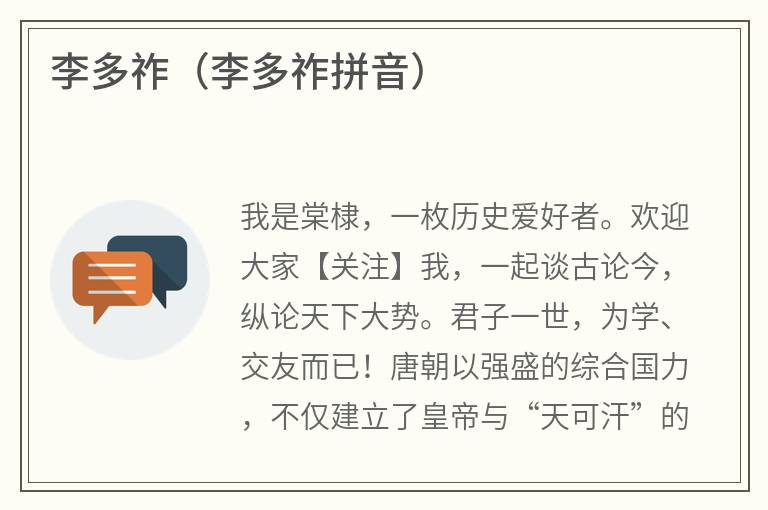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