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这样一个青年、中年和老年半个多世纪的日子都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度过的人来说,每每听到有人对北京人艺的赞誉之词,便会想起亲爱的老院长曹禺。从建院时的42岁开始,一直延续到辞世时的86岁为止,他当了我们44年的院长,既是院长、领导,更是可亲可爱的恩师。
时至今日,我耳边也经常响起曹禺老师那亲切的话语:“陆机的《文赋》说过这样一句话,‘观古今之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人生百年,演员和舞台艺术家们却把千种人物、万种姿态,传奇的、现实的生活与心情尝透。舞台,对今天北京人艺的艺术家来说,就是他们献身的艺术圣坛。”
由于剧本创作和社会活动的需要,我们经常要走进曹禺的家门,因为他并不是每天都来剧院。于是,只要我们一走进他的家门,他便忍不住询问起剧院里的各种情况,哪怕是他刚刚去过剧院不久。从剧院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及舞台工作人员,乃至行政干部,从工作情况到家庭生活、身体情况等,没有他关心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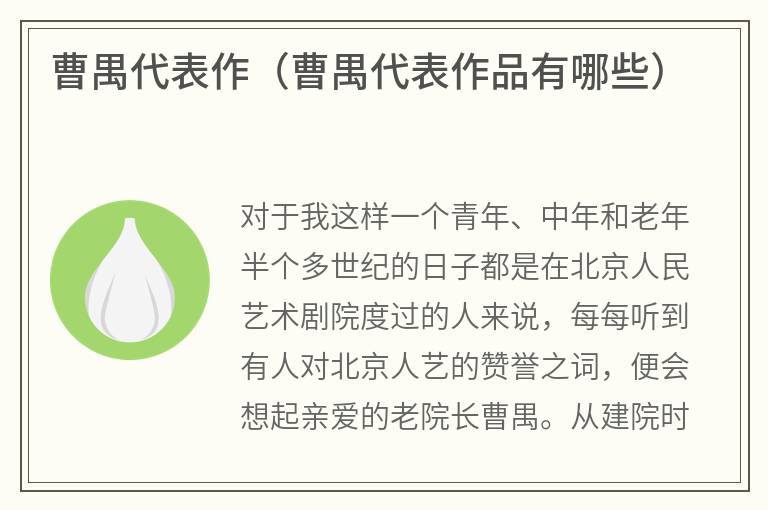
曹禺代表作(曹禺代表作品有哪些)
有一年,曹禺正在上海的家里写电影剧本《日出》,我和导演林兆华出差经过那里去看望他,说起剧院的工作,越说越兴奋,话题就无论如何也收不住了,我们几次要走都没有走成。就这样,从中午时分一直说到夜幕降临。正如曹禺的夫人李玉茹所说,只要一提起北京人艺来,曹禺“总是变得精神抖擞,如数家珍地侃侃而谈,即便生病住在医院里,只要一见到剧院的人,哪怕他身有病痛,疲惫不堪,微闭的双眼也会突然出现神采,精神顿时振奋起来”。
应当说,北京人艺已经变成了曹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熟悉剧院里的每一个人,而且亲如手足,息息相通。拉大幕的资深舞台工人杜广沛在退休时,曹禺也曾郑重地写上一幅墨宝相送:“广沛老友身体健康,感谢你多年的劳绩。”杜广沛眼中闪动着泪花接了过去,回家后便把它挂在家中客厅的墙壁上,逢人便说:“这是曹头儿主动给我写的!”
说来也怪,剧院里几乎没有人叫曹禺为“曹院长”或“曹老师”的,都叫他“曹头儿”,连家属院的小孩儿也是如此,而曹禺还答应得很响亮。我问他为什么要如此,他说:“这么叫是‘爱称’,听着觉得亲切,感动!如果你叫‘院长’,我反倒觉得生分,有距离了!”
曹禺不止一次这样说过,“我是爱北京人艺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的天地里,翻滚了四十年。我爱那些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好演员、好导演和那些多才多艺的可爱的舞台艺术工作者们。我爱剧院里有各种各样性格的工人们。我和他们说笑、谈天、诉苦恼,也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微弱的灯光照着硕大无比的空洞,使我留恋不舍。是否人生如梦,是否我在思索我这一生究竟为什么活着?”话不多,但是句句、字字都如同精灵一般,都是从曹禺的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真挚情感。
曹禺(右二)在北京人艺。梁秉堃供图
《雷雨》是曹禺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话剧的“代名词”。1954年,北京人艺排演《雷雨》,曹禺作为剧作者和院长,经常到排练场进行指导和修改剧本。这样一部在当时已经享有盛名的世界名著,在写出、演出20多年以后,剧作家还要改吗?是的。我印象最深的是,蘩漪在第二幕的一段独白中有156个台字: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口,热烈烈冒一次……曹禺觉得过于冗长,硬是删改成19个台字——“热极了,闷极了,这样的生活真没法子过下去了!”
这就是曹禺。他在创作上提出,要高度概括生活中的语言,要另辟蹊径,不嚼别人嚼过的馍,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对我们同样提出如此的高要求。有一次,我请教曹禺老师:“什么是一个戏的好效果?”他略微思考了一下回答:“是不是演出到了超凡入圣的地步,弄得观众神情恍惚,全神进入戏境,才算好呢?我们希望观众看了戏后,留有余味,去思考,去怀念。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才是我们朝夕追求的好演出。”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不管是专业剧作家还是业余剧作家,写戏都要先有一个提纲,而提纲往往首先要请曹禺给“号号脉”。然而,请他“号脉”也并非易事。针对我们“下笔千言万语,口若悬河无尽”的毛病,要求我们的提纲只能写在一张有300个字格的稿纸上,字字入格,多一字不可。这一下我们真作了难,每次写提纲要使出全身的本事来进行“浓缩”,甚至如同写诗一样,字斟句酌,惜墨如金。曹禺看一个提纲,不满意时,从来不用激烈的批评词句,只是轻声地说“普通普通”“一般一般”或者“现成现成”。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他一定是发现了你在提纲里,“借用”了别人用过的“套子”。他对于古今中外的经典剧本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在这方面想蒙混过关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一次,我为了把一个剧本的提纲挤进300个字的稿纸里去,整整开了两个通宵夜车才完成。当我把提纲给曹禺看的时候,心里总还觉得不满足,一心想着再补充点儿说明。可是,他摆摆手说:“不用了。一个剧本的提纲写得越是花哨就越是自欺欺人,或者说,是自欺而又欺不了人。真正有戏的地方,用不了几个字就能表达出来,因为它们一定会管不住地从你的脑袋里往出跳。”
在建院初期,曹禺认真地提出:“我们需要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就是要建立起中国的剧场艺术,我们一定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树立起我们剧院的这一‘派’。”
50年代末期,他大胆地提出:“要大力培养演员,培养‘红得发紫’的演员,特别是青年演员,这是为了剧院的前途着想。”60年代初期,他又尖锐地提出:“我感觉我们剧院有一种骄傲自满的空气,这庙太大,菩萨多。要知道自己的缺点,要追求更高的境界。现在给别人送‘经’太容易了,求‘经’的愿望不强烈。”80年代初期,他再次深刻地提出:“我终究佩服那些‘动手’的,不大佩服那些只‘动嘴’的,‘干’比‘说’有力。真干事的人,使人意气风发,有真实的生命。”
1996年,86岁的曹禺由于长期患病,已经住了8年医院。那年12月,时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的高占祥等人来到北京医院,向作为文联主席的曹禺汇报全国第六次文代会召开的筹备情况,邀请他一定要出席开幕式,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曹禺不无担心地表示:“我真是很惭愧,知道这次会议很重要,但是恐怕不能参加了。”高占祥听了以后摇摇头,又降低要求说:“您或者只到会几分钟,讲上几句话,和大家拍个照。这样总可以了吧?”为此,他们征求了主治医生的意见,医生毫不犹豫地表示不同意,因为曹禺的病是很怕感染的,不宜于参加任何在公共场合的社会活动。然而,曹禺自己却还是非常想参加的,甚至已经悄悄地让夫人李玉茹给拟就了一篇讲话稿子,内容主要是讲做人的道理,即做人要有高尚的情操、高尚的品德,同时特意强调还一定要有较高的文化。显然,这是他从一生经历中领悟出来的重要道理,真可谓语重心长的肺腑之言。事后,曹禺依然一直念念不忘这件事,为自己没有向大家讲出这些话来而耿耿于怀。那年的12月13日,被誉为“中国莎士比亚”的剧作家、世界闻名的戏剧大师曹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曾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刘锦云这样说:“人艺是曹禺大师辉煌业绩的一角。一曰德,一曰艺,是曹老留给剧院的辉煌基石。曹老以自身风范告诉我们,于清寒和寂寞中奉献自己,是每一个真正从艺者或曰真正艺者必备的品格。”
(本文刊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1年第9期,记者曹雅丽采访整理)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