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时候真是奇怪,一旦陷入往事的回忆中,就非常之执著,任世间再多诱惑也拉不出来。最近的心境呈现出老态了,喜欢上了回忆,所谓人未老,心先衰。 其实,不长的人生历史中倒也没啥可歌可泣的,但是,这样的字眼还是稳打稳扎地印在记忆中,比如,炊烟;比如,青苔;比如,艾草;再比如,蛙声。 不常听到蛙声有几个年头了,亦或十来个年头。 怀念它不像怀念老祖母的粽子,老外婆的汤圆,那么迫不及待。似有似无,可有可无之间,时间过了近二十年。 蛙声钻入我记忆的时候,我还不识一字,更别说什么唐诗宋词了,那个时候在我听来,没见蛙声有多动听,甚至还有点吵的感觉,乡间的夏日的晚饭常常是在如此场景下吃的,庭院里一张方方正正的小木桌,几个矮矮的小木凳,两三个菜,伴着夕阳的余光,一家人围坐在小桌旁,吃着晚饭,聊着天,偶尔还有几个串门的大叔大婶一起聊着家常里短,远处隐约可见的是迟归的人家屋顶的袅袅炊烟,“江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编。蜃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这个时候当然少不了奏鸣的就是这蛙声,随着夜色的越来越浓,蛙声由远及近,由稀及密,此起彼伏,非常有声势,而流萤也随着夜色的加深,出来四活动了,吃完晚饭的孩子们,就是踩着这蛙声,追着流萤度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稀松平常的夜晚,编织着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长大点后,知道了一个叫做辛弃疾的老人写过这样一句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不谙诗词的我,也觉得诗意盎然了,这蛙声改头换面般,登上了大雅之堂,心为之盈盈,乡土的,其实就是世界的。 乡人其实是不在乎什么世界不世界的,在他们眼里,蛙声,不就是青蛙的叫声吗?跟路边的野花野草一样,卑微得到处都是,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需要的是衣食无忧,是安详宁静。“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忙时,可劲的去忙,闲的时候,则洒脱的去找乐子,玩玩牌,下下棋,编编毛衣。这悠哉游哉的,神仙的日子莫不过如此。 怀念蛙声,不仅仅是怀念蛙声,其实它是与一种叫做思乡的“情结”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去年在浙江,夜晚经过田间,忽然就闻得蛙声一片,我像个远方的游子一样,心猛一下被这熟悉的属于故乡的声音砸得生疼,一瞬间,他乡就似了故乡。人跑得再远,当一幅疏雨梧桐,或者碧水乌蓬的国画层层铺开的时候,再刚强的人,心也会变得柔情似水,那是属于血液里固有的东西。
很想再重温下儿时的感觉,听听蛙声,追追流萤,于是,打电话给母亲,问及蛙声是否还是那个蛙声,流萤是否还是那个流萤,母亲说,不知道是气候原因,还是农药原因,现在也很少听到青蛙叫了,萤火虫几乎绝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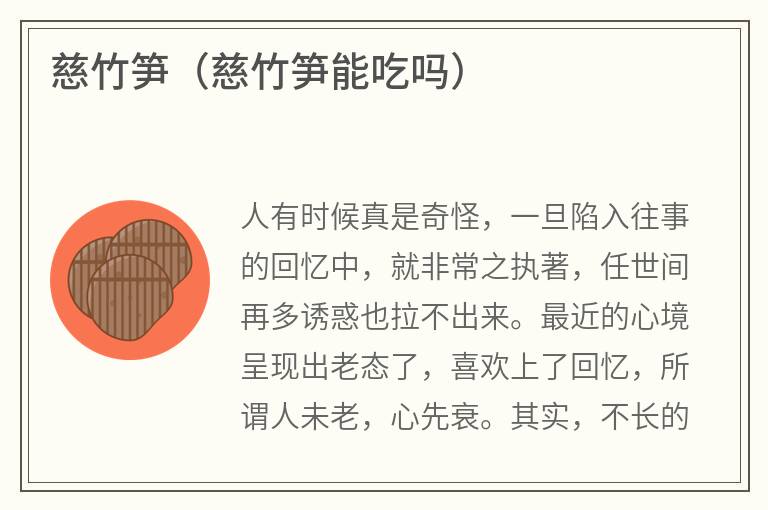
慈竹笋(慈竹笋能吃吗)
讶然。 世间万物,本有今无,本无今有,谁能说出个端倪,三世有法,无有是处。 只是这是一个事实:蛙声不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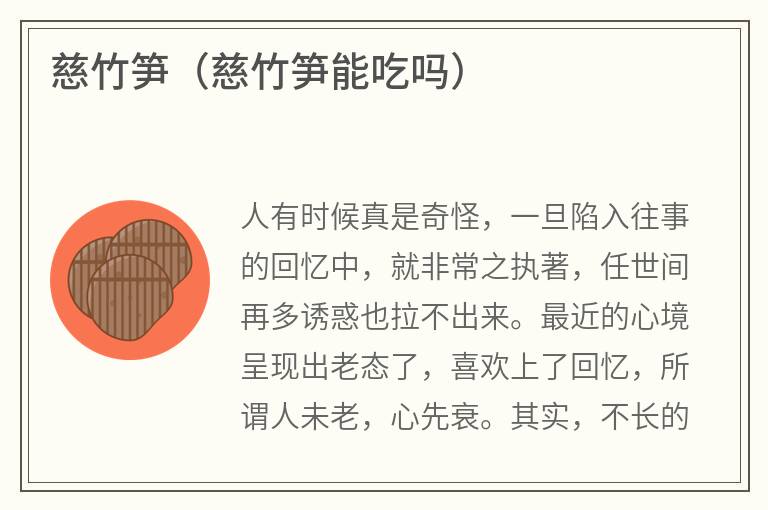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