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永兴时因家里穷,又受到挨户团的搜抢,临走时没有弄到一点钱,从李卜成家里筹借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为了今后的生活我们一边打听党组织的消息,一边了解是否有同乡好友在南京,以便求得经济上的帮助。过了几天我们打听到有个名叫曹日晖的永兴同乡,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现在是国民党军队中团一级的军官,在南京有公馆。我和李卜成在衡阳读书时曾与曹同学,彼此关系不错。李卜成主张去找曹日晖,一方面想向曹了解些情况,另一方面想向曹求帮点钱。我表示赞同。
一天晚上,我同李卜成到了南京城内曹日晖的公馆,李进到宅内,我留在外边观察动静,以便发生不测时好有个照应。李卜成进去没有几分钟,就出来了,匆忙拉着我离开曹宅,转回下关旅馆,进到房间以后,李卜成才告诉我去见曹日晖的情形,曹日晖一见到李卜成十分惊愕,张口便说“你真好胆大!竟敢到南京来!这里同乡人很多,正在到处通缉你们。前不久曹福昌逃到南京,当即被人告发枪毙了,幸好今天我这里没有别的同乡在,算你幸运,否则,真是太危险了!你赶快离开,不要在南京呆了。”李卜成见曹日晖这种神情,也不便向他打问什么情况,就干脆要求他接济点路费,好离开南京。曹日晖不肯在自己身上拔毛,就介绍李卜成去找另一个同乡刘乙光。说刘乙光现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工作,人靠得住,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按照曹日晖介绍的地址,找到了刘乙光。刘乙光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原来是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我们与他早就相识,彼此关系不错,是我鼓动他云投考黄浦军校的。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到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时,他逃离原来的部队,来到武汉,我曾在汉口的马路上碰到过他。那时他说他是从江西逃来武汉,并说江西方面的形势很紧张,难以存身。我告诉他武汉的形势也不妙,革命左派人士己纷纷离武汉去江西,我劝他还是回江西去。刘说身上已无盘缠,无法上路了。我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他答应立即回江西。此后便再无联系,不知他怎么到的中央军校做事。这次我们同刘乙光一见面,刘也感到愕然。我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一是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二是请他帮助解决去上海的路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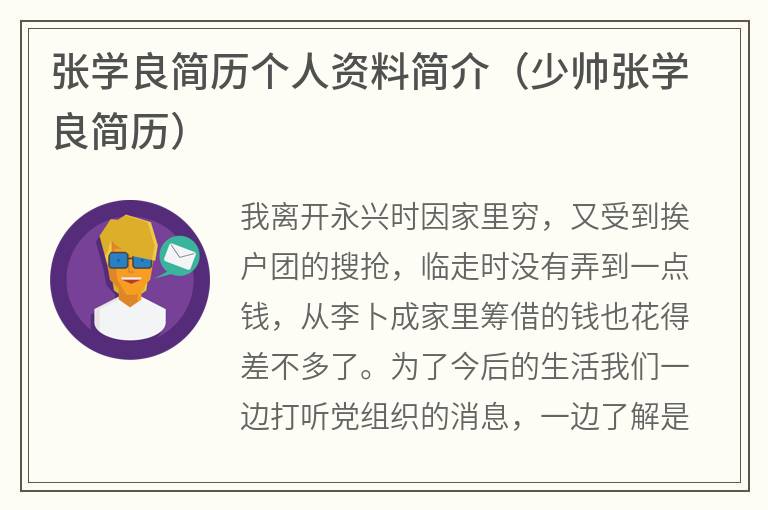
张学良简历个人资料简介(少帅张学良简历)
刘先对我们谈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后说,我们不能在南京久留,如果碰到坏同乡,就会出危险。但刘也不愿意为我们出这笔路费,他说过几天他要到上海公干,可以把我们一起带到上海。我们考虑随刘乙光去上海,比较安全些,就答应了。
两天以后的夜里,我们同刘乙光乘火车去上海。一路上既不用买车票,也没有受到盘查,很顺利地到达上海。刘乙光把我们送出车站,就与我们告别而去。临别前刘对我们说,在上海找下固定住所后,就给他写信,他每月给我们寄几块钱的生活费。
上海是当时我们党中央所在地,我们相信在这里一定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但由于自色恐怖气氛很浓,党的活动是在极为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我们究竟何时才能找到党组织,心里没有把握。考虑到我们身边的钱很少,不敢住旅馆,就采取白天逛大街、晚上在小店里租一张床位过夜的办法,以节省开支。这样过了几天,没有遇见一个熟悉的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我们感到这样没有固定住所,到处游荡也不是个办法,就设法找了一间出租的房屋,价钱很便宜房东是个家庭妇女,丈夫不在家住,在这里比较安全,但没住几天,房东的丈夫回家来看到我们既无行李,又无家具,也不像考大学的学生,就起了疑心,不准我们在那里住了,我们只好另找地方栖身。
这次我们在闸北一个茶馆的后楼上租下一间小房子,老板是个警察兼流氓,他不怕我们不交房租,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因为没有行李,我们就在街上买了块苇席,铺在地板上睡觉又买了几件简单的炊具,自己烧饭吃。
这时已是1928年的10月下旬了。我们两人都是第一次来大上海,人生地疏,每天除了上街东碰西撞想遇见熟识的同志外,就是钻书店看书。起初我们进书店,店员以为我们是来买书的顾客,热情地招呼我们,后来见我们光翻书不买书,就怀疑我们是偷书的扒手,店员的两只眼睛紧紧盯着我们,进行严密地监视。以后我们去的次数多了,他明白了我们是来揩油白看书的,便不大管我们了,由我们自己随便翻阅。
就这样,我们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时间,还没有找到组织关系,生活越来越拮据,心里更加焦急。开始,刘乙光还给我们寄来几块钱的生活费,后来他也失业了,又另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永兴同乡厉良圭,是个黄埔军校学生,在复旦大学任军训教官。我们到复旦找厉良圭求助,他给了我们三块钱后,就再不理会我们。别的关系又找不到,房东又天天催逼房租,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期间,我们尝尽了厚着脸皮求人告助的难堪滋味,但依然是走投无路。
...................
到了武汉,我们见到李卜,成彼此畅叙了别后情形。李卜成仍以李天赞的化名,在武汉考入清查丈量土地的清丈人员训练班,正在汉口的一所学校里受训。李卜成告诉我说,刘乙光也在武汉,现在陆军第二师第二旅某团任少校训练官。我当即写信与刘乙光联系,说明我在上海没有找到职业,又回到武汉请他帮助设法谋个职业。刘乙光当时已随部队驻在孝感,他接到我的信后,即派人接我去孝感。吴永钦因为与唐生智部队的历史关系较久,熟人亦多,就给在河南的唐部熟人写信,希望重回部队工作。河南方面很快来了回信,要吴永钦马上去河南这样,吴永钦即与我分手,单独去了河南。
我来到孝感,见到刘乙光,相互谈了别后的情形。这时我才知道,刘乙光所在的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陆军第二师第二旅,师长顾祝同,旅长郑洞国。我考虑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里开展工作有困难,又担心一旦唐生智部南下武汉后,我在蒋的嫡系部队里不容易出来,便没有急于要刘乙光介绍工作,暂在刘乙光处闲住。
过了一段时间,刘乙光对我说,你这么闲着也不是个办法,还是找个工作先干着,有了薪水慢慢积蓄点钱,将来做什么都方便。
我看唐生智部迟迟没有南下的消息,也感到长期闲住不是个办法,便同意由刘乙光给我介绍工作。刘乙光给我造了一份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几年小学教员的履历,并取了个黄仕诚的化名,介绍我到陆军第二师政治训练处训育科当少尉科员,具体工作就是管理图书。
不久,陆二师第二旅由孝感回到武汉。我随部队到了武汉后,立即到李卜成受训的学校去找他,一进到学校,就见学员们正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自习课。我进教室找了个遍,没有发现李卜成在里边。我就问那些学员李天赞哪里去了?我连问了几遍,那些学员自顾埋头看书写字,谁也不理睬我。我又一再间李天赞哪里去了?
这时有一个学员偷偷地朝我摇摇手,示意我快离开,我立时意识到李卜成可能出了问题,便扭头跑回我的住处。恰巧刘乙光来找我,我就告诉刘乙光说,李卜成多半是出了问题,我到学校去没有找到他,别人也不敢说明情况,为防万一,我向刘乙光表示要离武汉去上海,请刘给我筹措些路费。刘乙光听了我谈的情况后说:“你先不要急着马上就走,待我去打听一下情况再决定去留”我同意了刘乙光意见,就催他快去打听李卜成的消息。
刘乙光先到李卜成受训的学校了解到,李卜成被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便衣队抓走了,什么原因说不清楚,刘乙光又赶到武汉警备司令部找到熟人,证实了李卜成确系关押在警备司令部内。刘乙光通过朋友的帮助,到监所会见了李卜成。李卜成告诉刘乙光,中共武汉特别支部遭到破坏,特支书记刘家驹被捕后叛变,带领便衣特务将李卜成抓捕。刘乙光问李卜成,黄克诚现在有无危险?李卜成说,黄克诚与特支没有发生过关系,他也没向特支介绍过黄的情况,刘家驹根本不知道黄的情况,估计黄暂时不会有危险。
刘乙光回来后,把他探听到的这些情况告诉了我,劝我暂时不要走。刘还说他问过警备司令部的熟人,说李卜成不会有生命危险。我请刘乙光设法保释李卜成,刘说保释暂时不可能,需等等再看。我经过考虑,觉得李卜成分析得有道理,我暂时还不至于有危险,我决定暂时不离开武汉,先写信报告中央军委武汉发生的情况,请示我的去向,然后再筹积点钱,安顿李卜成在狱中的生活,同时还要为李卜成出狱后的生活准备点钱和其他用品。
我在陆二师政训处图书室上班工作后,每天除应付借阅图书的差事以外,我还将图书室所有的书籍进行了一次清查整理登记,并抽空剪贴报纸,到街上各书店购书等。工作之余,我一方面阅读书报杂志,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对政训处的工作人员进行接触,摸清他们的政洽思想倾向相机开展工作。
在这个政训处里工作的人员,情况相当复杂,既有死心塌地效忠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如政训处主任康泽之类;也有像刘乙光那样的左派军人,还有坐牢刚出来的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他们之中,有些是政局变幻中的失意者,也有共产党队伍中的脱党分子。大家对各人过去的历史大都相互了解,但都不认真对待,对彼此的遭遇相互很同情。上尉科员申孔国,湖北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对现实很不满,经常发牢骚,具有一定的革命倾向。还有一个勤务兵,已忘记姓名,是江苏徐州一带的人,家里很贫穷,为了糊口才出来当兵,不满现状,有反抗情绪。
我当时把申孔国和那个勤务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经常同他们谈心,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但还没有敢向他们暴露我的真实身份,因为我清楚地懂得,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犹如身在狼窝里,随时都会有危险发生,不得不小心谨慎从事,尤其是政训处主任康泽,虽然他那时尚未搞特务工作,但已是个很反动的角色。
到了1929年的10月,冯玉祥又鼓动西北军将领反蒋,蒋介石乘机纠集各路杂牌军,以蒋之嫡系军队为骨干,围攻西北军,蒋、冯再度开战后,陆二师奉命向河南开拔。我随陆二师政训处在汉口大智门车站乘火车,开抵河南许昌车站下车,稍事停留,即徒步向豫西开进。未等陆二师上到前线就听说西北军已被打败,我就随部队沿原路线开回武汉。在河南徒步行军中,我曾借宿营的机会,到附近找当地农民谈话,了解一些情祝农民对新军阀互相争战深恶痛绝,尤其是豫西一带的农民由于连年的灾荒和战乱,使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重新回到武汉不久的一天,我同刘乙光二人上街闲逛,在闹市区突然与刘雄迎面相遇。刘雄是湖南水兴县一个大地主的儿子,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曾和我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同过学。湘南暴动时,刘家曾被暴动农民抄没,刘雄有个兄弟也被杀掉。湘南暴动失败后,刘家便对参加过暴动的农民进行屠杀报复,刘雄更是像一条鹰犬,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干尽了坏事。后来李卜成就是死在刘雄之手。我的情况刘雄完全清楚,也是他日夜搜捕的目标之一。
这次我和他迎面相遇,已来不及躲避。乘刘雄还没反应过来,我就来了个先发制人,上前一把拉住他的手,装作很亲热的样子说道“啊,老朋友多年不见了,一向可好好?”我一边说着话,一边紧紧地攥住他的手,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他出其不意,弄得他瞠目结舌,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想抽开手,我更加用力地攥住,使他不得不就地站住听我讲话说完,未等他开口,我便一松手快步钻进大街上的人群中去。这时,刘乙光又拉住他的手继续缠住他讲话,问长问短,使他一时难以脱身。这样,我才得以跑脱。打这以后,我就不再轻易上街了,有空也呆在屋子里看别人下围棋。我后来爱好下围棋,就是这个时期看棋学得的一点基础知识。
蒋介石打败了西北军之后,进一步加紧了剪除异己、消灭各路杂牌军的步骤。陆二师又奉命开赴南京,参加讨伐石友三之役。我即随部队由武汉乘轮船到了南京。
这期间,我思想上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看到从大革命的失败,到目前白区党组织到处遭受敌人的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血流成河的现实,认识到我们在军队中只抓政治工作,而不注重抓军权,以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深深地感到,革命必须依靠武装斗争。没有革命武装作后盾,迟早会成为敌人的俎上肉,任人宰割。于是,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到游击区去,重回红军搞军事斗争。所以,我到南京一下船,就找了个借口请假,连夜乘火车赶到上海,立即找到徐德。详细地向徐德作了汇报。我请徐德将我的情况和请求,设法立即转报中央军委,希望迅速得到答复当天晚上,徐德告诉我说,已将我的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军委的同志说以前我写的信都收到了,情况都已了解,同意我去游击区参加军事斗争的请求,要我速作准备。徐德还告诉我说,军委已决定派他到赣东北方志敏处工作,问我是否可以同他一道前往。我说现在我还不能马上随他走,我得先回南京办理请假或辞职手续,免得不告而辞会使介绍人刘乙光受到牵累,同时我还必须回一趟武汉,去看看正在狱中的李卜成,待把李卜成的事情安排好之后,才能再回上海听候军委的工作分配。徐德说我下次来上海时,他可能已经离开了,他嘱咐我再回上海时,如果他不在了,要我去他家看看他的夫人。并要我在离上海去苏区之前,设法给他夫人留下点钱,以接济今后的生活。
我从上海回到南京,正是1930年元旦前夕。我赶着打请长假报告,以便名正言顺地离开陆二师。还未等我的报告送上去,陆二师政训处已奉命宣布解散,工作人员领一个月的薪铜,作为遣散费,自寻出路这样一来,我假也不用请了,就着手打点行装准备去武汉。遣散时政训处主任康泽对每个工作人员逐个谈话,询问各人的去向。当问到我打算去何处时,我回答说我过去当过小学教员,这次打算回家乡去,仍设法觅个小学教员的差事干。康泽听了后点头说:那很好嘛。
我与刘乙光这位同乡可算是有点患难交情了。通过这一段的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热情助人又能同情革命的人。因此,在临别时,我对自己的去向没有向他隐瞒,据实以告。刘乙光听了后对我说,他也有去当红军的想法,等将家属安顿好后,再考虑去苏区参加红军,但他以后并没有去苏区,我也没有再同他联系,可能他以后又向右转,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