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领域,有一个学派原本不显山,不露水,冷战后影响却日益扩大,它就是英国学派。
英国学派虽然是国际关系领域里的一个正经学派,形成过程却充满了各种不正经。
英国学派的诞生理应回溯到1959年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即英国委员会)的成立。
但正如将1648年同主权国家的概念相绑定一样,从长远来看,对任何时间点的确定都是比较武断的。
从组织层面来看,英国委员会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
从概念层面来看,“国际社会”一词被视为英国学派标志性概念。但该词并非英国学派的原创。至少从19世纪开始,国际社会是国际法的术语。
直到罗伊•琼斯呼吁终结英国学派的时候,英国学派这个名称才正式出现。
不管怎样,这个标签被学派内外的人所接受了。
和包括“现实主义”甚至“国际关系”在内的其他许多标签一样,“英国学派”并非完全字如其意。
英国学派部分创始人并非英国人。赫德利•布尔是澳大利亚人,查尔斯•曼宁是南非人。
英国学派从未对英国外交政策表现特别的兴趣。
英国学派的理念也并非特别突出英国特色,而更应被理解为一种欧洲史学、法学、社会学和政治理论的混合物。
与英国学派联系最为紧密的重要古典理论家是来自荷兰的格劳秀斯。
更为尴尬的是,英国学派的启动资金来自于美国的基金会。起先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后来是福特基金会。
尽管如此,“英国学派”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确立的品牌,而其他标签(“不列颠学派”、“古典方法”、“国际社会学派”)则很少被使用。
不正经的说完了,小编要说点儿正经的了。
该“学派”是如何起步的呢?
一开始,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国家社会及国际社会的理念。这更多是一种史学、法学、哲学以及某种程度上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的思考方法,而非像主导战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国际体系那样的机械性概念。
怀特进一步指出,国际社会的理念开辟了一种中间地带,或者说提出了其后被称为处于国际关系学自由主义(或革命主义)与现实主义两极之间的中间道路。
艾普认为,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概念一开始就“始终被视为一种颇为不同的领域”。
罗伯特•杰克逊对其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
英国学派是若干不同的理论探索,并不把国际关系看作仅仅是一个充满权力、审慎、财富、能力或支配的世界,而同样包含认可、联系、成员资格、平等、公正、合法利益、权利、互惠、习俗与传统、一致与分歧、争议、挑衅、伤害、损失、补偿等,即人类行为规范领域的世界。
”
在英国委员会首次集会之前,很多人就已经沿着这些思路进行思考。这其中不仅有施瓦曾伯格,还包括上世纪50年代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的马丁•怀特和查尔斯•曼宁(曼宁1930年起就在伦敦经济学院)。
德•阿尔梅达(De Almeida 2003:277-9)走得更远,认为英国委员会不仅仅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铺设一条中间道路。在怀特的带领下,英国委员会重新体现为思考国际关系的成熟的第三种立场——理性主义,植根于被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所遗忘的格劳秀斯、洛克、休谟、伯克和托克维尔的著作中。
随后,伴随国际社会的观念,诞生了一家最具英国特色的事物——社团。英国委员会是由部分来自历史学、哲学、国际关系和神学学者与外交部及财政部员工等自发组成的团体。
英国委员会避谈当前事务与政策问题,而关注从围绕国际社会的概念入手来发展一种对国际关系的总体认识。
相对而言,从推进并鼓励其成员思考的角度来看,英国学派是一个成功的讨论小组,而非是一个成功的有自己出版物的项目团体。
然而,我们也不能将其成员的个人成就与英国委员会的努力区分开来。英国委员会也编辑出版过两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外交研究》与《国际社会的扩展》。
英国委员会同时鼓励独立但相互关联的项目。
波特致力于英国学派的研究,同时在伦敦经济学院有一个平行的项目组,编辑出版了三卷从英国委员会国际社会观念著作的主题中所挑选并延伸的著作。
作为一个有明确参与者的社团,英国学派却引发了关于成员资格的无用的争议:谁在广义上可以成为英国学派网络中的一员。
英国委员会的参与者是登记过的(Vigezzi 2005),毫无疑问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和马丁•怀特是其中的关键成员。
未被英国委员会所纳入的主要人物包括查尔斯•曼宁与爱德华•卡尔。他们都有支持者认为其是英国学派的奠基人。
曼宁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将国际关系学发展为英国的一门独立学科,而且发展出一种将“国际社会”作为“双重抽象”的社会学、建构主义方式。
他认为国际社会是一种“国家作为玩家”的游戏。这也许与当代后结构主义者的看法比较契合,也许是由于他使用了过于夸张的比喻。
在曼宁看来,与现实主义的观念相反,由于国家和国际社会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此他们都具有可塑性。
卡尔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著作并没有表现对国际社会的显著青睐。卡尔反对自由主义的利益和谐论,并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国际社会是由主导大国所制造出来的。
他将主导大国看作“将自私的国家利益伪装成共同利益的大师”。但是同时他认可类似国际社会的存在,尽管认为其含义更多是由主导大国所界定,而非独立的概念。
他对乌托邦主义与现实主义进行了辩证批判,并且看到国际关系中权力与道德之间协调的必要性。
这一切看上去恰恰留出了与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的观念所契合的中间道路的空间。然而此时,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紧张对立消弭了思考国际社会的空间。
因此,英国学派创始学者们对于“从冷战政治的极端中挤出国际社会的空间”的思考是很寻常的事。
另外两位没有参加英国委员会的学者约翰•伯顿和埃文•路亚德当时也从在研究相似的课题。
路亚德主要讨论国际社会,而伯顿所关注的世界社会成为后来关于跨国主义与超越国家体系的争论的前奏。
尽管他们在英国工作,但并不被认为是英国学派的成员。尽管他们与英国学派有所交集,但与英国学派的概念和讨论并无关系。实际上,伯顿和英国学派相互敌视。
根据菅波英美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从上世纪70年代到尤其是80年代,英国学派不再是一家受限于成员与时空的社团,而更像是一个学者的网络,并且不断伴随着新鲜血液的输入而体现出延续性。
英国学派的社团形式在80年代逐渐衰微,被一种松散且更具全球性的网络形式,以及学者间代际传承的形式所取代。
这也让英国学派有关成员资格的争论变得更加无关紧要。
*以上内容,框外边是小编写的,框里边的摘自《英国学派理论导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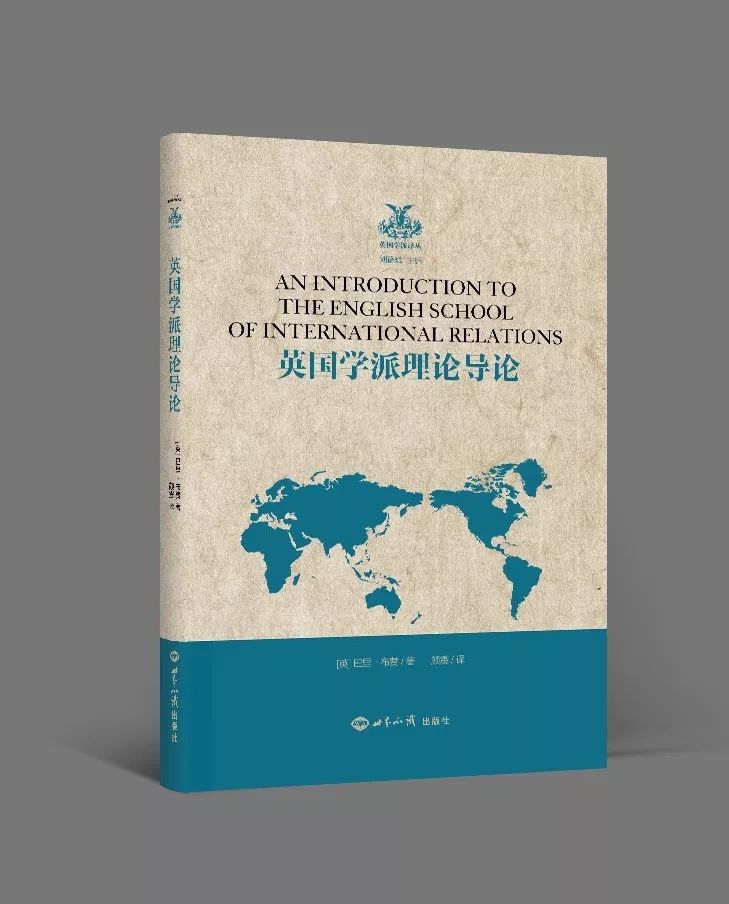
英国学派理论导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