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据差往虎门之弁驰回面禀:初六日晚间,靖远、镇远、威远暨巩固炮台亦俱失守,提督关天培不知下落。臣等闻之,不胜愤恨。”
——钦差大臣琦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七(1841年2月26日)奏报

关天培在哪场战争中为国捐躯(关天培的英雄事迹)
作为鸦片战争中清军英勇战死的最高级别将领,关天培在现代中国虽然谈不上家喻户晓,至少也是声名远扬,很可能是整场战争中仅次于林则徐的人气亚军。可是,正如琦善奏报所述,由于清军在虎门之战中一败涂地,几座炮台悉数沦陷,琦善等人又远离前线,因而起初竟然对关天培战死事迹一无所知,只能从士兵们口耳相传的消息里得出“不知下落”的糊涂结论,而且在奏报里表示要“查关天培下落,另行奏具”。
不过,由于关天培家仆很快就在尸堆中找到遗骸,英方也回之以军礼,他英勇战死遂成为朝野上下、对阵双方的共识。二月十二日(3月3日),琦善报称“提臣关天培及香山协副将刘大忠、游击麦廷章同时在台阵亡,臣等不胜愤恨”,二月二十七日(3月18日),道光上谕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香山协副将刘大忠、游击麦廷章……先后被害,殊堪悯恻,俱著加恩照例赐恤,以慰忠魂。”
其实,道光帝此时也是葫芦僧判断糊涂案,被错漏百出的前线报告玩得团团转。关天培、麦廷章战死自是毫无疑问,可上谕里的二号人物刘大忠却是跳海逃生,死而复活,于是只得在三月初七(3月29日)下令“所有刘大忠恤典,着即撤销”,后来干脆罢职回乡了事。
日后广东乃至全国各地文人编撰的纪念文字则充分发挥想象,对战死情节多方渲染。《英夷入粤纪略》虽然压根弄不清战死日期,却说得有鼻子有眼,还让义律给关天培当了一天孝子:
初四日,逆夷攻台,横档不支,关公在镇远,亲督将弁发轰八千斤大炮,一炸一竖,逆船环攻,关公力竭自刎,阵亡。逆夷登台,见关公尸,关公威名素著,夷目义律怜其精忠,取红毡二,移关公尸于毡上,复以红毡覆之,十二日始委官殡殓,关公面色如生。关公灵柩发引开船,义律令所有兵船各放炮以送,义律与各夷目夷兵,俱著黑一日,夷礼以黑为孝服故也。
《广东军务记》的想象力稍逊一筹,不过一样搞错了日期:
二月初七日,由后海而入,攻破横档炮台,竟入虎门,提督关天培自刎身死。
《中西纪事》甚至替“自刎说”发明了原因:
关提军善识炮性,凡高下远近,发皆洞中。因虎门之役,水师贪受土规,火药皆杂以沙土,军门后发之炮,辄试不中,方知受绐,愤激自刎。
光绪年间的文人刘长华不仅给奕山开了时光通道,还来了个骇人听闻的cult片场面:
时粤提督关天培紧守关隘,奕山等调遣失宜,竟被逆夷设计生擒关去,任夷剐剖处死。
相比之下,梁廷枬《夷氛闻记》虽然仍旧写错日期,但总归像是正常人的作品,也被现代人多次引用:
初五日……天培力竭,守御不支,手燃巨炮忽自炸裂,兵无人色,皆走。一弁大呼曰:“事急矣,盍去乎”。言次,伏使受背,将负以出。天培挥刀拟之,弁极闪避。一弹当胸至,洞焉不倒,夷众拥入。天培与都司署提标游击麦廷章俱阵亡,参将刘大忠先遁。夷见天培屹立如生,反骇而仆。续至者近前视之,知气已绝,相与惊叹。
丁晏《诰授振威将军广东省水师提督关忠节公传》则是少数写对日期且相对靠谱的记载之一:
辛丑年,夷兵攻陷大角、沙角二台,又进攻威远、靖远诸台。大吏一时主抚,尽行撤防,并木排、铁链皆毁弃之。公诣制府,恸哭请益兵,不许。守台仅赢兵二百,公自度众寡不敌,且藩篱既撤,孤力无援,乃决为死计。昼夜驻炮台督战,创痕遍体,血濡衣襟。会事急,公顾其仆孙立使去。仆裵回不忍决,公以刃逐之。曰:“吾上不能报天恩,下不能养老母,死有余恨。汝归告吾妻子,但能孝事吾亲,吾目瞑矣!”仆遂奔,至山半,回首视公,已为飞炮所中,陨绝于地。时辛丑二月初六日。仆以印送抚军,复返至炮台,求得公尸负以归,辫发已割,左腕刀伤,身受炮火,焦烂无完肤。同官赙金以殓。事闻,天子震悼。
那么,清军究竟是如何丢失看似固若金汤的虎门要塞,英军又是如何记载关天培战死情形呢?笔者还是从《联合兵种勤务期刊》上刊载的战报入手解析。
▲加尔布雷思手绘的虎门要塞炮台示意图
关于虎门之战,茅海建等研究者已从交战双方入手做了详尽分析,不过利用的英方材料仍以回忆录为主,未能采用伯麦写于同年3月10日的报告,殊为遗憾。伯麦在战斗部分首先分析了虎门要塞的诸多炮台:
[2月]25日,我制定了攻击我军正面炮台的计划,这些炮台都相当棘手,因而或许有必要在此先行介绍:一座崭新的花岗岩炮台[威远炮台]围绕在亚娘鞋旧堡周边,位于旧堡前方的高水位线上,形成了大约相当于三分之二个圆弧的圈子,这座炮台修得很好,上面安装了42门火炮,其中有一些非常重、口径也很大,几座坚固的堑壕工事延伸到炮台南面,山脊上设有火炮,还有据估计能容纳大约1200人的营地。北面是一座新建的直炮台[靖远炮台],装有60门重炮,此炮台和偏北的40炮圆炮台[镇远炮台]之间大约有150码的多石海滩。所有工事后方都有一直延伸到山上的高墙保护,上面设有可供开枪的踏跺或平台,内部还配备了军火库、兵营等建筑。
上文描述的是武山岛(亚娘鞋岛)上的三座炮台,自北向南依次为镇远、靖远和威远炮台,镇远炮台“临海起筑”,“前面敌台炮墙周围四十丈,开炮口四十个,山上围墙长八十丈”,靖远炮台“前面敌台炮墙长六十三丈,开炮口六十个,山上围墙长一百零八丈”,威远炮台“前面敌台炮墙长四十丈,后围墙长三十丈,开炮口四十个”。
▲《广东海防形势图》中的“三远”
上横档岛(NorthWangtong)东端是一座设有两层火炮的炮台[横档炮台],它负责保护那一侧的入口,此外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负责从翼侧保护诸多横贯河面的木排,木排由大量木材建成,相邻间隔约为12英尺,木排各配有两只锚,之间用一条分成四个部分的锁链连接起来,木排也为锁链提供支撑,排链两端都固定在石质建筑下方,一段位于下横档岛(SouthWangtong),另一端位于亚娘鞋。上横档岛西端有一座坚固的炮台,配有40门炮[永安炮台],翼侧有一座17炮的野战工事,实际上,整个岛屿都是一座连绵不断的炮台。水道最西边是一座配有22门重炮的炮台[巩固炮台],此外还有17炮的野战工事,它们护卫着一座能够容纳1500-2000人的设防营地。敌军并未占据下横档岛,这是一块非常好的[炮兵]阵地,于是,我下令在25日夜间在岛上修筑一座工事,架设2门8英寸榴弹炮(铁炮)和1门24磅榴弹炮(铜炮)。[1]26日天亮后,王家炮兵的诺尔斯上尉指挥该炮群射击,向上横档岛发射了榴弹和火箭,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战果,此外也不时朝亚娘鞋开火,亚娘鞋方向的中国人也劲头十足从位于正对面的炮台[威远炮台]展开还击。那里的中国人在前一晚修筑工事期间也持续不断地朝这里开火,当时的火力要到大约午夜2时才有所减弱,然后慢慢消失。
[1]英国的24磅榴弹炮口径为5.7英寸,从后文判断,英军炮兵还应当携带了若干具康格里夫火箭发射架。后一卷《期刊》还刊登了“一位‘复仇神’号军官”(约翰·冈特)写于同年5月15日的书信,称这3门火炮系2门24磅榴弹炮和1门18磅榴弹炮,可备一说。
前文中提到“死而复生”的香山协副将刘大忠,此战中便负责和庆宇、达邦阿等人把守上横档岛,两台“炮墙共计二百二十一丈,开炮口一百零四个”,看似火炮众多,却没有多少能打到下横档岛方向,此外也没有顶盖防御自天而降的榴弹。由于下横档岛毫无防御措施,英军得以在岛上轻松架设3门榴弹炮,以空中开花的榴弹肆意轰击仅仅五百米开外的上横档岛。据同年七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祁奏报,“本年二月初五六等日,夷船驶来攻击……庆宇在永安台内,刘大忠在横档马头,各自督率弁兵开炮抵拒。嗣被逆夷环台轰击,将台头及土墩击塌,打伤庆宇左臂左腿,刘大忠亦被打伤腰腿。伊等情急.奔至台北山湾下,跳落海内,顺流漂至白籐滘山边,经众兵瞥见捞救”、“达邦阿具禀,伊与庆宇、刘大忠分督弁兵开炮对敌,续因夷炮击塌台内望楼,将石块打中腰腿,受伤落海,适遇渔船捞救”。但也有中方研究表示“一些清军将领驾四、五艘小船北逃,愤怒的士兵调转炮口,向逃跑的将领开炮”,从“四、五艘小船”这个细节来看,此处记载应当是引自奥却他朗尼(Ouchterlony)的《中国战争纪事》(TheChineseWar)。[2]
[2]茅海建.1841年虎门之战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0,(第4期),20页.
▲《广东海防形势图》中的横档、永安、巩固炮台,由于暗沙影响,横档西侧水道很少有大船通行
总之,不论具体状况如何,早在英国海军投入战斗前,英国陆军炮兵这区区三门榴弹炮和若干火箭就把上横档岛上的将近一百门各式火炮压制得毫无脾气,刘大忠等人脱离战场更是给了守军士气沉重打击。随后,英国陆军和陆战队乘坐“复仇神”号和“马达加斯加”号蒸汽船登陆受降,据伯麦战报所述,上横档岛战斗合计打死打伤清军250人,俘虏1300人。
英军攻克上横档岛之后,虎门要塞的六大炮台已去其二,西面的巩固炮台“敌台长二十一丈,开炮口二十个”,又是“横档之西只此一台”,既实力薄弱又势单力孤,战斗重心自然转移到武山(亚娘鞋)岛上的镇远、靖远、威远炮台。中午11时许,英军舰队驶入虎门水道,开始与东侧的“三远”炮台交锋。
关于这几座炮台的缺陷,祁后来的奏报里说得还算恳切:
臣等详加询访,多谓旧台过低,防洋盗则有余,若夷船驶入,则彼船较高,我之炮台内情形彼皆一望而知,难以制胜。且台形有如扇面,炮台多在正面,而侧面炮口无几,若夷船驶靠侧面攻击,亦难抵御。
伯麦战报对此也有涉及:
亚娘鞋诸炮台已被“布莱尼姆”号[74炮战列舰]、“梅尔维尔”号[]和“女王”号[蒸汽船]以精准、漂亮的火力打哑。估计敌军业已动摇……陆战队与装备轻兵器的士兵就在南侧炮台[威远炮台]登陆,陆续将敌人逐出该炮台和另外两座炮台。1时,英国旗帜已经飘扬在这一连串赫赫有名的工事上。
作为与英军交手最久的炮台,威远炮台设有官兵327人、壮勇91人、大炮40门,英舰炮火在交战期间导致8名官兵阵亡,26名官兵负伤。此外还因为射击太久,出现了火炮炸膛的悲剧。清廷事后调查发现“因夷船开炮攻击,弁兵接连开炮回攻”,竟有两尊“八千斤”大炮“炮身烧热,以致炸裂”,迸溅出的铁片当场打伤官兵6人。其他人员则因“炮台破损不能抵御”径直退却。
关天培坐镇的靖远炮台和北面的镇远炮台虽然没有炸膛,可面对英军的优势火力,状况同样好不到哪里去,杨芳、奕山事后奏称:“关天培阵亡,因将备不敢强兵点炮,关天培亲手执火,而大炮火门早已透水”,“夷船近在咫尺,兵丁并不点放炮位,各自逃走,提督关天培手斩数人,不能禁止,是以被夷炮打伤而亡”。伯麦战报称:
我军损失轻微,共有5人受了轻伤。“布莱尼姆”号主桅中桅和前桅下帆横桁被洞穿,1门32磅炮无法继续投入战斗,船身也中了几炮,索具被截断颇多。“梅尔维尔”号主桅中桅受创,索具受损严重,“卡利奥佩”号船身中弹数处,其他船只则仅有几条绳索被切断。敌军损失相当惨重,但还是不及穿鼻之战,如前所述,1300名敌军放下武器。按照我的估计,敌军在横档死伤250人,亚娘鞋的死伤可能也是250人左右,中国的关提督和另外几名大人在那里阵亡。战斗次日,提督的遗体被他的家人指认出来带走,“布莱尼姆”号鸣响志哀礼炮为他送行。
如此看来,《英夷入粤纪略》里“关公灵柩发引开船,义律令所有兵船各放炮以送”倒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了。
关于关天培战死的具体情形,伯麦并未目击,也未曾费心描写。丁晏《关忠节公传》中“左腕刀伤,身受炮火,焦烂无完肤”的说法,应当源自认尸忠仆的叙述。奕山后续调查靖远炮台兵丁逃散情形时录有郭标口供,称“关提督受伤倒地后,夷兵攻入炮台,兵众抵御不住,一同走散”。英方个人记载也多有不同。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称:
战列舰猛烈的舷炮火力已经把墙炸成了废墟,不过[靖远炮台里]中国军队的损失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至多也就有12个人战死,其中还有英勇的老关[关天培]和他的副手。[*]
[*]宾汉原注:关那顶没有顶戴的帽子成了“梅尔维尔”号上一位青年绅士的战利品。
战后次日,有人打着一面休战旗前来,还带来了关的亲属提出的要求,希望能够准许带走他的遗体。要求立刻得到了批准,但由于尚不清楚他战死在那里,他的遗体是和其他人混杂在一起的,不过最终还是把他挖掘了出来。就在他悲伤的亲属将遗体带走时,“布莱尼姆”号鸣响了一轮志哀礼炮。
伯纳德(Bernard)《“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NarrativeoftheVoyagesandServicesoftheNemesis1840-1843)称:
[此战]俘获敌人1300人,但很快就放走了,当天总计打死打伤500人。有许多中国军官勇敢、高贵地赴死,其中有些人甚至是追求死亡。与死在国家的敌人手中相比,他们更害怕主子的怒火和自己的降职。在这些死者当中,最杰出也最令人悼念的是可怜的关老提督,他的死亡在军中激起了深切的同情。他在亚娘鞋[炮台]门口迎击对手时胸部被刺刀戳伤,倒下了……
次日,关的家属识别并认领了他的遗体,我们当然乐意把遗体交给他们。“布莱尼姆”号向这位勇敢战死的敌人鸣响志哀礼炮以示纪念。
麦华生(MacPherson)的《在华两年记》(TwoYearsinChina)则多少能够与郭标的口供对应起来:
300名水兵和陆战队登陆了,一发流弹撕开了[炮台]大门上的铰链,于是,这群人就立刻攻入炮台。壁垒上已经完全没有人了,但炮台中央还有一群武装人员,他们的人数与登陆部队相当,也以良好的秩序列队。这群人最前头是一位看上去颇为受人尊重的老人,帽子上面有着蓝色顶戴和花翎,显然是个不同凡响的大人。起初,人们还以为他们要投降。可一阵箭雨和几发火绳枪子弹很快就让我们的人确信事实恰恰相反。这位老长官挥舞着他的双手大剑向前冲击,似乎是在主动寻求死亡。一发子弹贯穿了他的胸部,终结了他的生涯,其后不久,这群人投降了。后来才知道前文提到的那位老长官是关提督。
不难看出,宾汉、伯纳德、麦华生三人的行文中都或多或少借鉴了伯麦的战报,但又都依靠自己的信息源加以补充,虽然他们提到的写法不尽相同,但关天培慷慨赴死终究是个不争的事实。
诸位读者,你们更认可哪个版本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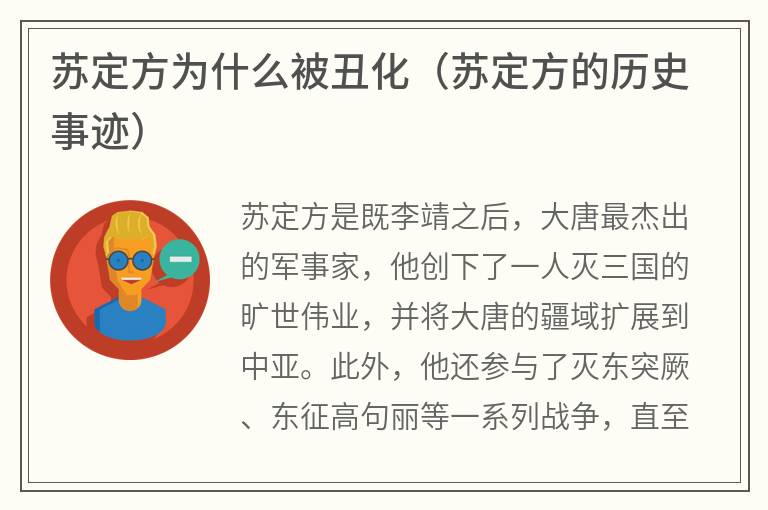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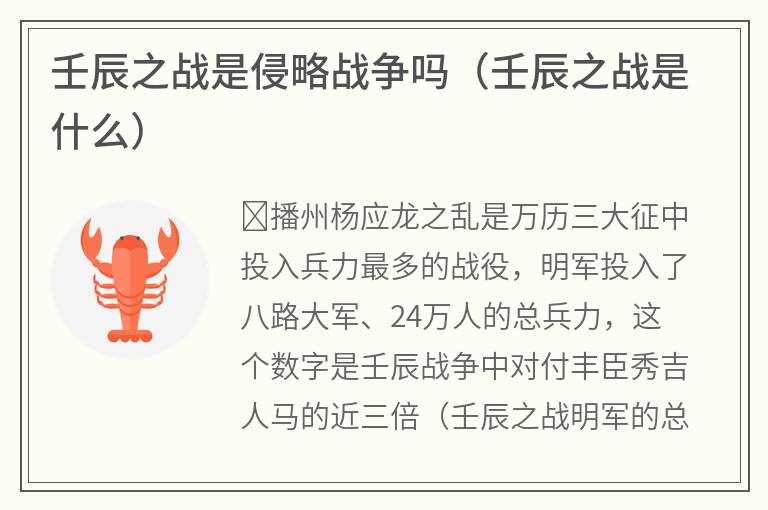
发表评论